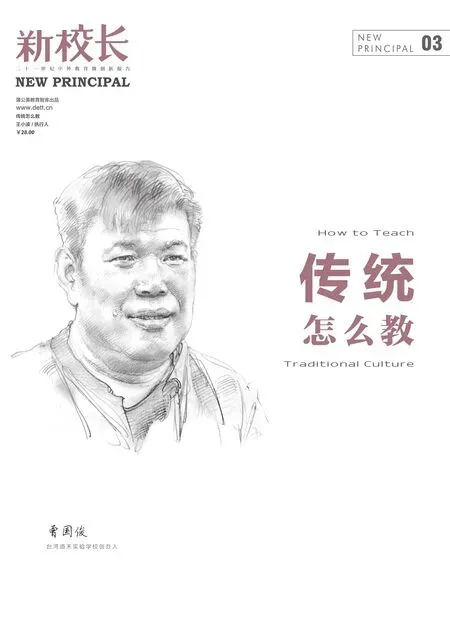在中國最通行的四本字典必須改革
2016-01-15 10:24:42徐健順首都師范大學
新校長
2016年3期
文 / 徐健順(首都師范大學)
一百年前,1915年夏,陳獨秀先生回到上海,開始籌備一個新雜志。9月15日,《青年》創(chuàng)刊號發(fā)行,先生作《敬告青年》,標舉“德先生”和“賽先生”。1916年,改名《新青年》。新文化運動就此拉開了帷幕。
25年以后,在歷經(jīng)風云變幻、跌宕起伏之后,貧病交加的陳獨秀先生隱居在重慶江津,謝絕高官厚祿,謝絕出國邀請,以至于因沒錢付費被醫(yī)院趕出去,而他卻埋頭在一件事中,那是他晚年最大的心愿,耗費了他巨大的精力——他在給小學教師們編一本字典:《小學識字教本》。當他終于完成書稿,把稿件送審時,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予以退回。陳獨秀先生則回復說“一字不能動!”于是書稿終于沒能出版。預支的八千元稿費也分文未動。就這樣,先生去世了。
《小學識字教本》才是這位新文化運動旗手的最后的標志。
這是一本怎樣的書?
《小學識字教本》是一本字典,詳解了三千多個常用漢字,從音形義一體的角度,考證其源流關(guān)系,是一本學術(shù)價值很高,教學價值也很高的書。
為什么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最后把心血傾注在這樣一本書中?
在《自敘》中,陳獨秀先生這樣說:
昔之塾師課童,授讀而不釋義,盲誦如習符咒,學童苦之。今之學校誦書釋義矣,而識字仍如習符咒,且盲記漫無統(tǒng)紀之符咒至二三千字,其戕賊學童之腦力為何如耶!
是啊,新文化運動已經(jīng)過去了25年,為什么識字還像習符咒?我們學習了西方人的方法,可是為什么連最基本的識字的情形還是沒有改變,我們的孩子還是在受苦?……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德育(2022年12期)2022-08-22 06:16:18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金橋(2022年1期)2022-02-12 01:37:0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shù)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啟蒙(3-7歲)(2018年8期)2018-08-13 09:31:10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18年3期)2018-02-06 18:09:23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17年37期)2017-11-11 23:33:41
散文百家(2014年11期)2014-08-21 07:16:24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08年11期)2008-12-31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