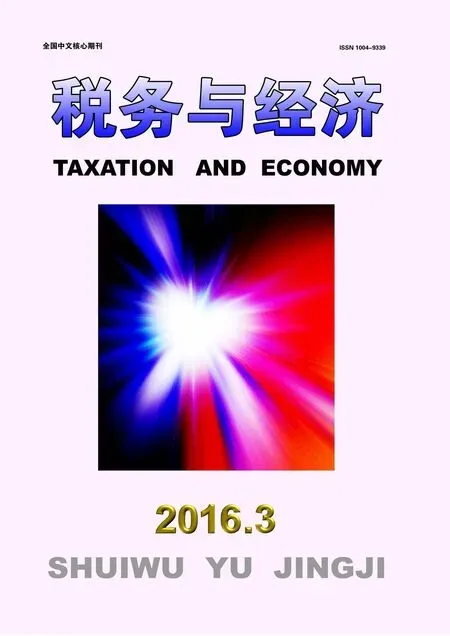營利性行為分類與民間非營利組織稅收優惠制度設計
張思強,朱學義,李 欣,3
(1.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江蘇徐州221116;2.鹽城工學院管理學院,江蘇鹽城224051;3.青島大學 商學院,山東青島266071)
民間非營利組織(以下簡稱“民間組織”)是由民間出資舉辦的,不以營利為目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宗教等社會服務和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主要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寺院等。與政府、企業相比,民間組織在擴大公共產品供給數量、提高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因而對民間組織及其營利性行為給予稅收上的特殊優惠,已成為管理體制完備國家的普遍做法。但由于營利性行為本身的復雜性,對民間組織“營利性行為”的本質,學術界的認識尚未統一,法律上沒有明確界定,實踐中也很難進行區分,稅收征管機構或者設計較高的門檻抑制民間組織的營利動機,或者降低非營利性的標準,導致稅收優惠政策被濫用。因此,必須將促進民間組織遵守非營利宗旨作為稅收優惠的根本目的,在此前提下,根據不同營利程度和營利方式對非營利宗旨的影響,制定民間組織的稅收優惠制度。
一、文獻綜述
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人們對民間組織應該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法理基礎已趨于統一,代表性理論主要有傳統的補貼理論、資本結構理論、利他主義理論、稅基定義理論和捐贈理論等。其中更為我國理論界接受的是Bittker和Rahdet(1976)提出的稅基定義理論,又稱收入定義理論,該理論認為所得稅只能針對營利行為。[1]因為非營利組織的會費和捐贈應當視為非營利組織接受的贈予,不應計入應稅收入,而非營利組織用于非營利項目的支出就應該等同于營利組織對外的公益捐贈而獲得稅前扣除。無論從收入還是支出角度看,非營利組織的應稅所得都應該為零。這一理論表明,非營利組織獲得減免稅的法理基礎是它的“非營利性”,正如國內學者張守文教授(2006)提出的,國家對非營利組織的免稅與非營利性和公益性相關。[2]但“非營利性”的界定一直是理論和稅收立法的難點所在。即使是非營利組織法律規范相對完善的美國,其律師協會制定的《美國示范非營利法人法》(修訂版)①在美國,非營利法屬于州立法的范疇,律師協會制定的《美國示范非營利法人法》沒有法律效力,只是一個范本。對此也沒有做出界定。
縱觀國內外理論和稅法規制對民間組織“非營利性”的認識,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必須遵守“非分配約束”原則(Henry B.Hansmann,1980),其基本內涵是,無論是否存在營利性行為,民間組織都不能向出資人分配“紅利”,也不能用于員工分配或變相分配。[3]我國《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第二條規定,民間組織應當同時具備的特征之一是“資源提供者向該組織投入資源并不得以取得經濟回報為目的”。這是民間組織“非營利性”本質的“底線”,世界各國均以此作為民間組織獲得稅收優惠的基本標準。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就是依據民間組織的活動是否具有營利性作為免稅和征稅的標準,即使民間組織符合免稅條件,也僅對從事非營利性活動取得的收入免稅,而從事營利性活動取得的收入必須依法納稅。2001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營利性科研機構稅收政策的通知》也細致詳盡地規定了非營利性科研機構才能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
具體實踐上,各國界定民間組織營利性行為稅收優惠的標準主要有兩個,包括“收入用途標準”和“宗旨相關標準”。“收入用途標準”是指非營利組織營利性行為獲取的收入必須全部或主要用于非營利事業支出方可獲得稅收優惠,如英國施樂會(Oxfam)在發達國家銷售二手服裝,盡管與基本宗旨無關但仍可以免稅,因其全部利潤用于慈善目的,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窮人;我國財稅〔2014〕13號也規定非營利組織獲取免稅資格的9個重要條件之一是非營利活動取得的收入除用于與該組織有關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記核定或者章程規定的公益性或者非營利性事業,但對民間組織營利性行為取得的收入用于與宗旨相關的活動是否減免稅并未做出明確規定。
“宗旨相關標準”是將民間組織的營利性行為按照與組織宗旨的相關性分為宗旨相關行為和宗旨無關行為,對于其從事與組織宗旨高度相關的營利性行為的所得免稅,而對于其從事的與組織宗旨不緊密相關甚至無關的營利性行為,則與營利組織的征稅方式相同。如美國對從事與民間組織的非營利使命相關的業務取得的所得,包括政府撥款、社會捐贈和服務性收入(包括會員費)免交公司所得稅。但其開展的與自身免稅事業不相關業務的無關營利所得不能享受免稅。我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營利性科研機構稅收政策的通知》規定非營利性科研機構與宗旨相關收入才能享受稅收優惠政策。而新加坡則禁止與非營利組織目的無關的營利活動,只有當某項業務或活動與非營利組織目的相關時,才享受所得稅等免稅待遇。
綜上所述,營利性行為是民間組織為獲取公益資源(包括財務資源、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在遵循“非分配約束原則”的基礎上,采取符合非營利宗旨的營利方式直接或間接為利益相關者(財務資源供給者、受益者、管理者、普通員工、志愿者、供貨商以及組織自身等)謀取合法利益的行為。因此,營利性行為是一個中性詞匯,民間組織存在營利性行為并不預示著該組織“以營利為目的”,關鍵是看其是否遵守“非分配約束原則”并符合“收入用途標準”和“宗旨相關標準”,即“一個原則和兩個標準”。然而,符合“一個原則和兩個標準”是否意味著民間組織自動符合稅法上的非營利標準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營利性行為還應受到特定“邊界”約束,即公益與商業一定要有邊界(王振耀,2011;Pamela Wicker,Christoph Breuer和 Ben Hennigs,2012)。[4,5]這種約束“邊界”至少包括兩個維度:(1)橫向邊界,即營利“范圍”邊界,一是營利主體范圍(為誰營利),二是營利方式范圍(差異化收費、與營利組織合作實現雙贏、對外投資、興辦產業以及近年來興起的公益創投等)[6];(2)縱向邊界,即營利“度”的邊界,一是盈利率高低,即盈利率小于還是等于、甚至高于同行業營利組織平均收益率,二是營利風險程度,即營利性行為運營風險大小。因此,我們有必要根據不同邊界標準對民間組織的營利性行為進行分類,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民間組織稅收優惠制度和稅收征管制度,以規范民間組織的營利性行為。
二、民間非營利組織營利性行為的分類
民間組織營利性行為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類,但依據稅制管理的要求,民間組織營利性行為主要可以按橫向和縱向進行如下分類。
(一)從橫向來看
1.按營利主體可分為狹義營利性行為和廣義營利性行為。通常人們將民間組織的營利性行為等同于為組織主體自身增加公益資源的行為,這屬于狹義的營利性行為,如增加組織主體當期收益、凈資產積累過多等;廣義的營利性行為還包括為組織外單位和個人的營利性行為,或者為人力資本供應者營利,如員工薪酬偏高甚至畸高、未在基金會擔任專職工作的理事從基金會獲取報酬等;或為財務資源供應者營利,如支付偏高的財務資金成本;或為供應商營利,如采購物品價格偏高等。
2.按與組織宗旨的相關性可分為與組織宗旨相關和無關的營利性行為。民間組織可能開展與宗旨相關、或者無關的營利性活動,前者是符合組織章程規定的營利性行為,如民辦高校在正常教學工作以外創辦各類培訓班所獲收益或教師在完成教學工作的前提下開展與專業相關并能夠促進教學的科研工作所獲收益,不僅能夠增加民辦高校的收益,而且能夠促進教學質量的提高,這在德國被稱為“理想的”收益;后者是與組織章程規定宗旨無關的營利性行為,如民辦高校的房屋出租、餐飲經營等,盡管是在完成使命前提下的營利性活動,不僅能夠增加社會就業,而且能夠增強民間組織自身的發展能力,但與組織宗旨無關,或者說不是完成使命的充分必要條件,因而在德國被稱為“私利的”收益。
(二)從縱向來看
1.按財務成果的高低可分為等于和低于同行業營利組織平均收益率的營利性行為。低于同行業營利組織平均收益率的營利性行為是指營利性行為的投資收益率或營業收益率明顯低于同行業營利組織的平均收益率,甚至由于接受政府資助和社會捐贈較多而采用低于平均成本定價法確定的收益率;而等于同行業營利組織平均收益率的營利性行為主要是指民間組織各種營利性行為的收益率完全按市場化規則來運作。
2.按營利性行為特有風險的大小可分為中低風險的營利性行為和高風險的營利性行為。營利性行為特有風險包括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經營風險是指戰略選擇、公益產品價格、營銷手段等經營決策引起的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營利性行為偏離組織宗旨帶來的公信力風險。財務風險是指組織財務結構不合理、融資不當使民間組織可能喪失償債能力而導致投資預期收益率下降的風險。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營利性行為分為兩大類,其中各種分類的前一類稱為理性營利性行為(以下簡稱“Y類行為”),而后一類稱為非理性營利性行為(以下簡稱“N類行為”),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民間組織營利性行為分類表
三、不同類別營利性行為的稅收優惠與約束制度設計
民間組織的稅收優惠是政府對稅收收入加以法定地放棄或讓與行為,立足于糾正和引導民間組織的運作行為,使之朝著與非營利宗旨相一致的方向發展。稅收優惠主要分為兩方面:一是對民間組織本身的稅收優惠,包括間接稅式支出和直接稅式支出,前者是通過延期納稅、稅收抵免等形式進行稅收優惠,后者指對民間組織實施減免稅、優惠稅率等直接形式進行優惠;二是對向民間組織捐贈的單位和個人的稅收優惠,即捐贈者優惠,包括單位所得稅前扣除額優惠和個人所得稅收入扣除額優惠,目的是通過稅收饒讓提高社會捐贈者的積極性,從制度上肯定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公益心,以及使得捐贈款項流入政府和公眾信賴的民間組織。間接稅式支出優惠對現階段我國民間組織的意義不大,因此,民間組織營利性行為的稅收優惠制度設計主要應遵循“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圍繞減免稅、優惠稅率等直接稅式支出和捐贈者稅收優惠來進行。
(一)重新認定營利性行為產生的民間組織所得稅減免稅資格條件
許多國家對公益組織的所得稅,只要用于非營利宗旨的都予以免征,這一貌似公正的做法實際上也存在不公平之處。因為非營利組織凈收益可能來自于非營利行為,也可能來自于營利性行為,而來自于營利性行為的凈收益,其營利主體、與宗旨的相關性、盈利率高低以及營利性行為風險大小等都存在顯著差別,同樣存在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因此,就營利性行為而言,必須結合營利性行為類別等研究民間組織減免稅的資格條件。
1.在滿足“一個原則和兩個標準”的前提下,對沒有Y、N類行為的民間組織,經申請可獲得所得稅免稅資格。世界各國民間組織獲取免稅資格的標準相同也相當嚴格,如在英國,以慈善為唯一目的的組織才能自動取得免稅資格;德國規定只有具有公益目的的社會組織才能獲得免稅資格,我國須同時滿足財稅〔2014〕13號規定的9個條件才能免交所得稅,而且民間組織獲得免稅資格并不是永久性的。各國稅務機關一般都規定有免稅資格審查制度,以判定非營利組織的活動是否符合免稅資格條件。
對于向具有免稅資格的民間組織捐贈的款項(不含實物),在繳納所得稅時可以從捐贈者的應納稅所得額中全額扣除,但我國現行規定比較嚴格,如帶中國字頭的民間組織有2000多家,而根據財政部財稅〔2013〕10號、35號文件,企業捐贈享受稅收減免資格的只有157家(列舉法),不到8%。這表明帶中國字頭的民間組織絕大多數存在或多或少的“現行制度認定的”營利性行為。這種列舉法規定,不僅對不同民間組織的稅收待遇存在歧視嫌疑,也不利于提高捐贈者的積極性,促進民間組織本身向“純公益性”目標邁進。因此,現階段應按財稅〔2014〕13號規定的9個條件,由稅收征管機構認定具有免稅資格的民間組織名單會更符合公平原則。
2.在遵守“非分配約束”原則的前提下,具有Y類行為而不存在N類行為的民間組織可減征民間組織所得稅。如《日本民法典》規定,非營利組織不能完全免繳公司所得稅。日本《團體稅法實施條例》規定,醫療法人按完全的所得稅稅率納稅,除非他們收到的醫療費由社保費支付,這種情況下屬于特定醫療法人,按27%的稅率納稅。因此,國內存在Y類行為的民間組織可減半征收民間組織所得稅(不論其符合項有多少)。對向存在Y類行為的民間組織捐贈財物的一律按公益性捐贈支出處理,其中企業、個人捐贈現金可獲得稅收優惠,分別按《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執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慈善捐助減免稅制度”的要求,因此,可對捐贈者的應稅收入做更大比例的稅前扣除,對捐贈者捐贈給民間組織而產生的贈與和遺產稅可參照國外做法①如美國企業公益性捐贈扣除限額是總收入的10%,個人扣除限額為總收入的50%;澳大利亞規定對企業公益性捐贈不封頂;新加坡對個人公益性現金捐贈金額稅前全部扣除。,規定更為優厚的稅前扣除。
3.不遵守“非分配約束”原則的民間組織,不論其有無營利性行為,都應當認定該組織以營利為首要目的,不能獲取減稅或免稅資格。如有學者估計,我國已登記的20萬家民辦非企業單位,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營利為目的的(金錦萍,2013)。[7]對這一類所謂的“民間組織”必須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堅持營利性、非營利性分開(李克強,2012)[8],并全額征收企業所得稅。
(二)嚴格N類行為的所得稅加征制度
存在Y類行為并享有減稅資格,并不意味著民間組織的一切活動都享有稅收優惠。會費、捐贈、政府資助、被動收入如銀行利息等,以及其他非營利行為所得一般都是免稅的。而營利性行為所得在大多數國家只要用于組織而非分紅也不禁止,但多數國家都借助稅收制度抑制民間組織的“過度”營利行為。也就是說,對民間組織的一部分營利性行為是減免稅的,而另一部分可能像其他經濟實體一樣依法納稅。因此,對民間組織存在N類行為的,應建立營利性行為項目所得稅加征制度,即不能因為存在N類行為而完全否定其非營利性,也不能允許N類行為存在而任其發展。具體原則構想如下:
1.在滿足“非分配約束”原則的前提下,對沒有Y類行為但有N類行為的,可針對該營利性行為項目(而不是民間組織)征收所得稅,即民間組織的任何N類行為都應當按照現行企業所得稅率(25%)征收,但鑒于所獲利潤全部用于公益目的,可按現行企業所得稅率下浮25%征收本項所得稅,如某國內民間組織存在N1、N2項營利性行為,則這兩項營利性行為所得按照25% ×(1-0.25)=18.75%征收所得稅。
2.在滿足“非分配約束”原則的前提下,民間組織同時存在Y類、N類行為的,則對符合N類行為的項目在執行Y類行為稅制的基礎上加征25%的所得稅。這種按非營利行為項目優惠所得稅率的方法不僅符合政府促進民間組織發展的目標,也符合國外非營利組織的稅法慣例。如日本《團體稅法實施條例》對公益性團體列舉了33類具體的經營活動,對這些活動按營業性公司的稅率37.5%下浮28%設定稅率(27%)。對于向存在N類行為的民間組織捐贈財物的一律不享受所得稅收優惠。
(三)創新營利性行為所得稅以外稅種的減免和加征制度
民間組織存在營利性行為除按照上述原則減免所得稅外,對其涉及的流轉稅及其他稅負是否應當減免或加征,仍然應當按照收入用途標準進行決策,具體原則如下:
1.存在廣義營利性行為,如違反規定,基金會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時,應調整應納稅所得額并繳納企業所得稅,其中工作人員工資福利若畸高,超過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民間組織免稅資格認定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123號)工作人員平均工資薪金水平不得超過上年度稅務登記所在地人均工資水平兩倍的規定,即可認定有為個人營利之嫌疑,可考慮將該民間組織轉為營利組織并加收懲罰性所得稅,同時向社會公示,以避免社會公眾被“騙捐”;如存在為組織的營利性行為,導致凈資產積累過多,違背代際公平原則,可增設并征收凈資產稅。
2.有與宗旨無關的營利性行為,應就此行為本身征收與營利組織相同的流轉稅及其他稅負等。德國稅法規定,無關商業活動,如開辦俱樂部、來自慈善雜志的廣告收入,超過6萬馬克的運動項目的入場費和來自商業贊助的收入雖然可以接受,但這些收入均要繳稅。我國現行稅收政策規定,對非營利組織與其宗旨相關或無關的營利性行為都應當征稅。但由于營利性與非營利性行為區分難度大,所以稅務部門對非營利組織與其宗旨相關或無關的商業活動實際上一律不征稅,這一狀況必須改變。這是因為宗旨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存在的理由,營利性行為如與組織宗旨不一致,可能導致民間組織“不務正業”,并造成與其他營利組織的不公平競爭。
3.有等于甚至超過營利組織收益率營利性行為的,應當按照營利組織的稅制征收流轉稅等。如2014年××公司計劃籌資15億元全部用于投資建設××國際醫學中心項目,凈利潤率經測算高達31.54%,遠遠高于同行業營利組織的平均水平。這一項目雖然名義上屬于公益項目,但顯然以營利為目的,因此應征收全部相關稅收。而介于營利組織收益率與平均成本定價法利率之間的營利性行為,除按A類行為減征所得稅外,應當免除該營利性行為的流轉稅等其他稅費。這是因為低于營利組織收益率的營利性行為能夠給社會挽回更多的剩余價值無形損失,平均成本定價能夠使剩余價值無形損失最小化。如圖1,縱軸代表收益率,用收費價格表示,橫軸代表組織的產品供給數量,SMC為短期邊際成本線,SAC為平均成本線,D為需求曲線,MR為邊際收益曲線。模型假設: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的供給條件相同,產品同質,且組織的管理效率相同。

圖1 非營利組織供給示意圖
按照假設,營利組織在利潤最大化目標驅使下,會按照短期內MR=SMC的利潤最大化均衡條件,以P1價格提供Q1單位數量公益產品。而民間組織遵循非分配約束原則,不具有追求利潤的動機和目的,在稅制約束下以平均成本定價法確定供給量,即SAC=P2時的供給量Q2確定價格,同時,民間組織還會受到社會捐贈和政府補助,還可能以低于P2的價格P3提供Q3的供給量。因此,非營利組織按照低于營利組織的收益率運營,并將獲得的收入用于公益性事業時會產生“雙重福利效應”。一方面,可以使民間組織發揮更大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挽回營利組織生產時損失的剩余價值,遂產生“第一重福利效應”。另一方面,民間組織按照服務宗旨將商業化運作的收入用于公益事業,使得社會福利提高,進而產生“第二重福利效應”。因此,政府應以稅制激勵民間組織按照P2、P3價格提供公益產品,以實現公益績效最大化。
即使是法律允許的營利性行為亦如此。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民辦學校“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這里的“合理回報”不高于社會資本平均利潤率(符合A類行為)的可以減稅,否則應按營利組織全額征收企業所得稅,并對出資者征收個人所得稅。
4.高風險營利性行為必須按章交納全部稅收。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風險與收益成正比,收益越高,風險越大。面對客觀存在的營利性行為風險,應根據民間組織的特質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原則,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其次要根據公益性本質滿足流動性要求,收益性應作為最后選擇。如民間組織購買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取得的高風險收入和其他收入產生的所得稅、流轉稅等必須全額繳納,以抑制民間組織的冒險性行為,而對民間組織在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國庫券利息等低風險投資收入不僅免征所得稅,還應免交其他相關稅費,以保證民間組織資產的穩定增長和保值、增值。需要說明的是,購買股票、債券并不都是高風險行為,可根據不同股票的貝塔系數和投資收益標準差確定營利性行為的風險,從而決定征收的稅種和采用的稅率。
[1]Boris I.Bittker,George K.Rahdet.The Exemp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from the Federal Incom Taxation[D].85Yale L.J.299,1976.
[2]張守文.略論對第三部門的稅法規制[J].法學評論,2006,(6).
[3]Henry B.Hansmann.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J].The Yale Law Journal,1980,89(5):842.
[4]王曉,王振耀.民間慈善有了很大轉型[J].瞭望東方周刊,2011,(32).
[5]Pamela Wicker,Christoph Breuer and Ben Hennigs.Disappearing Act:An Analysis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Nonprofit& for-profit Sectors[J].Sport Management Review,2012,15(3):318 -329.
[6]張思強,卞繼紅.營利性行為界定與完善非營利組織所得稅制標準[J].稅務與經濟,2011,(5).
[7]王名,等.社會組織三大條例如何修改[J].中國非營利評論,2013,(2):12.
[8]李克強.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N].人民日報,201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