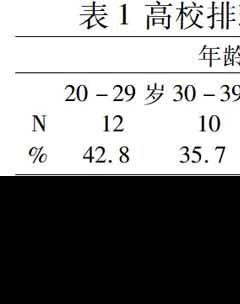徐懋庸的編輯生涯
李先國
摘 ? ?要: 徐懋庸的一生與編輯工作緊密相關(guān)。其編輯成果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整理編輯了自己的作品,二是主編了一些進步刊物,三是注釋整理了與魯迅的通信,從而為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留下了許多一手資料。
關(guān)鍵詞: 徐懋庸 ? ?編輯 ? ?成果
一
1.因編獲罪
1927年初,上虞縣正式成立了國民黨縣黨部,縣黨部門口掛著兩幅大標(biāo)語:“真革命的請進來,假革命的滾出去。”縣黨部主要的領(lǐng)導(dǎo)人是葉天底。徐懋庸的恩師徐用賓任組織部長,徐懋庸開始是組織部干事,后來又被分配在葉天底領(lǐng)導(dǎo)的宣傳部當(dāng)干事,負責(zé)編輯黨報《南針報》。
編輯《南針報》之余,徐懋庸讀了不少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建國大綱》,陳獨秀的《共產(chǎn)主義ABC》,布哈林的《唯物史觀》,以及《共產(chǎn)黨宣言》、《左派幼稚病》、《社會科學(xué)講義》(上海大學(xué)的課本)等。此外,他還經(jīng)常看中共的刊物《向?qū)А泛汀吨袊嗄辍贰Wx了這些書,徐懋庸覺得大開眼界,雖然理解得很少,卻也據(jù)此為知識分子訓(xùn)練班講過幾次課。
上海“四一二”政變的消息兩三天后就傳到上虞,國民黨的“清黨”不久波及上虞。徐懋庸逃到慈溪。5月中旬,徐懋庸接到消息說,上虞的國民黨縣黨部完全被反動分子把持,一些不顯眼的左派都潛伏起來了。秘密轉(zhuǎn)移到一個親戚家養(yǎng)病的葉天底主張辦一份秘密報紙,在上虞問題上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對立的宣傳。編輯由在慈溪的徐懋庸負責(zé),印刷由在余姚的徐鏡如負責(zé),印刷費用由大家拼湊。印好以后,由錢念先、葛紀昌等在上虞秘密散發(fā)。因為是5月創(chuàng)刊的,故定名《石榴》。編輯期間,徐懋庸常與葛紀昌通信,談些上虞情況和約稿的問題。6月20日左右,徐懋庸給葛紀昌的一封信被國民黨反動派在上虞郵局查獲了。信里提到的八個人包括他們兩人都遭到國民黨通緝。6月30日,得到消息的徐懋庸就在當(dāng)天下午乘火車到寧波,換乘輪船逃往上海。后來他考進了上海勞動大學(xué)。
2.因編生隙
在勞動大學(xué)畢業(yè)后,徐懋庸到了臨海回浦中學(xué)教書。1930年9月,徐懋庸把愛好文學(xué)的學(xué)生組織起來,成立了“藝波社”。“藝波社”曾編輯出版《波藝叢書》,第一輯收有作品20篇,于1931年6月出版。
該輯以《門檻》為名,因為首篇就是徐懋庸自己翻譯的屠格涅夫散文詩名篇《門檻》。《門檻》描寫一個俄羅斯少女決心為革命而奉獻自己的一生。他在勞大讀書時,這篇作品曾被選入教材,當(dāng)時他讀后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徐懋庸在本書的卷首,用分行的詩歌形式寫了一篇《題辭》,鼓勵青年參加革命。
徐懋庸的激進思想在一部分學(xué)生中產(chǎn)生極大影響,由此逐漸引起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人的不安以至于不滿,多次對徐懋庸提出了警告。1932年年底,他向陸翰文提出了辭呈。后來他闖入文壇,又回到上海。
1934年春徐懋庸加入“左聯(lián)”后,因為魯迅是“左聯(lián)”的委員長,徐懋庸是“左聯(lián)”理論研究會的一個組員,他同魯迅的關(guān)系進入一個新階段。這時候《自由談》被國民黨反動派所迫停刊,“左聯(lián)”想辦一個半月刊,代替《自由談》這個陣地。恰好有一個慣于投機而不負責(zé)任的光華書局愿意出版這個刊物。光華書局想利用《自由談》在群眾中的影響,力主刊名為《自由談半月刊》,“左聯(lián)”讓徐懋庸擔(dān)任編輯。徐懋庸將這事請示魯迅,魯迅于5月26日的復(fù)信中勸他不要做編輯①。
徐懋庸曾經(jīng)決定不干。魯迅5月31日給楊霽云信中認為他拒絕得好。然而“左聯(lián)”決定還是要在光華書店出版這半月刊,也還是要徐懋庸擔(dān)任編輯,不過經(jīng)過力爭,名稱改為《新語林》。徐懋庸為此還與魯迅面談。《魯迅日記》也有記載。《新語林》辦起來之后,魯迅先生卻是積極支持到底的,不但自己投過好幾篇稿子,還介紹許多別人的稿件。徐懋庸由此認識到魯迅先生很顧大局,決不固執(zhí)己見。
但《新語林》才出了兩三期就有問題了。首先是老板任意扣稿子,其次是拖欠稿費。于是徐懋庸又向魯迅訴苦。魯迅于8月3日給徐懋庸的信中勸他堅決放棄。8月間,經(jīng)“左聯(lián)”領(lǐng)導(dǎo)的同意,徐懋庸辭去了編輯。他編輯過四期《新語林》(半月刊)。接替他的人莊啟東也只搞了兩期,《新語林》終于夭折了。
1935年夏,“左聯(lián)”想恢復(fù)兩年多沒有辦的內(nèi)部刊物。徐懋庸把這事向魯迅報告,他表示同意。稿件湊齊以后,但碰到付印費的困難。要一百多元錢,從哪里來呢?辦法是,第一,把大家在《時事新報》辦的副刊《每周文學(xué)》的稿費充公,不給作者個人(作者都是常委會的幾個人)。第二是募捐,在一次宴會上,徐懋庸請茅盾、胡愈之各捐了十元。當(dāng)時魯迅也在座,徐懋庸向他募捐,他卻沒有答應(yīng)。徐懋庸著急得很,有一次同魯迅面談時,又向他要錢,他仍然說:“我沒有。”這樣拖了一個多月,最后《每周文學(xué)》又增加了一個月的稿費,徐懋庸自己也出了十來塊錢,總算付清了印費,把叫做《文藝群眾》的這批貨取回來了。徐懋庸把這刊物寄給魯迅兩冊,不料寄出的第三天,就收到他寄來的二十元錢。后來魯迅先生給徐懋庸作了解釋:開初不給錢是因為“左聯(lián)”已經(jīng)有兩年多常說要出機關(guān)刊物,卻總不見出。而且每月有人向他收取盟費二十元,也說是辦機關(guān)雜志用的。現(xiàn)在刊物和他見面了,就給徐懋庸寄錢了。
魯迅的解釋,最主要的一點是反映了“左聯(lián)”內(nèi)部的矛盾和不協(xié)調(diào),盟員之間缺乏了解,以致產(chǎn)生很多誤會。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魯迅與徐懋庸的關(guān)系原來并不是那么密切的。如果徐、魯二人關(guān)系良好,魯迅是不會拒絕捐款的,因為魯迅完全知道這份刊物是由徐懋庸主編,更不要說徐懋庸曾經(jīng)兩次親自向魯迅募捐。即使魯迅對周揚等人極為不滿,也不應(yīng)該把這不滿情緒轉(zhuǎn)嫁到徐懋庸身上去②。
3.因編懷念
1941年元旦,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的李文、劉大明、王華三人在太行區(qū)創(chuàng)辦的華北書店正式成立。1943年,該書店決定出版魯迅作品選注本,其中的《阿Q正傳》和《理水》的注釋工作由到太行文聯(lián)工作的徐懋庸擔(dān)任。
當(dāng)時魯迅的作品在中國已廣為人知。然而,由于含義深刻,取材精微,風(fēng)格獨特,語匯繁富,常使許多學(xué)識和經(jīng)驗較淺的青年難以理解。徐懋庸在平常學(xué)習(xí)討論的時候,既能結(jié)合以前與魯迅的接觸與了解,又能結(jié)合馬列主義和其他一些知識的幫助,往往被認為發(fā)言獨到,見解深刻。抗大的一個同志曾提議把徐對這些作品的意見寫出來發(fā)表。開始徐懋庸想到《阿Q正傳》的讀者最多,內(nèi)容最豐富,就從它注起。此后的計劃是,從《吶喊》里面選《孔乙己》、《明天》、《藥》,從《彷徨》里面選《祝福》、《肥皂》、《傷逝》、《離婚》,還從《故事新編》里面選《鑄劍》、《理水》、《采薇》、《出關(guān)》等篇或者選些論文來注釋。實際上徐懋庸注釋了魯迅小說《阿Q正傳》,之后從1943年到1946年還注釋了魯迅小說《理水》、雜文《拿來主義》及雜感《忽然想到》等篇目。
“文革”后期,政治動亂,經(jīng)濟蕭條,文化凋零,許多人處在絕望的黑暗之中。這使徐懋庸想到了魯迅。魯迅在青年時期,就痛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黑暗,立志要加以改革。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于是他感到無聊,寂寞,以至于失去改革的希望。他把中國社會看成一間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人們只能在這里悶死,毫無出路。但是朋友的鼓勵又讓他充滿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魯迅的思想,經(jīng)常動搖于希望和絕望之間。1925年1月1日,他寫了一首散文詩《希望》,認為希望和絕望同樣是虛妄,但存在希望總比陷于絕望要好。這恰恰可以解釋為什么徐懋庸要在1973年注釋魯迅的散文詩《希望》了。這一篇注釋不同于四十年代的注釋,以解釋意義為主。在其后的《一點讀后感》里,徐懋庸說:“現(xiàn)在的青年們,已經(jīng)不大容易體會魯迅在《希望》這篇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心情了。但是,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得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dǎo)的青年里面,倘有個別的人,只因為看到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上所不可避免的某些局部的,一時的消極現(xiàn)象,而看不到光明,失去了對前途的信心,甚至陷于絕望,那才是十分可悲的。這樣的人,除了應(yīng)該讀馬、恩、列、斯,毛主席的書以外,讀讀魯迅的這篇散文詩,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啟發(fā)的。”③
二
1.自編文集
上世紀三十年代徐懋庸是以寫作雜文而出名的,他常在《文學(xué)》、《新語林》等幾十種報刊上發(fā)表雜文,后收集出版的雜文集主要有:《不驚人集》,1934年編集,1937年出版,收有雜文五十二篇;《打雜集》,1935年出版,收有雜文五十四篇。
徐懋庸的文章,大部分是在生活書店辦的刊物——《新生》、《大眾生活》、《太白》、《世界知識》、《文學(xué)》、《世界文庫》、《譯文》上發(fā)表的。徐懋庸的譯著《社會主義講話》、《猶太人》、《伊特勒共和國》、《小鬼》等絕大部分是在生活書店出版的。生活書店所付給徐懋庸的稿費,是徐懋庸1933—1937年的生活費的主要來源。1934年,他曾將自己的雜文作品編過一本《不驚人集》,國民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不予通過,稿子也沒有退回。1937年由千秋出版社出版。1935年徐懋庸出版另一本雜文集《打雜集》,二十萬字。魯迅給他作序。
這一段時期,徐懋庸用雜文的筆法,發(fā)表了不少談文藝的短篇論文。收成集子的有《街頭文談》、《怎樣從事文藝修養(yǎng)》、《文藝思潮小史》等。
《街頭文談》由上海光明書局于1936年5月出版,共收文章28篇,附錄4篇。
在徐懋庸之前,用通俗的文筆寫文學(xué)論文的,已有夏征農(nóng)先生《文學(xué)問答集》。徐懋庸起初卻并沒有效顰的念頭。倒是《新生周刊》的編者艾寒松先生勸誘徐懋庸,說他可以寫些這樣的文章給《新生》的讀者看看,徐隨口答應(yīng)了,便一禮拜一次地試寫“街頭文談”。徐懋庸用“力生”的筆名在《新生周刊》上按期發(fā)表。當(dāng)發(fā)表到第十一篇的時候,《新生》便在“妨礙邦交”的罪名之下被禁止了,還有兩篇寫好了也不曾登出。隔了數(shù)月,《生活知識》創(chuàng)刊,要徐懋庸投稿,徐懋庸便寄去了那兩篇存稿,但抹掉了“街頭文談”的總稱,因為徐懋庸本來打算不再寫了。不料《生活知識》的編者,仍給加上原來的總稱,而且要徐懋庸繼續(xù)寫下去,也是每期一篇。情不可卻,于是徐懋庸只好重新動手,但是不滿十篇,終因忙于他事而停止了。1936年5月編印單行本時,還加了不少《街頭文談》之外的文藝論文進去。因為徐懋庸覺得自己的其他論文,也是“街頭”的講話。街頭的講話的特色是通俗,自然同時或者免不了淺薄。徐懋庸承認,《街頭文談》只是在學(xué)習(xí)中的筆記,雖然淺薄,卻也曾獲得不少讀者喜愛④。
徐懋庸的《文藝思潮小史》,1936年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光華書店發(fā)行。1948年又在哈爾濱出東北版。
徐懋庸認為這一本小冊子,不能算是一種著作,只是好幾種文學(xué)史和文藝思潮史的內(nèi)容撮述,尤以弗理契《歐洲文學(xué)發(fā)達史》和柯根《世界文學(xué)史綱》等幾種為主要的根據(jù)。這兩本書是中國當(dāng)時僅有的較詳細的唯物觀世界文學(xué)史,徐認為青年們必須一讀。
為什么有撮述的必要呢?徐懋庸解釋:一則許多書卷帙太大,內(nèi)容太繁,非自學(xué)的青年在短時間所能讀完,并且倘沒有一些預(yù)備的知識,讀了也難以完全了解。二則原有各書,所敘的時代,大抵不完全,如《歐洲文藝發(fā)達史》,從中世紀說起,而忽略了古代,《世界文學(xué)史綱》則敘述現(xiàn)代處很簡略,尤其是蘇聯(lián)的文藝思想,普通的文藝史上都還不曾說到。三則原有各書雖都有獨到之見,但也各有錯誤的觀點,初學(xué)的青年往往難以辨別。因此,徐懋庸認為有必要編一本簡明的包括各時代的、采原有各書之長而舍其所短的小冊子是必不可少的。故而,當(dāng)“青年自學(xué)叢書”的編者向他征稿時,他就認定了這一工作。著手之后,他又想到普通的世界文藝思潮史都不涉及中國的一部分,這也是一種缺陷,最后又自撰《中國文藝思潮的演變》一章,說明五四以來直到目前的中國新文藝思想的發(fā)展。這可以說是本書的一個特點。
徐懋庸的《街頭文談》的成功使他后來在《大眾生活》上,又用了“林矛”的筆名,寫起“文藝修養(yǎng)”來。可是后來《大眾生活》也和《新生》一樣,遭了禁止。“文藝修養(yǎng)”自然也像“街頭文談”那樣中斷了,先后只登了十二篇。徐懋庸想要留個紀念,所以決心把“文藝修養(yǎng)”編成一本書,除了已經(jīng)發(fā)表的十二篇之外,又新寫了九篇,并加三篇附錄。《怎樣從事文藝修養(yǎng)》由上海三江書店1936年12月15日初版。
2.主編刊物
三十年代徐懋庸除了主編《新語林》、“左聯(lián)”機關(guān)內(nèi)部刊物《文藝群眾》外,編過的刊物還有:
《時勢新報·青光》副刊《每周文學(xué)》,1935年9月15日創(chuàng)刊,1936年6月2日終刊,共出36期。每周文學(xué)社編,徐懋庸、王淑明主編。主要內(nèi)容為刊登文藝作品,譯文。有何家槐、風(fēng)子、立波、林淡秋、林煥平、旅岡、梅雨等投稿,多是左聯(lián)常委成員。
《新知識》半月刊,1936年12月10日創(chuàng)刊,1937年1月停刊。存見2期。編輯:王達夫、呂驥,徐懋庸、張庚、錢紹華,上海《新知識》社出版。
《希望》半月刊,1937年3月10日創(chuàng)刊,編輯人徐懋庸、王淑明,出一期后,徐懋庸辭去編輯職務(wù),從第二期起,由王淑明編輯。共出2期,由希望出版社出版,上海中國圖書雜志公司總發(fā)行。《希望》刊登各種短篇文藝作品,譯文。撰稿人有喬木、沙丁、羅烽、周木齋、周揚、郭沫若、何家槐、梅雨、立波、林淡秋、張庚等。
另外,徐懋庸也參與過編輯《太白》半月刊。該刊是1934年9月20日創(chuàng)刊,1935年9月停刊,共出24期。編輯艾寒松、傅東華、鄭振鐸、朱自清、黎烈文、陳望道、徐調(diào)孚、徐懋庸、曹聚仁、葉紹鈞、郁達夫。編輯人陳望道。上海生活書店發(fā)行,發(fā)行人徐伯昕。《太白》刊登各類文字,畫稿、木刻也刊載。特約艾蕪、巴金,冰心、草明、陳子展、豐子愷,夏丏尊、廖埜容、夏征農(nóng)、任白戈、胡愈之、杜重遠、黃源、風(fēng)子、洪深、楊騷等撰稿。
《太白》辦起的時候,正是中國出版界的困難時期的開頭。那時候編輯委員會雖曾有過較遠的志向,較大的計劃,然而后來大抵不能實現(xiàn)。但在陳望道先生獨力奮斗之下,這刊物在這困難的一年中,畢竟還成就了許多可貴的工作。手頭文字的采用和推行的便是其一。其二則是編成了“小品文與漫畫”特輯,將小品文和漫畫的綜合的知識提供給讀者。
1934年9月20日《太白》半月刊創(chuàng)刊號上徐懋庸發(fā)表了《要辦一個這樣的雜志》一文,作為對于《太白》編輯委員會的提議。停刊后,徐懋庸作為編輯委員,曾經(jīng)撰文談到《太白》的停刊。他相信《太白》在扭轉(zhuǎn)《論語》和《人間世》所造成的頹廢的個人主義的小品文作風(fēng)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4年七八兩月中,徐懋庸編過四期《新語林》的半月刊,后來因為發(fā)行這刊物的書店對稿費不負責(zé)任,使他覺得對不起作者就辭職了。辭后不久,《社會日報》上登出一個消息,說徐懋庸將繼《新語林》而編輯《芒種》半月刊。
辭掉《新語林》的編輯后,徐懋庸接著加入了生活書店的一個半月刊的編輯委員會。其時那個半月刊方在籌備,名稱未定,大家分頭擬想,他也想了幾個,但都不好,最后是決定采用了陳望道先生所擬的“太白”。在《太白》定名的次日,徐懋庸忽然想起《律歷志》上的二十四氣的名目,覺得其中的“驚蟄”和“芒種”等幾個頗可作刊物名之用;后與曹聚仁談起,他也以為很好,而且特愛“芒種”這一個。
群眾雜志公司要辦一個刊物,請徐和曹先生合編;徐稍稍考慮了一下,就答應(yīng)了,并且和曹先生商定,乘機就把“芒種”兩字用了出來。他們就把這個刊物辦了起來。《芒種》半月刊,1935年3月5日創(chuàng)刊,1935年10月5日起,刊行第2卷第1期,存見11期(第1卷共10期,第2卷1期)。編輯人徐懋庸,曹聚仁。第1期起至第8期,由上海群眾雜志公司發(fā)行,第9期起,改由上海北新書局發(fā)行,并組織編輯委員會,負責(zé)編輯人還是徐懋庸、曹聚仁。《芒種》刊登對社會大小事件的小評論、長篇論文、半月讀報記、國外消息、歷史小說、諷刺小品、隨筆,短長篇小說。投稿者有喬木、姚雪垠、方之中、陳子展、沙丁、韓滔、盛公木、李輝英,聶紺弩、魯迅、林煥平等。
到延安后,徐懋庸編輯過《華北文化》半月刊。這是晉冀魯豫文聯(lián)辦的刊物,《華北文化》社編輯,陳默君,張秀中主編,1942年1月25日創(chuàng)刊。出至第2卷第3期改刊,共9期。1943年4月25日改出革新號,由徐懋庸,林火主編,1944年2月25日停刊,共出16期,華北新華書店出版。
《華北文化》革新第3卷第3期徐懋庸發(fā)表了《寫作者要請工農(nóng)兵作顧問——向〈華北文化〉的投稿者提議》一文。針對當(dāng)時文化界的寫作者雖早就下了決心要把作品做到大眾化通俗化,但是又苦于沒有辦法實現(xiàn)這個決心,徐懋庸提出一個辦法,就是寫作者要請工農(nóng)兵做顧問。文中徐懋庸通過實例總結(jié)請工農(nóng)兵作顧問有五個好處:會啟發(fā)我們的思想,會提供給我們很好的材料,會幫助我們想出很好的譬喻,會指教我們怎樣很好地組織語言,會糾正我們的表現(xiàn)方法。還談到請工農(nóng)兵作顧問要注意六個方面的問題并希望大家都嘗試。
此外,徐懋庸還和方紀主編過《熱潮》半月刊,1946年6月創(chuàng)刊,承德《熱潮》社編輯,存見3期。
3.釋編通信
徐懋庸曾經(jīng)根據(jù)巴比塞編的法文譯本譯出《列寧家書集》,三十多萬字。1937年出版。此書稿費成為徐懋庸去延安的旅費。晚年他還編輯過自己與魯迅先生的通信。
徐懋庸第一次同魯迅通信,是1933年的11月間。那一年初,徐懋庸從黃巖到上海,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夏季開始寫雜文投寄給黎烈文編輯,受到黎烈文的歡迎。此后徐懋庸便成為《自由談》的撰稿者之一。11月間,徐懋庸翻譯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出版,就寄了一本給魯迅,魯迅當(dāng)夜就作復(fù)。17日和19日他又給徐懋庸兩封信,更正了他15日信中答復(fù)的一個錯誤,并指出徐懋庸的一句譯文的錯誤。在首尾5天內(nèi),魯迅給素未謀面的徐懋庸共寫了3封信。事實上,這在魯迅方面來說并不是很常有的。例如魯迅在1926年1月17日接到胡風(fēng)的信,便沒有回信。1934年4月28日,葉紫給魯迅的信,也是在三天后才作答。徐懋庸這次得到魯迅的優(yōu)待,可能是與他翻譯《托爾斯泰傳》有關(guān),另外就是他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發(fā)表的雜文,與魯迅的基本是同一步伐的⑤。自此,徐懋庸便經(jīng)常寫信給魯迅。據(jù)統(tǒng)計,自1933年11月15日魯迅收到徐懋庸的第一封信起,到1936年8月魯迅發(fā)表《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的公開信止,徐懋庸寫給魯迅的信共60封,魯迅給徐懋庸的信也有52封(公開信不算在內(nèi)),數(shù)目實在不小。不過,在王宏志看來,仔細分析現(xiàn)存魯迅給徐懋庸的45封信后,便不難發(fā)覺其實魯迅與徐懋庸并沒有深厚的個人友誼。第一,魯迅給徐懋庸的信,絕大部分都是篇幅短小的,四五百字的只有一兩封,大部分只有一二百字左右,而短至100字以下,甚至只有二三十字的也很多,與其說是書信,倒不如說是便條。第二,書信的內(nèi)容主要是圍繞出版的問題,大多只是談一些有關(guān)稿件的事,并不見有進一步涉及比較私人的事情。此外,比較魯迅寫給一些較親密的朋友的信如曹靖華、蕭軍、蕭紅和胡風(fēng)等,魯迅在那些信中不但經(jīng)常談及自己的生活、思想及健康狀況,對于對方的生活及近況也很清楚了解,且時常開玩笑、發(fā)牢騷等。這都是在寫給徐懋庸的信中所沒有的。此外,魯迅給徐懋庸的信中,處處表現(xiàn)得很客氣,例如始終稱徐為“先生”,語氣上也很能顯出二人的距離。所以,書信的數(shù)目,實在不能證明二人關(guān)系密切。主要的原因是徐懋庸當(dāng)時在編輯《新語林》和《芒種》等刊物,魯迅經(jīng)常投稿及介紹稿件,所以才有這么多的書信往還。顯然,這都是公事上的交往。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寫了一封信給魯迅,對魯迅提出詰難。當(dāng)時魯迅在病中,身體很差,“因為沒有氣力,花了4天工夫”⑥,寫成了公開信《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發(fā)表在8月15日的《作家》第1卷5號上。這就是當(dāng)時上海文壇所稱的“萬言長文”。
徐懋庸跟著又寫了一篇還擊的文章《還答魯迅先生》,發(fā)表在一份較小的雜志《今代文藝》上。另外,還有一篇叫《一封真的想請發(fā)表的私信》,刊登在1936年9月1日的《社會日報》上。
1937年1月,許廣平在《中流》雜志發(fā)布《許廣平為征集魯迅先生書信啟事》。
楊霽云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長虹、侍桁、徐懋庸等處藏魯迅先生的信件諒亦不少,我望他們光明地能貢獻出來。不過魯迅先生的信札全部發(fā)表出來,我想將刺痛一部分鬼魔的心,阻礙一定不少。這點要先生繼魯迅先生之志毅力戰(zhàn)斗才成。”⑦
高長虹、韓侍桁和徐懋庸,起初都是與魯迅過從甚密的青年,深得魯迅愛護提攜,魯迅與他們談文論藝,信札往來頻繁,最終他們卻都與魯迅反目成仇。許廣平征集魯迅書信的啟事發(fā)出后,果然不出楊霽云所料,高長虹、韓侍桁都沒能將他們手中的任何一封魯迅書信“光明地貢獻出來”。直到1938年10月,許廣平在提起韓侍桁時,還對他不愿出借魯迅書信一事耿耿于懷⑧。
1937年1月13日,當(dāng)徐懋庸在10日出版的《報告》雜志上看到許廣平征集書信的啟事,他當(dāng)日就去函詢問,顯然他是一看到征集啟事就行動起來了,可見其關(guān)切之情。但就徐懋庸信中所言,則他對出借魯迅書簡一事也顧慮重重,主要是顧忌到許廣平等人是否“對收信者擬有所甄別”⑨,這里的“收信者”當(dāng)然是指徐懋庸自己。這種疑慮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在剛剛過去的魯迅葬儀中,徐懋庸挽聯(lián)被取消的遭遇,使此刻的他依然心有余悸,擔(dān)心作為“收信者”的自己還會受到排斥。
當(dāng)徐懋庸得到許廣平回復(fù),被告知征集魯迅書信的原則是“對于征求信稿文件,是向各方普遍收集的”,并且保證“至于編輯方面,則請先生不必擔(dān)心也”⑩之后,徐懋庸才將所集魯迅手札一本,共四十余封通寄給許廣平,但依然格外小心謹慎,不忘在信末附言中叮囑許廣平:“所有手札原件,希勿使多人看到,幸甚。”?輥?輯?訛后來《魯迅書簡》中印出來的是四十三封。
“文革”結(jié)束之后,徐懋庸應(yīng)陳漱渝之邀決定整理注釋他與魯迅之間的通信。徐懋庸希望自己的注釋,將與曹靖華的《魯迅書簡——致曹靖華》注釋法不同,范圍要寬一些,將說明一些事實,并對魯迅先生的思想作些分析,有些地方,還要聯(lián)系魯迅先生給別人的一些信。計劃在三四個月內(nèi)完成。然而寫作時面臨的困難不少。一是當(dāng)年冬天南京天氣不好,他身體感到不適。二是缺少必要的資料和助手——沒有幫助抄寫的人,更沒有復(fù)寫、打印的條件。但徐懋庸以高昂的精神狀態(tài)不斷克服著面臨的困難。在此期間,陳漱渝跟他書信往返頻繁。
1976年12月23日,新華社發(fā)布了一則電訊,刊登于次日《人民日報》第4版下方,題為《新發(fā)現(xiàn)一批魯迅書信》。標(biāo)題下有一段按語:“這些書信,都是魯迅成為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者的最后十年寫下的,其中對徐懋庸伙同周揚、張春橋之流,‘以文壇皇帝自居,圍攻魯迅的反革命面目的揭露,對我們今天深入揭發(fā)、批判‘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斗爭有重要意義。”這條電訊使徐懋庸大吃一驚。這離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后僅僅兩個月,徐懋庸居然又跟“四人幫”成了拴在同一根繩上的螞蚱。這種荒謬是徐懋庸萬萬想不到的,對他的打擊之大也是局外人難于體會到的。不久之后,徐懋庸含冤而逝。在病中,徐懋庸懷著十分沉重的心情,寫出了《對一條電訊的意見》,成為他四十余年文字生涯中的絕筆。徐懋庸對他與魯迅的通信的注釋和編輯工作雖然沒有完成,但已經(jīng)進行的無疑也是一份珍貴的魯迅研究資料。
注釋:
①魯迅.魯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124.
②王宏志.魯迅與左聯(lián).新星出版社,2006:230.
③徐懋庸.釋魯迅散文《希望》·一點讀后感.徐懋庸選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72.
④徐懋庸.《街頭文談》小引.徐懋庸選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304.
⑤王宏志.魯迅與左聯(lián).新星出版社,2006:221.
⑥魯迅1936年9月15日給增田涉信.譯文見《魯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396.
⑦周海嬰,編.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244.
⑧程振興.魯迅書信的征集與擇取.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10(1).
⑨⑩周海嬰,編.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