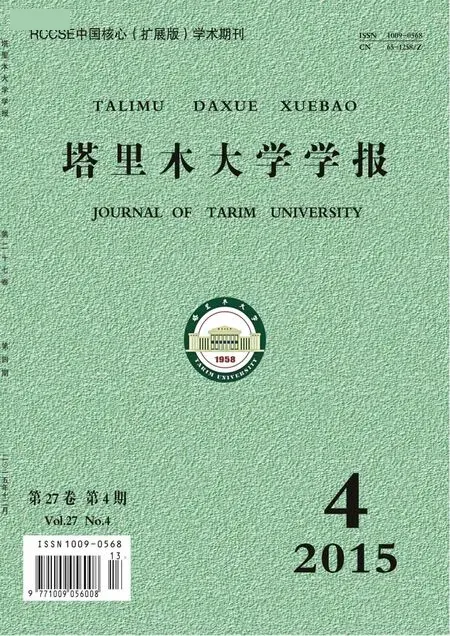新疆甕城起源芻議
徐承炎 曹中月
(1 塔里木大學西域文化研究院, 新疆 阿拉爾 843300)(2 塔里木大學圖書館, 新疆 阿拉爾 843300)
?
新疆甕城起源芻議
徐承炎1曹中月2*
(1 塔里木大學西域文化研究院, 新疆 阿拉爾 843300)(2 塔里木大學圖書館, 新疆 阿拉爾 843300)
摘要甕城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與角樓、馬面等共同構筑起了古代城池的防御體系。經系統梳理和考證新疆的古城材料后發現:新疆現存形制可辨的甕城最早見于北庭故城,其修建年代在唐初的顯慶三年(658)至龍朔二年(662)之間,它是唐廷加強邊州防御力量應對西北邊境復雜、殘酷的軍事斗爭形勢的歷史產物。新疆甕城隸屬于中國的邊城防御體系,是散落在祖國西北邊陲的歷史遺珍,具有重要的歷史考古價值。
關鍵詞甕城; 新疆; 邊城; 唐朝
新疆為當今我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區,地處亞歐大陸的中心,自古以來就是中西聯系的前沿要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歷史時期,這里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競相爭奪的戰略要地而備受青睞,現今新疆境內所存數量眾多的古城、戍堡遺址便是當年這種復雜、殘酷軍事斗爭的產物和實物見證。
筆者在翻檢新疆古城考古調查資料時,發現部分古城附有甕城遺跡,就目前筆者所據材料來看未見有學者對這一現象給予過關注、開展過研究。開展新疆境內的甕城研究或有助于了解古代新疆地區的軍事戰爭史和城市建筑發展史,故筆者不揣淺陋擬就新疆地區的甕城起源時間及其出現原因略陳管見,不妥之處,還請方家批評指正!
1唐代及其以前的新疆筑城
新疆古稱西域[1],地處祖國西北邊陲,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早在漢代以前,這里就與中原發生了聯系[2],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之后,這種往來、交流又獲進一步發展。西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都護府設立后,中央為加強和鞏固在西域的統治地位,又進一步落實了西漢初年晁錯提出的移民實邊政策。隨著這一策略的貫徹執行,大批內地軍民來此屯駐,不僅極大的促進了西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影響和改變了西域先民的生產生活方式。
“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的出現,標志著古老的氏族社會將結束,新的文明時代就要來臨”[3]。漢代以前新疆地區的筑城不見于文獻記載,但考古資料顯示,這里的筑城或有著較為長久的歷史淵源。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艾濤館員在對莎車縣的蘭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了一座采用卵石包墻技術修筑的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古城遺址[4]。此前,學界一直認為地處哈密盆地的焉布拉克古城與伊吾縣的鹽池古城是新疆地區年代最早的古城遺址[5],蘭干古城的發現再一次改寫了新疆地區的筑城歷史,并將該區域的筑城歷史提早到了青銅時代。目前新疆地區發現年代較早的古城遺址除蘭干古城、焉布拉克古城和鹽池古城外,還有和田克里雅河流域的圓沙古城和圓沙北古城2處,兩者的始建年代均早于西漢[6]。漢代以前的新疆古城在構筑技術上,主要以木骨泥墻和卵石壘砌、夯土夯筑、局部土坯壘砌的建筑形式為主,且這一時期新疆境內所存的古城數量也十分有限,或表明漢代以前新疆的筑城尚不發達,這可能是受其近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的習俗影響。
兩漢時期新疆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范圍,這進一步的促使了新疆與中原內地間的文化交流和技術傳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西域的筑城歷史。文獻所載兩漢新筑的古城有烏壘城、它乾城、依循城、高昌壁、柳中城、金蒲城等,這些新城無一例外的都是中央派駐西域的駐軍所筑。除此之外,西域的土著邦國中也有因仰慕漢家文化,而主動新修漢式建筑的記載。《漢書·西域傳》載“(龜茲王絳賓)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檄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便是對西域邦國學習內地筑造宮室技術和禮儀制度的真實寫照。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王朝戰亂不斷,政權更迭頻繁,統治集團無法全面有效的管理西域,這間接的影響了新疆地區的筑城發展。目前所見這一時期的新筑城址僅若羌縣境內的海頭古城[7]。隋唐時期結束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分裂割據局面,完成了國家統一,并于新疆境內創設了以北庭和安西都護府為主要行政管理機構的羈縻督府制度,有效治理新疆百余年。這一時期中央為鞏固在西域的統治地位,有效抵御吐蕃、突厥與大食的侵擾,陸續在漢魏以來的交通要道上興修了大批軍鎮、守捉、烽鋪等軍事機構,并增派西域駐軍、擴大西域屯田規模,伴隨著這些舉措的實施,新疆地區的筑城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新五代史》載 “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余城,常以中國兵更戍”[8]便是對唐代西域筑城盛況的著述。
近年來,新疆地區第三次文物普查結果顯示“全疆共發現城址370處……從年代上劃分,史前城址4處,漢唐時期城址255處、宋元時期城址30處、明清城址(清代為主)81處”[9],這一調查數據不僅與文獻所記漢唐時期西域的筑城盛況相吻合,同時也表明漢唐或是整個新疆筑城史上最為繁榮興盛的歷史時期。雖然普查數據反映了漢、唐時期新疆古城快速增長的共性,但卻忽視了兩個時期里各自所存有的個性。分論漢、唐時期的新疆筑城則不難發現,唐代新疆的筑城不僅在數量上較漢代有大幅增長,在筑城技術和城防御體系的構建上也比漢代有所進步。1980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隊的成員在對唐代的北庭古城開展考古調查時發現“馬面、敵臺、角樓和甕城等都使用了絍木的做法。這種平面布局和構筑特點完全反映了我國中原地區傳統的筑城技法在新疆地區的推廣使用”[10]。
綜觀唐代及其以前的新疆筑城歷史不難發現,史前至漢唐的新疆不僅在筑城數量上有所增加、技術上有所進步,在筑城理念和城防體系的構筑上也有所創新。然這些筑城技術的改進,都得益于自漢以來新疆不斷與中原內地所開展的交流與學習。甕城這種特殊的建筑,在新疆地區古城中的出現當有著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對新疆地區甕城出現時間與時代背景的探討也正是開展新疆甕城研究的重要內容。
2新疆甕城出現年代考證
甕城是一種修筑于城門內外護衛城門,增強城池防御力量的附屬建筑,形制主要有半圓形和方形兩種。關于甕城的起源,朝鮮和韓國的一些學者曾有異議,并認為甕城之制起于高句麗[11]。我國著名的古代建筑史專家張馭寰先生則認為“甕城之制是我國特有的。無論是從軍事防御上,戰略進攻上以及平日之防守,都離不開它,都是必然著重建立的。”[12]近年來國內的考古發現也印證了張先生的論斷。201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多家單位組成的考古隊在對神木縣石峁城址外城東門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了年代約當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甕城遺跡[13]。石峁古城中甕城遺跡的發現,有力地反駁了甕城之制起源于高句麗的說法,間接的說明了甕城之制起源于中國。
新疆境內的甕城起于何時,史料中無確切記載,但從文獻資料來看,清代就已出現甕城。《新編肅州志》載“(巴里坤縣東破城子)城周長二里五分,高一丈六尺,開南北兩門,筑有門洞、小甕城、門樓,設吊橋,四角設有角樓”[14],此城及其相鄰的西破城子古城是清雍正九年(1731)寧遠大將軍岳鐘琪在修筑巴里坤漢城告竣后,于漢城東西各5里所修筑的兩座小型兵城[15]。

圖1 新疆所見年代較早的甕城遺跡
清代以前的新疆甕城情況不見于文獻記載,有學者在對樓蘭古城與海頭古城進行考古調查時發現了疑似甕城的遺跡現象[16],這一對兩城中甕城遺跡的辨識曾一度將新疆地區的甕城出現年代提早到了魏晉時期。但筆者在翻檢兩處古城的資料時發現,前人學者對兩城中甕城遺跡的判識并無十分的把握,而是僅據樓蘭古城西城垣的中部北端有“東西錯列的土墩兩個”[17]、海頭古城外有與“城墻相連的不規則夯土臺”[18]這些現象給出的一個初步推斷,這似乎并不能作為魏晉時期新疆就已出現甕城的確鑿證據。目前,新疆境內考古所見甕城形制清楚,且年代早于清的古城址共有9處(圖一),分別為昌吉市的昌吉古城、吉木莎爾縣的北庭故城、吐魯番市的高昌故城、庫車縣的唐王城和阿艾古城、新和縣的喬拉克海協爾古城和通古孜巴什古城、沙雅縣的博提巴什古城與且末縣的蘇堂古城。在上述古城中除昌吉古城的年代稍晚,約當中原王朝的宋、元之際外[19],其余古城的年代據文物工作者推斷均為唐代,但諸城的具體年代仍不清楚,尚有進一步考證的必要,茲就各城情況分述如下。
位于絲綢之路咽喉要道上的高昌故城曾是漢代高昌壁、前涼高昌郡、北魏高昌國、唐代西州城和高昌回鶻國的治所(或都城)所在,前后共歷時1 400余年。故城現存宮城、內城和外城三部分,其中在外城的西城門外還存有曲折的甕城遺跡。20世紀50年代,閻文儒先生對高昌故城進行過踏查,并初步推斷外城的修筑年代在唐或唐之后。[20]近年來,孟凡人先生在對高昌故城進行系統研究后,指出“現在高昌故城的外城,在麴氏和唐代并不存在,而是回鶻高昌國時期新建的”,而“高昌回鶻大規模的改筑擴建高昌城,可能在10世紀中葉左右”。[21]孟凡人先生這一有關高昌故城外城修筑年代的考證也得到考古發掘材料的印證。200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國家啟動的絲綢之路(新疆段)重點文物保護工程項目,對高昌故城外城西門和西南角的大佛寺進行了考古發掘清理,清理結束后工作人員根據發掘情況和采集標本的碳十四測量年數據判定:大佛寺和西門在時代上的差異并不明顯,二者絕對年代在距今700~1 000年左右。[22]考古測年數據與專家考證相吻合,進一步的將新疆地區甕城出現的時間從清代提早到了公元1 000~1 300年之間的高昌回鶻時期。
同處絲綢之路要道,與高昌齊名的北庭古城,曾是唐代庭州城、北庭大都護府和高昌回鶻時期的夏都駐地。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隊的成員在對北庭古城進行調查時,發現外城的“北門北側有曲折的甕城,甕城西墻和北墻相連,呈‘┏━’形”,“北庭古城現存的外城墻可能始建于唐朝初年”[23]。這一推測也得到了孟凡人先生的肯定,但他在對北庭故城進行系統研究后又進一步指出,外城是唐在平定阿史那賀魯之亂后重置庭州時所重修的,重修時間在唐顯慶三年(658)至龍朔二年(662)之間[24]。北庭古城從高宗朝重修完成直至毀棄不用的時間里,雖曾屢遭唐與突厥、突騎施、吐蕃等少數民族政權間戰爭所帶來的損毀,但卻不見有毀壞嚴重而致重建的文獻記載。其后的回鶻高昌時期此城雖經歷過一次重建,但重建的范圍卻較為有限,僅限于內城城門和內城的王宮,并未涉及重建外城。[25]是故,孟凡人先生對北庭外城始建年代的考證是值得信服的。北庭古城的外城修筑年代既已確定,而外城北門處的甕城筑于何時呢?經考證,筆者認為甕城與外城是同時完成修筑的。首先,甕城的墻基寬度(西墻寬8、北墻寬7、東墻寬5米)與外城的基寬相當(調查發現外城的墻基寬5~8米)[26];其次,甕城北墻存有縱橫布置的纴木,墻體夯筑的方式為薄夯層、密夯窩,這種建筑方式與內城所見的厚夯層、無夯窩差別較大,另據孟凡人先生在新疆東部地區多年來開展考古調查的經驗推知:這種夯筑加纴木的建筑方式是新疆唐代建筑的特點之一[27];再次,文物工作者在對北庭故城調查時發現有增筑馬面的情況,而對甕城記述時則僅言有多次修補的痕跡,未見談及甕城是否系增筑,這也間接說明甕城主體當是與外城同時修筑的[28]。最后,北庭城是在歷經阿史那賀魯叛亂被毀后重新修建的新唐城,且其又是唐代所轄50余邊州之一[29],是故其在修筑時必會更多的考慮軍事防御體系的構筑,而甕城這一在中原出現時間較早、軍事防御效果極佳的建筑也必在其修筑之列。綜合以上各點,我們認為北庭古城外城門處的甕城必與北庭城是同時修筑的,具體時間在唐顯慶三年至龍朔二年之間,甕城修筑完成后曾在唐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戰爭中屢有損壞,但卻并未致廢毀重筑,而是在不斷修補后一直沿用至古城廢棄。
相較于昌吉城、高昌城和北庭城,余下六處有甕城遺跡的唐代古城均位于唐代的安西之地,且針對這些古城所開展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均較少。目前僅見黃文弼[30]、張平[31]、邢春林[32]、李并成[33]等學者集中對通古孜巴什古城、庫車縣唐王城(俗稱“大黑汰克沁古城”)和阿艾古城三城中的某個進行過調查和局部試掘。雖然以上三城有或多或少的考古發掘與調查資料,但終因所得資料比較零散而無法系統整合并斷定三城的具體年代,更遑論古城城門外的甕城修建年代。雖然此六處古城的具體修筑年代無法準確判定,但關于唐代安西局勢的文獻記載或對這些古城修筑年代的考證有所裨益。唐廷自貞觀十四年(640),侯君集率軍平高昌國改置安西都護府起,一直積極經營西域。隨著在與西突厥斗爭中的不斷勝利,唐廷逐漸控制了天山南北的大片區域,貞觀末移安西都護府于龜茲城,兼統于闐、疏勒、焉耆、龜茲四鎮,后因高宗“不欲廣地勞人”而棄四鎮,重將安西都護府遷回西州。從顯慶三年(658)五月,唐廷移安西都護府于龜茲起,至長壽元年(692)王孝杰率軍克服四鎮的三十余年中,新興的吐蕃王朝與唐在安西地區展開了一系列的爭奪戰,唐廷數戰不利,四鎮之地多次易手。有學者曾對這一現象開展過研究,并認為初唐時期所設的安西四鎮僅具《新唐書·百官志》中“防人五百”的上鎮規模,是一個介乎州縣制與小邦國間的過渡形式,四鎮的主要職能是協助安西都護府做好境內的“掌撫慰諸番、輯寧外寇、覘候奸譎”工作,此時的四鎮只有防人而并無鎮軍,并不能算的上是嚴格意義上的軍鎮。唐與吐蕃在西域的軍事較量中被動、不利的局面,直到長壽元年王孝杰率軍收復四鎮、中原征調“漢兵三萬”來安西鎮戍之后才漸有改變,并逐漸完成四鎮由都護府下轄“鎮”向節度使下轄“軍鎮”的轉變。[34]四鎮初設至長壽年間,唐廷在安西一直采取著“蕃漢相兼,以之制邊”的經營策略,這一時期四鎮的駐軍數量十分有限,且唐廷在安西的統治地位也尚未穩固,試想在此情形下征調大量勞力、興修數量眾多的軍事意義突出、功能結構復雜的帶甕城遺跡的古城幾乎是不可能的。近年來,文物工作者對這些古城開展考古調查時所獲的部分資料也可印證以上論斷。張平先生對阿艾古城調查時發現“城內地表以下約1米處有文化層,經碳十四測年,時代在公元650~720年間”[35]。另,曾有村民在通古孜巴什古城中拾得有大歷年號的殘紙[36],城內還曾一次性挖掘出3000余枚大歷元寶、建中通寶等唐代中期的錢幣[37]。雖然銅錢和帶有年號的殘紙并不能直接作為斷定古城年代的依據,但這些遺物的出土或可說明大歷年間是通古孜巴什古城社會生活較為活躍的一個時期。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安西地區現存的帶有甕城遺跡的唐代古城均修筑于王孝杰率軍收復四鎮、唐廷征調三萬漢軍進駐安西之后的一個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里。易言之,安西地區唐代古城中出現甕城的年代不早于公元692年。
從疆內現存形制清楚的甕城遺跡來看,這里的甕城最早見于唐代的北庭故城,其修筑年代在顯慶三年(658)至龍朔二年(662)之間。
3新疆甕城出現原因試析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繼漢之后經營西域的又一高峰。立國之初,國力孱弱,且國內割據政權林立,尚無力經營西域。直至太宗時期,國內初定,始有余力應對時常侵擾北部邊境的突厥政權。突厥本北方游牧民族,興起于北魏末年,至唐初其軍事實力已達“控弦百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38]的程度,嚴重的威脅了新興的大唐政權。貞觀四年(630年),唐滅東突厥,據有西域的伊吾之地,并于此設立了唐代經營西域的第一個州府——伊州。此后的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又滅高昌,并收降屯駐于可汗浮圖城的突厥葉護,在高昌與可汗浮圖城分設西州和庭州,同時置安西都護府于高昌城。此時,轄境在阿爾泰山以西的西突厥迫于唐的軍事壓力曾一度臣服于唐,但當唐撤軍西域后,其對唐的敵對行動便開始了。《新唐書》地理志載:“北庭大都護府,本庭州,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缽羅葉護阿史那賀魯部落置,并置蒲昌縣,尋廢,顯慶三年復置”[39],文獻所記庭州在設州之后不久便遭廢毀,而據《新唐書·突厥列傳》所載阿史那賀魯叛時“以咥運為莫賀咄葉護。遂寇庭州,敗數縣,殺掠數千人去”可知庭州的廢棄當與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的叛亂有關。庭州是唐初在西域所設三州之一,它的毀建歷程或可間接反映早期西域形勢的復雜與唐經營西域時的艱難。高宗至玄宗時期,新興的唐帝國雖逐漸步入了鼎盛時期,并在經營西域的過程中展現出了強大的軍事實力,但終也無法徹底摧垮突厥與吐蕃勢力,是故在多元勢力并存的西域,唐廷設置于此的州、縣與羈縻都督府等機構,時常處在敵對勢力的侵襲威脅之中。這種情況在唐歷經安史之亂、大批精銳回調勤王之后更甚,北庭、安西賴以與唐廷聯絡的河湟地區為吐蕃所據,兩地淪為了孤懸塞外的朝廷棄兒。終唐一代,整個西域都處在唐、突厥,唐、吐蕃的不斷爭奪之中,西域作為唐西北邊境軍事斗爭的前沿陣地的屬性始終未變。
為加強對邊境地區的經營、抵御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擄掠,唐自高祖建國之時起,就已采取種種措施,其中影響最大、意義最深的一項舉措便是在邊境地區大力興修邊城。唐武德七年(624)“遣邊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備胡”[40]便是這一舉措的開端,此后又有兩次規模較大且見諸于史的修筑邊城行動:一次是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張仁愿在黃河北岸修筑受降城[41];另一次是天寶四年(745)王忠嗣在朔方節度使任內筑靜邊城和云內城[42]。其中張仁愿在修筑受降城時因“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而遭人詰問,《資治通鑒》卷209《唐紀二十五》中宗景龍二年條“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守備之具”下胡三省注稱:“壅門,即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筑垣以遮壅城門,今之甕城是也”。壅門既是甕城,且唐景龍年間張仁愿因修筑邊城時不筑甕城而受詰問,則表明至遲在唐中宗景龍年間將甕城修筑于邊城已成一種慣例。此外,在同處邊州的隋唐勝州榆林城[43]、安西鎖陽城[44]等也都發現有甕城遺跡。《唐六典》記:“安東、平、營、……、北庭、安西、河、……、驩、容為邊州”[45],地處西北邊境的北庭與安西同屬唐代的邊州體系,其轄境內的邊城在修筑時無論是出于西域復雜、緊張的邊境環境考慮,還是沿襲唐在邊城修筑時慣筑甕城的做法,都會修筑甕城來增強城池防御力量應對復雜的邊境局勢。
4余論
入唐以后,隨著州縣制和羈縻督府制在西域的推行,西域民眾在社會生活中對中原制度、習俗、文化表現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模仿和趨同。吐魯番出土文書《唐西州高昌縣諸防雜物牒》中記載高昌縣內有安樂、大順、永和等坊[46],而高昌縣又屬郭下縣(即高昌縣與西州同治于高昌城)[47],故知唐代的高昌城中已有仿長安、洛陽而建的里坊布局。無獨有偶,同處西域的龜茲、于闐等鎮也都見有里坊布局的文獻記載。[48]除文獻記載中的這種坊制外,新疆境內現存于唐代古城中的馬面、角樓、甕城等實物遺跡也是對西域模仿、學習中原城防制度的有力說明。
甕城之制起于我國,考古所見與新疆緊鄰的安西縣隋唐鎖陽城曾有形制清楚的甕城遺跡[49],而與新疆毗鄰的中亞和南亞地區的古城考古工作中卻不見有關于甕城的相關報道,這也可輔助說明新疆地區的甕城之制是源于中國,但具體是如何傳入的尚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外,在梳理新疆古城材料時還發現,甕城建筑在唐代的新疆一經出現便遍布天山兩側,而又以天山以南的區域所見為最多,這既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又是一個值得深思與探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在我國史書中“西域”有廣、狹兩層含義:廣義則泛指我國的西部疆域,大致包括現在的新疆全境、中亞細亞、阿富汗、伊朗、印度諸國;狹義則指陽關、玉門關以西,蔥嶺以東的地區,這一區域大致相當于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版圖范圍。本文所論乃就狹義而言。
[2]我國先秦典籍《逸周書》、《管子》等曾對昆侖之玉有所記載,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婦好墓中發現的隨葬用玉經專家鑒定大部分都產于新疆地區。關于殷墟婦好墓中所出玉器來源的檢測,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14-115.
[3]馬世之.試論我國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J].中原文物,1984(4):59.
[4]王瑟.新疆莎車發現年代最早古城——為新時期至青銅時代遺址[N].光明日報,2015-2-26,(1).
[5][6][9]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著.新疆古城遺址[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7-10,11-14,3-5.
[7][14][1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編.新疆通志·文物志[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140,290,140.
[8][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913.
[10][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隊.新疆吉木薩爾北庭古城調查[J],考古,1982(2):174,167-175.
[11]鄭元喆.高句麗山城甕城的類型[J].考古與文物.2009(3):54-59.
[12]張馭寰.中國城池史[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343.
[1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神木縣文體局.陜西神木縣石卯遺址[J].考古,2013(7):15-24.
[15]張建國主編.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志[M].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3:410.
[16]侯燦.論樓蘭城的發展及其衰廢[J].中國社會科學,1984(2):155-171;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編.新疆通志·文物志[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138-140;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著.新疆古城遺址[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16-24.
[17]侯燦.論樓蘭城的發展及其衰廢[J].中國社會科學,1984(2):155-171.
[19]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昌吉古城調查[A].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4)[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18-222.
[20]閻文儒.吐魯番的高昌故城[J].文物,1962(Z2):28-32.
[21]孟凡人.高昌城形制初探[A].殷晴主編.吐魯番學新論[C].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226-229.
[2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度高昌故城考古發掘簡報[A].伊弟利斯·阿不都熱蘇勒、安尼瓦爾·哈斯木主編.新疆文物考古資料匯編[C].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1808-1826.
[24][27]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86-202,194.
[25]付馬.回鶻時代的北庭城——德藏Mainz354號文書所見北庭城重建年代考[J].西域研究,2014(2):9-22.
[26][2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隊.新疆吉木薩爾北庭古城調查[J].考古,1982(2):165-167,168.
[29][唐]李吉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2:73.
[30]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22;黃文弼.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57-1958)[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67-71.
[31]張平.龜茲考古中所見唐代重要駐屯史跡[A].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9輯)[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171-197.
[32]邢春林.唐代安西都護府渭干河西岸遺址群的調查與研究[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1):115-123.
[33]李并成.新疆渭干河下游古綠洲沙漠化考[J].西域研究,2012(2):46-53.
[3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8-9;榮新江.唐代于闐史概說[A].中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術研究機構編著.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5-31.
[35]張平.唐代龜茲軍鎮駐防史跡的調查與研究[A].龜茲學會主編.龜茲學研究(第五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12:176-208.
[36]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22.
[37]王永生.大歷元寶、建中通寶駐地考——兼論上元元年以后唐對西域的堅守[J].中國錢幣,1996(3):3-11.
[38][五代]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5153.
[39][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47.
[40][宋]王欽若.冊府元龜[M].北京:中華書局,1960:11634.
[41][宋]司馬光,胡三省注.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6621.
[42][清]董誥.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3752.
[43]李作智.隋唐勝州榆林城的發現[J].文物,1976(2):74.
[44][49]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安西縣博物館.安西縣鎖陽城遺址內城西北角發掘簡報[J].敦煌研究,2003(1):6,1-7.
[45][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2:73.
[46]國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80.
[47][唐]李吉甫等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3:1032.
[48]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第一冊)[M].東京:法藏館,1985:74;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292-295.
The Origin of Wengcheng in Xinjiang
Xu Chengyan1Cao Zhongyue2*
(1 Institute of Western Region Culture,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2 Library of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AbstractWengcheng is the product of the social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a certain stage, together with turret and house build up ancient city defense system.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irst Town which take Wengcheng structure was Tang Beiting City in Xinjiang province, which was firstly constructed between 658~662 years. It is resulted by Tang imperial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defense forces to deal with the North-West Frontier region. Wengcheng as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scattered in the border town,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value.
Key wordsWengcheng; Xinjiang; border town; Tang Dynasty
中圖分類號:K878.3
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9-0568.2016.01.009
文章編號:1009-0568(2016)01-0055-08
通訊作者*為E-mail:838964662@qq.com
作者簡介:徐承炎(1988-),男,助理研究員,碩士,主要從事西域古城的考古學研究。E-mail:2008-xuchengyan@163.com
基金項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4QN20);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塔里木大學西域文化研究院開放課題(XY1404)。
收稿日期:2015-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