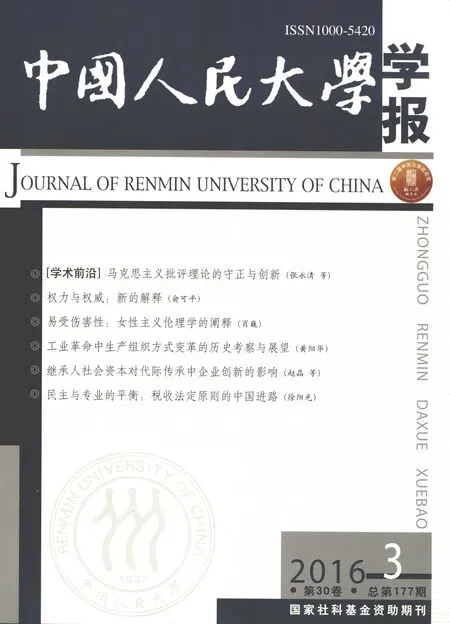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前史形態
——試論馬克思恩格斯1833—1844年的批評理論
張永清
?
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前史形態
——試論馬克思恩格斯1833—1844年的批評理論
張永清
馬克思恩格斯在1833年至1844年8月時期的文學創作與評論活動,不僅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前史形態”,而且還是其他五種批評形態的基礎。國外相關研究經歷了萌芽與胚胎、形成和發展、反思和深化三大階段;國內相關研究經歷了“蘇聯化”和“西馬化”兩大階段。學界對馬克思的相關研究主要存在梅林式的“狹義化”與維塞爾式的“擴大化”兩種傾向,對恩格斯的相關研究主要存在盧卡奇等的“有意拔高”與德梅茲等的“無端貶損”兩種傾向。我們必須結合歷史與現實兩種語境加強對該問題的整體性研究。
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前史形態;蘇聯化;西馬化
時至今日,面對浩如煙海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相關研究文獻,我們對任何問題的關注都極有可能陷入某一既定理論范式的牢籠。從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這一問題出發,我們發現:國內外以往的諸多研究傾向將馬克思恩格斯1844年以后的相關批評思想與實踐即“初始形態”①筆者根據理論界關于“何謂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討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五個“歷史形態”與一個“發展形態”。其中,五個“歷史形態”分別是前史、初始、科學、政治以及文化形態,一個“發展形態”指的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中國形態”。之所以說前者是“歷史形態”,是因為它們曾作為某一歷史時期的理論潮流,引導、規范甚至主宰所處時代的批評格局,形成自身獨有的問題域、話語系統、文體風格,體現所處時代的批評精神;之所以說后者是“發展形態”,是因為它還沒有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相對完備的理論形態、核心問題以及批評特征等,還需要在對以往的批評形態與其他理論資源充分吸納的基礎上進行不斷創新和構建。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只是提出問題,對一些重要問題只作了粗略描述,尤其是關于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五個歷史形態的劃分依據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都未能作更深入的剖析。鑒于此,筆者將以系列論文的形式對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作進一步的思考與探索。本文主要圍繞“前史形態”這一論題作相關探究。作為馬克思主義批評的“理論基點”,而對馬、恩此前的文學活動等做了現象學式的“懸擱”處理。這種相關的研究態勢都或多或少存在著對馬、恩自身批評觀念、批評實踐整體性的“任性”割裂,缺少對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完整性的關注。
因此,無論是從馬克思恩格斯自身批評觀念、批評實踐的“嬗變”出發,還是從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完整性考慮,我們都有必要重新“追溯”它的“理論基點”:由“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構成的理論基點產生于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前史”時期(1833年至1844年8月),這一時期的相關思想構成了他們批評理論與實踐的“前史形態”。需要指出的是,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并不否認“前史形態”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整體性的一個必然組成部分,但認為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因而不屬于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組成部分。而筆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1833年至1844年8月這一時期的文學及其相關活動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不僅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前史形態”,而且還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其他五種批評形態的“基石”,它在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史中有著無可替代的意義和作用。鑒于此,文章主要就以下三個問題作一些探討:緣何提出“前史形態”這個問題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在“前史”時期的文學及其他活動的基本情況;國內外既有研究的基本狀況;國內外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加強對“前史形態”研究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下面我們就圍繞上述問題分別展開論述。
一
客觀地講,由于不同研究者關注的問題及視角不同,因此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的階段劃分自然會存在不同甚至是本質性的差異,比如關于“兩個馬克思”、“認識論斷裂”以及所謂的“恩格斯主義”等問題的相關爭論。眾所周知的“巴黎相見”*“巴黎相見”并非馬克思、恩格斯兩人的首次見面,而是他們的第二次“握手”。第一次是在1842年11月,馬克思當時正擔任《萊茵報》主編,由于“自由人”的問題,馬克思對前往英國途中專程繞道科倫來訪的恩格斯十分冷淡。此外,在編排體例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新版與舊版存在的顯著差異之一就在于前者就是以“巴黎相見”來“劃界”的:第一、二、三卷收錄的是馬克思、恩格斯1844年8月之前的論著,其中,第一卷是關于馬克思1833年—1843年3月(退出萊茵報)期間的著作;第二卷是關于恩格斯1833年12月—1842年10月(去英國前)的著作;第三卷則是關于兩人此后到1844年8月前的著作。在我們看來,這樣的編排既符合兩人思想發展的實際狀況,也體現了對歷史事實的充分尊重。未必是學界公認的劃分馬克思主義“之前”與“之后”的里程碑,但一定是馬克思、恩格斯兩人“思想獨立期”與“理論共創期”的分水嶺。就文學活動,尤其是批評理論這一問題而言,“1844年8月28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巴黎相見”之所以是劃分“前史形態”和“初始形態”的基本“坐標”,原因在于:一方面宣告了他們各自獨立從事文學、哲學、政治等活動歷史的結束;另一方面又昭示著兩人攜手“共創”馬克思主義歷史的開啟,《神圣家族》*由于恩格斯在巴黎只停留了10天左右就回到了家鄉巴門,因此只寫了一小部分,大部分由馬克思撰寫,但出版時,馬克思將恩格斯署為第一作者。有關《神圣家族》的相關情況,具體見恩格斯在巴門期間給馬克思的四封信:1844年10月初、1844年11月19日,1845年1月20日、1845年3月17日,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13、26、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即是肇端。毫無疑問,“巴黎相見”之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獨立”從事文學、政治、思想活動和理論研究工作,不存在任何“合作”的情況。如果說兩人之間存在思想影響的話,那么這種影響還只是單向度的而非交互性的,主要是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思想產生了影響,比如《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對《1844年經濟學者哲學手稿》的影響。*根據現有的考證和研究,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大約寫于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先于“巴黎相見”。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筆者粗略概括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六大形態中,只有“前史”和“初始”這兩種形態屬于馬克思、恩格斯本人思想整體的有機部分,其他幾種形態都是由不同歷史時期的思想家和理論家發展而成的。在此之所以強調這種區分,是因為它不僅關系到如何準確理解“前史”與“初始”這兩種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批評觀念和批評實踐方面存在的共性與差異性等問題,而且關系到這兩種形態在整個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整體格局中的位置與功能等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學批評觀念、批評思想等固然與其哲學、宗教、政治等思想密切關聯,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早期的文學觀念、審美趣味、批評理論與實踐等更為集中地體現在其文學創作、文學評論中。基于這種基本判斷,與以往研究注重“初始形態”以及與其他形態之間的斷裂性、差異性不同,我們把探究的重點轉換到了“前史形態”以及這一形態與其他形態之間的關聯性、同一性等問題上。
筆者主要從創作、評論、書信以及政論、哲學論著等方面重點考察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學觀念及其相關活動。與現有的其他各種劃分方式略有不同的是,我們以馬克思、恩格斯是否主要從事文學活動為依據,將1833年至1844年8月這一“前史”時期也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對馬克思而言,前一階段(1833年至1841年4月)*馬克思1841年3月30日畢業于柏林大學,1841年4月15日獲得耶拿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意味著馬克思大學生活的徹底結束。即特利爾、波恩、柏林時期,后一階段(1841年5月—1844年8月)即《萊茵報》、克羅茨納赫、巴黎時期;對恩格斯而言,前一階段(1833年—1842年10月)即巴門、不來梅、柏林時期,后一階段(1842年11月—1844年8月)即英國時期。總體看來,前史時期的馬克思有論著170部篇左右,恩格斯有論著94部篇左右。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馬克思、恩格斯倆人在前一階段均為“文學青年”,而在后一階段又“不約而同”地“放棄”文學,因此,前一階段是他們從事文學活動的最為重要的歷史時期。
從現有的文獻資料看,在馬克思前期的126部論著中,除3篇中學作文和1篇博士論文外,其余的均為詩歌*它們分別為:中學時期2首,大學時期118首,未完成的悲劇、小說各1部。其中,馬克思大學時期的詩歌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獻給燕妮的詩,有《愛之書》第一、二部和《歌之書》一部;第二部分為獻給父親的詩集;第三部分則是馬克思的姐姐索菲亞抄錄于紀念冊和筆記本的詩歌,這些詩歌有些與前兩部分重合,有些則是前兩者所沒有的。第一部分的三本詩集分別有12、22、23首,總計57首;第二部分有36首詩歌,1部未完成的悲劇《烏蘭內姆》以及1部未完成的幽默小說《斯考爾皮昂和菲利克斯》;索菲婭的紀念冊摘錄39首、筆記本摘錄10首,總計49首,其中與前兩部分重復的有22首,實際為27首。具體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7—9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等文學作品。從創作看,馬克思的文學活動最早始于1833年,最晚結束于1837年底1838年初,前后持續時間大致有5年,但主要作品是他在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的前兩年,尤其是在1836年創作的。從參與的其他文學活動看,作為法律專業學生的馬克思在大學的第一年不僅選修了希臘羅馬神話、荷馬研究諸問題、近代藝術史、普羅佩爾提烏斯的哀歌等文學藝術方面的課程(它們占其修課總量的40%),而且還參加了波恩大學的青年詩人小組。從這一時期父子之間的18封書信看,創作詩歌、編寫劇本、籌辦文學刊物等內容構成了其中8封書信的主題,而戴上“詩人”的桂冠無疑是青年馬克思的第一人生“夢想”,這樣的理想使得他的父親不無憂慮:“如果看到你成了一個平庸的詩人,我會感到傷心的。”[1](P523)與前一階段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馬克思在后一階段已從文學轉向了政治、哲學、經濟學等活動,在諸如《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論猶太人問題》等44部篇政治、哲學、經濟等方面的論著中,既無文學創作也無批評方面的任何專論。*盡管馬克思在 1842年3月20日、4月27日致盧格的信中談及了自己論宗教藝術、浪漫主義等文章,但并未保留下來。具體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6—2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從文獻留存角度看,馬克思在整個前史時期沒有一篇文學評論方面的專論。不過,文學依然是馬克思十分關注的“話題”之一,他關于悲劇、美學、內容與形式以及詩人與作品之間關系等的深刻論述主要是通過散見于上述這些論著,尤其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這一非系統的方式來呈現的。從發表的角度看,馬克思以《狂歌》為總標題于1841年1月23日在《雅典神殿》雜志第4期發表的《小提琴手》和《夜戀》兩首小詩,是他在大學期間以自己的名義正式發表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發表的文學作品。此外,如果僅就保留下來的文獻資料看,馬克思一生從未寫過一篇完整的美學論文或一篇正式的文學評論。
恩格斯在前一階段共有65部論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收錄57部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收錄7部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此外,還有1首中學的詩作《伊托克列斯和波呂涅克斯決斗》收錄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644—64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其中,文學創作與評論等占37部篇,其他如政論、通訊、哲學等28部篇。從創作看,恩格斯的文學活動最早始于 1833年,最晚結束于1842年6月,前后持續時間大致有9年,但其著述主要是在不來梅期間完成的(1838年9月—1841年3月)。*在37部篇的作品和評論中,巴門期間5篇,不來梅期間29篇,柏林期間3篇。與馬克思完全專注于創作活動不同,恩格斯不僅當時就是小有名氣的“青年德意志”詩人,而且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青年德意志”的文學評論家。從這一時期的56封書信看*家信32封,給盧格3封,給許·金2封。其中,在給格雷培兄弟的19封書信中,內容不僅有恩格斯的文學創作、文學評論,而且有恩格斯的宗教、政治、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的真實展示,是研究恩格斯文學與思想、批評觀念等的珍貴文獻。比如,詩歌《佛羅里達》以及以報刊為名的《諷刺短詩》(1839年1月20日),評論《當代文學》(以青年德意志為題,1839年4月8日—9日),悲喜劇《刀槍不入的齊格弗里特》(1839年4月24日—5月1日),德文六步韻詩《詩作》(1839年4月29日),文學評論《當代文學文稿》(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小詩《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1839年7月27日)等,具體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恩格斯有關文學、宗教、政治、哲學等問題的討論就占了三分之一。不過,恩格斯書信的主題不像馬克思那樣主要是在“父子之間”,而是在“同學之間”展開討論,這些書信不僅表達了恩格斯成為“巴門市的詩人”[2](P173)的文學理想,而且還談及了他作為詩人的前途,“據說我作為一個詩人已經完了,許多人正在為此爭論不休”[3](P277)。在后一階段,恩格斯與文學也漸行漸遠,從文學徹底轉向政治、哲學、經濟等活動,在諸如《英國對國內危機的看法》、《倫敦來信》、《國民經濟學批評大綱》、《論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大路上的運動》等29部有關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論著中,恩格斯同樣是既無一部作品也無一篇美學或文學方面的專論,其相關的文學藝術思想也散見于上述論著中。從發表的情況看,恩格斯于1838年首次發表詩作《貝都英人》;在前史時期發表了10余首詩歌、3篇游記、9篇文學評論;在此后的“初始時期”也有諸如《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等評論的正式發表。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創作、評論還是政論、通訊等,前一階段的恩格斯發表時都用“筆名”而非“實名”;只有到了后一階段即以1842年12月8日刊于《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上的《英國對國內危機的看法》一文為肇端,恩格斯才使用“實名”發表自己的論著。
還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前史”時期前后兩個階段的這種“巨變”,即放棄文學夢想,不僅有來自家庭、社會、時代等諸多“外在”因素的深刻影響,也有他們對自身文學天賦等內在因素的客觀認識與正確判斷。比如馬克思寫道:“對當代的抨擊,漫無邊際、異常奔放的感情,毫無自然的東西,純粹的憑空想像,現有之物和應有之物的截然對立,以修辭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滿詩意的構思、不過或許也有某種熱烈的感情和奮發向上的追求……無邊無際的、廣泛的渴求在這里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使‘精煉’變成了‘冗長’。”[4](P7)再比如,恩格斯寫道:“我對自己的詩和創作詩的能力,日益感到絕望……每當我讀到一首好詩時,內心總是感到苦惱:你就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5](P95)正因如此,馬克思才大約在1837年底1838年初“忍痛割舍”了心愛的文學,一頭扎進黑格爾及其左派的哲學世界,之后轉向費爾巴哈、空想社會主義等哲學和社會理論著作,其思想經歷了從費希特主義、青年黑格爾主義、費爾巴哈主義到孕育“歷史唯物主義”的“蛻變”過程。與馬克思的情況相似,恩格斯盡管于1839年11月聲稱他“正處于要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的時刻”[6](P224),這只表明他正經歷著從文學的“青年德意志分子”轉向哲學的“青年黑格爾主義者”的思想“陣痛”期,只有到了1841年,恩格斯才徹底放棄了文學的優先性而將哲學、政治等置于首要地位,此后他不僅參加了青年黑格爾派、“自由人”團體等哲學活動,而且在英國期間還了解了英國社會、憲章運動以及工人階級狀況等,從不同于馬克思的路徑“孕育”出了“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幼芽。
二
圍繞本文探究的核心論題,筆者擬從國外與國內兩個方面分別對批評理論“前史形態”的相關研究做粗略描述和概要分析。簡言之,國外的研究可以大致劃分為: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20世紀70年代至今三個時期;國內的相關研究也可以大致分為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20世紀80年代至今兩個時期。
先從國外的相關研究來看。首先,從嚴格意義上講,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不僅是批評理論“前史形態”研究的萌芽與胚胎期,而且也是列寧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與形成期。*《怎么辦》(1902年)、《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1905年)、《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年)等論著標志著列寧主義的形成。1923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與哲學》問世以及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成立,則標志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對研究所而言,對文學藝術真正產生影響則要到20世紀30年代,由霍克海默于1931年接任所長之后,其研究重心與旨趣才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即由此前追求的經濟學、歷史學式的實證性分析轉向哲學、文化等跨學科的總體性社會批判。參見馬丁·杰伊:《法蘭克福學派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就“前史形態”的相關研究而言,只有極個別論著、傳記等注意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學創作及評論,還談不上對其作全面、系統、深入的專門研究。我們認為,這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盡管確有部分著作及相關文獻在這一時期得以問世,諸如《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的通信》(1902年)、《恩格斯早期著作集》(1920年)、《馬克思傳》(1919年)等的出版以及《新時代》、《德意志評論》等刊物登載的部分創作、評論、書信等,但其他“原始”文獻資料畢竟尚未得到整理與出版,客觀上影響人們的思想認識和理論判斷;另一方面也許是更為重要的原因,與以考茨基等為代表的第二國際多數理論家的認識偏頗密切相關,他們主要把馬克思、恩格斯視為經濟、社會而非哲學、文學、美學等理論的奠基者與創建者。換言之,在他們看來,由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學及其批評活動只具“業余性”而不具“專業性”,自然就不需要對其文學思想、批評觀念、審美理想等進行認真挖掘與細致闡發,因而就將研究的重心置于把“歷史唯物主義”等基本原理逐步“拓展”到文學、藝術和美學領域這一問題上。在這樣的認知視野里,梅林、普列漢諾夫在當時被公認為馬克思主義美學與文學批評等方面的奠基者,梅林主要通過“走向康德”、而普列漢諾夫則主要通過引進“實證主義”來完成這種建構。比如,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文學理論界有一種觀點:盡管梅林既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尤其是文學文獻資料的最早整理者與編輯者,是最早對馬克思恩格斯相關文學活動作具體分析和判斷的研究者,同時也是在文藝批評領域內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開拓者,但在基本原理的系統化方面,普列漢諾夫而非梅林才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的真正奠基者,盧那察爾斯基的相關論斷就十分典型地體現了此種認知。[7](P300-301)順便提及的是,“拉普”在20世紀30年代之所以被清算,其嚴重錯誤之一就在于他們要為“恢復普列漢諾夫的正統而斗爭”。
其次,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是“前史形態”研究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兩大傳統*與柯爾施、葛蘭西、里夫希茨、希列爾等不同,盧卡奇在兩大批評潮流中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理論地位很獨特:他不僅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而且是“正統馬克思主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另外,希列爾還有希里爾、謝勒等譯法。即列寧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確立和繁盛期。對批評理論的“前史形態”而言,20世紀30年代具有極其重要的標志性意義,這是因為里夫希茨、盧卡奇等在理論與批評方面完成了兩項“首創性”工作:其一,他們完全“恢復”了馬克思、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美學、文學、藝術領域內不可動搖的“奠基者”地位,當然,這一活動并非孤立進行而是與“去普列漢諾夫化”[8](P12)[9](P130)、確立列寧作為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繼承者尤其是發展者的地位等同步推進的;其二,他們不僅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前史時期的創作、評論等作了較為全面的審視,而且將文學、美學觀念與其哲學、經濟等思想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
之所以能夠取得上述的理論突破,與以下兩個重要因素密不可分:其一,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原作”及資料選編本*1932年,《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馬克思、恩格斯“五封書信”等出版;1933年,由盧那察爾斯基主編、里夫希茨和希列爾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出版。首次面世,它們毋庸置疑地為哲學、美學、文論等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堅實的文獻基礎,比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不僅在哲學上引發了兩個馬克思的爭論,而且開啟了馬克思美學理論研究的先河。其二,開拓性研究論著的相繼問世。1933年,里夫希茨的《馬克思的藝術哲學》出版,小冊子共有14部分,其中,前九部分主要討論前史時期論著中的文學藝術問題。里夫希茨十分自覺地將審美和藝術問題與馬克思的思想整體發展聯系起來研究;十分關注馬克思早期書信以及散見于其他著作里的美學、藝術思想*由于馬克思致燕妮的三本詩集在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才得以搜集整理完畢,里夫希茨在這一時期對原始文獻的掌握還不能說已十分完備,但也比較詳盡了。;比如,他認為馬克思在其精神生活的第一階段完全被浪漫主義所主宰[10](P14),以及馬克思的詩歌具有席勒式的語言和風格等。同樣是在1933年,希列爾的《文學批評家恩格斯》一書首次對恩格斯的文學批評思想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闡釋,其中的第一章主要關注的就是恩格斯在“前史時期”的創作和評論;認為恩格斯的文藝思想不是“片言只語”式的“意見”,而是呈現出某種整體性的典范。[11]盧卡奇早在1930—1931年間就完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之間的濟金根論爭》一文;在1935年的《作為文藝理論家和文藝批評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他不僅對恩格斯不同時期的批評理論作了整體性剖析,而且首次提出了“偉大的現實主義”這一理論問題。
在20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除了以科爾紐的《馬克思恩格斯傳》等為代表所秉持的“正統”觀點外,研究者中再度出現了質疑甚至根本否定美學、文學、藝術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機部分的“另類”聲音。它以兩種迥然不同的形式呈現:其一,以德國的彼特·德梅茲的《馬克思、恩格斯和詩人們》(1959年)的論著等為代表,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創作、評論、書信等文本的具體分析后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學思想并無原創性;其二,以法國的列斐伏爾、費歇爾、戈德曼等為代表,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美學、文學的思想已經“過時”,轉而挖掘他們的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思想,力圖在此基礎上與其他理論資源進行整合后創新馬克思主義美學與文論。
再次,20世紀70年代以來則是批評理論“前史形態”研究的反思和深化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英文版等在這一時期陸續出齊,為“前史形態”等相關研究提供了相對完備的資料基礎。除此之外,這一時期的研究總體上還呈現出以下幾個顯著特征。其一,從研究的地理圖譜看,英美地區成為相關研究的重鎮,主要以英國的柏拉威爾、伊格爾頓、威廉斯以及美國的詹姆遜、維塞爾、萊文等為代表。此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批評理論的兩大傳統中,“蘇聯”的影響力在日漸式微、而“西方”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威廉斯的論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馬克思主義文化及文學理論首先是由普列漢諾夫根據恩格斯晚期著作的觀點加以系統化,隨后又由蘇聯占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加以普及的……我那時還從不同的視角閱讀了英國3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的著作,有關考德威爾的爭論頗具代表性。”[12](P3-4)人們十分熟知的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評在這一時期經歷了“葛蘭西轉向”、“阿爾都塞主義”等思想的洗禮,在此就不再贅述。其二,從探究問題時的“切口”看,存在著程度不一的“視角反轉”傾向。比如,柏拉威爾認為,自己之所以刻意區別于此前里夫希茨等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1933年)那種以“主題”形式編選材料的結構方式,是因為它往往混淆了馬克思不同時期的言論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見解,按照年代順序組織材料的結構方式則能更好地呈現出馬克思批評觀念的起源及演進。[13](P1)再比如,與此前諸多研究者多從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視角審視它們對馬克思的文學、美學的深刻影響不同的是,維塞爾在《馬克思與浪漫派的反諷》(1979年)中則以詩學作為基本理論立場來審視它在馬克思的哲學等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功能與作用等。其三,相比較而言,盡管諸多研究者在批評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中的有機構成部分這一問題上取得了高度“共識”,但依然將論述的重心放在“初始形態”方面,對“前史形態”往往都是一筆帶過,諸如伊格爾頓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詹姆斯的《馬克思主義與形式》等著作中的相關論斷即是“佐證”。當然,也有以萊文等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不僅有意識地區分“前史時期”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思想,而且還注重它們與文學之間關系的探究,比如萊文認為:“在1839年至1940年末這段時間,青年恩格斯是一個文學研究者,主要關注的是黑格爾與藝術有關的思想。青年恩格斯試圖在美學領域確認黑格爾的重要性”[14](P143)。
為了避免重復,下面我們將以國外相關研究作為基本理論參照,來簡述國內的相關研究:第一階段即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末,其問題框架與理論范式基本上是“蘇聯化”的即列寧—斯大林主義的;第二階段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其問題框架與理論范式則基本上經歷了由起初的“蘇聯化”到中后期的“西馬化”發展態勢。概言之,理論界在第一階段主要關注的是典型、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美學的與歷史的觀點、悲劇、莎士比亞化、席勒式、文藝的上層建筑性與意識形態性,以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等等問題。此外,與20世紀50年代國內圍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討論而形成的美學熱相比,由于文獻資料等方面的原因,整個第一階段還談不上對批評理論“前史形態”的真正研究,其中心工作之一是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著作及其研究論著,但絕大部分中譯本不是直接源于德文本而主要是通過俄文本以及日文、英文本等。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與蘇聯相似,20世紀30年代對我們也同樣具有“肇始性”意義,瞿秋白、陸侃如、胡風、孟式鈞、稚吾、曹葆華等幾乎是在“在第一時間”分別從俄文、日文、英文、法文等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悲劇、現實主義等問題的“5封書信”,以及里夫希茨論馬克思的2篇論文、希列爾論恩格斯的5篇論文等。[15]在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間,里夫希茨等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多個節譯本、全譯本與格·索洛維耶夫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等譯本相繼出版;梅林的《馬克思傳》、梅爾的《恩格斯傳》、科爾紐的《馬克思恩格斯傳》及格姆科夫的《恩格斯傳》與《馬克思傳》等不同譯本也陸續出版。上述這些文獻充其量只能為“前史形態”的相關研究提供“第二手”資料,只有到了第二階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第40卷、第41卷于1982年的出版才能說是為“前史形態”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此前,柏拉威爾的《馬克思和世界文學》、伊格爾頓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以及《盧卡奇文學論文集》等中譯本已于1980年出版,這些研究著作的部分內容與“前史形態”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們共同促成了國內研究*這一時期代表性論文有:陳歷榮:《恩格斯青年時代的文藝創作活動》,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0(3);曹俊峰:《恩格斯早期文藝觀》,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1);陳遼:《論馬克思主義產生前的馬克思文藝思想》,載《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3(1);陳遼:《青年恩格斯的文學活動》,載《錦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2);許崇信:《青年馬克思——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札記》,載《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1);王春元:《恩格斯早期美學思想初論》,載《文學評論》,1983(2);賴耀先:《淺談青年馬克思的詩歌創作》,載《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1);林保全:《略談對馬克思青年時代詩歌的評價》,載《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3)。“前史形態”批評理論的小高潮,前后大致持續了三年左右時間。因此,盡管“前史形態”這一問題不是第二階段理論研究的“重中之重”,但也是這一階段十分搶眼的“亮點”之一。不過,1985年之后,隨著“西馬”等思想潮流的席卷而來,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也很少再被人“問津”。
三
在前一部分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作“歷時性”描述的基礎上,我們在這一部分著重審視在既往研究中存在的整體性問題。由于馬克思、恩格斯在“前史時期”是獨立從事文學、哲學活動的,這也就要求我們將馬、恩兩者“分開來談”。
先來看對馬克思的相關研究。究竟如何認識“詩人”馬克思的詩作?理論界存在著以梅林等為代表的“狹義化”與以維塞爾等為代表的“擴大化”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梅林在《馬克思傳》中作出了如下論斷:“這些青年時代的詩作散發著平庸的浪漫主義氣息,而很少響徹著真實的音調。而且,詩的技巧是笨拙的,這種情況在海涅和普拉頓之后是不應該再出現的……在繆斯放在馬克思的搖籃里的諸多天賦中,畢竟沒有韻文的才能。”[16](P19)梅林這種“就詩論詩”、“就事論事”的認知方式深刻影響了此后的眾多傳記作者和研究者:美學、藝術方面的研究者認為它們是“失敗之作”而不再關注;哲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則認為這些“保留下來的作品只在推動馬克思個人心理研究方面值得重視”[17](P5),“這些詩歌使我們感到興趣毋寧說是在傳記和心理方面,而不是在文學方面”[18](P73)。與此相反,維塞爾在《馬克思與浪漫派的反諷》(1979年)中不僅把“詩歌”拓展到了馬克思一生的思想活動中,而且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對馬克思而言,無產階級本質上是一種詩力。如果我的論點是對的,那么,理解馬克思的詩是理解馬克思哲學的關鍵。”[19](P6)維塞爾認為,不應將馬克思的詩僅僅評價為不成熟的浪漫主義詩歌就棄之不顧,抑或僅僅將其放在傳記或回憶錄里,而應將其早期的浪漫詩定位為渴望主題,并從整體之詩、異化之詩、反抗之詩三個維度來探究馬克思哲學等思想的發展。[20](P13-14)值得注意的是,國內的相關研究在21世紀之前基本上受到了梅林、里夫希茨等思想觀點的深刻影響,而在進入21世紀之后,維塞爾的觀點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我們看來,對馬克思“前史時期”的文學、美學思想的相關研究還存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突出問題。其一,注重對馬克思美學思想的研究而輕視對其文學思想的探討。比如,將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視為其哲學、美學思想的發源地,這一“定論”已經足以看出對其在美學方面真知灼見的高度肯定,但對其文學思想而言,如前所述,由于研究者已經認同或接受了梅林等的判斷,因而對其文學思想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其二,在對馬克思詩歌創作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存在著整體性與具體性的雙重缺失。整體性缺失表現在:一些研究者要么純粹從詩歌技巧與形式的角度審視作品,要么純粹從內容出發只探究馬克思思想的崇高面,因而不自覺地以一種極其片面的方式把藝術的笨拙性與思想的深刻性“對置”起來,從而將作品的整一性割裂開來。具體性缺失則表現為:一些研究者提煉出的某種思想不是“細讀”作品的結果,而是用詩歌來“印證”某種外在的既定觀念,因而無論將馬克思的詩歌視為“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都一樣缺乏說服力。事實上,馬克思這一時期的部分詩作中還流露出十分明顯的宗教意識以及希臘精神,還有一些詩作則體現出他的批評觀念、批評風格等,但它們在以往的研究中都是闕如的。其三,對馬克思的文學與哲學思想關系的探討表面上看起來十分充分,實際上還不夠細致與深入。比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無疑受到了黑格爾的影響,此說是否也適合于馬克思的詩歌創作?再比如,阿爾都塞認為,除了博士論文和《手稿》外,馬克思起先是康德和費希特派,之后是費爾巴哈派,但從來都不是青年黑格爾派[21](P18),我們又如何在阿爾都塞們和盧卡奇們這種截然不同的論斷之間進行取舍,這些思想與馬克思的詩歌創作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我們認為,要想作出符合文本實際的判斷,不能只在各種論斷之間簡單地“選邊站”,而應回到詩歌作品自身和當時的思想語境中,這樣才能確切解決馬克思的詩歌緣何就是費希特式的而非黑格爾式的、浪漫主義的而非現實主義的等問題。比如,浪漫主義作為一種影響廣泛的社會思潮,涵蓋了政治、哲學、宗教、法律、文學等方面,如果馬克思曾經是浪漫主義主義者,那么他接受的是哪一層面的浪漫主義;馬克思后來對浪漫主義的拒斥究竟是政治、哲學方面的原因,還是審美趣味、藝術理想等方面的原因。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立足于馬克思的詩歌創作,結合他當時的哲學、政治思想等作具體分析。
再來看對恩格斯的相關研究。究竟如何認識詩人與評論家恩格斯的創作與評論?理論界同樣存在著以盧卡奇等為代表的“有意拔高”與德梅茲等為代表的“無端貶損”兩種迥然相異的觀點。盧卡奇在《作為文藝理論家和文藝批評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35年)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論斷:“恩格斯在文學領域的活動始終是由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偉大任務決定的……他們在文藝理論領域的斗爭,從開始階段起,就已經是針對著無產階級在階級意識上的資產階級化。”[22](P1-2)這一判斷是盧卡奇“從后往前看”恩格斯的必然結果,但這并不完全符合恩格斯“前史時期”文學活動的實際情況,對思想演進的考察而言,“從前往后看”才是更為恰當的方式。德梅茲于1959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與詩人們》一書為他個人贏得了所謂“馬克思主義新批評”的稱號。單就書中的各部分標題看,恩格斯在全書九個部分中就占據了三分之一,是德梅茲重點論述的對象。除此之外,他還對馬克思、梅林、普列漢諾夫、盧卡奇以及阿多諾、戈德曼等作了詳略有別的理論闡發。與盧卡奇的“褒獎”相反,德梅茲是一種典型的“酷評”,他不僅沿襲了恩格斯文學上的“領路人”——谷茲科的觀點,認為無論就創作還是就評論看,恩格斯都不過是“青年德意志的辦事員”,甚至有“模仿過度”之嫌,而且還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文學藝術方面根本沒有值得稱道的理論建樹等等。*Demetz,Peter.Marx,EngelsandthePoets:OriginsofMarxistLiteraryCritic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pp.13-15.這本書是德梅茲在其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1959年以德文首次出版于斯圖加特,1967年的英文版是修訂版。從接受與傳播范圍看,盧卡奇的觀點對“蘇東”地區與國內的相關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而德梅茲的相關觀點則在西方學界產生著持續的影響。[23](P141-142)
對恩格斯“前史時期”文學思想的研究同樣存在著以下三個突出的問題。其一,從恩格斯的文學活動軌跡看,絕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他是從青年德意志“起步”的,但這種論斷缺乏相關根據,并不符合實際。恩格斯本人在1838年9月17—18日致格雷培兄弟的信中明確寫道:“我現在告訴你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的西班牙浪漫詩碰壁了,那個家伙顯然是一個反對浪漫主義的人”[24](P93);在 1839年4月8—9日的信中說:“我應當成為青年德意志派,更確切地說,我已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25](P139);在同年5月24日—6月15日信的署名處還明確標明:弗里德里希·奧斯瓦爾德 青年德意志派。由此可見,恩格斯是作為浪漫主義者開始其文學活動,而以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終結其文學生涯的。其二,多數傳記作者和研究者主要還是從哲學立場、政治傾向、社會理想等方面來探究恩格斯的詩歌創作,而很少關注恩格斯在詩歌形式與技巧方面的成敗得失,更談不上將內容與形式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看待。其三,對恩格斯的文學評論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從未進行過深入研究。前文部分已提及,與馬克思一生未寫過一篇專門的美學論文或文學評論不同的是,恩格斯這一時期撰寫了11篇評論,當時刊發的就有9篇,涉及作家論、作品論等內容,它們既是研究恩格斯“前史時期”批評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文本,也為理解與把握恩格斯批評觀念的演變提供了文本基礎,比如,在“前史”與“初始”這兩個不同時期,恩格斯都有關于歌德、卡爾·倍克、歐仁·蘇論以及青年德意志等的評論,多數研究往往采取的是孤立化而不是整體化的方式來把握。此外,迄今為止,我們也未能認真探究恩格斯與谷茲科、白爾尼等之間的文學、思想關系,自然也就很難對德梅茲的“非難”作出恰切的理論回應。
以上我們分別探究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存在的突出問題,這一部分我們還需指出在對兩者的研究過程中存在的共性問題。在我們看來,一些研究者在面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詩歌文本時往往采取了一種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研究方式,無法區分兩者間存在的共性與差異。比如,細讀文本后我們不難發現:“自由”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處時代的主題,也是他們詩歌創作的基本主題之一;不同的是,馬克思的詩歌更多的是追求一種個人的情感自由,因而其詩歌的基調是“主情”的,而恩格斯的詩歌更多的是呼喚一種個人的思想自由與政治解放,因而其詩歌的基調是“主理”的。不過,無論他們兩位的詩歌是“主情”還是“主理”,都未能做到他們后來所概括的“莎士比亞化”,即未能處理好情感與形式或思想與形式之間的有機關系,不自覺地落到了“席勒式”的窠臼之中。從這個意義上,這一時期的創作甘苦也融貫在此后的批評理論與實踐中。此外,盡管馬克思、恩格斯都具有廣博深厚的文學修養,但兩人的詩歌與評論同樣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生長于自由主義家庭的馬克思更加注重古希臘羅馬傳統,普羅米修斯成為馬克思一生的精神象征;而出身于虔誠主義家庭的恩格斯則不僅注重德意志民族的文學傳統如民間故事,而且比馬克思更熟悉“當代德國文學”,浮士德、齊格弗里特等成為恩格斯當時的精神象征。
總之,我們有必要回返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前史時期”,即馬克思主義批評的理論基點,進而加強對批評理論“前史形態”的深入研究。那么,我們該用何種態度與方式來展開相關研究?首先,必須回到根基,即回到馬克思、恩格斯“前史時期”的詩歌、評論等文本自身,誠如阿爾都塞所言:“這是整個當代思想史中最大的丑聞:每個人都談論馬克思,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所有人幾乎都在說自己多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誰曾經不怕麻煩地去仔細閱讀過馬克思、理解他的創新性并接受他的理論結果了呢?”[26](P348)其次,回到文本但又不能止步于文本,它還要求我們必須將文本放置于文本得以產生的時代語境與整體思想格局中,同時還必須立足于我們當下的社會現實與文學現狀中。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
[1][2][3][4][5][6][24][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盧那察爾斯基:《關于藝術的對話:盧那察爾斯基美學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8] 里夫希茨:《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9] 盧卡奇:《盧卡奇自傳》,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10] Mikhail Lifshitz.ThePhilosophyofArtofKarlMarx.London:Pluto Press,1973.
[11] 吳元邁:《關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遺產——西方對馬恩文藝遺產研究的歷史考察》,載《江淮論壇》,1982(5)。
[12] 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13] 希·薩·柏拉威爾:《馬克思和世界文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
[14][23] 萊文:《不同的路徑:馬克思主義與恩格斯主義中的黑格爾》,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5] 劉慶福:《蘇聯有關馬、恩文藝論著的編譯和研究論著在中國的傳播》,載《蘇聯文學》,1983(2)。
[16] 梅林:《馬克思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
[17] 伊林·費徹爾:《馬克思:思想傳記》,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18] 奧古斯特·科爾紐:《馬克思恩格斯傳·第一卷:1818—1844》(1),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
[19][20] 維塞爾:《馬克思與浪漫派的反諷——論馬克思主義神話詩學的本源》,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21]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22] 盧卡奇:《盧卡奇文學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26] 路易·阿爾都塞:《黑格爾的幽靈:政治哲學論文集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 張 靜)
The Pre-History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A Study of Marx and Engels’ Literary Criticism between 1833 and 1844
ZHANG Yong-q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From 1833 to August 1844,Marx and Engels produced their own literary works and comments,which was not only the “pre-history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but has also become the basis of the other five critical forms.Overseas studies of these works have undergone three phases,namely those of initial appearance and embryonic form,of birth and development,as well as of reflexion and furthering.However,Chinese scholars’ approaches to these works have changed from following the Soviet model to adopting Western Marxism.Furthermore,on the spectrum of Marx studies,the tendency towards “narrowing” in the style of Franz Mehring is counterbalanced by that towards “broadening”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Leonard P.Wessell,Jr.A similar phenomenon can be detected in Engels studies,for Gy?rgy Lukács’s “intentional elevation” exists side by side with Peter Demetz’s “denunciation without any reason.”The present paper,therefore,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promoting an integrated research into Marx and Engels’ literary works and comments so as to combine the two contexts of history and social realities.
Marxism;critical theory;pre-history form;Soviet model;Western Marxism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規劃項目“馬克思恩格斯(1844年8月28日之前)的批評理論”(2014010203)
張永清: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