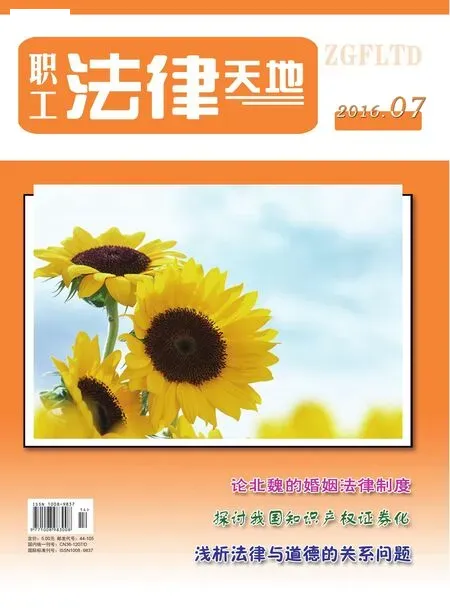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兩種方法啟示
陶必霞
(610207 四川大學法學院 四川 成都)
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兩種方法啟示
陶必霞
(610207 四川大學法學院 四川 成都)
法律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尤其注重研究方法的選擇。不同的方法選擇、不同的切入點有可能會導致對同一問題的結論大相徑庭。區域比較的視角和生態的視角,前者著眼于比較量化分析,后者注重研究對象整體性及對象內部各要素相互關系。前者可使研究者由淺入深層層遞進地研究一個問題;后者則讓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有一個宏觀整體的理解。
鄉村視角;區域比較;生態視角
作為一門非常注重研究方法選擇及田野調查的法律社會學科,研究方法的選擇對研究結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鄉村視角與區域比較的視角是一種能夠發現問題深層本質、理解研究對象自身特殊性的研究方法;生態視角則借鑒了生物學上的生態系統理論,是從宏觀角度研究問題的方法。我們必須首先宏觀地,其次由淺入深地對問題展開研究,而這兩種研究方法不失為一種很好的啟示。
一、《鄉村江湖》中的研究方法啟示
《鄉村江湖》是作者陳柏峰對兩湖平原“混混”的研究,通過對“混混”這一群體的研究,作者得出結論認為鄉土邏輯已經衰弱。農村社會既不是處于依靠宗族治理的社會,又尚未形成現代化的法理社會,而是處于二者之間的過渡狀態。因此,農村社會“混混”橫行,極大地影響了基層農村的社會秩序。
關于本書的研究方法,作者提到,一是村莊生活的視角;二是區域比較的視角。①本書大部分章節題目都是“XX與XX”的格式,這十分直接地表達出了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寫作思路。作者首先提出了一種所謂“鄉土邏輯”的四個原則:情面原則、不走極端原則、歧視原則和鄉情原則。論述了鄉村“混混”對鄉土邏輯的破壞,使得農村社會的灰色化。作者認為,農業稅尚存的時期,鄉村基層政府為了完成國家的稅收、計劃生育、殯葬制度改革等的任務,而默許“混混”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二者結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在農業稅取消后,鄉村基層政府的稅收任務已經不存在,且國家開始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開始了“資源下鄉”。但是在這一“資源下鄉”過程中,由于鄉村混混的存在并截取了很多本應該是農民的利益,因而導致了農民對基層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同時,因為“資源下鄉”,原本鄉村基層政府與鄉村“混混”結成的利益共同體存在著被打破的可能,基層政府不再需要“混混”輔助稅收繳納。但事實卻是相反:“官退”之后,往往不是“民進”,而是鄉村混混與邪教組織的跟進。②資源下鄉的增加不但沒有增進基層政府的合法性,反而削弱了基層政府的合法性,基層政府陷入了鄉村治理的內卷化。③至此,作者論述了由于鄉村混混的存在,鄉村治理開始灰色化和內卷化,混混作為一種取代了國家在農村的暴力而存在,破壞了鄉村的治理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混混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基層政府的“默許”態度以及基層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考慮,混混作為一種游離于國家權力之外但又具有某種“合法性”的暴力一直存在于農村,對基層農村秩序的威脅和破壞日益加深。作者行文思路大致是先分別研究華北、華南以及華中農村社會的鄉村混混現象,并做區域性的比較研究,得出鄉村混混在華中農村對鄉村秩序的破壞程度要大于華北和華南農村的結論。
總的來說,作者的這一研究方法,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研究方法,因為作為法律社會學的研究,首要的便是進行區域性的定性定量研究,得出一個區域性的結論,然后對多個區域也用同樣的方法研究得出結論,最后將多個區域研究結果拿來做個比較,得出最后的結論。區域性的研究也只有通過比較才有意義,因為一個區域內的任何制度、文化等,若不與其他地區進行一個比較,便無法發現其特殊性和問題所在。
二、《割據的邏輯》中研究方法的啟示
劉思達的《割據的邏輯》一書是對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生態分析。作者運用的是法律社會學中的“生態分析”理論,作者認為法律系統中的行為主體和其他地方的行為主體一樣,都進行著兩種基本的互動過程:定界和交換。定界即一個社會行為主體試圖界定它相對于其他社會行為主體的生態位置的文化過程。定界包括三種形式,即分界、合界和維界。交換式兩個行為主體以相互獎勵和效益為預期而對彼此實施的行為。交換包括協商交換和互惠交換。④基于此,作者將中國法律服務市場視為一個生態系統,律師在這一生態系統中進行著分界的過程,試圖將自身與其市場競爭者區分開來,而那些魚律師共存的五花八門的競爭者則進行著合界的過程,試圖讓自身顯得和律師更為相似。而司法部和其他管理機關則用他們的管理權來維系這些職業之間的邊界,當然,這些國家機關之間對于他們的行政管轄權也同樣存在著定界的過程。所有這些定界過程的結果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上的法律職業者與國家的司法和行政官員之間對于金錢、人員和資源的交換。⑤作者將中國的法律服務市場劃分為五個地域空間,即邊疆(農村地區法律服務)、戰場(城市個人法律服務)、高端(涉外法律服務)、后院(企業、政府與知識產權服務)和雷區(刑事法律服務)。并對著五個區域的法律服務分別用“生態理論”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在邊疆,赤腳律師基本壟斷行政訴訟,基層法律工作者基本壟斷民商事案件,司法助理員基本壟斷調解和控制基層糾紛,因此,律師的主要業務僅剩刑事案件和法律援助;在戰場,由于各種“掛牌所”、“法律事務所”、“社會所”和“法律服務中心”的存在,律師面臨著來著律師團體內部和外部的激烈競爭,且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取得很大的優勢;在高端,國內所依然或多或少地依賴于外國所來介紹業務,在市場結構里還是處于較低地位⑥;在后院,國家內部的政治斗爭會影響法律服務市場的定界過程;在雷區,刑事司法系統的國家官員是唯一能夠給刑事辯護律師提供保護并能改變案件結果的力量,律師一方面代表當事人對抗國家,一方面卻不得不依靠其與司法機關之間形成的共生關系來進行辯護。作者得出結論認為:決定中國法律職業的結構性變革的關鍵力量并不是其經濟基礎,而是其上層建筑,也就是國家的管理規范體系⑦。
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基于“生態理論”對中國法律服務的分析并得出的結論是頗有見的。首先是在作者對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劃分上,作者提出了創新性的劃分,很好地并且準確地對研究對象進行了劃分,使得研究不至于顯得太籠統。其次在是作者對這每一個劃分出來的法律服務區域進行“生態”的分析,準確地揭示了中國法律服務行業中的各種定界混亂現象和導致定界混亂的原因。誠如作者所說,生態理論是動態的,也更能夠全面把握市場與國家交換的動態以及建構法律服務市場社會結構的政治斗爭⑧。
總體看來,作者的這一“生態理論”的分析方法是一種很有獨創性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注重社會主體之間的動態過程,能夠看到國家權力斗爭對法律服務市場的滲透和影響。也看到了法律服務者內部之間的競爭和沖突。這幾乎完整地呈現了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表象以及表象下面更深刻的,導致中國法律服務市場成為今天這樣一個格局的原因。筆者認為,這樣一種研究方法可以適用于對某一群體某一行為的研究,借助這一“生態理論”,我們首先分析這一群體某一行為的表象(這一群體內部的定界,即分界、合界和維界的狀態和過程),其次,分析這一群體與相關群體的交換過程(協商交換或互惠交換),最后,分析這種交換過程對群體內部定界過程的影響。通過這樣一種方法,我們可以對某一群體某一行為作出動態的合理的解釋。
三、一個可能的問題切入點
陳柏峰在《鄉村江湖》一書中提到,隨著鄉土邏輯的衰退,國家權力從農村社會的退出,“官退”并未造成“民進”,鄉村社會并沒有形成現代的法理社會,并沒有實現村民的“自治”,而是鄉土混混大行其道,一種非法的暴力在代替國家合法的暴力發揮著作用。在此,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官退”之后卻為造成“民進”的法治鄉土社會狀態,反而是混混橫行?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或者說,我們如何治理鄉村混混這一現象?很顯然,作者籠統地提出的兩條建議(遏制基層政府的自利性和遏制鄉村混混)并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我們也知道,“國退民進”,國家權力從社會民間退出,公民人格的養成是眾多法律人的夢想,哈耶克認為,自由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外在的強制被限制在最小的狀態。盧梭也說,人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除了人民授予的權力之外,政府的權力不具有任何的合法性。孟德斯鳩也主張,自由就是能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他們主張國家權力應被限制在一定范圍內,退出私人領域,培養公民意識、公民人格,所謂“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但是,陳柏峰的研究卻顯示,政府權力的退出,并不必然意味著公民意識、公民人格的健全以及法治社會的形成。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如果說國家權力的退出,到法治社會的形成中間有這么一段過渡期的話,那么這個過渡期的秩序應當如何維護,或者說,鄉村混混的存在是否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合法性?因為,我們完全可以樂觀地說,鄉村社會沒有被更加暴力和極端的黑社會組織或是邪教組織控制,相比于這種更壞的情況,鄉村混混是否是一個更好的選擇?是否應當如作者建議的那樣,現階段國家權力不應匆忙退出鄉村基層,應當保持著對鄉村基層一定的控制?因為蘇力在《送法下鄉》中也提到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之所以要“送法下鄉”是因為某種程度上國家權力無法下達農村基層社會。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國家權力在鄉村基層的薄弱。因此,蘇力也隱約地主張國家權力應當適當往農村深入以推進農村法治的現代化。筆者卻認為,國家權力除非必要,不應深入農村基層,應當給基層留下足夠的空間,以培育公民意識和精神。我們知道,封建時代“皇權不下縣”,縣以下沒有官方正式的政權建制,但是也未曾聽說鄉村社會的秩序因此而混亂不堪。相反,鄉村因為有宗族的存在,鄉村的糾紛可以通過宗族來解決。筆者提及宗族制度并不是主張恢復這種制度,而是說,我們可以將宗族視為一種“自律組織”,在鄉村社會中大多數糾紛可以通過這個大家都成人的“自律組織”來解決。因此,問題歸根到底就是:我們如何在鄉村基層培育這樣一種“自律組織”?而這在筆者看來,有待于鄉村民眾的公民意識和精神的提升,但是這需要時間,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時間是超出任何個人或一些人的能力的,是“上帝”的事業⑨。
注釋:
①陳柏峰著,《鄉村江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9頁。
②陳柏峰著,《鄉村江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39頁。
③陳柏峰著,《鄉村江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76頁。
④劉思達著,《割據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5-9頁。
⑤劉思達著,《割據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9頁。
⑥劉思達著,《割據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48頁。
⑦劉思達著,《割據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22頁。
⑧劉思達著,《割據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22頁。
⑨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年10月版,第22頁。
陶必霞,四川大學法學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