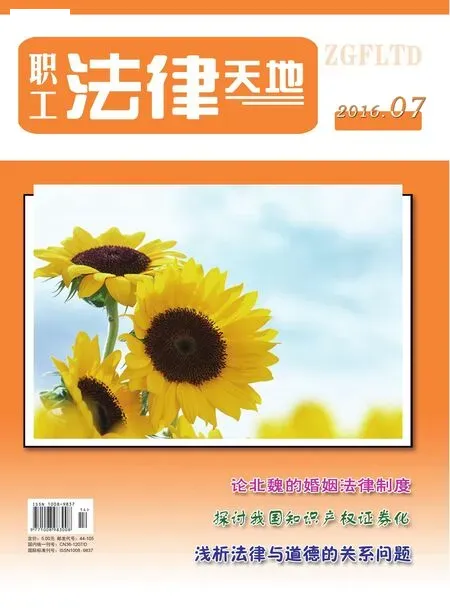論高空拋物的罪名認定
金 潔
(210093 南京大學 江蘇 南京)
論高空拋物的罪名認定
金 潔
(210093 南京大學 江蘇 南京)
現實生活中涌現出了大量的高空拋物的實例,如發生在山東的“刀砧板傷人案”、深圳“好又多物業公司賠償案”,此類案件往往伴隨著重大的人身及財產損害,當面對這些情況時,很多當事人會選擇息事寧人或者提請民事損害賠償,事實上實務中的此種高空拋物行為在發生重大人身及財產損害時已經構成了刑事意義上犯罪,在刑事領域內對于此類行為該如何處理,在司法審判實踐中各地區法院在審判中定罪罪名時并不一致,存在爭議,本文便意在探討對該類型犯罪的罪名究竟應當如何認定才屬于合理,并著重分析了目前司法審判實務的定罪傾向,即“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存在的合理性,并針對此類型犯罪的罪名認定及責任承擔提出自己了的觀點和看法。
高空拋物;刑事罪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近年來,高空拋物逐漸成為了一個全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始于2000年5月在重慶市渝中區發生的“煙灰缸傷人案”,法院在判決的過程中依據民事《侵權責任法》中的過錯的一般認定原則,推定該幢居民樓內所有住戶都有實施該行為的可能性,因此判決該幢樓內的所有居民連帶對本案被砸傷的受害人進行賠償。這個案件判決后,其他地區也發生了一些類似案例,在全國范圍內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們對于法院的判決產生了很大的爭議,一方面看,類似于連坐的責任承擔方式無疑放任了真正施暴者的行為,加重了周圍其他居民的責任,但另一方面從救濟受害者的角度看,這種連帶責任的承擔方式在彌補受害者損失方面卻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高空拋物的概念及其民法處理路徑
(一)高空拋物的概念
在研究高空拋物這一行為的刑事罪名的認定之前,一個必要的前提便是對高空拋物的概念加以界定,對于這一概念的界定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展開,凡是行為人從高處拋擲物品,致使損害的行為都可以被稱為廣義的高空拋物,而狹義的高空拋物則是加上了一個限制條件,即無法確定誰才是該拋擲行為的真正實施者的情形,而本文所研究的高空拋物行為的罪名認定則在一個更狹窄的領域,即專指在區分所有的建筑物內拋擲出物品,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財產損害, 可見,對于此處的高空拋物行為的范圍作了嚴格的限定。
(二)高空拋物致害案件的民事侵權處理路徑
在多年的司法審判實踐的過程中,我國對于高空拋物致害的民事案件的處理在審判實踐中出現了很多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侵權責任法》出臺前,法院的審理依據通常是我國《民法通則》條文第一百二十六條的規定,即關于建筑物致人損害的責任分配的規定。該條文明確規定了建筑物致人損害責任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責任。除了民法通則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的第155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6條等規定中也做了類似的規定。但這些規定長期在理論界存在著極大的爭議,并未實際解決高空拋物侵權案件的爭議,伴隨著我國《侵權責任法》的出臺,《侵權責任法》第八十七條對不明拋擲物、墜落物損害責任作出了具體規定,法條明確規定,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致使他人遭受損害的,在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情況下,除自己能夠舉證證明自己沒有實施上述拋物行為的外,其他所有具有加害可能性的建筑物使用者都負有連帶的賠償責任。但是,新《侵權責任法》的頒布以及第87條的專門規定似乎并沒有終止學界對于其具體法律適用的爭議,反而引發了更多的關于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適用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探討。
(三)高空拋物致害案件的單一民事處理路徑的困境
筆者總結前人的研究可以發現,對于高空拋物侵權行為的責任認定在民事領域內已受到了重視并已經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結合民事領域的研究以及我所進行的調查問卷的數據分析可知,對于生活中不斷涌現出的“高空亂扔煙頭、垃圾、酒瓶”之類的現象,應當如何認識這些具有危險性的高空拋物行為的性質,以及如何應對此類行為所可能引發的責任后果,大多數民眾可能都停留在道德譴責以及民事賠償等的層面,尚未深入到刑事領域的研究。
以我所生活的城市近年來發生的一起典型高空拋物致人損害案件而言,某公司的員工金某在受公司委派修補某小區的自來水管時遭遇“飛來橫禍”,被從天而降的垃圾袋砸成了五級傷殘。雖然法院最終審理只是基于民事《侵權責任法》判定肇事者承擔損害賠償金等其他費用共計31萬余元,但筆者認為,肇事者的行為已經超越了普通民事侵權領域的范疇,構成了刑事上的犯罪行為。
二、高空拋物致害行為的罪名認定爭議
(一)審判實踐領域中的罪名認定爭議
高空拋物行為極具危險性,極易造成更為嚴重的損害后果,在造成嚴重人身損害及重大財產損失的情況下,在刑事立法上應該如何認定施暴者的刑事責任,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在法學理論界以及審判實務領域長期以來都存在著爭議。
2013年我省連云港市中院審理的丁某剛案可以看作是眾多此類型案件中的一個典型,被告丁某剛因為心情煩躁,從其工作的建筑小區16樓隨手拋下2塊紅磚,致使臨街行走的被害人被磚塊砸死,同時磚塊的碎片也造成了停靠在路邊的汽車玻璃的損壞,連云港中院在審理此案件時認定丁某剛的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法官在說理中指出,高空拋落或者掉落的物體由于物理原因的作用速度極快可能造成不特定的人員或者財產的損失是基本常識,被告人作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在其供述中提及扔完就后悔,但對到底有沒有砸到人或車卻未進行查驗,可見對于自己行為的可能結果,被告人在意識到可能造成損害的情況下并未在意,反而采取的聽之任之的態度,因此法官認定其存在主觀故意。
法官在具體認定其罪名時采取了傳統的刑法四要件分析方法,從本案侵害的客體(即危害的社會關系),侵權人的客觀施暴行為以及案發時其主觀心態入手,綜合認定被告觸犯的罪名,法官在說理論證中著眼于本案的案發場所、具體的實施行為、其拋擲物體的種類、體積及重量、被告人明知其實施的行為可能會造成危害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財產安全的嚴重后果等因素考量,雖然現有證據并不能證明其對于此結果的發生具有積極追求的心態,但其在實施了上述行為以后也并未采取任何補救措施,反而放任危害后果的發生,認定在犯罪時其主觀心態應為故意。法院綜合多方面因素,最終認定其行為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非故意傷害罪。
這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拋物致人損害案件,法院認定被告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樣以該罪名認定的還有2015年10月沈陽市大東區法院判決的劉某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在該案中,劉某某隨意向窗外拋扔酒瓶、罐頭瓶,致使路邊停放的轎車發生了損毀,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14條,認定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除去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人民法院法院也審理過一起類似的高空拋物案件,被告董松山在沒有采取任何安全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從十三米高的建筑除塵器上向樓下拋擲建筑垃圾,砸中了孫某,并導致了其死亡。法院判決認定施暴者的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法官認為其在明知樓下有人打掃衛生的環境下,在已經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死亡的情況下仍然主觀上輕信自己可以避免危害后果的發生,并最終導致了他人死亡的法律后果,該行為已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
在本案中,法院依據我國《刑法》第15條對犯罪過失的認定,將被告人的主觀心態歸結為是過失。2015年5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審理的建筑工人高空拋鋼管,致使工友死亡案,法院對此行為的定罪也是“過失致人死亡罪”。
在2015年撫順市望花區人民法院判決的李某因高空拋擲啤酒瓶致使被害者鼻梁被砸斷一案中,法院審理認定拋擲者的行為屬于故意傷害致人死亡。
在審判實務中,還有的法院則對同類案件審理則認定拋物者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
筆者查閱了近年來各地法院審判實踐過程中對于高空拋物致害的判決罪名的認定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分析,歸納出了各地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時呈現的以下特點:
(1)對于此類行為的刑事罪名的認定,法院內部也存在著爭議。從實務審判中的判決結果來看,目前針對高空拋物致害案件的刑事判決,罪名認定呈現出五花八門的特點。以造成人死亡的后果這一情況為基準加以判斷,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致人死亡、過失致人死亡罪以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審判實例都存在。
(2)目前各級人民法院的審判依據大都是綜合了高空拋物行為所造成的人身傷亡和重大財產損失程度以及拋物者的主觀惡意程度等眾多因素加以判斷的。
(3)在各級法院的審判實踐中,越來越多的法院傾向于將此類高空拋物行為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4)即便從判決結果看對于兩起性質相近的案件,法院審理定罪都認定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也需要加以區分,其也包含著故意與過失兩種不同的主觀心態,我國刑法第114與第115條第二款對此作了區別規定。
(二)刑法學界對于此類型案件的罪名認定爭議
爭議的焦點:部分法院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是否合適?
對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其他罪名之間認定的論爭,學界曾展開了激烈的交鋒。
張明楷先生等學者曾在其著作中指出基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罪名所承載的“公眾性”與“社會性”基礎,因此要求在認定該罪名時必須排除“少數”的情形,重視量的“多數”。這也契合了這一罪名的“不特定性”的特點,具有了隨時有可能向“多數人”發展的現實可能性。張明楷先生曾專程撰文分析高空拋物行為在觸犯刑法情形下的罪名認定,在其看來,雖然對于高空拋物行為,可能砸死或者砸傷的人無法事先確定,但只要事態不可能向多數人的損害發展,就意味著不可能侵犯公眾的利益,這就意味著不符合該罪的構成要件,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事前不能確定傷亡者是誰,也不應當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陳興良教授也曾經從手段的相當性角度明確指出對于高空拋物此類案件的認定,不應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其看來,高空拋物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情況下應當被認定為故意殺人罪,這是社會法益與個人法益這兩種利益相比較權衡的結果,對于高空拋物此類行為的危險性遠沒有達到與放火、爆炸、決水等危險性相抗衡的程度,因此不能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罪名內涵解讀
如上文所述,目前刑法學理論界以及實務界對于高空拋物行為的罪名認定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各級法院對于此類罪名的認定的爭議的解決路徑應當著眼于對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內涵的解讀以及其與其他可能混淆的具體罪名的辨析。筆者認為對于部分法院在審判實踐中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認定此類行為,這一罪名適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以下筆者將通過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內涵的解讀以及其與其他罪名之間的區別的辨析來分析審判實務中對于此類行為罪名認定的合理性:
(一)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之界定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罪名長期以來都是扮演的兜底條款的作用,其著眼于公共安全這一法益的保護,具有社會性,要想準確的認定此罪名,就需要對于公共安全的內涵進行解釋,但對于“公共安全”的含義,長期以來,刑法學界對于這一概念的解讀都存在著爭議。筆者梳理可以發現,目前學界爭議的幾種學說的共同點是都是圍繞著該罪名的“不特定性”展開的,張明楷先生在其著作中認為,“所謂不特定性,更深層次的理解是犯罪行為可能侵犯的對象以及可能會導致的后果無法事先確定,超越了行為人的實際控制以及可預料程度,難以預料和控制,同時這種行為可能造成的具體危險或者損害結果具有隨時擴大的可能性。”筆者贊同此觀點并且認為此處的公共安全應當是指排除了特定多數人的人身財產法益的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健康以及重大公私財產,這種理解能夠在最大范圍內保護除特定人以外的最廣泛群體的利益,真正契合了其“公共性”與“社會性”的特點。
長期以來學界對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認定已逐漸形成一項共識,即認為該罪屬于具體危險犯,對于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財產等可能造成緊迫的危險,典型的高空拋物行為正符合“具體危險犯”的構成要件,侵害對象的不確定性致使其在拋物的一瞬間對于可能造成的損害結果難以預料,受害者以及受害程度都處于不確定之中,雖然張明楷先生認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須可能造成多數人的損害,而高空拋物這一行為不可能使得事態向多數人的損害發展,從而不可能構成對公眾利益的侵害,但筆者認為高空拋物這一行為可能造成的事態的嚴重性是難以預料的,因為高空拋物的致害人數究竟是一人還是多數在實施這一行為時并不可知,最終造成的損害結果的嚴重程度也與拋擲的時間、地點密切相關,因時因地不同。
(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險方法”之界定
筆者認為,僅從字面分析刑法第114、115條的規定的意思可以看出,刑法以連接詞“或者”列舉了“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可見其立法本意認為這些其他方法與條文中明確規定的“放火”等具體方法在危害的程度上是相當的,這在刑法學界也形成了廣泛的共識,但筆者并不認同陳興良教授所提出的認為高空拋物的危險性難以與前述具體危險方法匹及的觀點,在筆者看來,高空拋物致人損害其危險程度并不低于放火、爆炸等實施手段的危險程度,在判斷一項危險行為的危險性時應當綜合該危險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可能造成的損害結果來判斷,而高空拋物行為由于高空慣性的作用,倘若發生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其可能造成的損害后果是難以估量的,因此筆者認為就其危險性而言,完全可能與“放火”、“決水”、“爆炸”等行為造成相當程度的危險,因而應當歸屬于“其他危險方法”的范疇。
雖然陳興良教授等知名法學學者曾經提出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應當盡可能減少使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尋釁滋事罪、非法經營罪等“口袋罪名”。因為此類罪名的犯罪構成要件具有模糊性、開放性、概然性的特點。其認為這些罪名貌似擔負起了承接遺漏犯罪的使命,但實際上是大大擴張了刑事司法的范圍,是不應當被推廣適用的,同時他們也提出了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規制該項罪名擴大適用的一些具體規則,但筆者在綜合分析各罪名的特點的基礎上結合高空拋物行為的特點認為,現階段在現有的刑法規范框架下,對于高考拋物行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具有合理性,近年來各地區法院對于此類案件的審理判決,也多以該罪名認定也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綜上所述,目前各級法院審理的高空拋物類型的刑事案件正在日益增多,對于此類案件的處理,雖然學界仍在不斷爭議,但筆者認為,對于典型性的高空拋物致害案件,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罪名進行認定是比較合理的,但這也并不是絕對的,在認定高空拋物行為的罪名認定時,我認為仍然應當從刑法犯罪的基本理論,“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入手,分析該犯罪的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四大要素。其中尤其要加以重視的便是犯罪目的,故意與過失的區分,對于案件的最終量刑影響巨大,在可能出現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其他罪名的認定爭議時,可以結合具體案情,比較各罪名的區別,再在此基礎上對這一類型的案件做出正確的判斷。
[1]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5年版.
[2]王澤鑒,《侵權行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杜景林、盧湛譯:《德國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5]江平,《羅馬法基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6]劉士國,《侵權責任法重大疑難問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7]田國興,《高空拋物侵權行為探究》,載《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
[8]陽庚德,《高空拋物侵權連帶責任制度否定論》,載《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9]王成、魯智勇,《高空拋物侵權行為探究》,載《法學評論》第2期.
[10]李霞,《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的法律救濟》,載《山東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11]史尊魁,《共同危險行為與高空拋物之區分》,載《武漢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12]李迎春,杜慶華,《論高空拋物侵權訴訟的復合結構》,載《廣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金潔(1992~),江蘇常州人,南京大學2014級法律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