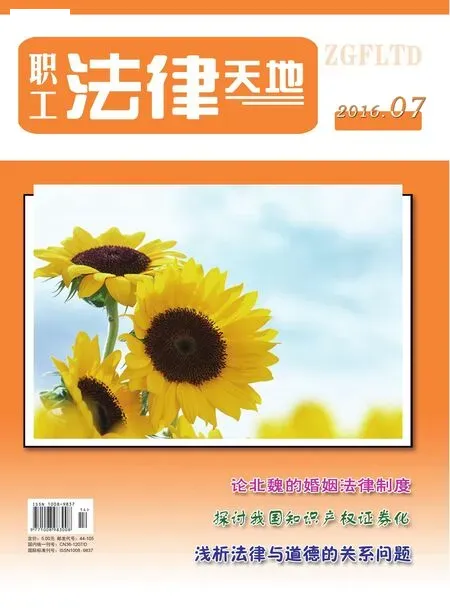校園欺凌事件的法律思考
馮彥波
(200444 上海大學法學院 上海)
校園欺凌事件的法律思考
馮彥波
(200444 上海大學法學院 上海)
近幾年,“校園欺凌”事件在我國各地發(fā)生,給受害學生造成嚴重的身心傷害。本文從校園欺凌的成因入手,并以法律的視角分析其侵權責任并探討相應的防控措施。
一、校園欺凌的成因
(一)學生自身價值取向的錯位以及性格的偏激
當代中小學生大部分都屬于獨生子女家庭中,“4+2+1”的家庭模式使孩子時刻都處在大人們溺愛的氛圍中。孩子從記事起便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處于家庭唯我獨尊的核心位置,一切欲望都會由家人幫助滿足,價值觀逐步陷入錯覺的深淵,這種錯覺,使他難以承受任何輕視與挫敗。同時,某些影視作品、網(wǎng)絡游戲等都會不同程度的影響著他們的行為方式,使他們在面對自身的挫敗與不滿時往往用暴力的手段去尋求解決。
(二)學校懲戒作用的不斷弱化
隨著我國民主化進程不斷加快,教育民主自然而然也成為公眾尤其是眾多媒體聚焦的焦點,學校怕引發(fā)媒體曝光或其他后果而不敢對學生處以“開除”等嚴厲處罰,而對于這類學校的“小霸王”,批評教育等溫和的處理方式基本屬于“罰酒三杯”式的敷衍了事。因此,懲戒功能的不斷弱化和放任,最終使得這類學生的欺凌行為變得無所畏懼,甚至迫使一些校園欺凌事件的受害者加入其中,形成“被欺凌——加入欺凌集團——欺凌別人”的惡性循環(huán)。
(三)法律法規(guī)的滯后性和局限性
中國現(xiàn)有的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如《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刑法》等相關規(guī)定嚴重滯后,尤其是針對14歲以下未成年人犯罪顯得束手無策。在網(wǎng)絡傳媒無比發(fā)達的今天,大部分青少年都很清楚的知道未滿14歲未成年人無需承擔刑事責任這一相關規(guī)定,使得他們在實施校園欺凌行為時缺少一把懸在頭上威懾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二、校園欺凌的法律責任分析
校園欺凌行為的發(fā)生不是“小霸王們“單純的個體行為,而是社會多方面因素在無數(shù)次的放縱及漠視下催生的產(chǎn)物,以下對其相關責任進行簡要分析:
(一)欺凌實施者的法律責任
對于未成年學生的欺凌行為,如上文所述,未滿14周歲的行為人不負任何刑責,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行為人,實施法律限定的嚴重犯罪以外的刑法中其他危害行為,雖然依法不負刑事責任,但根據(jù)刑法第17條第4款的規(guī)定,應當責令其家長或者監(jiān)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yǎng)。
同時,近期各地發(fā)生的不同校園欺凌行為也表明,當今社會所發(fā)生的校園欺凌或暴力行為已經(jīng)不僅局限于同學間的欺侮,而且有和校外不良勢力相勾結的情況發(fā)生,甚至成為這些不良勢力實施敲詐、搶劫、強奸等行為的“馬仔”。根據(jù)《刑法》第二十九條規(guī)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因此,對于這類校外成年群體,應承擔欺凌行為的連帶責任,并按照間接正犯,依法從重處理。
(二)監(jiān)護人的法律責任
對于大部分未成年侵害人來說,由于尚屬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根據(jù)《侵權責任法》第32條規(guī)定,應由其監(jiān)護人承擔替代責任。對于校園欺凌群體中占很大比例的“留守兒童”,根據(jù)《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相關規(guī)定,其近親屬、村(居)民委員會、縣級民政部門等有關人員或者單位要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監(jiān)護人資格,另行指定監(jiān)護人。
此外,某些校園欺凌行為的受害者,迫于欺凌者的人身威脅或教唆,而去實施侵害他人的行為的,如果監(jiān)護人能證明盡到了監(jiān)護責任的,可以減輕處罰。
(三)學校的法律責任
對于大多數(shù)學生來說,每天在學校的時間往往比家里更甚,學校當然應該承擔起校園欺凌的相應責任。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guī)定:“對未成年人依法負有教育、管理、保護義務的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職責范圍內(nèi)的相關義務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損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使他人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學校、幼兒園等教育機構有過錯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
而且,針對校內(nèi)外不良分子校外堵門,或在放學路上實施侵害的情況,筆者認為,此處的學校責任理應包含學生上下學必要時間所發(fā)生的侵害行為,盡最大可能維護學生良好的學習環(huán)境和身心健康。
三、校園欺凌的法律防控措施
首先,建立健全對校園欺凌的監(jiān)督、舉報、處置機制。在學校及基層公安設立24小時舉報求助熱線,一旦接到舉報,必須在第一時間展開調(diào)查,并積極介入,經(jīng)學校和公安機關共同評估,對施暴人采取批評教育、開除學籍、訓誡、人身限制令及其他隔離措施。避免施暴者事后對舉報人打擊報復或受害學生因害怕而逃學輟學等后果的發(fā)生。任何學校老師發(fā)現(xiàn)或接到校園欺凌舉報,都有義務按程序嚴格上報,否則會承擔相應的行政或民事責任,在學校形成對校園欺凌長久的嚴打高壓態(tài)勢。
其次,出臺和修訂針對校園欺凌的法律法規(guī)。對于未滿14 或16周歲的刑事責任年齡規(guī)定,在當年的立法環(huán)境下,相對于社會或成年人來說,未成年人盡管實施了犯罪行為,但仍屬弱勢群體,應對其重教育而輕懲罰,并且從其年齡所屬的身體和心理條件來看,對社會的危害性也較低。但是,校園欺凌恰恰相反,被欺凌者同為未成年人,而且是更加處于弱勢的受害群體,更需要法律的保護。筆者建議,我們應參考西方國家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經(jīng)驗,盡早出臺專門的反校園欺凌(暴力)法,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受害人同為未成年人的,則根據(jù)情況降低刑罰適用年齡,擴大入罪種類,尤其是對于拍裸照上傳這類對于心理傷害巨大的犯罪行為。當然,本著教育為主的精神,不能簡單的施以拘役或有期徒刑,而是要結合強制心理輔導、社區(qū)矯正等多種方式,“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加強對學校的問責機制。我國現(xiàn)有《侵權責任法》規(guī)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的,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承擔責任,但能夠證明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不承擔責任”。筆者認為,這種歸責原則和責任承擔方式不足以保護校園受害者,也不足以引起教育機構的重視,學校往往會以各種校紀校規(guī)等證明自身起到了教育責任,進而怠于采取相關安全措施,使侵害者變本加厲。因此建議法律規(guī)定學校在面對校園欺凌事件時采取無過錯原則,倒逼學校加強各種措施維護學生和諧的就學環(huán)境,減少校園欺凌的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