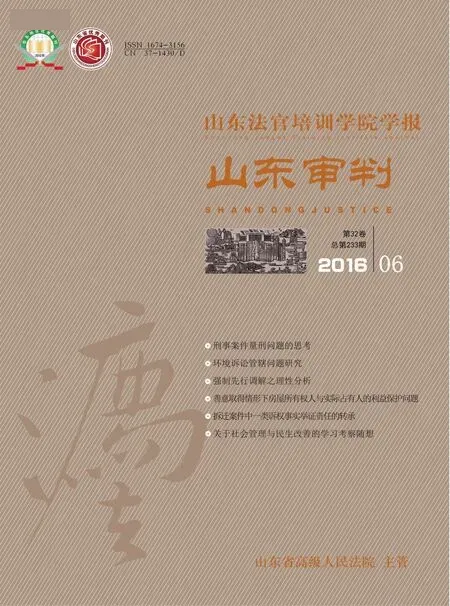從信仰說信訪
——對信訪工作的一點感悟
●王志華
從信仰說信訪
——對信訪工作的一點感悟
●王志華
在立案庭從事信訪工作,已經有幾年時間了。期間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信訪人,聽到了各式各樣的信訪事。處理信訪的過程,也是一個積累與思考的過程。在這里,就把其中的點滴心得分享給大家。
常在想,為什么信訪人不信法卻堅持信訪?
我想,首先,要看信訪對信訪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對信訪人而言,法院是做出裁判的機關,法官是做出裁判的主體,信訪部門是“處理”裁判問題的部門。因此,在信訪人認為裁判過程或者結果“有問題”時,便會想要選擇信訪這種救濟渠道。因為對于信訪人而言,相較于再次通過司法程序救濟權利,他們更容易也更愿意選擇信訪這種在他們認為只需要說一下,甚至是發泄一通的“簡單”方式。只要是有救濟渠道,不管這個渠道的職責范圍如何、解決問題依照的方式如何等等,渠道僅僅是工具而已。
其次,要看信訪人是如何“信仰”法律的。對部分信訪人來說,法律是神圣的,神圣到每一個自己都是弱勢群體,神圣到自己的訴求沒有得到支持便是褻瀆了法律。很多信訪人都會說:案子是你們法院判的,現在找不到人、拿不回錢就得跟法院要。有個問題需要強調,信訪人運用法律維權的成本確實是存在的,有時還不是個小數目。當維權成本高于信訪人想要維護卻沒有維護或者沒有全面維護的利益時,部分信訪人便會把所有的維權成本,不僅包括經濟支出,更包括人情冷暖、社會倫理、愁苦冤屈等各種感情帳,一并加到法院和法官頭上,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部分信訪人對司法維權認知的不準確和對法律的一知半解卻一意孤行的強烈矛盾,也就造成了不信法卻堅持信訪的現象。
再次,要看合法性與合理性在信訪中是如何并存的。依法治國的提出看似是對信訪工作的合法性提出了要求,但維護公平正義亦是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如何維護公平正義,是需要理性參與的,但現狀卻是信訪人或者不想理性、或者不能理性。信訪需要依法進行,我國對信訪制度也進行了改革和完善,像是取消信訪排名、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終結等制度,都正式賦予了信訪既具合法性又具合理性的生命。怎么來理解呢?簡單地說就是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是并存的,因此,落實這些制度的過程既是證明的過程,也是革新的過程——依法信訪,就能維護公平正義。
最后,法院、法官應該如何信仰法律。對于這個問題,一千個人會有一千個答案,比如加強立法、統一認識、普法宣傳等等。但是這么說來總是空洞的,因為法律本身就是抽象的概念。我認為,對于信訪工作來說,信仰法律就是引導信訪工作、引導信訪人、引導負責信訪工作的我們自己,自覺全面正確地踐行信訪制度的初衷和現實意義,絕不讓信訪淪為信訪人不信法卻隨意地選擇通過信訪途徑解決問題的工具。這就要保證良好的溝通、正確的引導、及時的傳達和轉辦,同時也回到了第一個問題中提到的觀點——司法應該不卑不亢。
說到了信訪,也便會有如何與信訪人溝通的問題。幾年的信訪處置歷練,讓我在這方面也多少獲得了一些經驗和感悟。其實,與當事人溝通貫穿于整個司法過程的始終。就信訪工作而言,它的職能就是溝通、引導、傳達和轉辦。與信訪人溝通,我想至少要考慮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堅持“對事不對人”。首先,我始終堅持一個觀點就是司法應該不卑不亢。在這個基礎之上,我想將對事不對人中的“事”落腳在一些具體的行為上。例如在接訪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情緒激動、言辭激烈的信訪人,某些信訪行為會擾亂工作秩序乃至造成工作被動。在耐心地答疑解惑之后,憤懣甚至委屈的情緒有時在所難免。當這樣的信訪人三番五次來訪過后再次出現,仍然情緒激動、言辭激烈,而此次信訪人要求復印卷宗卻不知道履行什么手續、要求盡快裝訂上訴卷宗并移送、要求支取案款盡快填寫案款發還通知單等等。這種情形下的這些具體的“事”不應該被貼上情緒化的標簽,而應當是被認真尤其是被及時處理的,因為整個司法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走勢都是具體化、精細化地被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的。
二是可以將那些最傳統、最樸素的道理應用在日常工作中。比如實踐出真知,沒接觸過每一種信訪人,就不會總結出如何與每一種信訪人溝通的方式。因此我們要多做,多做就可能會出錯,出錯了就改正,因為做的過程就是實踐的過程,改正的過程就是出真知的過程;再比如好記性不如爛筆頭,信訪工作的溝通既要善于傾聽,也要勤于記錄,用最簡潔的文字概括最全面的來訪過程,是思考的過程,也是做好匯報、答復的第一步。其實這些道理就像是父母從小到大一直跟我們重復的早上一定要吃飯、腳暖和了全身就不冷了的道理是一樣的。時間越久我們就越會發現這些道理都是真理。同樣的,我相信,在工作中我們越是這樣做,就越會收獲良多。
(作者單位: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法院)
責任編校:姜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