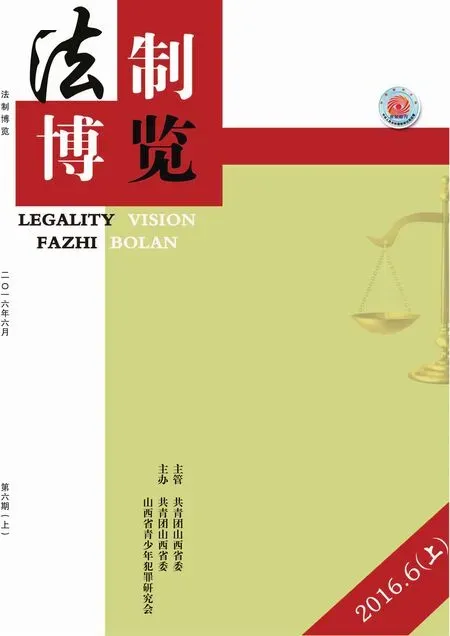淺議大學校園內流浪動物侵權損害責任
劉穎超
北京理工大學,北京 100081
?
淺議大學校園內流浪動物侵權損害責任
劉穎超
北京理工大學,北京100081
摘要:本文將結合身邊的真實案例,通過分析侵權行為構成四要件,解決在具體場合流浪動物侵權時的責任主體認定問題,并對我國該方面的法律條文提出自己的見解。
關鍵詞:大學校園;流浪動物;侵權;責任主體
一、事實簡介
2015年10月初,學生黃某看到宿舍門口的紙箱里蜷縮著一只長毛貓,名大白(大白是一只流浪貓,常徘徊于某大學某女生宿舍樓內。不定期有不特定的人在宿舍樓門口的固定位置給大白投喂貓糧、布置貓窩,大白可隨意進出宿舍樓,常于廁所、水房、不特定女生宿舍停留。前一系列行為招致不特定流浪貓狗在樓門口覓食),伸手撫摸卻被大白撓傷,傷口有少量血跡滲出。后去學校醫務室問診,北京某醫院治療,接種疫苗等,共花去費用近1000元,未啟動任何救濟程序。
二、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
本文將采用侵權行為四要件說,即侵權行為、損害事實、過錯及因果關系。鑒于前兩項于本事實中基本無爭議,故僅討論過錯及因果關系。
(一)分析要件之一:過錯。在該法律事實中,可能擔責的主體有:流浪貓的投喂人,宿舍管理人員,學校安保人員,而后兩者又由于是職務行為的過失,故最后的擔責主體有可能是學校,其從屬的安保公司等。
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78條及82條的規定,根據特殊條款優于一般條款的原則,該侵權案件的實際責任承擔者應是該流浪貓的原飼養人或管理人。但是根據筆者數日的走訪調查,該流浪貓在某女生公寓生活已有數載,靠歷屆學生投喂食物生活。這樣說來,大白的原飼養人及管理人自然無從確定。那么,誰是新的飼養人或管理人呢?
分析投喂者的行為,筆者更傾向于其成立無因管理之債。這里,大白的原飼養人、管理人無從確定,故該投喂行為不可能基于與原貓主的約定或任何法律上的義務,純粹是基于善心替原貓主履行喂養義務,故成立無因管理之債。而在無因管理的情形下,因為管理人出于善心,且無先法律義務的規束,故無因管理人僅需盡到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可。譬如,投食于流浪貓時,要提醒過往的行人不要觸碰進食中的動物,因為部分動物由于護食的本性在此時容易傷人。鑒于此,投喂人的無因管理行為并不要求其時時刻刻蹲守在其所投喂的流浪動物旁對其進行全面看守,防止其傷人行為的發生。進而,不特定學生的投喂行為無過錯。
分析宿管人員的行為。對于流浪貓長棲于宿舍門口甚至隨意進出宿舍,宿管人員是知情的。根據其工作職責的要求,筆者認為宿管人員未盡到相應的注意義務。首先,對于流浪貓在宿舍門口長期棲住,且招致其他流浪貓狗一同前來,宿管人員對此應有警覺,即可預見性。因為流浪動物畢竟有潛在的危險,這點不因其曾被人類馴養而消除。其次,對于放任流浪貓隨意進出宿舍,宿管人員更不能免責。其職責,就是管理整個宿舍,解決其中存在的安全、衛生等問題。宿管人員值班室正好在樓道門口,距離流浪貓的長住窩僅兩三米,且室內裝有各樓道的監控影像視頻儀,宿管人員對于流浪貓隨意進出宿舍是放任的態度。但是應該注意的是,作為宿舍管理人員,應該注意到流浪貓可能帶來的衛生問題和可能傷人的安全隱患,有可避免性,但是卻沒有對此予以重視。鑒于此,宿管人員未完全履行工作職責和盡到注意義務,存在一定過失。該過失,來源其工作職務要求,也基于法律規定。
再分析學校安保人員,根據《侵權法》第37條的規定,大學校園是一個公共場所,那么學校的管理人員及安保人員應該盡到一定的職責。對于校園內的流浪貓、狗等應進行定期的管控。鑒于此,學校安保人員存在工作上的不到位,亦有過失。
(二)分析要件之二:因果關系。首先,《侵權法》中的因果關系是指人的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聯,所以可能為黃某損失擔責的主體有:投喂人、宿管人員、學校安保人員。其中,投喂人的行為一定程度上導致流浪貓狗在宿舍樓固定地點聚集;宿管人員放任流浪貓在宿舍樓門口長住且任意進出宿舍樓;安保人員未對學校內的流浪動物進行嚴格的規范化管理。三者共同作用導致了損害事實的發生。筆者認為,后兩者的行為是更直接的原因力,因果關系更明確。
所以,筆者認為,應該為黃某損失擔責的是宿舍管理人員及學校安保人員。其二者對于工作義務的懈怠在一定程度上為流浪貓傷人提供了先決條件,從而為后續事件的發生埋下隱患。但是鑒于二者都是履行職務過程中的失職行為,所以最后學校及安保公司將為這二者的職務行為擔責,承擔一個最終責任。
三、筆者的看法
(一)針對案件,分析如下。首先,不特定學生不因偶爾的投喂行為而成為新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投喂區別于飼養和管理,飼養是一種基于所有權的物權行為,管理是基于飼養人的委托等;其次,投喂的主體不特定,并不是固定一人對大白進行投喂,適用共同危險行為的處分原則又明顯不妥;再次,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承擔的是一種無過錯責任,好心學生不能因為偶爾的投喂行為就讓其承擔與所有人同等的責任,這樣有違法理;最后,站在公序良俗的角度分析,給流浪動物投喂食物是一項善舉,投喂行為本身是一種好善樂施,不能因此讓善人擔責,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法律從業者,沒有人會覺得做了好事還要承擔做好事之后的一系列后續責任,這有違相當因果關系原則。本案的宿管人員及學校的安保人員,其不作為本身已是過失,且構成了對損害結果的原因力之一。
(二)針對流浪動物侵權的法律條文,分析如下。縱觀《侵權法》第十章,總共7條,竟然涵蓋了對于飼養動物侵權領域的所有規定,且章末兜底性條款并無實際操作意義。在司法實踐中,具體的法條含義、目的等大多通過學理解釋來擴充,缺乏規范性和權威性。再者,對于流浪動物侵權僅在第82條提及,將責任簡單歸至“原動物的飼養人或者管理人”,但是在中國對于動物的飼養、領養,流浪等均沒有嚴格管理,流浪貓狗等隨處可見。正是由于流浪動物數量極多,又缺乏前期的登記體制,真正在流浪動物侵權后確定原飼養人、管理人根本不切實際。針對以上情況,筆者對《侵權法》第十章規定提出如下見解:
首先,對于流浪動物的界定不全面。“遺棄”、“逃逸”動物是《侵權法》對于所有流浪動物的統稱。但是,諸如“走失”的動物及上述幾種動物自然狀態下產生的后代性質并無界定。筆者認為,這三個詞的區分可以從原飼養人或者管理人對于所飼養的動物丟失的態度和被飼養動物的習性來著手分析。態度決定主觀惡性大小,習性決定該類動物是否適合人類飼養。通俗來講,“遺棄”是主人不想要動物,而動物并不想走;“逃逸”是主人想要動物,動物自己跑了;“走失”是主人想要動物,動物也不想走,但就是由于各種原因力作用,丟了。試假設,如果主人主觀上不要動物,那其主觀惡性比較大;如果某一類動物頻繁逃逸,那就要考慮該類動物是否適合人類飼養。綜合考慮這兩項因素,才能更好地判斷流浪動物侵權時原飼養人或者管理人的責任大小。
其次,對于飼養人和管理人的界定也不清楚。特別是當管理人作為責任主體時,具體應滿足的要件并未提及。對此筆者建議,將管理人的責任細化:管理人應為有因管理人,且為合法占有。
最后,關于流浪動物侵權的責任承擔主體,應該將一定區域的安保人員、城市管理部門考慮在內,并不能只局限于動物的原飼養人、管理人,甚至好意施惠的人。
我期待,流浪動物管理措施的出臺,也期待更多具體可操作措施的問世。這樣,不管是對于流浪動物還是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都是約束,也是保護。
[參考文獻]
[1]李汶龍.芻議流浪動物侵權與投喂人賠償責任——以北京流浪貓傷人案為例[J].湖南商學院學報,2014(4):116-128.
[2]楊立新.飼養動物損害責任一般條款的理解與適用[J].法學,2013(7).
[3]張娟.流浪動物侵權責任主體的認定——兼議“流浪貓傷人”案[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2013(9):51-53.
[4]楊立新.侵權責任法條文背后的故事與難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16-0202-02
作者簡介:劉穎超(1992-),女,漢族,河北邯鄲人,北京理工大學法學專業,法學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法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