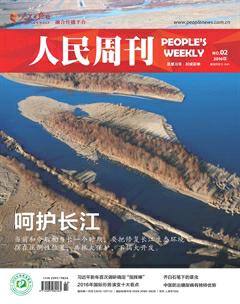魯迅是個“老孩子”
潘彩霞++趙光亞


頑童似的執拗
最早對魯迅這一特質進行明確指認的是一個童言無忌的孩子——其好友的女兒馬玨。在沒有見到魯迅之前,她透過魯迅的文章把他想象成小孩似的老頭兒,“看了他(魯迅)的作品里面,有許多都是跟小孩說話一樣,很痛快……在我想來,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愛同小孩在一起的”。
一個多喜易嗔、極富柔情,甚至特別孩子氣、頑童般的“老孩子”形象已經躍然紙上,這在魯迅的私交圈內多得到認同。他有金剛怒目的一面,但也是一個詼諧善謔、隨性的人,他私人化的空間跟普通人一樣飽滿而且不乏情趣。在許多情形之下,他的刻薄與尖酸也是出自這種老頑童式的游戲化口吻,他的不肯“費厄潑賴”、不愿寬恕與不合常情是因為他時常會像頑童似的執拗、不肯世故。
最具權威的判斷出自茅盾。1927年,茅盾在讀了《寫在〈墳〉后面》之后,不由自主地驚呼:“看!這個老孩子的口吻何等嫵媚!”而且聲言:“如果你把魯迅的雜感集三種(當時已出的前三種)仔細讀過了一遍,你大概不會反對我稱他為‘老孩子!”而且茅盾還敏銳地發現:“魯迅的胸中燃著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個‘老孩子!”
魯迅的確是一個“老孩子”,無論是為人還是為文,無論是具象的行為還是抽象的精神。魯迅的“老孩子”精神,究其實質是一種游戲精神。也難怪,1928年創造社攻擊魯迅時,不無貶義地把魯迅屢屢斥為“中國的堂吉訶德”,撇開創造社的立場與觀點,僅就他為人與為文的游戲精神這一面來說,也算是歪打正著了。
在魯迅眾多的“影像”中,為什么要獨獨拈出這一點?因為這才是“元氣”淋漓的本真的魯迅,白象也罷,戰士也罷,好斗者也罷……他的誠與愛、他的種種“搗亂”,都是從這里生發的,都是童心的種子在生活、時代的枝枝丫丫上長出的片片綠葉,這些互不相同的葉片有著同一脈根須、同一種基因。這些在不同鏡面中的不同成像,都源自于同一個“老孩子”在種種不同語境中的不同反應,與在種種不同價值立場、文化立場中的被反映。在這里,魯迅的“老孩子”精神或曰游戲精神是“源”,他為人、行事的方式與文體風格是“流”。
難怪有人說魯迅很好玩,因為他是個“老孩子”,他是文化人類學者赫伊津哈筆下的“游戲的人”,他是一個近乎于席勒游戲理念中所謂“完整的人”,他是先哲所說的大智慧者心靈狀態宛若嬰兒般的人。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對魯迅內心的黑暗、痛苦、緊張與焦慮作了過多的甚至是過度的解讀與強調,忽視了生活、創作可能給他帶來的愉悅與輕松,忽視了這種愉悅輕松對內心可能存在的緊張與焦慮的緩沖和稀釋。康德說:藝術是一種自由的游戲。弗洛伊德說:文學是一種精神的游戲。那么,處于創作狀態的魯迅,其內宇宙一定是緊張而又舒展、豐盈、自由、快樂的吧。那種享受,非外人所能輕易體味。當然,魯迅創作的出發點都是嚴肅的,但其寫作過程或作品本身卻充溢著游戲性,何況魯迅天性就是一個富于智慧與幽默的人。從個體生命的角度說,他的這種寫作、生活姿態讓人覺得似乎才是一個知識分子真正應有的心態。
魯迅日記里的吃食
某個紹興特產,堂而皇之打著“魯迅最愛”的旗號,可見,魯迅的吃,是大大的有名的。一個時刻準備舉起匕首、投槍的金鋼戰士,一個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經常怒發沖冠的鋼鐵英雄,居然也是個“吃貨”。
在《朝花夕拾》中,魯迅曾這樣說:“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魯迅愛吃,卻并非山珍海味大魚大肉,自家吃的菜和普通市民沒什么區別,常常只是“老三樣”,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筍炒咸菜,一碗黃花魚,用蕭紅的話說“簡單到極點”,只有有客時,才會豐盛一些。讓魯迅情有獨鐘的,是零食,尤其是甜食。當魯迅還是周樹人時,這個嗜好就已經養成了。在日本留學時,周樹人特別青睞一種叫“羊羹”的茶點,這羊羹與羊肉無關,而是“用小豆做成細餡,加糖精制而成,理應叫‘豆沙糖才是正辦”。回國后,周樹人思之念之,不惜托人從日本漂洋過海寄來食之,有日記記載:“午后得羽太家寄來羊羹一匣,與同人分食大半。”以為樂趣。
周樹人那個著名的胃還甚喜水果。飯后出去喝茶,喝完茶又“步至楊家園子買葡萄,即在棚下啖之”。難以想象,令敵人聞風喪膽的革命家也曾買完葡萄急不可耐地站于街市大吃特吃,這是不是讓人忍俊不禁?魯迅日記還有記載:“夜作書兩通,啖梨三枚,甚甘。”一口氣吃下三個梨,真叫人替他的胃擔心!魯迅愛吃水果,在朋友中應是很有名的,有次上街買日本產的青森蘋果,遇到日本朋友,遂“強贈一筐”,魯迅樂呵呵攜之而歸。
正如周海嬰所言,或許是政治需要,魯迅的形象一直被塑造為“橫眉冷對”,其實他也有著溫和、慈愛,甚至孩子氣的一面。1926年,魯迅作《馬上日記》,爆料了吃柿霜糖的情節:有朋友從河南來,送給魯迅一包方糖,魯迅打開一嘗,“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迫不及待地吃起來。許廣平告訴他這是河南名產,用柿霜作成,性涼,如果嘴上生些小瘡之類,一搽便好。“可惜她說的時候,我已經吃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余收起,預備嘴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收是收了,可是這美味卻讓魯迅惦記著,以至夜里都睡不著,實在忍不住,爬起來又吃掉大半。“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如此率真可愛如孩童,讀罷令人莞爾。
魯迅愛吃點心,除了買來送給母親,好客的他也經常招待客人同吃,不過這招待,卻是男女有別。最初,魯迅是一視同仁的,誰料先生們戰斗力實在太強,漸漸地,這些“光盤族”讓魯迅有了戒心,開始算計起來,不得已以落花生取代。女士就無妨了,“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這損失,微乎其微,魯迅樂得送個人情。
對零食的青睞,讓魯迅不僅屢以記載,還在雜文中對點心的來龍去脈、演變歷史娓娓道來,如數家珍,《零食》一文中所述“那功效,據說,是在消閑之中,得養生之益,而且味道好”,更為他喜歡零食找到了理論依據。
然而,魯迅病了,“什么都吃不落”,連茶也不愿意吃,況零食乎?許廣平端到樓上的方盤,去時滿滿的,半小時后,又照原樣一動沒有動地端下來了。“我們都是馬二先生,吳敬梓寫馬二先生那么饞,吳敬梓自己一定很饞的”,魯迅這個很饞的“馬二先生”的舌尖終敵不過肺病的折磨,1936年10月19日,戰士魯迅工作完了,休息了,放下他的匕首,只留下嗜好零食的鄰家周大哥供后人去瞻仰。
“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魯迅是個“老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