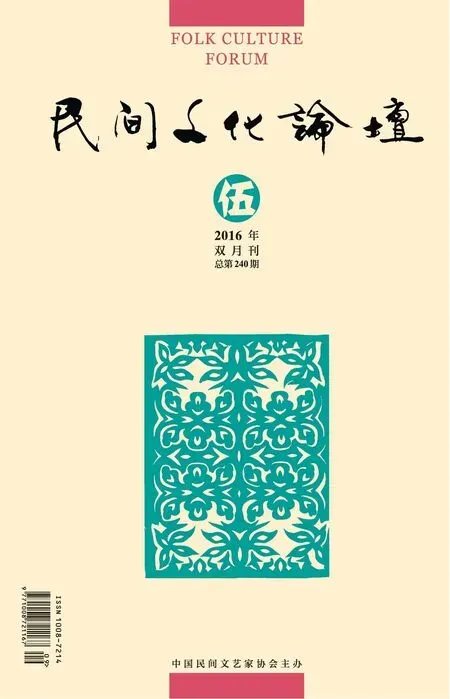多元文化發展與跨文化對話
樂黛云
多元文化發展與跨文化對話
樂黛云
一、多元文化的發展及其當前遇到的問題
(一)《查理周刊》事件引起的思考
歐洲《查理周刊》的事件引起人們心里很大的震動! 到底這個世界的前景會怎樣、未來會怎樣?從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講 “文化沖突”到現在,似乎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反而好像是越來越壞了。在我們中國人看來, 恐怖分子殺人固然不對,侮辱別人的宗教也不對。如何才能把雙方協調起來呢?這就需要多元、和諧等觀念,需要承認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有自由的思考,可是現在已經不太可能這么做了,問題越來越尖銳,而且更為嚴重。
不同文化的接觸越來越多,如何對待多元文化引起的紛爭已經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以移民問題為例,首先是歐洲不能沒有移民,研究者們得出結論,歐洲將必須每年招募一百多萬移民,才能相當于歐洲女性平均生育一個以上的孩子。僅僅是德國就必須在未來的三十年里每年迎來五十萬年輕移民(這個數字相當于它的生育率的兩倍),才能避免人口數量的巨大滑坡。 不同文化體系之間人們的通婚提出了更復雜的問題。如果說在1960 年的德國,只有1.3% 的新生嬰兒有外國父親或母親,那么,1994 年,卻有18.4% 的新生嬰兒都有外國父親或母親,這種趨勢今后還會有增無減。近兩年中國廣州也出現了50萬人規模的非裔移民潮。不同文化的婚姻雖然開啟了不同文化間新的溝通渠道,彌合了某些文化鴻溝,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某些文化的衰亡感,并導致對外國人更加充滿敵意的文化壓制和報復,《查理周刊》事件只是一個結果。
事實上,如果不能實現多元文化共生,那就只能實行文化一元化的文化霸權和文化單邊統治,這是美國一向所追求的。他們希望用自己的文化覆蓋其他的文化,例如在伊拉克強行實現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在一些國家煽動所謂“顏色革命”,其結果都是適得其反,引起更大沖突。
(二)文化沖突的加劇與對多元文化發展的疑慮
在未來數十年內沒有移民洪流涌入,歐洲將會老化,歐洲的經濟計劃將會衰退;但另一方面,移民潮又將威脅,甚至壓垮已經十分緊張的政府福利預算和人們自身的文化認同感。如何公平合理地對待移民就成了嚴重問題。他們沒有經濟能力給移民和本地人同樣的福利待遇,又認為你既然到了我們國家,就應該遵守我們的文化、生活,風俗、習慣,而不能保留你原來故土的一切。我自己在巴黎時,有一件事使我很有觸動。按照伊斯蘭風俗,在巴黎上學的伊斯蘭小女孩也必須像在家鄉一樣,帶上頭巾。可是校長卻認為在校學生應該按法國學校的規定穿制服,不能戴頭巾。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甚至游行抗爭。其實按照多元共存互禮互讓的中國中庸原則,通過對話,問題并非不能解決。
但是一元化單邊統治在全世界仍然占統治地位,其結果必然是失敗的。多元文化共處是世界無法避免的前景。但是多元思想如今遇到了很大的危機。特別是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有些領導人,包括默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等比較開放的領導人,都表示“多元主義實際上是失敗了”。 默克爾認為,在他們的國家如果允許這么多移民遷入,而不使之融入當地社會的話,那爭斗將無法停止。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的領導人也承認了多元主義的失敗。但是,這些國家由于勞動力缺乏和老齡化的壓力,不能沒有移民!如何公平合理地對待移民就成了嚴重問題。只有跨文化對話方法才能解決這一問題。
(三)建構多元文化共存的命運共同體
我們反對文化單邊統治,也反對文化原教旨主義, 我們必須努力建構多元文化共存的命運共同體,既避免原教旨主義引起的文化沖突、又要避免單邊統治、一元化征服,壓制他種文化,引向戰爭,而跨文化對話是必由之路。 “修身”“齊家”“治國”,最后是“平天下”, 這個“平天下”跟原來帝國主義統治全球的譜系是很不一樣的。中國現在有很多人認為中國要強大!什么叫“強大”?他們認為“強大”就是要像過去的“羅馬帝國”“日本帝國”“不列顛帝國”一樣……走它們的老路,用強力統治其他民族和地區。這就是一元化思想。美國哲學家安樂哲認為這不是中國的傳統。他認為習近平在許多場合都強調了多元性,強調了互相學習和包容。他認為中國現在在非洲的政策很好,是讓他們做他們自己。
二、多元文化對話的幾種方式及其結果
多元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必由之路是跨文化對話,但這種對話會遇到一些悖論,主要有以下幾種。
普遍與特殊的悖論。有些人認為普遍性籠罩一切,沒有強調特殊性,也就沒有對話的必要;有些人認為只有特殊性,根本沒有對話,沒有相互理解的可能。例如后現代思潮不承認普遍性,認為一切被指為“普遍”的東西多是獨斷的、僵化的,并有強加于人的暴力傾向;他們反對任何結構性的制約,認為不存在中心,也沒有所謂普遍性,只有互不關聯的特殊性。他們認同 “無深度概念”,消解一切現象與本質,必然與偶然、普遍與特殊、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系(所謂能指的漂浮),使一切事物成為既無時間連續,又無空間相關性的孤立個體,他們只強調差別而忽視聯系,只承認個別而反對一般。文化孤立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都是如此。這就取消了對話的必要。必須承認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承認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對話才有根據。
保持純粹與互相影響的悖論。一方面是全球化(趨同),另一方面是多元化(離異),認同趨勢現在仍很強大,因為科技的一體化和人為的文化霸權單邊統治相一致;另一方面,堅持文化多元的趨勢也十分頑強,其極端就是文化原教旨主義。這就存在一個悖論:要保存文化的多樣性,那當然是每種文化越純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間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滲透吸取,這種滲透交流的結果是不是會使世界文化的差異逐漸縮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從歷史發展來看,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吸收總是通過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來進行,也就是要通過自身文化的過濾,很少會全盤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得到很大發展,但在印度曾頗為發達的佛教唯識宗,由于其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抵觸過大,就很難得到傳播和發展;又如陳寅恪所指出的:由于與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諸要義”的部分,“縱篤信之教徒,亦復不能奉受”,“大抵噤默不置一語”,“惟有隱秘閉藏,禁止其流布”①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5頁。。法國象征派詩歌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詩歌的影響亦復如是。當時,蘭波、凡爾侖的詩歌被大量譯介,而作為法國象征主義詩歌杰出代表的馬拉梅在中國的影響卻絕無僅有。金絲燕的《文學接受與文化過濾》一書對此有深刻的分析。這些都說明了本土文化在文化接觸中的一種最初的選擇。同時,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動地移植。一種文化被引進后,往往不會再按原來軌道發展,而是與當地文化相結合產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輝煌的結果。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傳入西歐,成為西歐文化的基石,這是一種嶄新的文化,與原有的母體文化已有很多不同。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原有的文化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臺、華嚴、禪宗等;這些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又成為中國宋明新儒學發展的重要契機。這種文化異地發展,滋生出新文化的現象,在歷史上屢屢發生。實際上,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和吸收不是一個“同化”“合一”的過程,而是一個在不同環境中轉化為新物的過程。在不同選擇、不同條件相互作用下創造出來的新物,不再有舊物原來的“純粹”,但它仍然是從舊物中脫穎而出,仍然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獨特之處,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結果并不是“趨同”乃至“混一”,而是在新的基礎上產生新質和新的差異。當然,這并不排斥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人們會逐漸形成某些共同的價值標準,但即使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共同標準在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也還有其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現形式,在普遍性中體現著原有的特殊。
對話中的自我與他者。在對話中我們總是從自我出發,總想同化對方,說服他同意我的方案,接受我的想法,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犧牲對方的特色而趨同。這就是過去的打通思想,我打你通。中國人相信不同的東西可以凝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一體”,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和能生物,同則不繼”。“和”就是協調不同的人和事,使之在參差不齊中,和諧發展(并非融合為一)。如《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幫”。協和萬幫就是要使各有特色的多種文化和諧共處,而不是融為“一幫”。融為“一幫”就是“同”,而不再是“和”;對話的結果是產生 “使物豐長”而發展的新的“和”,而不是“以同裨同,盡乃棄矣”的那個“同”。因此,勒維納斯特別強調,應該從他者出發,關注他者最不清楚,甚至最不可能理解的那一面。這樣,在與他者相觸的過程中,就不會順應岔路中你自身的欲望,將你推向你思索中的局限,而是引向你所不知道的另一個新的方向。勒維納斯認為:“與我相遇的是處處超越我,能夠從他那里得到新觀念的他人,是不會封閉于任何知識之中的他人。”②勒維納斯(E.Levinas):《整體與無限》,參閱《跨文化對話》第7輯,第29頁。總之,“他者”是我所“不是”,不是因為他的性格、外貌和心理的特色,而僅僅是因為他的相異性本身。正是由于這種相異性,“我與他人的關系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融合’,而是一種‘面對面’的關系”③勒維納斯(E.Levinas):《 時間與他人》,參閱杜小真《勒維納斯》,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然而,只強調相異性,就很難達到理解和溝通的目的,不強調相異性,又會發生混同融合等情形。但如果“取消他者性,這將是模糊的單一和沉默”。
差異與間距。在跨文化對話中,差距之外, “間距”或“之間”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差異建立在分辨(distinction)的基礎上,它需要一個共同的前提。間距則來自距離(distance)。例如要分辨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就得把它們想成是屬于一種更普遍的類型(家具類)。間距沒有共同歸屬的問題,它不需歸類為范疇,而是當下的對看。間距的形象不是整理排列存放,而是打擾。例如,若說椅子是可以充氣的,它所凸顯的就是一種完全新的想法,打亂了原來的差別分類。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稱之為“有孕育力(f é condit é)”,即有生產力的(productive)。間距不像差異那般緊抓著認同,差異是按照一種認同視點而進行的,那是在所謂的多種特征當中選取同和異凸顯出來而彼此有別。間距是在“對看”之中,內部發展當中發現其 “異質性”(l’h é t é rotopie)。亦即突出一種思想為了自我確立而與其他的思想分別的特殊分叉之處。研究這個“分叉之處”是一切預見,也是創造和新思想的開始。于連舉了一個例子:蘇東坡說:“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畫工往往只捕捉到馬的外在特征,但馬所具有的俊發之氣全都消失了。可見馬的氣質并不在皮毛之間,但又要有摸得到的事物——有形有體——才能使俊發之氣穿越而顯現。故清人方薰(懶儒)說“然舍鞭策、皮毛,并無馬矣”,因此,俊發之氣,“莫非鞭策、皮毛之間耳”。于連認為方薰強調的不是本體而是非本體的流動的“之間”。這正是中國藝術最根本的“氣韻生動”。歐洲現代派畫家們早在哲學家們之前也從事去本體論的嘗試。布哈格(Braque)說:“在蘋果和盤子之間的,也畫了,甚至這個‘在兩者之間’在我看來也跟他們所謂的‘客體’一樣重要。”
中國道家哲學強調一切事物的意義并非一成不變,也不一定有預定的答案。答案和意義形成于千變萬化的互動關系和不確定的無窮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種機緣,多種可能性中的一種變成了現實。這就是老子說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簡作“有狀混成”)。一切事物都是從這個無形無象的“混沌”之中產生的,這就是“有生于無”。“有”的最后結局又是 “復歸于無物”。“無物”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這“無物”“無狀”并不是真的無物、無狀,因為“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這“象”和“物”都存在于“無”中,都還不是“實有”,它只是一種在醞釀中的無形無象的、不確定的、尚未成形的某種可能性,它尚不存在而又確實有,是一種“不存在而有”。這就是“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的道理。也就是于連所說的“尚無主體性”的不確定的流動主體。因此,從中國道家的宇宙觀出發,最重要的就不是拘泥于人們以為是“已定的”,其實仍在不斷變化的“確定性”,而是去研究當下的、即時的、能有效解決問題的、從現實當中涌現出來的各種不確定性中的可能性。只有向“未知”進發,才能創造新路,一切都已固定的,只能是老路。這也就是《黃帝內經》所說的已成形的“已病”和尚未露跡象的“未病”的關系。而上述《道德經》中論述的 “惚恍”和“不存在而有”的宇宙觀,與當今的混沌科學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混沌七鑒——來自易學的永恒智慧》一書的作者指出:“《易經》對我們特別有啟示。混沌的科學思想源于研究人員對氣象學、電路、湍流等復雜物理系統的研究。很明顯,《易經》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長期深入思考過自然界和人類活動中的秩序和無序間的關系,他們最終將這種關系稱為‘太極’。”又說:“歐洲、美國、中國的社會正處在一個巨變的時代,正如過去《易經》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樣,此時此刻人們正試圖洞察個體與集體的關系,尋求永恒變易中的穩定。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來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產生出巨大能量的時代。當代世界的社會狀況類似于物理系統中的非平衡態。新的相對穩定和意外結構有時會突然產生。或許,當未來社會朝我們未曾指望的方向發展時,混沌科學會幫助我們理解所發生的一切。”①[美]約翰·布里格斯(J.Briggs)、[英]戴維·皮特(F.D.Peat):《混沌七鑒——來自易學的永恒智慧》,陳忠等譯,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
最后,我想用弗朗索瓦·于連的話來結束我此文。他說:我不主張匯合所有文化,也不主張在一切文化當中進行篩選,從中選取最小的共同點,作為眾文化之間的共同基礎。聯合國教科文基金會(UNESCO)近幾年來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毫無成果——我們應該反省這個失敗。因為,正如共同之處只能通過間距才發揮作用,文化的本性在趨向同質化(s’homog é n é iser)的同時也不停地異質化(s’h é t é rog é n éiser);在趨向統一性(l’unification)的同時也不斷地多元化(se pluraliser);在趨向融合與順應(se confondre et se conformer)的同時也不停地標示自身的特色。去認同而再認同(de se d é marquer, de se d é sidentifier et de se r é identifier);在趨向自我提升到主流文化(s’é lever en culture dominante)的同時也不斷地讓異議發揮作用(d’ê tre travaill é par la dissidence),這就是為何文化肯定是復數的,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不過是典范例子,我們今天要一起思索這兩種文化的“面對面”。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為了避免張冠李戴的錯誤和“差不多”的領會,也為了避免使我們相信我們通過現在的標準化語言可以完全彼此理解的錯誤,我們必須真正理解佛菩薩所說:“我為爾道是第二義。”也就是說,用語言說出來的已不是我心中原來所想的原貌,因為已經過了語言的歸納、編排和改造。人們卻往往忽略了這第一義與第二義的重要差別而以為大家的共同用語表現著共同的思想和意義,傳遞著分歧的含義而渾然不覺。
[責任編輯:馮 莉]
G122
A
1008-7214(2016)05-0010-05
樂黛云,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