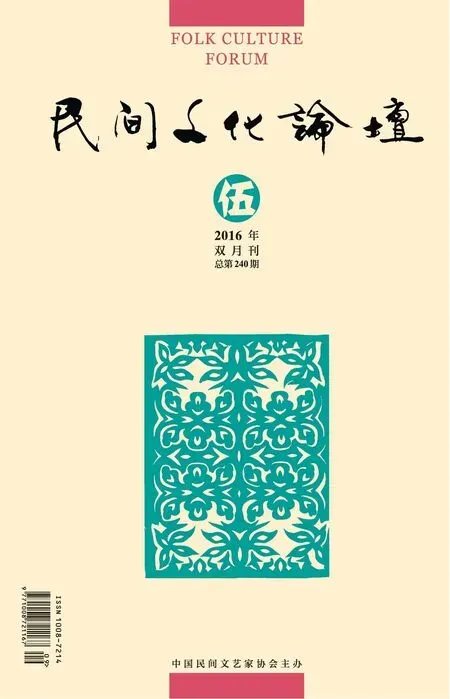民俗學視角對敦煌藝術研究的新洞見—評鄺藍嵐新著《敦煌壁畫樂舞》
張 多
民俗學視角對敦煌藝術研究的新洞見—評鄺藍嵐新著《敦煌壁畫樂舞》
張 多
敦煌學(Dunhuangology)作為一門國際顯學,發端于1920年—1930年。伴隨著世界范圍內對來自敦煌洞窟文獻、文物研究的熱潮,中國國內學術界開始認識敦煌學。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先生所編《敦煌劫余錄》所作的序中,闡述了“敦煌學”的概念。近百年來,敦煌學領域在大批中外一流學者的建設下,成就斐然。在這樣厚重的學術積累之下,后學要想在此領域出新,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鄺藍嵐(Lanlan Kuang)博士為美國華裔青年學者,于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民俗學與民族音樂學系(Department of Folklore and Ethnomusicology, IUB)①Ethnomusicology一詞,鄺藍嵐翻譯為“音樂人類學”,但按照中國學界通行譯法,常譯為“民族音樂學”,本文采取后一種譯法。獲得博士學位。2012年,她的博士論文Staging the Cosmopolitan Nation: The Re-creation of the “Dunhuang Bihua Yuewu”, a Multifaceted Music, Dance, and Theatrical Drama from China (《盛世中國:中國多元化敦煌樂舞之重塑》)在美出版,同時出版了同名紀錄片。鄺藍嵐在碩士階段受訓于印第安納大學民俗學與民族音樂學系,她2004年完成的碩士論文As Time Unfold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Folk Song “Liuyeliu” through Intertextual Processes and Multimedia Representation就選取了中國山西寧武民歌作為田野研究對象。碩士畢業后,鄺藍嵐因選取了敦煌壁畫和樂舞藝術作為主攻研究領域,開始了長達八年對敦煌壁畫、歷史和樂舞的田野研究、訪學和紀錄片拍攝。
2016年,鄺藍嵐在結合博士論文完成后四年時間的追蹤研究,翻譯并修訂了英文版博士論文,以《敦煌壁畫樂舞:“中國景觀”在國際語境中的建構、傳播與意義》的標題,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一、敦煌藝術研究的新視域
敦煌學研究雖然集中了國際上許多一流的學者和團隊,但是由于涵蓋范圍廣,具體的微觀論題研究上仍有許多薄弱之處。鄺藍嵐敏銳地看到,在基于敦煌壁畫樂舞資源的現代創編、表演、傳播方面,鮮有研究力量介入。作者將研究的領域框定在“敦煌表演藝術”,尤其關注將中國古典美學和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相結合,將敦煌壁畫樂舞表演視為當代中國文化軟實力進行系統分析,并且通過拍攝紀錄片,親身實踐這種表演藝術傳播與展示的過程。
鄺藍嵐在經過長期田野作業之后,將敦煌壁畫樂舞在現代語境、國際語境中的建構、傳播歸納為“自我指涉性敦煌元元素系統”(self-referentail system of Dunhuang meta-elements),進一步簡稱為“敦煌元系統”
在中文修訂版中,鄺藍嵐進一步區分了敦煌元系統中的“展示性傳播內容”和“隱性論述性內容”。“展示性傳播內容”主要指敦煌壁畫、雕塑中體現的樂舞服飾、造型、場景等直觀視覺圖景,以及根據遺跡圖景發展出來的現代敦煌舞臺美學。“隱性論述性內容”則是敦煌樂舞在哲學層面的詩學、審美和東方意象。在這樣的研究思路下,作者跳脫出了敦煌壁畫、雕塑、古代樂舞文獻的釋讀與考證,將目光聚焦于現代中國古典舞“敦煌舞派”的藝術實踐,從一個當下的田野現場,觀察敦煌藝術再語境化(recontextualize)之后的藝術景觀。
鄺藍嵐重點跟蹤調查了西北民族大學的高金榮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董錫玖教授。高金榮教授是古典舞重要流派敦煌舞派的創始人之一,她在西北民族大學舞蹈學院(前身為舞蹈系、音樂舞蹈學院)深耕數十年,培養了大批優秀的舞蹈家,開創了學院派創編、傳承、教學、科研、表演敦煌舞的模范樣例。在西北民大,敦煌舞的表演、欣賞蔚然成風。敦煌藝術與蒙古、回、藏、維吾爾、裕固等民族的音樂舞蹈藝術共同交織,塑造了西北民大獨特的校園文化景觀。①筆者畢業于西北民族大學,對敦煌舞派的教學、表演、校園文化深有體會。西北民大多元文化的在高先生等一批甘肅藝術家的努力下,敦煌藝術的演藝產業也成為甘肅的文化品牌,《絲路花雨》《千手觀音》等劇目還上升為國家文化的標志性作品,在國際舞臺上演。這是敦煌藝術在當代傳承、傳播的重要事實,但是以往的敦煌學研究并未充分關注敦煌藝術的當代生命力問題。鄺藍嵐不僅跟隨高金榮先生學習基本舞姿,還使用先進數碼手段對敦煌舞的教學、表演進行非線性記錄與呈現。這種參與觀察、非線性攝錄、訪談、文獻與洞窟考察相結合的田野研究方式,保證了作者“從洞窟到舞臺”的研究預設得以實現。
在鄺藍嵐的研究中,關鍵的問題是分析現代敦煌舞的姿態、舞美、音樂、編導如何將壁畫中的視覺資源轉化為與敦煌壁畫樂舞一脈相承的現代藝術景觀。因此,她嘗試借鑒音樂景觀(soundscape)、表演理論(performance studies)、民族志詩學(ethnopoetics)、民族音樂學、軟實力理論、中國古典美學等多種理論視角,試圖盡可能細致地分析從洞窟壁畫到現代舞臺的轉化過程。這些理論方法深受印第安納大學民俗學學術傳統的影響,也是敦煌學研究在方法論層面上的一次嘗試。
二、民俗學視角為敦煌藝術研究帶來的新洞見
《敦煌壁畫樂舞》是一部注重理論視角的著作,作者的學術訓練背景主要繼承了印第安納大學民俗學與民族音樂學系的傳統。該系是世界民俗學與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重鎮,與中國民俗學界長期保持學術交流關系。當然,鄺藍嵐著作所選取的理論方法不僅限于民俗學,兼有民族音樂學、人類學、傳播學、藝術學、政治學、美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方法。但是限于筆者的專業背景,對其在民俗學理論方面的運用感受較深,因此本文將著重評論其民俗學理論的探索。
鄺藍嵐在該著中使用的民俗學理論方法主要是表演理論和民族志詩學。她力圖在呈現、描寫敦煌壁畫樂舞在當代語境中表演、展示的過程中,注重“語境”因素對舞蹈語言交流產生的影響,十分注
校園文化環境,與敦煌文化本身的民族文化多元特征相吻合,而這一點也是鄺藍嵐著作所強調的。意將研究本身作為一種交流框架,從而探究敦煌舞實踐的意義。這一部分研究,將表演理論和民族志詩學所擅長的口頭藝術研究,拓展到舞蹈和舞劇的研究中,較好地探索了表演理論和民族志詩學的理論張力。但這一部分研究僅僅是全書的一個分析環節,全書的主要脈絡仍是要探究敦煌壁畫樂舞的現代建構與傳播,探究“中國景觀”發生成立的機制。作者宏觀的追求是要研究敦煌藝術作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標志性項目,其發生發展過程中如何通過表演語境的轉化,從而產生國際影響,塑造中國形象。
但正是這樣的宏觀追求與主要脈絡,深深烙印了美國民俗學20世紀后半葉發生轉變的學術思想。美國民俗學在20世紀前半葉一度盛行“歷史-地理”和比較的方法,但其研究在20世紀后期逐漸偏向實踐的研究,也即關注民俗個體、事件、行動、語境、當代建構和公共文化。口頭藝術的研究也越來越注意其與社會、文化政治、公共生活、戰爭、性別、商業、文化遺產等議題的聯系。鄺藍嵐在書中提到的幾位民俗學家,如羅杰·吉奈里(Roger Janelli)、查爾斯·布里格斯(Charles L.Briggs)、芭芭拉·科申布萊特-吉布麗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等,都是十分注意將口頭藝術、民俗文化、日常生活放置在特定語境中研究,注重對文化變遷、交流、傳播與展示的追蹤。
鄺藍嵐的著作秉承美國民俗學、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特色,有效闡釋了敦煌樂舞的建構歷程,分析了從洞窟、壁畫到舞臺、劇目的文化景觀形成機制。書中對現代敦煌舞姿態與壁畫人物姿態創編關系的分析頗為精彩。鄺藍嵐采訪了董錫玖教授對舞姿的觀點,梳理了前輩藝術家對“飛天”的舞臺化實踐,最后請高金榮教授為自己示范敦煌舞的基本姿態。這些“典型姿態”是高先生研究壁畫人物,經過長期舞蹈實踐總結出來的。為便于教學,高先生將這些姿態逐一命名,比如手部姿態的靈感多源于千手千眼觀音像,有合掌式、平托式、佛手式、抱笙式等。進而鄺藍嵐結合壁畫與佛教文獻分析了不同時期佛教壁畫中的體態特征,同時也注意到南亞舞蹈、南傳佛教藝術對敦煌舞姿態創作的影響。最后作者選取《千手觀音》來分析這些舞蹈姿態如何被塑造成為舞臺的景觀。這種基于田野作業的研究,不僅體現了民俗學關注語境、關注傳承個體的理論特色,也使得作者在敦煌壁畫樂舞的實踐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
民俗學理論對敦煌藝術研究最大的啟示意義,在于倡導“朝向當下”的敦煌藝術研究,倡導實踐的研究。當代民俗學理論注重文化傳承、文化媒介等的視角,注重對個體、事件、語境、過程的實踐研究,而這些對敦煌藝術的現代生命力而言無疑是重要的議題。鄺藍嵐的著作較好地示范了如何進行敦煌藝術傳承的當代研究,如何對壁畫樂舞的創編和敘述進行研究。
三、多學科理論融匯的探索
該著作將不同領域的理論用于闡釋敦煌壁畫樂舞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地理概念在國際語境中的特殊位置,闡釋敦煌壁畫樂舞依附時空的詩性美學被激發重塑的過程。這些理論對敦煌學研究來說是一次全新的嘗試。敦煌文化博大精深,其藝術內涵之深廣,對研究者的廣博與專精都有極高要求。鄺藍嵐的研究大膽嘗試多學科前沿理論與方法,無疑為敦煌藝術研究的理論創新做出了探索。
該著作在分析“敦煌元系統”概念時,主要運用了元理論、認知科學的思想與方法,在這基礎上探討作為軟實力的“中國景觀”如何得以建構。作者論述敦煌的語境重置問題主要借鑒人類學景觀概念、藝術表演景觀概念,細化了“中國景觀”的具體細節分析。作者還積極借鑒民族音樂學、表演理論和民族志詩學來分析敦煌樂舞的表演實踐。這些來自相鄰學科領域的理論在闡釋具體問題時都發揮了各自的專長,也顯示了作者扎實的理論訓練。
以表演理論為例,鄺藍嵐區分了21世紀的四種表演研究范式:劇場表演學、人類表演學、口頭表演學、社會表演學。作者重點介紹了理查德·鮑曼和戲劇家理查德·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的兩種表演觀。鮑曼的表演觀注重交流(communication),倡導民俗學研究從事象(item)轉向事件(event),最終指向民俗的實踐。后來露絲·斯通(Ruth M.Stone)將這種表演觀用于音樂表演的田野研究。謝克納的表演觀則是從戲劇出發的,他將舞臺藝術從劇本排演的窠臼中解脫出來,重視環境戲劇實踐中的語境塑造。他提出的人類表演學在戲劇學界影響深遠。鄺藍嵐抓住了兩種表演觀都重視交流的特征,致力于特定語境中的事件研究。雖然兩種表演觀有理論出發點的較大差異,但鄺藍嵐基本做到了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就敦煌壁畫樂舞本身的特點而言,壁畫人物飄逸、飛升、靈動的特色十分突出。敦煌舞演繹飛天,正是將這一特點通過傳統綢舞表現出來。鄺藍嵐注意到了用綢舞表演飛天的早期歷史,試圖抓住敦煌壁畫人物飄逸藝術特質,闡釋從宗教壁畫形象到舞臺表演的美學過程。宗白華先生曾指出敦煌藝術“以人物為中心”是其獨步中國藝術史之處,壁畫彩塑人物“全是在飛騰的舞姿中”,人像的重點在于其克服了地心引力的飛舞旋律。敦煌之藝境全以音樂舞蹈為基調。①宗白華:《略談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1948年。收入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因此,將“樂舞”放置于敦煌人物藝術的整體風格中,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前提。鄺藍嵐將這種藝術美學特征融入到對舞蹈家著力表現輕盈體態的分析中,揭示了“中國景觀”建立的核心性藝術要素。
盡管該著作在多學科理論融合方面還需進一步打磨,但是瑕不掩瑜。這一著作不僅將民俗學、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到一個新的領域,反過來推動了敦煌學研究朝向當下的進展。作者選取這一重大論題的勇氣,多年來田野作業的辛苦,都使這一著作具備了啟迪讀者、提出問題、引領方向的特質。
(鄺藍嵐:《敦煌壁畫樂舞:“中國景觀”在國際語境中的建構、傳播與意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Kuang, Lanlan: Staging the Cosmopolitan Nation: The Re-creation of the “Dunhuang Bihua Yuewu”, a Multifaceted Music, Dance, and Theatrical Drama from China, ProQuest.UMI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2012.)
[責任編輯:王素珍]
K890
A
1008-7214(2016)05-0117-04
張多,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Dunhuang meta system)。在這個機制下,敦煌壁畫樂舞作為一個元認知、元文化的有機體,從古老的洞窟中走出,在現代社會的舞臺、媒介中煥發出生機,為世界展示了一個蘊意厚重的“中國景觀”(Chinasc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