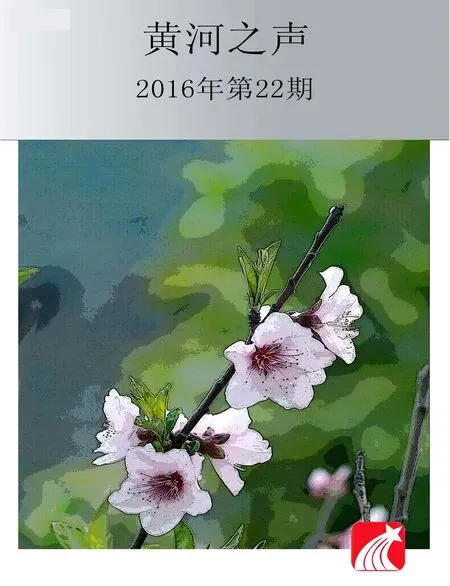東西吟月 各顯珠暉
——對《“月光”奏鳴曲》、《月光曲》、《二泉映月》的比較分析
廉 瑩
(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東西吟月 各顯珠暉
——對《“月光”奏鳴曲》、《月光曲》、《二泉映月》的比較分析
廉 瑩
(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古往今來,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月一直是詩人、畫家、音樂家熱衷吟詠描繪的對象,比如我國唐代大詩人李白的《靜夜思》、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月之愁》、俄國畫家克拉姆斯柯依的世界名畫《月夜名畫》等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國度、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都通過觀察與想象,借“月”抒懷,表達思想。也有通過具體的語言文字直接描繪月光與月色,比如我國著名作家巴金的《家》中對滿月的描述,足見月之魅力。本文通過對三首著名的中外音樂作品《“月光”奏鳴曲》、《月光曲》、《二泉映月》的比較分析,從無國界的音樂語言表達之中體會音樂風格、人文思想與精神內涵,進一步闡釋東西方音樂文化觀與音樂價值觀的樹立等問題。
“月光”奏鳴曲;月光曲;二泉映月;音樂價值觀
一、三首作品的來源及創作背景
鋼琴奏鳴曲《“月光”奏鳴曲》是被稱為樂圣的德國作曲家貝多芬的重要鋼琴作品之一,作品編號op.27的第二首,被命名“月光”奏鳴曲,并非作曲家本人命名。說法不一,有的說法是源于一個美麗的傳說,貝多芬為一位盲女演奏鋼琴時月光灑在鋼琴上而產生的即興創作。還有一種說法是德國詩人路德維希-萊爾什塔勃將此曲第一樂章比作“猶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閃爍的湖面上搖蕩的小舟一般”而來,后者是現在比較通行的說法。
《月光曲》是法國作曲家德彪西創作的鋼琴獨奏曲,作于19世紀90年代,是德彪西較早時期的作品,但已經初步顯露出印象派音樂的風格。德彪西的聲樂作品中還有兩首同名歌曲,用魏倫的詩填詞。
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是我國民間二胡演奏家華彥鈞的代表作。阿炳是華彥鈞的小名,因此也被世人親切的喚作了藝名-阿炳。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和生活背景下,阿炳的一生坎坷流離。這首作品最初無標題,阿炳常常在行街穿巷途中信手拉奏,被他自己稱為“自來腔”,鄰居們稱之為《依心曲》。后來著名民族音樂學者楊柳蔭、曹安和在聽到錄音時聯想到無錫著名的景點惠山泉(被譽為“天下第二泉”),因此得名《二泉映月》。
二、三首作品的結構內涵比較
這三首作品來源于不同的國度、不同的作曲家、不同的音樂創作時期,采取不同的器樂體裁形式和不同的音樂表達方式。但都與一個情景主題有關,那就是“月”。如何將器樂體裁形式與音樂的精神內涵相結合,如何看待不同人生經歷的作曲家對音樂作品精神內涵的表達與理解?以下繼續從這三首作品的曲式結構、旋律節奏、和聲語言、音色色彩等方面來做進一步分析比較。
1、《“月光”奏鳴曲》的曲式是奏鳴曲式結構,三個樂章。第一樂章是持續的柔板(Adagio sostenuto),升c小調2/2拍,采用三部曲式;第二樂章是小快板(Allegretto),降D大調,3/4拍,三部曲式;第三樂章是激動的急板(Prestoa agitato)升c小調4/4拍,采用奏鳴曲式。主題與和聲方面,第一樂章的主題是寧靜夢幻的,主副部沒有明顯的性格對比,持續的三連音音型奠定了音樂的基調,沉靜厚重,仿如月色靜謐。左手持續的旋律線條,音域較低,使得音樂感覺更加深沉。中段三連音獨自歌唱,線條流暢,和聲色彩斑斕,但左手的持續低音,仍然把音樂拉到低沉的陰郁之中。再現部加重了憂郁的氣氛,平靜的第一主題之后,持續的屬音和小調的導音,持續的三連音及下行走向的低沉和弦,凝重的思考漸漸消逝在黑暗里。第二樂章短小歡樂,李斯特曾形容二樂章是“兩個深淵之間的一朵小花”,長句連奏與小連線的交織,跳動的音符似有歡笑,也有撫慰。Trio三聲中部的長音氣息寬廣,宛如大自然中自由的呼吸。第三樂章是奏鳴曲式,在嚴整的形式下,音樂具有令人驚奇的激情,連串琶音構成的主部主題猶如革命的風暴,層層遞進,高音的突強展現了沸騰的熱情,副部進一步加大力量,左手十六分音符仿佛轟鳴的雷聲滾滾,右手的旋律剛強有力,表達出堅強的意志力。展開部短小有力,盡管節奏放緩,表情舒展,但是右手的動機仍然表達了不安與斗爭的熱情。再現部,主部主題規模縮短,副部的樂思繼續被擴展成暴風雨般的琶音,逐步推進到最高峰,但是突然間的休止,仿佛陷入沉寂,似乎思考被打斷,革命力量暫時失敗,但是貝多芬的精神是永不屈服的,最后一段華彩般的上行,終止于八度的低音,沉重的和弦暗示一股永存的精神力量,那份力量是永不磨滅的。
2、《月光曲》是三段體結構,第一段降D大調,淡淡的和聲襯托出輕吟般的旋律,速度舒緩,樂思溫和,調性比較明朗,仿佛皎潔的月光、幽靜的月夜給人們產生的印象。中段轉調到了E大調,短小的樂句和左手分解和弦,像是陣陣輕柔的風,搖曳的樹枝,充滿靈動。第三樂段基本是第一樂段的再現,調性回歸到降D大調,音型略有變化。最后尾聲的部分又再現了開頭的樂思,曲調委婉,分解和弦沉靜流動,如夢如幻的意境,柔美而充滿詩意。中段與第一、第三樂段產生了和聲、色彩、織體方面的對比。加快流動的琶音、重疊的踏板、逐漸交織的和聲,好似搖動的枝葉間、浮動的云際、時緩時急的風纏繞著、交錯著,變幻著,那婆娑斑斕的月色朦朧,使人沉醉。
3、《二泉映月》的結構分為六個段落,包括引子+主題,以及主題的五次變奏+尾聲。引子是下行的短句,帶著嘆息的語氣,二胡音色輕柔、含蓄。接下來是兩個對比鮮明的主題,兩個主題發展采用變奏、衍展手法,第一主題旋律在二胡的低音區,宛轉的吟唱,沉悶壓抑,表現了作者內心深處的郁悶無奈;第二主題利用不斷上行的旋律和多變的節奏,表達了作者的憤懣不甘,對舊社會的強烈控訴。兩個主題做了五次變奏,第一變奏采取將第一主題壓縮,第二主題結構擴充的手法;第二變奏將第一主題結構擴充,第二主題調性離調的發展手法,樂曲情緒逐步激烈;第三變奏節奏平緩迂回,為后面段落推向高潮做好鋪墊;第四變奏繼續將第二主題擴充發展,層層推進;第五變奏以全曲的最低音作為開始,通過反復變奏和力度的大幅度對比,全曲在這一段發展到了高潮。后音調婉轉下行,由揚到抑進入尾聲,旋律與節奏更加輕柔舒緩,令人無比慨嘆,意猶未盡。主題的變奏隨著旋律的發展,時而深沉、時而激昂;時而悲怨、時而抗爭,深刻的展示了作者的辛酸苦悶,以及對現實生活的憤怒控訴。
三、三首作品的文化內涵比較
1、《鋼琴奏鳴曲“月光”》貝多芬的作品受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和德國狂飆突進運動的影響,創作個性鮮明,充滿戲劇性情節和情感表現力。他的創作幾乎涉及到當時所有的音樂體裁,鋼琴的交響性表現力、及交響曲體裁形式的突破與發展是他音樂創作中最重要的成就。32首鋼琴奏鳴曲是貝多芬最重要的鋼琴作品系列之一,這首“月光”奏鳴曲創作于1801年,當時的作曲家曾在書信中提到了自己的耳疾,以及生活中的憂慮和困惑情緒。貝多芬自己稱這首作品為“quasi una fantasia”譯為“像一首幻想曲一樣”,音樂特點直接反映了作曲家一貫的創作風格及當時的情感思想。
這首奏鳴曲在古典音樂時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第一樂章采用自由的三部曲式而非奏鳴曲式,展現其不拘一格的創作精神。音樂組織方式突破,不再拘束于古典奏鳴曲式的平衡結構,弱化主部副部的主題對比性格,更加強調樂思的發展。整部作品的情緒以及強烈的戲劇性沖突,不僅表達了貝多芬的沉思、貝多芬式永不屈服的抗爭精神,更加掙脫了古典主義的典雅情趣,更加注重個人的內心世界的表達。可以說這一切都預示著音樂的情感掙脫形式的浪漫主義音樂語言創作時代的到來,對浪漫主義時代的鋼琴作曲家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鋼琴獨奏曲《月光曲》是德彪西青年時期的創作,當時德彪西的一部音樂作品—康塔塔《浪子》剛剛獲得大獎,得到了許多贊揚。與此同時,德彪西還熱情的結交了歐洲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作曲家們,創作意圖革新、充滿信心,可以說正值他的創作黃金期。本首鋼琴作品采用了大調的調性,音樂整體的氣氛清新明亮,描繪的月色生動明朗。和聲的運用和音樂的形式,引領著人們展開豐富的想象。充滿浪漫色彩的和聲,時而柔美、時而變幻,與豐富變化的演奏技法交織,那云、那月,靈動、飄忽;那景、那境,閃爍,迷人。作曲家用高超的創作技法,為人們展現了一幅浪漫生動的夜月之景,《月光曲》已經初步具有了印象主義的風格。與《“月光”奏鳴曲》比較不同的是,貝多芬音樂營造出的“月光”氛圍只是一種借喻,音樂強調表達的是作曲家的沉思,也可以說是欣賞者的臆斷想象;而德彪西和聲的“月光”是更加真實的,是更加具象的描繪,宛如一幅幅月色時空圖景的展現,是作曲家愉悅心情映襯下所觀察感受到的月色印象。
3、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首先的不同就是演奏樂器,作為弓弦樂器胡琴的一種,若追溯歷史,二胡從唐朝衍變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其獨有的中國風特質和音色特點,使得音樂本身更具有獨特的韻味。二胡具備擦弦、摳揉、壓弦、滾滑等多種演奏技法,能夠表現柔和、纏綿、輕快的美感,也能表現哀婉、悲涼、悲憤的情感。雖然這首樂曲最初的成型并不是阿炳因“月”而作,但樂曲產生于阿炳真實的生活,借寒月之光映襯悲戚之感。正如阿炳的鄰居訴說的--月黑風高,阿炳奔波的賣藝遲歸,慘淡的孤獨身影,冷清的寒夜街道……音樂呈現的辛酸與悲涼,訴不盡的蕭瑟與幽婉,恰如“泉凄月冷”,世態炎涼。
四、結語
通過比較分析,我們看到作曲家的生活經歷不同,個性不同,音樂創作的風格完全迥異,音樂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也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同時音樂也的確具有情感表達的功能,三首有“月”的信息的音樂作品中蘊含的音樂符號所具有豐富的內涵和象征意義。從音樂學分析的角度來看,作曲家對音樂情感表達的手段必然是通過聲音,即通過節奏、旋律、和聲及音色等聲音的要素來實現。而這些音樂符號的背后都具有某種涵義,這些涵義構成作品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傳遞著作曲家的創作初衷和構思想法,引起演奏者和欣賞者情感的共鳴。這個特定的過程:作曲家—創作—音樂符號—認知—演奏(欣賞),圍繞著人進行的音樂活動又進一步發展到了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層面。音樂不僅僅具有審美意義,西方音樂理論學者曾提出的情感美學論、自律論等,認為音樂是一種“自足的藝術”的觀點,是局限的。其實在我們中國的音樂傳統里,也從來不認為音樂是“自足的”,音樂是與宇宙、社會、人生密切相關的。《樂記》中說到“樂者,樂也。”這樣的表述蘊涵了我國民間音樂思想,而無論是民間價值系統還是精英價值系統,都承認音樂具有的教化意義。諸如有云“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
現如今音樂研究學術成果卓著、日新月異,不同的音樂專業領域—作曲家、音樂史學家、音樂美學家等從其不同的專業和觀念范疇作為切入點,自然也會對音樂內涵作出不同的角度與層面的解釋。理解音樂、表達音樂、欣賞音樂、分析音樂等不能僅僅局限于音樂學分析的基礎層面,要在此基礎上,看到不同的文化傳統背景下音樂文化的價值。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的音樂認識、不同的音樂觀念下產生的不同的音樂思想。這些音樂思想推動著理論者、指導著實踐者。這也要求我們要樹立科學的音樂價值觀,音樂觀念必然需要文化觀念的支撐,無論是大文化(文化傳統),還是小文化(專業知識),任何研究與理解、認識與分析,都要建立并放諸于更加開放多元、客觀科學的藝術文化視野之中進行。
[1] 朱秋華.西方音樂史[A].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12.
[2] 鄭興三.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研究[A].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
[3] 林丹.德彪西“月光”的印象主義風格探究[J].藝術百家,2007,S2.
[4] 洛秦著.羅藝峰導讀《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A].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01.
廉瑩(1981-),女,內蒙古呼和浩特人,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鋼琴演奏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