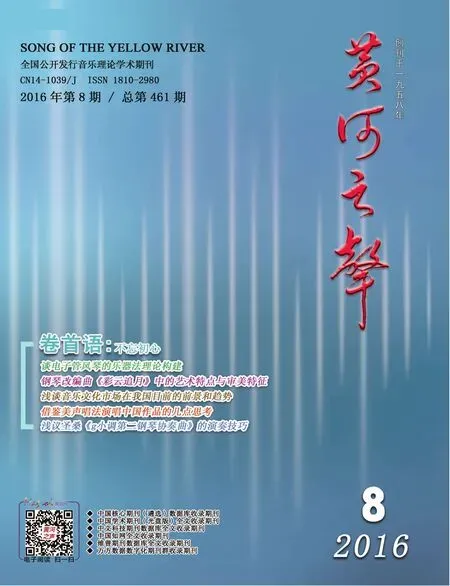嵇康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探討
楊永崗
(信陽(yáng)師范學(xué)院,河南 信陽(yáng) 464000)
嵇康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探討
楊永崗
(信陽(yáng)師范學(xué)院,河南 信陽(yáng) 464000)
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既是我國(guó)歷史上最為混亂、動(dòng)蕩的時(shí)期,同時(shí)也是人類思想史上最為開放自由的特殊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涌現(xiàn)出大量的文人音樂(lè)家,他們借音樂(lè)來(lái)表達(dá)自己的內(nèi)心情感,抒發(fā)自己的理想抱負(fù),而嵇康正是我國(guó)古典音樂(lè)歷史上的一朵奇葩,其音樂(lè)著作《聲無(wú)哀樂(lè)論》被譽(yù)為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典范。本論文以美學(xué)思想為切入點(diǎn),探討了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起源,并在此基礎(chǔ)上剖析了其主要的論斷,進(jìn)而揭示出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獨(dú)特性與深刻性。
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儒家音樂(lè)美學(xué)觀
嵇康(223前后-263前后),字叔夜,后稱嵇中散,魏晉譙郡桎人(今安徽省亳州市渦陽(yáng)縣人),三國(guó)時(shí)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學(xué)家及音樂(lè)家,同時(shí)也是當(dāng)時(shí)文人組織“竹林七賢”的重要成員之一。由于其音樂(lè)思想倍受道教玄學(xué)的影響,因而嵇康提倡擺脫儒學(xué)禮教的束縛,挑戰(zhàn)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回歸自然,進(jìn)而成為我國(guó)古代最早的自然推崇者和人本思想家。其代表著作《聲無(wú)哀樂(lè)論》充分體現(xiàn)出嵇康在多次音樂(lè)實(shí)踐中所積累的美學(xué)思想,這對(duì)后世的音樂(lè)美學(xué)研究有著重要的影響。這篇長(zhǎng)達(dá)萬(wàn)字的論著針對(duì)音樂(lè)的本源和音樂(lè)與情感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進(jìn)行了深入的思考,通過(guò)“秦客”與“東野主人”八個(gè)回合的對(duì)話式辯論,進(jìn)一步提出“聲無(wú)哀樂(lè)”的基本觀點(diǎn),批判傳統(tǒng)的儒家樂(lè)論,凸顯出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內(nèi)涵和本質(zhì)。因此,本論文對(duì)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研究與探討,對(duì)我國(guó)古典音樂(lè)理論的發(fā)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起源
提到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起源就必然會(huì)聯(lián)系到傳統(tǒng)的儒學(xué)思想。準(zhǔn)確來(lái)說(shuō),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是我國(guó)最早的古典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倡導(dǎo)者,其主張美善共存與質(zhì)文并重相統(tǒng)一,充滿了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功利與倫理道德色彩。孔子自身還具備良好的音樂(lè)鑒賞內(nèi)涵與素養(yǎng),例如《論語(yǔ)》有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這就說(shuō)明孔子有著較高的音樂(lè)審美能力。此外,孔子重視音樂(lè)的教化作用和政治作用,并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要力求盡善盡美,由此看來(lái),音樂(lè)對(duì)于個(gè)人的修身立德與社會(huì)的發(fā)展有著責(zé)無(wú)旁貸的使命,例如“子曰:興于詩(shī)、立于禮,成于樂(lè)。”縱觀我國(guó)古典音樂(lè)理論發(fā)展的歷程,不難總結(jié)得出:孔子有力地推動(dòng)了后世儒家音樂(lè)的發(fā)展與進(jìn)步。但是在筆者看來(lái),孔子的音樂(lè)美學(xué)發(fā)展呈現(xiàn)畸形狀態(tài),這是因?yàn)槿寮覙?lè)論中的“形式美”觀點(diǎn)未被繼承,而將音樂(lè)倫理美學(xué)觀推向了高潮,比如儒學(xué)相關(guān)論斷“聲樂(lè)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樂(lè)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lè)肅莊則民齊不亂”,這就說(shuō)明音樂(lè)具有訓(xùn)化泄導(dǎo)功能;《禮記·樂(lè)記》中“治世之音安以樂(lè)、其政和;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這意在表明音樂(lè)具有社會(huì)政治功能;湯作《護(hù)》中“聞其宮聲,使人溫涼而寬大;聞其徽聲,使人樂(lè)養(yǎng)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之恭敬而好禮”,這就將我國(guó)古樂(lè)中的五音階(即宮、商、角、徽、羽)與社會(huì)倫理道德進(jìn)行牽強(qiáng)的結(jié)合。
總而言之,儒家音樂(lè)美學(xué)觀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兩個(gè)極端:其一將音樂(lè)和社會(huì)倫理道德、政治捆綁在一起,力求維護(hù)封建社會(huì)統(tǒng)治,音樂(lè)僅僅發(fā)揮“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的作用;其二是將“天人感應(yīng)”哲學(xué)思想融入到儒家樂(lè)論,使之更為神秘化。時(shí)至嵇康所處的魏晉時(shí)期,民族矛盾和階級(jí)矛盾日益激化、政局頻繁更替取代了漢朝統(tǒng)一的局面,儒學(xué)必然也讓位于玄學(xué),古典音樂(lè)美學(xué)觀點(diǎn)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越來(lái)越多的音樂(lè)家開始探索音樂(lè)藝術(shù)的內(nèi)在規(guī)律和形式美,而嵇康的《聲無(wú)哀樂(lè)論》正是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發(fā)展的產(chǎn)物,其相關(guān)音樂(lè)美學(xué)觀點(diǎn)主要在于對(duì)傳統(tǒng)的儒家樂(lè)論進(jìn)行系統(tǒng)地批判,并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和道德理念不存在任何的聯(lián)系,這也與當(dāng)時(shí)的主流精神是一致的。
二、嵇康的音樂(lè)思想與其作品《聲無(wú)哀樂(lè)論》
(一)嵇康的音樂(lè)思想
作為一種自然的存在,音樂(lè)實(shí)質(zhì)上只是一種虛幻概念的產(chǎn)物,沒有任何的物質(zhì)基礎(chǔ)。然而在嵇康看來(lái),音樂(lè)是一種真實(shí)有“體”的東西。有關(guān)音樂(lè)的來(lái)源與本體,他曾經(jīng)也提出:“天地合德,萬(wàn)物資生。……章為五色,發(fā)為五音”、“樂(lè)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wú)聲之樂(lè),民之父母也”等論斷,根據(jù)此種說(shuō)法,音樂(lè)即是一種精神(和、平和、太和、至和),也是所謂的“無(wú)聲之樂(lè)”。除此之外,嵇康認(rèn)為音樂(lè)的精神作用并非是依靠具體的內(nèi)容使人受到啟發(fā),音樂(lè)與人們的情感無(wú)直接關(guān)系,而是依賴于音樂(lè)本身“和”的性質(zhì)使人受到感染,抒發(fā)心中的喜怒哀樂(lè),比如其相關(guān)樂(lè)論“和聲無(wú)像”、“若資不固之音,含一致之聲”等。上述可見,嵇康音樂(lè)思想的特點(diǎn)在于:將音樂(lè)視為一種虛幻的概念與形式;排除音樂(lè)的現(xiàn)實(shí)存在和其所產(chǎn)生的作用;形式主義和唯物主義的結(jié)合體。
(二)《聲無(wú)哀樂(lè)論》
《聲無(wú)哀樂(lè)論》是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觀的重要著作,該樂(lè)論采用問(wèn)答式的辯難進(jìn)行詳細(xì)地論述與分析,并集中體現(xiàn)出嵇康的音樂(lè)思想,具有較強(qiáng)的思辯色彩。該著作中主人公“秦客”依據(jù)《禮記·樂(lè)記》的相關(guān)音樂(lè)思想進(jìn)行質(zhì)問(wèn),而主人公“東野主人”則一一進(jìn)行反駁,其實(shí)質(zhì)是對(duì)《禮記·樂(lè)記》的嚴(yán)厲批判。由此可見,二者之間的辯述也就是一場(chǎng)在音樂(lè)美學(xué)理論領(lǐng)域上的思想爭(zhēng)辯。《聲無(wú)哀樂(lè)論》從音樂(lè)理論的角度出發(fā),全面地否定了相關(guān)《樂(lè)記》的觀點(diǎn),標(biāo)志著我國(guó)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由儒學(xué)向玄學(xué)轉(zhuǎn)變。然而,嵇康也吸收了《樂(lè)記》中的部分音樂(lè)思想,例如“大樂(lè)與天地和”、“夫天地合德,萬(wàn)物資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為五色,發(fā)為無(wú)音”等等。
三、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觀點(diǎn)剖析
(一)音樂(lè)內(nèi)容與形式之間的關(guān)系
嵇康指出:“聲音有自然之和,而無(wú)系于人情”,這就說(shuō)明音樂(lè)只具備形式美,而不具有其思想內(nèi)容,自然也不能傳達(dá)出人的喜怒哀樂(lè)之情,也就是所謂的“和聲無(wú)象”與“音聲無(wú)常”。音樂(lè)只是單純地通過(guò)自然的聲音來(lái)呈現(xiàn)出一種和諧的形式,就音樂(lè)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特異功能,對(duì)人類生活也不必承諾義務(wù)與責(zé)任,也不能反映政治情感與倫理變化,比如其論斷“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此外,嵇康將音樂(lè)視為“自然之和”,獨(dú)立于音樂(lè)內(nèi)容與價(jià)值,這和儒家樂(lè)論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
(二)音樂(lè)的本質(zhì)
《禮記·樂(lè)記》認(rèn)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dòng),物使之然也”,音樂(lè)即是“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樂(lè)來(lái)自人類的大腦,最終受到客觀世界的限制,這種對(duì)樂(lè)論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是基于唯物主義哲學(xué)理論,而嵇康卻認(rèn)為音樂(lè)僅僅是“自然之和”,不關(guān)乎人的情感變化,比如“宮商集比,聲音克偕,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鐘”。因此,嵇康對(duì)于音樂(lè)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區(qū)別于儒學(xué)樂(lè)論,即是一種道性與人性相呼應(yīng)的“和”精神。
(三)音樂(lè)的本源和特征
就音樂(lè)的本源和特征而言,嵇康指出:音樂(lè)是由天地二氣相互交融而構(gòu)成,其相關(guān)論斷“夫天地合德,萬(wàn)物滋生……章為五色,發(fā)為五音”,音樂(lè)通過(guò)交融產(chǎn)生之后就如氣泡一樣存于天地之間,不以人的意志(人的喜怒哀樂(lè)情感)而發(fā)生變化,如論斷“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哀樂(lè)改度哉”。然而,筆者認(rèn)為音樂(lè)是由人所創(chuàng),必然會(huì)涉及到人的情感思想,所以任何音樂(lè)都能抒發(fā)一定的理念,純粹的自然之音是不存在的。因此,傳統(tǒng)儒學(xué)樂(lè)論中的“音由心生”觀點(diǎn)是值得借鑒的。
四、結(jié)語(yǔ)
作為我國(guó)古典音樂(lè)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嵇康在音樂(lè)理論方面有著極高的造詣,他的《聲無(wú)哀樂(lè)論》對(duì)于今天的樂(lè)論研究有著重要的作用。嵇康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在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具有一種思想進(jìn)步意義,但在當(dāng)今社會(huì)主義潮流下,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中的某些觀點(diǎn)已不具時(shí)代特征,因而我們需加以批判地借鑒與學(xué)習(xí)。
[1] 杜洪泉.嵇康是“儒”還是“道”——評(píng)嵇康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的影響與貢獻(xiàn)[J].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6,02.
[2] 丁園.淺談嵇康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J].黑龍江科技信息,2009,04.
[3] 張澤.“音聲無(wú)常,和聲無(wú)象”——嵇康《聲無(wú)哀樂(lè)論》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探微[J].黃山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4,02.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