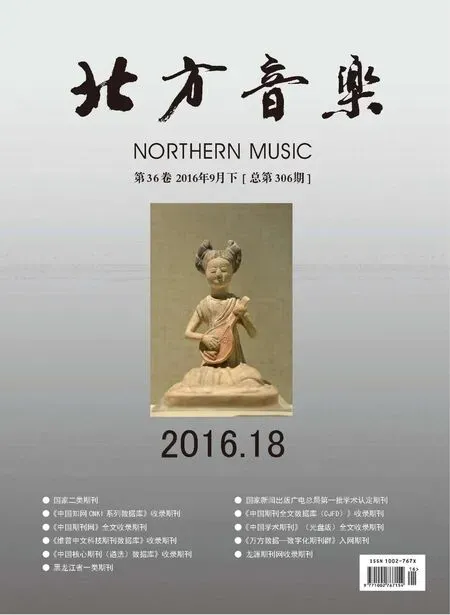淺談斯克里亞賓晚期音樂作曲技法的特征
孫嘉瞳
(吉林大學藝術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淺談斯克里亞賓晚期音樂作曲技法的特征
孫嘉瞳
(吉林大學藝術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世界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俄羅斯也在這個時期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在這期間,俄羅斯經歷了三次重大變革,對俄羅斯的社會發(fā)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響。斯克里亞賓,這位對世界音樂起著重要影響的俄羅斯作曲家的一生正處在這個時期。他的一生為后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音樂作品,涉及的體裁廣泛且都具有重要價值。也正因為他的一生處于這個歷史變遷的時期,他的創(chuàng)作思想受到了“神秘主義”的宗教影響,因此在他的晚期創(chuàng)作中,他的“神秘主義”觀念逐漸形成,并且運用到創(chuàng)作中。本文正是對斯克里亞賓晚期音樂的作曲技法進行研究,從音階、主題、和聲、節(jié)奏、調式、調性、形式、音色等不同方面進行分析。
斯克里亞賓;神秘主義; 創(chuàng)作特點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斯克里亞賓出生于1871年,處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時期是世界歷史的巨大轉折時期。對于當時的俄羅斯來說,這個時期也是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中產生重大變革的時期。
斯克里亞賓從5歲起正式學習鋼琴,11歲時開始接受正規(guī)的音樂教育,14歲時創(chuàng)作了他第一部正式的音樂作品——肖邦風格的鋼琴曲《升C小調練習曲》。1907年,35歲的斯克里亞賓開始創(chuàng)作單樂章管弦樂曲《狂喜之詩》。這部作品充分地體現(xiàn)了他的“神秘主意”思想,并在“格林卡音樂比賽”上獲得二等獎。這時的斯克里亞賓進入晚期創(chuàng)作,他的音樂越來越神秘莫測。從他完成《第五鋼琴奏鳴曲》之后,他的作品便不再使用調號,鋼琴奏鳴曲和管弦樂曲也都只采用一個樂章。
1914年,斯克里亞賓開始著手創(chuàng)作宗教儀式劇《神秘劇》,一部將音樂、舞蹈、燈光、香氣為一體的宗教儀式劇。并且這一年,他已經開始遭受病痛的折磨。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個冬天,斯克里亞賓舉辦了一系列的個人作品音樂會,將他生前各個時期的作品都一一演奏。而短短幾天后,這位年僅43歲的作曲家和演奏家便去世了。在斯克里亞賓晚期的創(chuàng)作中,音階的選擇和主題的形象是非常與眾不同的。在音階的選擇上,斯克里亞賓不僅使用傳統(tǒng)的大小調音階和半音音階,也使用了“八音音階”、“全音音階”和“斯克里亞賓音階”這樣的人工音階。在主題的創(chuàng)作上,他經常使用簡短而統(tǒng)一的主題,將整首作品所要表達的情緒通過主題集中表達出來。在他的晚期創(chuàng)作過程中,不同作品的主題也常出現(xiàn)“似曾相識”的感覺。
半音音階:對十二個音的平均劃分就形成了“半音音階”,這種音階使自然音和變化音的界限被消除,也削弱了大、小調式的色彩性;八音音階:將一個八度內的音由半音和全音交替組成形成了“八音音階”;全音音階:這個音階中全部是相隔大二度的音程,主音以單音出現(xiàn),有著非常特殊的色彩,晚期浪漫主義作曲家德彪西經常使用這個音階;斯克里亞賓音階:是作曲家本人在自己獨創(chuàng)的神秘和弦的基礎上形成的音階,是將四度疊置的和弦橫向排列形成的。
斯克里亞賓在晚期創(chuàng)作中,主題的創(chuàng)作多是短小而統(tǒng)一的。他認為主題是最具有表現(xiàn)力的獨立樂思,作品所要表達的情緒最能通過主題表現(xiàn)出來。他晚期創(chuàng)作的兩首管弦樂曲《狂喜之詩》和《普羅米修斯》中,就通過多個短小而統(tǒng)一的主題組成的主題群來表達他完整的構思。
斯克里亞賓對于和弦的結構和作品中和聲的發(fā)展在晚期創(chuàng)作中的運用與傳統(tǒng)和聲大不相同,這也是他在創(chuàng)作上做出的非常大的貢獻。此外,在節(jié)奏上他也使用了在當時看來非常新奇獨特的手法,對后來的音樂創(chuàng)作有了很大的啟發(fā)。
“神秘和弦”的使用:“神秘和弦”不同于傳統(tǒng)的和弦構成,它是按照四度音程關系疊置而成的和弦,按照“增、減、增、純、純”的方式排列,這個和弦是斯克里亞賓所獨有的;節(jié)奏型的變化:斯克里亞賓對于節(jié)奏型的改變主要表現(xiàn)在對勻稱概念的放棄或接近放棄。他的表現(xiàn)特點是,節(jié)拍形態(tài)和鋼琴演奏的雙手結合,在表面上看依然是傳統(tǒng)的形式,但在深層上卻使節(jié)奏更加復雜。
斯克里亞賓的創(chuàng)作從早期到晚期,和聲思維經過了嚴密的思考而形成了一種獨有的調式體系,而這種體系一直沒有一個名詞可以說明。俄羅斯音樂理論家維耶魯在《斯克里亞賓誕辰100周年紀念文集》里的《斯克里亞賓與現(xiàn)代藝術的傾向》一文中提出了“和弦—調式”這一名詞來代表斯克里亞賓這種和聲體系,經過研究和分析確定這一名稱應該是合適的。
斯克里亞賓的晚期創(chuàng)作在外部的形式上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從復雜到簡單的變化。在斯克里亞賓的創(chuàng)作中,音色有時就是主題的另一種表現(xiàn)。他的作品從譜面上就能夠給人一種視覺沖擊。他的創(chuàng)作雖動搖了傳統(tǒng)音樂的調式調性、和聲體系,但并不是完全拋棄了傳統(tǒng)的調式調性和和聲體系,他的創(chuàng)作是在傳統(tǒng)的基礎上進行的。
音階選擇的多樣性:斯克里亞賓晚期音樂的創(chuàng)作在音階的使用上極為寬泛,他既使用了傳統(tǒng)的大小調音階,也有半音音階、八音音階、全音音階和斯克里亞賓音階這種人工音階。這使他的作品更具有色彩性,不局限于大小調式中,打破了傳統(tǒng)的原則,為音樂創(chuàng)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主音觀念的固守:斯克里亞賓晚期的音樂雖不一定要從主音開始,但一定結束在主和弦上,這是斯克里亞賓始終堅持的。無論他的音樂創(chuàng)作怎樣的復雜,怎樣變化,這都是他始終遵循的法則,也為后人分析他的作品提供了最準確的判斷依據(jù)。
調式調性的擴展:斯克里亞賓認為:“旋律是展開的和聲,和聲是合并的旋律。”因此,這兩方面的擴展應該是同時的。斯克里亞賓樂曲的結束不一定要結束在主音上,他通過和弦就可以終止樂曲。他的和弦結構也突破了傳統(tǒng)的和弦,但不會放棄調式調性,也不會改變主音的位置。從《狂喜之詩》之后,他的作品就取消了調號,全部采用臨時升降號,這也標志著斯克里亞賓調性觀念的轉變。
不協(xié)和的觀念:斯克里亞賓在晚期創(chuàng)作中使用的和弦形式非常豐富,再加上不同和弦的交替使用,各種不同的終止式、和聲的摸進、低音的處理和豐富的調性布局都為傳統(tǒng)的和聲體系與音樂的創(chuàng)作增添了新的色彩。由于傳統(tǒng)音樂已經占據(jù)了協(xié)和音響的大部分,所以20世紀的作曲家們只能開發(fā)不協(xié)和的區(qū)域。
孫嘉瞳(1991—),女,漢族,吉林長春,學生,碩士在讀,吉林大學藝術學院,音樂與舞蹈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