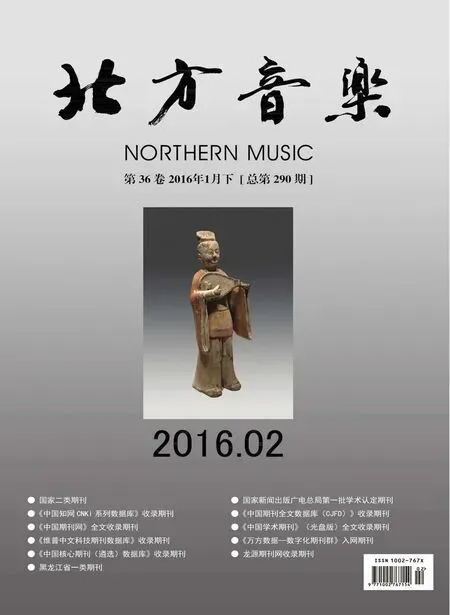知識(shí)轉(zhuǎn)型與音樂教育改革
卞尚文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13)
?
知識(shí)轉(zhuǎn)型與音樂教育改革
卞尚文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13)
【摘要】知識(shí)與教育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guān)聯(lián),音樂教育的發(fā)展自然也離不開知識(shí)的支撐。在當(dāng)今社會(huì),“知識(shí)型”概念的提出以及知識(shí)轉(zhuǎn)型的現(xiàn)象對(duì)音樂教育事業(y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如何推動(dòng)當(dāng)代音樂教育的改革,使其緊跟知識(shí)轉(zhuǎn)型的步伐,確保音樂課堂中所教授的內(nèi)容最大限度貼合當(dāng)今時(shí)代和學(xué)生的需求,成為了當(dāng)代音樂教育工作者刻不容緩的議題。本文通過淺析人類歷史上的三次知識(shí)轉(zhuǎn)型,以及后現(xiàn)代知識(shí)轉(zhuǎn)型的現(xiàn)狀,簡要剖析了現(xiàn)當(dāng)代音樂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zhàn),并聯(lián)系實(shí)際對(duì)音樂教育改革提出淺顯的看法和觀點(diǎn)。
【關(guān)鍵詞】知識(shí)轉(zhuǎn)型;音樂教育改革;音樂課程;知識(shí)型
關(guān)于知識(shí)與教育的關(guān)系的研究已經(jīng)由來已久。然而對(duì)于什么是知識(shí)這個(gè)問題,卻并沒有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的定義,其中一個(gè)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知識(shí)”概念的外延非常寬廣,包括了很多不同的認(rèn)識(shí)結(jié)果。但這并不影響人們追求知識(shí)的決心。歷史上人們對(duì)于知識(shí)的概念的問題的回答涉及到的四個(gè)問題:知識(shí)與認(rèn)識(shí)者的關(guān)系,知識(shí)與認(rèn)識(shí)對(duì)象的關(guān)系,知識(shí)作為一種陳述本身的邏輯問題以及知識(shí)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問題,就構(gòu)成了知識(shí)型的主要構(gòu)成部分。知識(shí)型概念的提出,對(duì)于人們理解知識(shí)本身有著重要的意義,并且擺脫了對(duì)于“什么是知識(shí)”這樣短期內(nèi)無法達(dá)成一致的問題的困擾,使得我們可以在無法回答“什么是知識(shí)”這個(gè)問題的前提下充分展開有關(guān)知識(shí)和教育的關(guān)系的研究。
本文所要重點(diǎn)闡述的兩個(gè)方面,知識(shí)轉(zhuǎn)型與音樂教育改革,其本質(zhì)上并不屬于一個(gè)層面的概念。人類歷史上經(jīng)歷的三次知識(shí)轉(zhuǎn)型,不僅近乎貫穿了人類發(fā)展歷史的全過程,更是深入到了人類社會(huì)的方方面面,而音樂教育僅僅是在教育領(lǐng)域中的一個(gè)分支學(xué)科。但是,這樣兩種看似不在一個(gè)層面上的事物卻是很值得我們來研究。一方面,教育不僅是一個(gè)名詞,也是一個(gè)動(dòng)詞,只有落實(shí)到具體的實(shí)踐中,知識(shí)的傳承才有了可能。另一方面,知識(shí)轉(zhuǎn)型對(duì)于教育領(lǐng)域的沖擊是持續(xù)而全面的,音樂教育在發(fā)展的過程中不可能回避這一現(xiàn)實(shí)問題。就如同20世紀(jì)初受西方音樂思想影響而誕生的學(xué)堂樂歌,開啟了我國近代音樂教育事業(yè)一樣,隨著第三次知識(shí)轉(zhuǎn)型的深入以及后現(xiàn)代知識(shí)型(文化知識(shí)型)的逐漸形成,音樂教育的發(fā)展理應(yīng)順應(yīng)社會(huì)發(fā)展的浪潮尋求自身的改變。
一、現(xiàn)代知識(shí)型對(duì)音樂教育的影響
人類歷史上一共存在過四種知識(shí)型。
首先出現(xiàn)的原始知識(shí)型由于沒有任何的記錄而無法充分的論證和闡述,而之后出現(xiàn)的古代知識(shí)型則意味著知識(shí)轉(zhuǎn)型開始進(jìn)入人類歷史。就如同人類社會(huì)制度的發(fā)展一樣,知識(shí)轉(zhuǎn)型有它所遵循的規(guī)律和原因,一是知識(shí)分子內(nèi)部對(duì)知識(shí)性質(zhì)或標(biāo)準(zhǔn)問題的不屑質(zhì)疑與反思,二是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或文化結(jié)構(gòu)發(fā)生重大的變動(dòng)。古代知識(shí)型是伴隨著人類社會(huì)進(jìn)入階級(jí)社會(huì)而誕生的,此時(shí)人們對(duì)于知識(shí)的理解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巫師、神話對(duì)于世界的解釋,而是更多的去探求世界的本質(zhì)以及人類自身。而之后第二次知識(shí)轉(zhuǎn)型將現(xiàn)代知識(shí)型呈現(xiàn)在了人類社會(huì)面前。現(xiàn)代知識(shí)型也被稱之為科學(xué)知識(shí)型,不僅僅在于其產(chǎn)生的背景正處于科學(xué)技術(shù)迅猛發(fā)展的年代,更體現(xiàn)在科學(xué)對(duì)于知識(shí)近乎支配性的統(tǒng)治地位。可以說,整個(gè)現(xiàn)代知識(shí)型就是在當(dāng)今學(xué)校音樂教育學(xué)科基本上屬于現(xiàn)代知識(shí)型,科學(xué)的指導(dǎo)下,將所有知識(shí)按照門類科學(xué)化地進(jìn)行歸納和總結(jié),使之成為這個(gè)學(xué)科的系統(tǒng),并且按照一定的規(guī)律進(jìn)行傳授。在這個(gè)過程中音樂自然也不例外,與音樂相關(guān)的內(nèi)容也按科學(xué)的方式系統(tǒng)地進(jìn)行了歸納和總結(jié),樂理、和聲學(xué)、復(fù)調(diào)、曲式學(xué)等科目應(yīng)運(yùn)而生,逐步完善了音樂理論,使之成為了類似于自然科學(xué)的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科。
現(xiàn)代知識(shí)型對(duì)音樂教育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從知識(shí)與認(rèn)識(shí)者來看,現(xiàn)代知識(shí)型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家或研究人員是“知識(shí)分子”,音響物理的觀察、實(shí)驗(yàn)或推理是建構(gòu)音樂知識(shí)的主要途徑,因而專業(yè)化的音樂院校和系科開始誕生,音樂的教育開始落實(shí)在書面客觀的音樂作品上,口傳心授面對(duì)面的主體與主體間的傳授被主觀對(duì)客觀作品的把握所替代了。
從知識(shí)與認(rèn)識(shí)對(duì)象來看,現(xiàn)代知識(shí)型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的客觀性,音樂作品也被更多地賦予了客觀的色彩。從知識(shí)的陳述來看,現(xiàn)代知識(shí)型通過概念、范疇、符號(hào)和命題加以表述,五線譜的記譜法成為了音樂知識(shí)表述的主要途徑。從知識(shí)與社會(huì)來看,現(xiàn)代知識(shí)型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是人類的共同財(cái)富,音樂的標(biāo)準(zhǔn)化也隨著西方國家殖民擴(kuò)張而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正如前面所述,知識(shí)型的轉(zhuǎn)變除了歸因于社會(huì)的變革,還有來自知識(shí)分子自身的反思。現(xiàn)代知識(shí)型的誕生除了科學(xué)技術(shù)的迅猛發(fā)展,來自歐洲的哲學(xué)家們對(duì)于人類及社會(huì)的發(fā)展問題的思考和探索也是促使現(xiàn)代知識(shí)型構(gòu)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7世紀(jì)與牛頓、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學(xué)巨匠同時(shí)誕生的還有培根、笛卡爾、斯賓諾莎等理性主義認(rèn)識(shí)論哲學(xué)家,他們對(duì)于科學(xué)領(lǐng)域?qū)映霾桓F的發(fā)現(xiàn)一次次地革新人們對(duì)于知識(shí)的理解。
在現(xiàn)代知識(shí)型的沖擊下,音樂學(xué)科取得了空前的發(fā)展,大型的歌劇、舞臺(tái)劇、交響樂的誕生豐富了人們的視野,極大地促進(jìn)了音樂表現(xiàn)的形式。然而,我們應(yīng)當(dāng)看到,現(xiàn)代知識(shí)型盡管在其誕生之時(shí)為音樂教育的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在其自身發(fā)展的幾個(gè)世紀(jì)里依舊存在著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因?yàn)椋F(xiàn)代知識(shí)型是在以歐洲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的背景下誕生的。率先從歐洲開始的工業(yè)革命不僅為歐洲各國的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更是成為主導(dǎo)世界發(fā)展潮流的動(dòng)力。
近代中國由于貧窮落后而保受西方列強(qiáng)欺凌,學(xué)習(xí)西方先進(jìn)技術(shù)成為了近代中國的主要潮流。進(jìn)入20世紀(jì)以來,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fā),五四運(yùn)動(dòng)的開展,西方思想開始不斷涌入中國社會(huì),專業(yè)化的音樂教育也隨著學(xué)堂樂歌的發(fā)展而不斷出現(xiàn)。西方的音樂理論——基本樂理,和聲,曲式,復(fù)調(diào),配器開始成為我國音樂教育課程的基礎(chǔ),西方的音樂作品也越來越多地成為我國音樂院校和系科的學(xué)生學(xué)習(xí)和效仿的楷模。這一切都使得我國的音樂教育以西方的音樂體系為標(biāo)準(zhǔn)而摒棄了我國幾千年來形成的獨(dú)有的音樂文化傳統(tǒng)。音樂院校開始像工廠批量生產(chǎn)商品一樣標(biāo)準(zhǔn)化地培養(yǎng)音樂人才,普通學(xué)校也以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教授學(xué)生相同的知識(shí)。
二、后現(xiàn)代知識(shí)轉(zhuǎn)型與音樂教育所面臨的挑戰(zhàn)
前面所述的現(xiàn)代知識(shí)型對(duì)于音樂教育的影響,有其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其一成不變的教條式的教授方法已經(jīng)越來越多的暴露出了與社會(huì)的脫節(jié)和不適應(yīng)。
回顧人類歷史上經(jīng)歷的三次社會(huì)轉(zhuǎn)型,我們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知識(shí)轉(zhuǎn)型的速度是越來越快了,這與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階段規(guī)律是相吻合的。原始知識(shí)型和原始社會(huì)一樣漫長,古代知識(shí)型也是占據(jù)了人類文明史的絕大部分時(shí)間,而現(xiàn)代知識(shí)型更是剛剛形成就遭到了各方面的質(zhì)疑和批評(píng)。而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是,音樂教育領(lǐng)域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jī)和挑戰(zhàn)。
一方面,伴隨著工業(yè)化也現(xiàn)代性而建立起來的標(biāo)準(zhǔn)化的音樂教育體系在其發(fā)展的過程中遇到了問題,另一方面,信息化和后現(xiàn)代的猛烈沖擊使得舊有的音樂教育體系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在西方,兩次世界大戰(zhàn)所帶來的對(duì)于人類道德、倫理和心理上的顛覆是沉重而深刻的,西方哲學(xué)家和思想家開始反思傳統(tǒng)認(rèn)識(shí)論所處的困境。英國分析哲學(xué)家羅素就將克服傳統(tǒng)認(rèn)識(shí)論的關(guān)鍵歸結(jié)為消解主體,而他的學(xué)生維特根斯坦也致力于批判近代西方哲學(xué)笛卡爾主義,即主客體二分的傳統(tǒng)。而曾經(jīng)誕生過黑格爾這樣的古典主義哲學(xué)的德國在30世紀(jì)先后出現(xiàn)了胡塞爾、海德格爾等現(xiàn)象學(xué)哲學(xué)家,他們也從不同的角度批判了西方傳統(tǒng)的認(rèn)識(shí)論哲學(xué),并在同時(shí)興起的分析哲學(xué)有衰落之勢的時(shí)候依然充滿活力。
從社會(huì)背景來看,后現(xiàn)代知識(shí)轉(zhuǎn)型與后工業(yè)社會(huì)的到來是密切相關(guān)的。在后工業(yè)社會(huì),文化不僅僅作為逃避現(xiàn)實(shí)的一種方法,所謂的“高雅藝術(shù)”,“高雅文學(xué)”與通俗文化之間的距離正在逐步消失。文化產(chǎn)業(yè)的形成也拉進(jìn)了普通民眾與藝術(shù)家們之間的距離,使得文化的傳播越來越不局限于特定的人群。后現(xiàn)代知識(shí)型不再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的認(rèn)識(shí)主體,而主張權(quán)威知識(shí)特權(quán)的廢除。這也使得傳統(tǒng)而古老的音樂學(xué)科越來越多地融入了新鮮的元素。人們了解和學(xué)習(xí)音樂的方式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課堂上的學(xué)習(xí)以及在音樂廳的觀賞。一方面世界多元文化音樂的知識(shí)信息開始大量進(jìn)入音樂教育領(lǐng)域,在學(xué)校教育開始生產(chǎn)多元文化的音樂知識(shí)。另一方面,音樂文化產(chǎn)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其發(fā)展速度和影響早已大大超出了各種傳統(tǒng)音樂文化。音樂不再是單純的作為文化和知識(shí)而被學(xué)習(xí),同時(shí)也被作為一種產(chǎn)業(yè)被消費(fèi)。
19世紀(jì)末,大發(fā)明家愛迪生發(fā)明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臺(tái)錄音機(jī),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欣賞音樂的方法。20世紀(jì)初,唱片的發(fā)明和改進(jìn)促進(jìn)了保留音樂的科技和手段。1963年,荷蘭飛利浦公司研制成了盒式錄音帶,大大減少了音樂存儲(chǔ)介質(zhì)的用料和大小。20實(shí)際90年代,VCD、DCD等碟片的出現(xiàn)更是使得普通民眾可以通過放映機(jī)來反復(fù)欣賞音樂表演的全過程。進(jìn)入21實(shí)際之后,以MP3為標(biāo)志的數(shù)碼音頻開始占領(lǐng)市場,更清晰的音質(zhì)和更輕便的設(shè)備使得人們可以更加方便和隨意地收錄自己喜歡的音樂。
2009年1月7日,工信部同時(shí)下發(fā)了3張3G牌照,我國正式進(jìn)入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今天,我們可以使用智能移動(dòng)終端,通過快速的移動(dòng)網(wǎng)絡(luò)隨時(shí)隨地下載自己喜愛的音樂,觀賞音樂會(huì)、演唱會(huì)的視頻資料。不僅如此,以微博為代表的網(wǎng)絡(luò)營銷媒介更是使得著名音樂家與普通民眾之間可以直接的溝通和交流。在這樣一個(gè)背景下,我們?cè)僖槐橐槐椴粎捚錈┑叵驅(qū)W生們傳授歐洲兩百年前建立的音樂課程知識(shí),在我國近一個(gè)世紀(jì)之前所建立起來的音樂教育體系,不斷地將所謂歐洲高雅音樂和古典音樂技術(shù)在課堂上反復(fù)教授,其效果恐怕不比向年輕人宣講封建倫理道德強(qiáng)多少。
當(dāng)然,推崇后現(xiàn)代知識(shí)型與后現(xiàn)代社會(huì)并不是要全盤否認(rèn)現(xiàn)代知識(shí)型所帶來的成果和積極意義。歐洲傳統(tǒng)的古典音樂在人類歷史上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作為人類文化歷史上燦爛的藝術(shù)瑰寶,理應(yīng)得到尊重和傳承。但是,在當(dāng)今信息膨脹的社會(huì)即后工業(yè)社會(huì),流行、搖滾音樂早已充斥著我們的媒體,流行音樂之所以能夠在全社會(huì)取得如此廣泛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自誕生伊始就摒棄了西方傳統(tǒng)認(rèn)識(shí)論哲學(xué)的音樂審美路向,即不以表現(xiàn)音樂自身結(jié)構(gòu)的美為主導(dǎo),而是注重音樂與聽眾的互動(dòng)以及反映大眾社會(huì)生活文化思潮涌動(dòng)的音樂潮流,這就使得流行音樂更具有煽動(dòng)性,贏得更多聽眾的共鳴。而要理解后工業(yè)社會(huì)的音樂文化,就必須要有相對(duì)應(yīng)的后現(xiàn)代的知識(shí)型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化知識(shí)型的音樂教育。與此相對(duì)應(yīng)的是,我們依舊按照19世紀(jì)工業(yè)化的標(biāo)準(zhǔn)來闡述傳統(tǒng)音樂,統(tǒng)一化、標(biāo)準(zhǔn)化地呈現(xiàn)各個(gè)時(shí)代的作品。千篇一律的作者生平,墨守成規(guī)的風(fēng)格介紹,使得一部一部原本生動(dòng)的作品臉譜化,僵硬化。甚至,再談到浪漫主義音樂,如貝多芬第五交響樂,不外乎就是“命運(yùn)在敲門”,“命運(yùn)動(dòng)機(jī)”,卻很少有人去關(guān)注那個(gè)時(shí)代的背景和文化,以及貝多芬本人在那個(gè)年代的履歷和思想,他的音樂作為資本主義興起時(shí)的文化精神是什么。沒有這些人文知識(shí)型的理解,便使得音樂完完全全停留在了譜面上,這不僅完全喪失了音樂作為文化存在的本質(zhì),其理解恐怕也與作曲家創(chuàng)作的本意背道而馳。
三、結(jié)語
今天的藝術(shù)院校或音樂院校的課程基本屬于現(xiàn)代知識(shí)型的類型,主要是音樂技能學(xué)習(xí)。人類學(xué)、社會(huì)學(xué)、音樂人類學(xué)、哲學(xué)、宗教學(xué)、文化研究、全球化研究等等人文知識(shí)并沒有進(jìn)入大學(xué)生和研究生的課程體系。這是否意味著當(dāng)代音樂人才的培養(yǎng)方面在知識(shí)型方面有很大的欠缺?當(dāng)代音樂教育知識(shí)體系是否應(yīng)該考慮后現(xiàn)代人文知識(shí)型的介入?
參考文獻(xiàn)
[1]管建華.音樂課程與教學(xué)研究[M].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
[2]朱玉江.論知識(shí)轉(zhuǎn)型視野中的音樂教育[J].星海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5(02).
[3]石中英.知識(shí)轉(zhuǎn)型與教育改革[M].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01.
作者簡介:卞尚文(1990-),男,漢族,江蘇徐州人,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音樂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音樂教育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