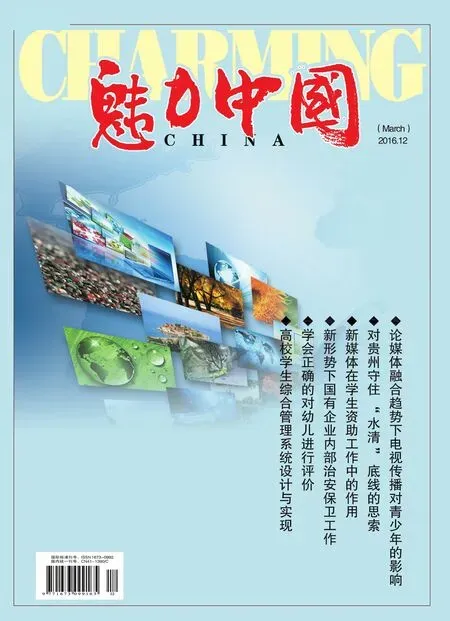何處春江無月明
——賞析琵琶曲《春江花月夜》
葛榮桃
(中國平煤神馬集團豫劇團,河南 平頂山 467000)
《春江花月夜》是一首琵琶獨奏曲,名《夕陽簫鼓》,又名《夕陽簫歌》,此外還有《潯陽琵琶》、《潯陽夜月》、《潯陽曲》等不同版本流傳于世。
《春江花月夜》旋律雅致優美。左手多用推、拉、揉、吟、打、帶等演奏技法,描繪出一幅清麗的山水畫卷。音樂開始,鼓聲、簫聲,疏密有致地悠然興起;接著,委婉如歌的、富有江南情調的主題款款陳述;其后各段,運用擴展、緊縮、移易音區和“換頭合尾”等變奏手法,并適時點綴以水波聲、槳櫓聲等造型樂匯,表達了意境幽遠的情趣。
樂曲通過委婉質樸的旋律,流暢多變的節奏,巧妙細膩的構思,絲絲入扣的演奏,形象地描繪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盡情贊頌江南水鄉的風姿異態。它的原名《夕陽蕭鼓》四字,已經包含了意境深遠,樂音悠長。后取意唐詩名篇《春江花月夜》更名。
全曲就像一幅工筆精細、色彩柔和、清麗淡雅的山水長卷,引人入勝。
第一段“江樓鐘鼓”描繪出夕陽映江面,熏風拂漣漪的景色。然后,奏出優美如歌的主題,樂句間同音相連,委婉平靜;模仿大鼓輕聲滾奏,意境深遠。由琵琶模擬鼓聲,奏出輕微的波音,描繪出“夕陽映江面,熏風拂漣漪”的景色。然后,樂隊齊奏出優美如歌的主題,樂句間同音相連,委婉平靜;大鼓輕聲滾奏,意境深遠,拉開了《春江花月夜》景色的序幕。
第二、三段,表現了“月上東山”和“風回曲水”的意境。接著如見江風習習,花草搖曳,水中倒影,層迭恍惚。旋律向上引發,描寫了夕陽西下,一輪明月從東山升起的情景,在我們面前展現了一幅“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秀麗畫面。曲調層層下旋后又回升。描寫微風陣陣、水滾回旋、繁星閃閃、五光十色,令人神往。
進入第五段“水深云際”,那種“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的壯闊景色油然而生。樂隊齊奏,速度加快,猶如白帆點點,遙聞漁歌,由遠而近,逐歌四起的畫面。出現四個快疾繁節的樂句。描摹簇簇鮮花,倒映在平靜的江中,相映生輝。在描繪了花影層疊和水天一色的自然景觀以后,音樂情緒又有了新的轉變,第六段“漁舟唱晚”出現了情景交融的景象:在寧靜的江面上,柔美的旋律,猶如悠揚的漁歌自遠處飛來,而琵琶的輕奏,就像是漁人們在一唱一和,表達了他們滿載而歸的喜悅心情。
第七段,琵琶用掃輪彈奏,恰似漁舟破水,掀起波濤拍岸的動態。進入了全曲的第一次高潮。在琵琶用“掃輪”技法奏出強烈的樂聲,描繪了群舟競歸、浪花飛濺的情景
全曲的高潮是第九段“欸乃歸舟”,表現歸舟破水,浪花飛濺,櫓聲“欸乃”,由遠而近的意境。歸舟遠去,萬籟皆寂,春江顯得更加寧靜。全曲在悠揚徐緩的旋律中結束,使人回味無窮。以柔婉的旋律,安寧的情調,描繪出人間的良辰美景:暮鼓送走夕陽,簫聲迎來圓月的傍晚;人們泛著輕舟,蕩漾春江之上;兩岸青山疊翠,花枝弄影;水面波心蕩月,槳櫓添聲……
《春江花月夜》作為十大中國古典名曲之一,是民族音樂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人音樂。它融入了一些哲學、美學的范疇,其對民族音樂有深遠的影響,它所追求的如:“中正平和、清微淡遠”的意韻美;崇尚自然、寄情山水、希求“天人合一”、返樸歸真的自然美等等,被廣泛的融合和傳承。它猶如一幅長卷畫面,把豐姿多彩的情景聯合在一起,通過動與靜、遠與近、情與景的結合,使整個樂曲富有層次,高潮突出,音樂所表達的詩情畫意引人入勝。
同時,《春江花月夜》是一首著名的漢族琵琶傳統大套文曲,明清就早已流傳了,該曲名最早見于清姚燮(1805~1864)的《今樂考證》。樂譜最早見于鞠士林(1820年前)與吳畹卿(1875年)的手抄本,1875年前后吳畹卿抄本傳譜為共6段加1尾聲,無分段標題。其后各派傳譜分段不一。在平湖派李芳園1895年所編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中,曲名《潯陽琵琶》,曲體有所擴展,共10段,其分段標題為:①夕陽簫鼓、②花蕊散回風、③關山臨卻月、④臨水斜陽、⑤楓荻秋聲、⑥巫峽千尋、⑦簫聲紅樹里、⑧臨江晚眺、⑨漁舟唱晚、⑩夕陽影里一歸舟。在浦東沈浩初1929年所編的《養正軒琵琶譜》中,曲名叫《夕陽簫鼓》,其分段標題為:①回風、②卻月、③臨水、④登山、⑤嘯嚷、⑥晚眺、⑦歸舟。1923至1925年上海大同樂會的柳堯章、鄭覲文將此曲改為絲竹合奏曲。
《春江花月夜》的曲情基本來自《春江花月夜》的詩情。《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張若虛在初唐算不上是著名詩人,甚至不入《舊唐書》人物列傳。《舊唐書》只是在賀知章的列傳里簡略的提到了張若虛。張若虛是揚州人,曾任兗州兵曹。與賀知章、張旭、包融一起被譽為吳中四士。賀知章是初唐著名詩人,張旭是書法大家,兩人都是杜甫“飲中八仙”詩中的絕頂人物。相比之下,張若虛的名氣遠遠不及與賀知章和張旭。《全唐詩》里只有兩首張若虛的詩,除《春江花月夜》外,另外一首為《代答孤夢遠》。
張若虛雖不著名,但他擁有這首被后人稱為“孤篇冠全唐”的《春江花月夜》,足以使他在初唐至盛唐那個天才輩出的年代里占有一席之地。《春江花月夜》本為樂府舊題,屬樂府清商曲,據說此曲為陳后主叔寶所創,在隋唐時較為流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其格調與境界遠在同題的宮廷詩之上。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此詩一開始便立意高遠,氣勢雄渾。從春江到海潮,從江樹到花林,從月升到月落,從現實到夢境,張若虛給世人描繪出一副似幻似真的圖景,蒼茫深闊,靜謐優美。“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四句,歷來被認為包含了對人生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此詩結尾有游子思歸、離愁別恨等情緒,雖略顯感傷,仍不減大氣。
奇怪的是,從唐、宋到明代前期,各家詩評很少關注此詩,自然也無人承認它是一篇曠世杰作了。自明代以后的唐詩選本里才開始收錄這首詩。明代鐘惺在《唐詩歸》中評價道:“淺淺說去,節節相生,使人傷感,未免有情,自不能讀,讀不能厭,將‘春江花月夜’五字,煉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清代王夫之《唐詩評選卷一》中說此詩“句句翻新,千條一縷,以動古今人心脾,靈愚共感。其自然獨絕處,則在順手積去,宛然成章。”清末王闿運在《王志·論唐詩諸家源流》中評此詩說:“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調,孤篇橫絕,竟為大家。”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人們對《春江花月夜》的評價極高。聞一多在《唐詩雜論》中認為,該詩一脫宮廷空洞艷體之詩風,“清除了盛唐的路”,為雄奇壯美的一代盛唐詩風的到來,起到了重要的啟承作用。因而,“張若虛的功績是無從估計的。”聞一多進而稱之為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向盛唐過渡的標志性詩作,兼具初唐氣度和盛唐氣象。博大,進取,寬容,唯美,已經成為唐朝的一種“時代氣質”。身處初唐與盛唐前期的張若虛,其作品不自覺流露出時代的“脈象”,這是很自然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幾個盛世之一。近來“盛世”一詞頻頻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有人甚至撰文提出,中國歷史上共出現過三個盛世,即漢初盛世、唐初盛世和康乾盛世,并暗示中國即將進入中國歷史上第四個盛世。
《春江花月夜》的琵琶聲陣陣傳來,繪聲繪影,曲中所描述的那種畫韻詩境盡現于眼前,使人有如夢回唐朝,進而無限感懷大唐盛世之萬千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