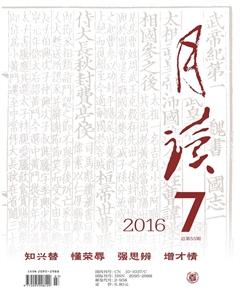魯濱遜眼中的中國
張國剛
編者按:“《資治通鑒》講座”欄目因故暫停一期,下月恢復連載
《魯濱遜漂流記》是18世紀英國著名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一部長篇小說。故事說主人公魯濱遜出海經商,中途遇險,流落于無名荒島。他孤身奮斗,創造了生存條件,與他救起的仆人星期五為生存而努力拼搏。馬克思的《資本論》曾經提到魯濱遜與星期五的故事,使笛福和他的魯濱遜在中國大名鼎鼎,家喻戶曉。其實,笛福在1719年發表初集不久,還寫了一本不那么知名的《魯濱遜二次漂流記》(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在這本續集中,魯濱遜在東方旅行的最后一站就是中國,他關于中國究竟說了些什么?有什么“觀感”?反映了什么現實?都是國人較少知道的。
魯濱遜是笛福筆下的人物,要了解魯濱遜對中國的印象,就要了解笛福。而笛福似乎對中國“知之甚多”。他在1705年發表《團結:或月球世界活動記錄》說:所有人都知道中國人是一個古老、智慧、彬彬有禮并且最心靈手巧的民族,所以中俄貿易不僅使俄羅斯人富有,也幫助俄羅斯人敦化風俗。中國人擁有多種西方世界從未聽聞的知識,書中主角自稱在中國每天都能發現新的和沒聽說過的知識領域。中國人早在西方有人定居之前很久就開始使用火藥、印刷術、磁石和指南針,技術也比歐洲人完美得多。中國人在航海術方面有最令人仰慕的論文,他們的皇帝察覺到普遍性洪水將到來,預備了100000只帆船提供給他所統治的每座城市和城鎮,每艘船的容量與一個城鎮的居民相匹配。船只容納了所有人,并載著他們認為應該挽救的可移動的東西和供應120天的食物,去迎接洪水;其余財物則被裝入巨大的陶器中并用封泥封住而幸免于水患。中國的數學也很神奇,超出現代數學成就到不可思議的程度。聽說在中國的某些地方,中國人的知識水平已經達到能夠懂得其他人的思想的完美地步,能夠有效對抗各種詭計、欺騙、刻薄,以及幾千種歐洲人發明的這類性質的行為,從而極好地維持社會秩序。
別以為笛福在贊美中國,其實,笛福的這篇作品有很強的現實目的,談論中國的背后流露出諷刺歐洲政治、政論家的意圖。他說中國皇帝根據自然指導人民,把權力交付給最堪當此職的人,而歐洲君主堅持君權神授,一班政論家也鼓吹統治者天生高貴、人民生來被動服從等等,所以有關中國政治的論文還是別引入歐洲,以免動搖這些論調。笛福似乎對近代哲學和科學研究很不滿,這也通過他對中國人的描述來表達。他說,中國人寫有關于風的博學論文,對風的規則和不規則運動、它的組成和重量都有奇怪的報告,還通過一種代數學計算出風的持續期間、強度和廣度,能宣布風的暴發,并預告在任何時期那里將發生多少風暴以及何時發生。這也許是涉及到中國古代占星術的只言片語,但其實是在諷刺熱衷研究彗星規律的歐洲哲學家和科學家。他還說,中國人有各種關于自然諸多秘密的研究,多得沒必要啰唆列舉,像是醫生為何總是無神論者,為何無神論者一般都是傻瓜,并且一般都活到自己知道阻止傻瓜變成瘋子的真正障礙是什么、愛的所有自然原因是
什么等等。
笛福借助中國來表達的這些情緒,顯得有些陰陽怪氣。他對中國的各種描述并不是贊美中國,而是想說歐洲所孜孜以求的東西中國都有了,而中國之所以擁有這一切,是因為它們來自月球的傳授。中國人擁有能輕易飛往月球的飛行器,依靠這個,中國人得以在世界各民族中脫穎而出,否則也跟其他民族一樣平庸。所以歐洲人只要也去月球一趟就什么都有了,像政治家、哲學家、醫生、江湖郎中、股票經紀人、法律從業者,以及耍刀弄槍的和玩筆桿子的,都很有必要到月球旅行一趟。當然,到月球旅行并從月球獲得一切想要的知識,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笛福冷嘲熱諷的態度,不僅在說歐洲人的這些追逐沒有多大現實意義,也表露出對中國文明成就的不信任和不以為然,“來自月球”一說隱含著作者認為有關中國文明的種種傳聞屬于夸飾之辭甚至是子虛烏有,而他并不認為中國人比起歐洲人和其他民族有多了不起。
現在來看笛福的《魯濱遜二次漂流記》,其中流露出的對中國的尖刻態度就更加明顯了。書中講到魯濱遜在東方歷險的最后一站中國的故事。魯濱遜和他的伙伴們在中國海岸遇到一位葡萄牙老領航員,在這位老領航員的幫助下,得以停泊在南京灣(事實上南京不靠海,這里可能是指杭州灣或長江入海口一帶)西南一處錨地。停在那里后,他們每天上岸取水兩次,發現這個地方的居民都很文明,還帶來大量供給品賣給他們。他們在此港口停留四個月,期間在這個國家旅行了兩三次,首先是10天的南京行。魯濱遜認為南京值得一看,它有整齊的建筑,筆直的街道,街與街以直線相交,人稱有百萬居民。但是若把南京以及它所反映出的中國同英國相比,則毫無可稱道之處:“當我把這些國家的可憐的人民同我們國家的相比時,他們的衣著、生活方式,他們的政府、宗教,他們的財產和有些人所說的榮耀,我必須承認我幾乎不認為在這里值得提起。我對這些人的排場、富裕、浮華、典禮、政府、手工業、商業以及行為感到驚訝;并非真有任何值得驚訝之事,而是因為對那些盛行粗魯和無知的國家的野蠻有了一個真實觀念之后,我們并不指望遠離粗魯和無知。否則,他們的建筑拿什么同歐洲宮殿和皇家建筑相比?他們拿什么同英國、荷蘭、法國和西班牙進行普遍貿易?他們的城市在財富、堅固、外觀的艷麗、富足的設施和無窮的樣式上有什么可與我們的城市相比?他們那停泊了幾艘帆船和小艇的港口如何同我們的航運、我們的商船、我們巨大而有力的海軍相比?
“我們的倫敦的貿易量就超過他們全國一半的貿易量,一艘配備80架槍炮的英國、荷蘭或法國軍艦就能摧毀所有中國船只;但他們財富之巨、貿易之盛,他們政府的力量之強和他們的軍隊之眾可能會略略使我們吃驚,因為,如我所說,考慮到他們是個異教徒的野蠻邦國,只比野人略強些,我們沒指望在他們中看到這些東西。但是盡管他們有200萬人的軍隊,這個帝國的全部武裝卻什么也做不了而只能毀滅這個國家并使自己挨餓;他們的100萬步兵在我們嚴陣以待的一個步兵團面前就會潰敗,飛快地逃跑以免投降,盡管他們在數量上并非以一當二十,如果我說3萬德國或英國步兵和1萬騎兵在很好的組織下可以打敗整個中國的武裝力量,這并非言過其實。中國沒有一個設防的城鎮能夠抵擋歐洲軍隊一個月的炮轟和攻打。他們有火器,這是事實,但他們對怎么使用感到難操作和不確定;而且他們的火藥威力太小。他們的軍隊紀律渙散,并且缺乏進攻的技巧,或撤退的勇氣;因此,我必須承認,當我回到家鄉,聽到我們的人民在談論中國人的力量、光榮、輝煌和貿易這類美好事情時,我感到很奇怪;因為就我所見,他們顯然是不值一提的一群人或無知群氓、卑賤的奴隸,臣服于一個只配統治這種人的政府;而且它距俄羅斯的距離并非遠得不可思議,而俄羅斯是個與中國一樣舉止粗魯、孱弱無力以及被糟糕地統治的國家,俄國沙皇能夠輕易在一場戰役中就把他們全部逐出自己的國家并征服他們;可惜沙皇正與好戰的瑞典人打仗,戰爭藝術也有欠缺,否則他現在可能已經是中國皇帝,而不是挨瑞典國王的打。
“由于他們的力量和他們的步兵團,同樣還有航海術、商業和農業與歐洲同類事物相比都很不完善;他們的知識、學問、科學技巧也拙劣非常或缺陷百出,盡管他們有地球儀或天體儀,和一點淺顯的數學,并自以為比世界其他人知道得都多,但他們對天體的運行幾乎一無所知;他們的普通人極端的和荒謬的無知,以至發生日食時,他們以為是一條巨龍襲擊了它,并在隨巨龍逃跑;于是他們敲打全國所有的鼓和壺把妖怪嚇跑,就像我們使一群蜜蜂入巢時的做法一樣!”
笛福在這幾段話中借魯濱遜之口已經把中國的繁榮、富足、強大、文明的形象統統粉碎。這還不夠,他還貶低中國人的品行。魯濱遜停泊南京灣期間,遇到一位想進京傳教的西蒙(Simon)神父,在神父的鼓動下,再加上對北京也慕名已久,于是決定隨神父進京。他們跟在一位總督的隨從隊伍中,每天有充足供給,但要按市面價格付賬。還有另外30個人也以同樣的方式隨隊旅行以受庇護。這位總督無疑因此大賺一筆,因為國家無償供給他旅行用品,他則有償提供給旅行者。中國人除了像這位總督這般貪婪,也很傲慢,富人喜歡擺架子,并且以蓄養眾多奴仆來賣弄;普通人也很傲慢,其他很多地方只有乞丐和苦力才像中國平民這樣兼具驕傲和無禮,而這在某些方面加劇了貧窮之人的悲慘。魯濱遜說,盡管中國的公路修筑得很好也保養得很好,并且對旅行者來說十分便捷,但他覺得在大韃靼的沙漠和無際荒野中旅行會更愉快,因為一路看到這樣傲慢、專橫、無禮而內里又最最愚蠢和無知的中國人使他非常窘迫。中國沒有人們所說的那么富裕,去北京途中盡管經過人口稠密的地方,但其耕作很差,中國的農業和經濟生活方式與英國人相比都很悲慘,中國人的所謂勤勞并不能令他們的情況改觀。他對北京沒有什么敘述,很快講到準備跟隨俄國商隊取道陸路回歐洲。在敘述從北京出發后的路程時,對沿路所見一幢用瓷磚鑲飾的房屋有詳細的和較為肯定的描述。即使如此,他也堅持認為他聽到的中國人對于這幢瓷屋的描述比實際情況仍夸大太多,暗示中國人喜愛撒謊吹牛,包括對長城長度的描述,中國人說近1000英里長,但魯濱遜說中國的直線距離只有500英里。
魯濱遜稱贊長城是件宏偉的作品,利用山上無法通行的堅巖峭壁阻止敵人進入或攀爬,但他覺得長城不過是道大而無用的墻,哪怕它有4英尋高,以及在有些地方有4英尋厚,也抵擋不住英國的軍隊和帶著礦工的工程師。魯濱遜說他所看到的韃靼部隊的力量也是不值一顧,但中華帝國竟能被這樣的家伙征服,言下之意,中國的軍隊糟糕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笛福對中國似乎言之不盡,繼《二次漂流記》之后又寫了《魯濱遜的真誠感想》(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不僅重復了《二次漂流記》中對中國軍力、工藝技術、國力等的評價,還增加了對孔子學說和中國宗教的意見。笛福說,孔子學說中政治、道德和迷信糾纏在一起,既不一貫,實際上也沒有多少道理。中國的宗教是最野蠻的,中國人在一個怪物的偶像前面彎腰致敬,而那個偶像一點不可愛,一點不和善,是人類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難看、最使人看了惡心反胃的東西。笛福的結論是:中國是許多野蠻國家中一個還算開化的國家,或許多開化國家中一個仍很愚昧的國家。這一結論在前面引述的《二次漂流記》中已經表達出來了。鑒于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難怪許多熱心的傳教士花了莫大氣力,卻只能使那里的異教徒知道救世主的名字和對圣母瑪利亞的一些禱詞。
笛福沒有到過東方,他的游記也是根據各種文本資料匯編而成,其關于中國的知識也直接得自于耶穌會士的報告。比如,《魯濱遜漂流記》中的中國知識,就是通過閱讀法國傳教士李明的著作而獲得的。但是,笛福并沒有正面接受李明對于中國文化、政治和經濟的描述,也沒有受李明書中像其他耶穌會士那樣渲染的中國形象的影響。笛福完全是在針對耶穌會士所描述的中國形象進行反駁,他既是在貶低中國,更是在攻擊耶穌會士。笛福顯然對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傳教行為和他們所描述的中國形象不滿。
笛福為何對耶穌會士持批判態度,也許與他出身于新教家庭(且屬于不能擔任公職的非英國國教的教派)有關,不過能夠看出,他評價中國時著重于依據英國現狀比較軍事力量、國家實力、經濟狀況,而不像同時期歐洲大陸的作家們那樣普遍熱衷于道德水準、歷史傳統、文化內涵等事項,這也就反映出18世紀初英國和大陸國家間的國情差異。英國只經歷過短暫的專制集權時代就走上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之路,無論軍事力量、綜合國力還是貿易能力都在節節上升,這就使得生活在不同于法國的制度之下的英國人,對文明與先進的看法與法國人和仍仰望法國的其他大陸人大不相同。
笛福(1660—1731)是英國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魯濱遜——不管其原型是誰——則是一個到海外去闖蕩世界、開辟世界并且想占有世界的新興資產階級的“英雄”。毫無疑問的是,“他”或“他”對中國文明的評論,滲透著當時正代表著西方文明進步方向的英國人的傲慢與偏見,也折射了東西方時代的巨大落差。了解了笛福或魯濱遜的“中國觀”,再看數十年后即18世紀末葉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留下的我們所熟知的對中國的各種輕視言辭,實在是不足為奇。盡管習慣上認為馬戛爾尼使團代表了歐洲重新認識中國的開始,但事實上掙脫耶穌會士的指引而對中國文明的價值采取否定態度,這種趨勢在18世紀前期的英國已經在醞釀。他們愈益相信理性之光存在于歐洲在近代科學發展導引下的進步機能中,而不在于對遙遠異邦的神話般的描繪中。
誠然,魯濱遜的游船還不是馬戛爾尼傲慢的船隊,更不是鴉片戰爭中英國人兇猛的炮艦,但是,魯濱遜打量中國的目光背后,分明流露出經歷著資產階級革命的西方,對于沉浸在落日余暉中的天朝上國的睥睨和輕視。這是我們今日在歌頌18世紀康乾盛世的時候需要加以警醒的!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國小說家、新聞記者。其作品主要描述個人通過努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戰勝困難,表現了當時追求冒險、倡導個人奮斗的社會風氣。其代表作《魯濱遜漂流記》聞名后世,魯濱遜也成為與困難抗爭的典型。左圖為笛福畫像,右圖為《魯濱遜漂流記》英文版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