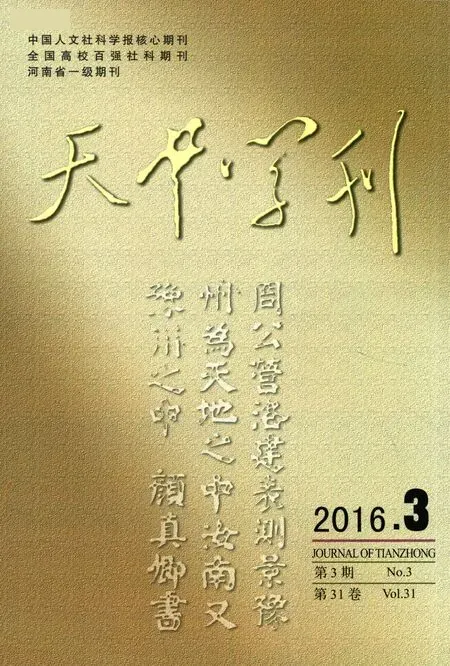從主客二分到天人合一
——西方生態批評的東方轉向
吳桂輝
(信陽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從主客二分到天人合一
——西方生態批評的東方轉向
吳桂輝
(信陽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作為解構主義思潮的產物,生態批評不僅繼承了西方近代理性精神,而且帶有濃厚的二元論色彩,這使得它在理論構建方面不僅陷入了只破不立的困境,而且容易走向由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轉向強調生態中心主義的另一個極端。西方生態批評要建構起完整、自洽的理論體系,必須借助外部思想文化資源以突破傳統二元思維模式的禁錮。中國古代先哲以自然宇宙為參照標準來解釋人在宇宙之中的位置,把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共同納入陰陽五行模式中加以考察,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天人合一整體思維模式與博大精深的生態思想體系。中國傳統文化中豐富的生態智慧將引導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東方轉向”趨勢。
主客二分;天人合一;東方轉向;生態批評
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生態批評并不是一種純文學批評,而是一種將生態哲學中的整體觀、聯系觀、和諧觀等基本觀念引入文學研究的新興文化批評模式。生態批評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指導思想,以挖掘文學作品中蘊含的生態思想為己任,把“有助于維持生命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1]224作為評判人類活動與社會發展的終極標準。因此,生態批評在理念上不僅超越了長期以來被人類普遍認同的經濟增長、物質欲求、生活消費等價值評價標準,批判了僅僅關注人類自身利益的科技至上、消費之上、欲望至上等傳統價值觀,而且顛覆了西方傳統哲學中的主體與客體、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等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在生態危機日益加劇的今天,盡管這種著眼于生態整體利益的新興批評模式在文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但作為產生于后現代語境的解構主義思潮的產物,生態批評完全繼承了西方近代科學基于邏輯分析推理之上的理性精神,并且仍帶有濃厚的二元論色彩;不僅在理論構建方面陷入了只破不立的困境,而且還容易走向由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轉向強調生態中心主義另一個極端。生態批評雖然意識到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下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產生當今生態危機的根源,但要建構起完整、自洽的理論體系,必須轉向東方,從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整體性思維中尋求理論根據。
一、西方生態批評的困境
生態批評產生于地球環境惡化、生態危機四伏的后現代語境,是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產物。人類中心主義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主宰萬物的主體,而把一切非人存在的自然萬物看作是受主體操控的客體。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觀并不是由來已久的,而是伴隨人類對自身存在價值的思考逐漸被確立下來的。中世紀以前的遠古社會中,初民們生活在對自然與上帝意愿的服從與敬畏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和諧融洽的。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以后,隨著人類思想的解放與自然科學的發展,人類在改造自然、改善生存條件與環境的道路上不斷取得勝利,人的主導地位不斷得到提升,自然的地位不斷遭到貶損。如培根曾提出“使我們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2]33。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命題的提出則進一步明確了主客二分世界中作為主體人的獨立性與優越性。受這種二元對立思想的影響,處于劣勢地位的自然被看成是一個供人任意索取原料的倉庫和隨意排污排毒的垃圾桶,一個沉默的“他者”。人類認識上的誤區、盲區與短視使自身陷入生態災難之困境,氣候變暖、空氣水體污染、自然資源枯竭等生態危機日益凸顯出來。在由人類自身行為引發的地球生態災難面前,人們逐漸意識到,導致生態危機最主要的思想根源,是數千年來一直支配并主宰人類行為意識的“人類中心主義”。因此,為糾正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偏見,生態批評主張“一只腳立于文學,另一只腳立于大地”[3]序言,從生態整體角度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強調通過重新整合人與自然的一體化來拯救現代社會的生態危機。
但生態批評畢竟從西方近代理性科學脫胎而來,同時還借用傳統科學分析的許多概念與方法,這種現實語境使得這一新的理論話語在一開始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傳統二元對立的烙印,從而在理論構建方面陷入了只破不立的困境。對生態問題的追根溯源使生態批評家認識到,人類不應該君臨于自然之上,而是應該與自然和諧共存共生,成為一體。因此生態批評強調將世界萬物視為完整的生態整體,并以生態整體利益為考察的價值尺度,但這種整體觀完全是主客二分思維方式的產物。在近代理性精神的指導下,宇宙世界被人為割裂成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兩部分,并將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精神與物質、現象與本質分離并對立起來。人對自身的認識以“我思”“我欲”“我類”為基本原則,以人的理性判斷、情感欲望、群性特征為參照標準,而自然界則被看成是一架完全受力學控制、進行機械運轉的機器。人類與自然界、精神和物質界被看成是兩個彼此獨立、外在的二元,對其一的研究不牽涉另外一個,人類社會有專屬人類自身的社會道德法則,自然界有專屬自然本身的運轉規則,它們分屬不同的類別,擁有兩套不同的理論體系,并最終形成了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立。主客二分認識論同時強調理性在對自然知識追求中的作用,宣揚用人的理性去把握世界,把握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在這種理性精神的指導下,人與自然宇宙的天然、本質聯系被割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認知性的關系,其中人被看作認知活動的主體,自然則被看成被認知的客體。而生態批評是人類對生態危機反思的產物,它源于人類對現實的關注與對未來的擔憂,它雖然強調生態整體主義,但這種整體觀完全是機械論與還原論的,而不是萌發于人與自然的天然整體聯系。建立在這種人與自然分裂、對立理念之上的生態批評充其量把人類自身看成是自然界的恩賜者與道德關懷者,自然仍被置于人的對立面,是一個沉默的“他者”。生態批評要將生態環境從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必須消除人與自然之間的斷裂。因此,基于這種主客二分思想之上的批評模式無法凸顯其生態底蘊,更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整體目標,從而在理論建構上陷入只破不立的困境。
同時,與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相伴隨的非此即彼二元價值判斷標準,將主體與客體絕對化、簡單化,還容易造成由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轉向強調生態中心主義的另一個極端。基于對人類中心主義造成生態危機這一問題的深刻認識與反思,許多生態學者主張將人視為與自然平等的存在,并要求把人與人之間的道德義務擴展到人之外的動物、植物、大地、巖石、河流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給地球圈所有生物以道德關懷,以建立一種與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不同的新的生態倫理,即非人類中心主義。它包括動物解放/動物權利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三大流派,其中以生態中心主義為主。生態中心主義強調生態整體主義,認為生物之間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生態系統內人與自然不再是主客體之間統治與被統治、征服與被征服的對立關系,而是平等和諧、共為一體的。如生態中心主義者阿爾多·利奧波德提出的“大地倫理”論認為:“大地倫理使人類的角色從大地共同體的征服者變為其中的普通成員和公民。它蘊涵著對它的同道成員的尊重,也包括對共同體的尊重。大地倫理簡單的擴充共同體的邊界,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由它們組成的整體——大地。于是,大地倫理反映了生態良心的存在,進而反映了個體對大地健康的義務的確信。健康是大地自我更新的能力,保護是我們了解和保持這種能力的努力。對于我來說沒有對大地的愛、尊重、贊美,和對它的價值的注意,對大地的道德聯系能存在是難以想象的。”[1]225這種整體生態觀有利于強化人們的生態整體意識,摒棄了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在增強人類的道德自律、規范人類干預自然環境的行為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但生態中心主義在強調人與自然平等的同時,完全忽略了人類要維持生存就必須依靠、甚至剝奪一些動植物的生存權利以獲得各種物質材料這一無法回避的事實,必然會陷入認識上的誤區,這種烏托邦色彩濃厚的臆想與現實相去甚遠,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無法為從整體上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批評提供理論依據。它因為強調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而把人貶低為一般的自然存在,無視人與自然的差異與不同,這實質是走進了另一個極端。
綜上所述,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雖然表面對立,但實質都是偏執一端的,都屬于理性精神指導下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在他們那里,人與自然的關系被完全割裂斷開,也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整體。生態批評要建構起完整、自洽的理論體系,實現宇宙萬物相互依存、彼此共生共存的生態整體目標,必須尋求有別于西方主客二元對立的整體論作為理論根據。
二、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整體論
中國古代先哲以自然宇宙為參照標準來解釋人在宇宙之中的位置,并通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方式來指導人類活動,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緊張、斷裂的,而是有著天然聯系的。同時,中國古代思想家習慣于以直覺體驗來把握對象的整體表象特征,心通萬物,將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聯系在一起,把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都納入陰陽五行模式加以考察,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天人合一整體思維模式與有機整體觀。
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 宇宙觀源于伏羲八卦。傳說中的伏羲通過上觀天文,下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用陰爻“--”和陽爻“—”符號演繹為八卦,以窮極萬物的生成變化之道。在由陰陽兩個符號重疊構成的三畫卦中,上爻為天,中爻為人,下爻為地,反映的是先民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即所謂“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4]509。而“天”之所以能與“人”合一,是因為“天”并非僅僅是與精神相對的物質自然,“人”也不是與物質、存在相對應的精神和思維。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研究者李約瑟曾指出:“天愈來愈被看作是產生自然界諸種模式的一種非人力,現象被看成是形成宇宙模式的整個等級制度的各個部分,在其中每一種物體都作用于其他各種物質,不是通過機械的推動,而是通過與其自身內在性質的一致合作。”[5]336在這個整體模式中,“人在宇宙中的作用是‘幫助天和地的轉變與養育過程’,這就是為什么人們常說人與天、地形成三位一體。對人來說,他不應探究天的方式或與天競爭,而是要在符合其基本必然性規律時,與它保持一致”[5]338。李約瑟雖然注意到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與西方建立于機械論之上的主客二元對立思維的差別,但并沒意識到“天人合一”并不僅僅指遵守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更指涉天地人之間、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同源、同構、同律性。
天地同源是指人與宇宙萬物在生成演化過程中具有同一之根源。在探討宇宙本源的問題時,我國古代存在著三種看法。第一是易家,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4]408,其中“太極”被認為是天地未開、混沌未分陰陽之前萬物統一之狀態,是天地人三才同居之源。第二是道家,認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是世界的本原,宇宙萬物的開始,即所謂“道生萬物”。《道德經》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6]153道是天下萬物的根源,也是宇宙萬物內在本質性統一的依據。第三是陰陽五行家,主張“氣”是人與萬物之根源。氣的運行導致了宇宙天地間萬事萬物的生滅變化,氣聚則生,氣散則亡。氣又分陰陽,即相互對立和消長的兩種勢力。陰陽雖然對立,但絕非水火不容,而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互濟互補、沖克激蕩而成五行金木水火土。在五行相互滋生、相互制約的運動中,生成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從以上可以看出,不論是“太極”“道”或是“氣”的范疇,其概念表達雖略有差異,但都有效地解決了人類與世界萬物生成的本原問題,突出了天人之間的天然、和諧與整體統一關系。
天人同構是指天人地內在構成上有著數上相符、類上相合的同構性。一方面,從數的角度上看,人是天的副本,天是人的放大。如漢儒董仲舒指出:“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于身,身猶天也。”[7]163天地的符契,陰陽二氣的符合,經常在人的身體上有體現。具體來說,“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7]95。另一方面,從類的角度看,天地人皆秉陰陽之氣而生,均可歸為陰陽兩類。《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4]408,宇宙萬物的生成與千變萬化都是陰陽相互作用的結果。天、地、人三才依當時的時機與所處的地位也各具陰陽,即“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7]169。因為天地人三才都是由相反而又相互補充的陰陽組成,結構類別是相同的,所以才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4]519。道家也認為“道”的本身包含著陰陽兩方面,這兩方面互相沖突交和成為均勻和諧狀態,從而產生天地人三才。天地人雖處于不同的位置,有形態、物種之差異,但結構相似,功能相當,天是人的放大,人是天的縮小,天地人三才是合而為一的。他們同時既自成體系,又互成體系,共同組成一個全息整體。
天地同序是指人與天地萬物具有相同秩序、共同遵守統一的準則。《周易》認為天地萬物雖錯綜復雜、變化多端,但仍是變化有道、有序可循的。人應觀察這種變化之道的運行特征與規律,遵循事物變化過程中“時”“位”的變化之序,“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當位而應”。要做到陰陽相推、剛柔相易,就必須“行時中”“居位正”,以順應天地萬物變化、實現“與天地參”的境界。這正是古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則與目標,即所謂“易之為書也,廣大備悉。其道甚大,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之謂易之道也。易之為書也不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4]408。道家也同樣認為天道是人與自然萬物的共同法則和秩序,而“道”的本性是自然無為的,天地萬物都是由“道”所化生,天地遵循自然之道,推及人類,人也遵循自然之道,因此《道德經》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遵循道的自然法則,遵循客觀規律,進而達到與自然萬物和諧共生。
三、中國古代生態思想
中國古人以天人合一的整體思維考察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并且把這種思維模式融入保護自然環境的實踐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生態思想體系,為解決當今困擾人類的生態危機問題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智慧成果。這其中包括萬物齊一的生態平衡思想、與天地相參的生態和諧思想、敬畏天命的生態消費思想。
與西方基于主客二分基礎之上的世界觀不同,中國古代思想家立足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實基礎,將人、社會與自然視為一個平等、有機的整體。人不是萬物之靈、自然的主宰者,而是與世界其他萬物平等的一部分。《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4]546在天地產生的萬物中,人只是與自然界平等存在的一部分。道家也認為人與萬物雖有差別,但同為天地所生,人只是宇宙中之一“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6]86。因此人在整個宇宙之中的地位并不比其他三“大”高。莊子繼承了老子的萬物平等觀,反對唯人獨尊,提出“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天地與我并存,萬物與我為一”[8]181,認為萬物都是平等的,并無貴賤高下之分。漢儒董仲舒認為:“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不可一無也。”[7]132天地人三才處于不同的位置,各司其職同時又相互匹配,形成一個平等有機的整體。
“天人合一”的核心精神體現為“和合”觀,即和諧、差別與多樣的統一。《周易·乾卦》:“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先天而弗違,后天而奉天時。”[4]25強調掌握自然規律,順應自然,以做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道家也認為,宇宙萬物的發生發展都有其自身的法則,要順應自然,輔助萬物而不妄加干涉,“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6]240,尊重萬物生長的規律性,使之保持其各自的差異和特點,達到各關系間的“生生和諧”平衡狀態。《莊子》認為宇宙萬物都有其內在的本性和規律,“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凡事皆守道而行,“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8]146。天和是人和的前提與根本,并遵循“天道無為,任物自然”,才能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古代先賢早已意識到自然界中各種資源的有限性,提出“順應天常”“寡欲節用”等生態消費思想,要求對自然資源的索取速度不能超過自然界的再生能力,以保持生態平衡。《易經》將天地人統一于一個整體,并教導人們效法天地運行之道,充分認識到保護自然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身,不逆天時而動。《系辭·上傳》載:“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知天命,故不憂。安士敦乎仁,故能愛”。孔子接受了圣人所以崇德而廣業的觀點,并把自己的“仁愛”思想由愛親而及自然萬物,將天命與人命結合起來,認為:“王者動必以其道,靜必以其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共興,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也。”[9]260老子也提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6]170要求人們按照四時變化和生物生長規律組織生產和生活。在順應天時進行消費的同時,儒道兩家都主張有節制地取舍自然所賜之物,避免斬盡殺絕,使自然物能夠自然地持續繁衍,并積極宣揚“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生活節約思想。老子也反對鋪張浪費,提出“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6]162,認為過多采食和貯藏會導致巨大的損失和浪費,所以提出“知足常樂”才能使自身生命保持安全長久。總而言之,儒家與道家的生態思想有利于形成當今既能促進社會物質發展又能保持生態平衡、既能滿足社會的消費需求又不危害生態環境的綠色生態消費模式,對拯救當前生態危機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和實踐指導作用。
當前,西方生態批評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重新閱讀文學經典,借助后現代思想,對指導現代社會發展的機械論、還原論以及二元論予以深刻的批判與揭露,同時對生態學理論的建構進行探討。西方生態批評對于促使人們認清“人類中心主義”這種傳統思想和文化意識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由于它無法走出西方思維模式中非此即彼、主客分離的二元論誤區,其理論走向成熟就不能止于批判,還必須轉向具有整體思維方式的東方文化,以解決近代西方未能解決的若干重大思想問題,進而構建完整的生態批評體系。中國古代文化蘊含的萬物一體、休戚相關的“生態整體主義”意識不僅超越了西方“人類中心主義”這一傳統觀念,而且挑戰了西方啟蒙理性精神、非此即彼的簡單化思維原則,能夠為西方的生態學研究提供新話語、新洞識、新范式。同時,將中國古代生態思想引入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建構之中,不僅有利于改變以往那種不加辨別、一味地“以西釋中”的單向闡釋的畸形現狀,更能以開放的姿態和嶄新的視角對中西兩種不同的詩學進行深度的探索和闡釋,以探尋一條試圖融貫中西的理論之路,促進世界各族文化的共同發展與繁榮。
[1] 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
[2] [德]漢斯·薩克塞.生態哲學[M].文韜,佩云,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
[3]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M].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4] [清]李道平.周易季解纂疏[M].王承弼,整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5] 潘吉星.李約瑟文集[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6] [春秋]老子.道德經[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4.
[7] [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M].周桂鈿,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8] 王亞寧.莊子全解[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
[9]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M].北京:中華書局,1983.
〔責任編輯 劉小兵〕
B08;B21
A
1006-5261(2016)03-0058-05
2015-09-28
2014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2014 BWX027)
吳桂輝(1974—),女,河南信陽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