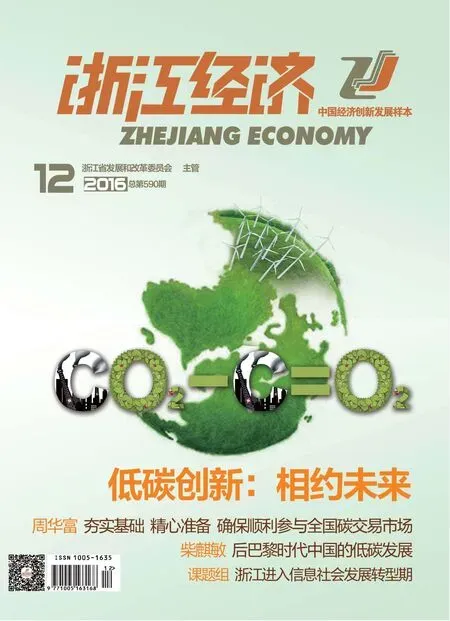著力化解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地矛盾
潘毅剛 張偉明 于蕾
著力化解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地矛盾
潘毅剛 張偉明 于蕾
(一)
浙江是城市化進程推進較快的省份,總體走在全國前列。2015年浙江省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達65.8%,成為全國8個城市化率高于60%的省份之一。
但是,也必須看到,總體水平的領(lǐng)先,并不意味著城市化質(zhì)量的領(lǐng)先。從城市化發(fā)展階段看,浙江城市化處于快速發(fā)展階段的后期,即將進入成熟階段。在這一階段,從人的城市化推進來看,浙江省人口城市化的“兩個背離”現(xiàn)象值得關(guān)注。
背離一: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與戶籍人口城市化率背離。當(dāng)前浙江65.8%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雖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近10個百分點(全國平均為56.10%)。但是,戶籍人口城市化率較低,按最新口徑也僅為51.2%,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差距較大。戶籍與常住地不統(tǒng)一的城市化,意味著同一個城市中不同戶籍的人口享受的服務(wù)和保障的差異,人的城市化在這個意思上講尚處在“半拉子”階段,還未真正破題。
背離二: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進城現(xiàn)實與真實意愿的背離。根據(jù)統(tǒng)計,浙江85%以上的就業(yè)人口早已從事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大量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生產(chǎn)生活都在城鎮(zhèn)。但根據(jù)近年來的一項對浙江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的抽樣調(diào)查,這些進城工作生活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卻并未或者說還不能將城鎮(zhèn)作為他們最后的歸宿。2013年浙江省發(fā)展規(guī)劃研究院進行的一次調(diào)查研究發(fā)現(xiàn),僅有35.2%的被調(diào)查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愿意永久遷居城市,37.4%表示不愿意把戶口遷到城市,有27.3%的人表示無所謂。不愿遷戶口主要原因是對農(nóng)村權(quán)益得不到保障的擔(dān)心,26.3%怕戶口遷出農(nóng)村后失去既有權(quán)益、23.3%認為城市住房不好解決,還有11.0%認為戶口不遷也可以享受城市的各種公共服務(wù)和福利,所以沒有必要把戶口遷到城市。
這“兩個背離”現(xiàn)象,對于浙江而言,有其客觀原因。那就是,農(nóng)村向城市轉(zhuǎn)移的人口中有相當(dāng)部分是省外流入人口。根據(jù)“六普”數(shù)據(jù),在浙江居住半年以上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有2399萬人,其中省外流入為1135萬人,占47.3%。但是必須看到,即使剔除這部分人口的影響,在浙江本省人口中“兩個背離”現(xiàn)象也是存在的。這說明,其中必然存在著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人已進了城,卻不以城市為最終歸宿。究其原因,無非三個:一是進城是暫時性的,本就沒意愿永久居住;二是想進城,但農(nóng)村有其不可割舍的東西;三是進了城,沒法落戶生存,只能返鄉(xiāng)。
(二)
從調(diào)查來看,真正沒意愿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多是年紀(jì)較大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這部分人“重土難遷、葉落歸根”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較重。新一代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更多的是第二和第三個原因,前一個是“不敢進城”,后一個是“進不了城”。不想進城的意愿與用腳投票常住城里的現(xiàn)實,反映出了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內(nèi)心的“糾結(jié)”,而“不敢進城”和“進不了城”的背后,隱藏的是對人和地之間現(xiàn)實制度約束的無奈,體現(xiàn)的是“地進人難進、人進地難離、要地不要人”的人地尖銳沖突。
城市要要素、卻不要負擔(dān),“要地不要人”的問題較為突出。過去的二三十年中,不少地區(qū)城市化更多地體現(xiàn)為土地的城市化,城市框架不斷拉伸,規(guī)模不斷擴大,吸納人口的能力卻沒有相應(yīng)提高。雖然浙江有既聚人又聚業(yè)還建城的“小縣大城”經(jīng)驗,但各地也依然存在“地進城、人難融”,城市包圍農(nóng)村“城中村”等現(xiàn)象,這很大程度可歸因于城市化過程中更多考慮了土地因素,而忽略了“化人”的因素。
農(nóng)民有資產(chǎn),但卻是死資產(chǎn),“人地難分離”的問題較為突出。農(nóng)房、宅基地、林地、山地以及承包地等都是農(nóng)民最重要的資產(chǎn),然而受制于產(chǎn)權(quán)不完整、不清晰,農(nóng)村財產(chǎn)處置的市場化機制缺失,既不能變現(xiàn)帶到就業(yè)的城鎮(zhèn),又不能輕易改變身份,人和地的依附關(guān)系無法解除。這使得廣大農(nóng)民在進城與留村之間出現(xiàn)“兩難”選擇,阻礙城市化過程自發(fā)推進。
戶籍設(shè)門檻,財力有困難,“內(nèi)外有區(qū)別”的問題較為突出。從我國人口管理的歷史來看,戶籍制度很大程度是因城市就業(yè)和服務(wù)保障的財力難以保障而產(chǎn)生的。對浙江而言,本省人口城市化對于財力保障總體是有能力統(tǒng)籌的。但由于浙江一半以上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是省外流入,這也導(dǎo)致各地對于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的態(tài)度不同。其中,子女義務(wù)教育、公共衛(wèi)生、就業(yè)培訓(xùn)、社會保障和住房保障以及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等方面的財力負擔(dān)加大,社會責(zé)任也很大,經(jīng)濟效益卻相對不大。據(jù)測算,浙江各地吸納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的成本,大概因城市規(guī)模和發(fā)達程度不同,為人均9-13萬元/年不等。這就使得不少地區(qū),因為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收入水平低,市民化給當(dāng)?shù)貛淼氖找孢h低于支出,導(dǎo)致政府推進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的動力不足,特別是面對省外流入人口時,顧慮較多。
(三)
上述問題的存在,表面上看是導(dǎo)向問題、意愿問題、財力問題,但實質(zhì)上都可以歸因于人與地的制度性矛盾問題。從經(jīng)濟角度看,盤活閑置土地這一農(nóng)民最大資產(chǎn),既能提高農(nóng)民資本實力,帶來現(xiàn)金流和收入流,又能通過人口的集中和土地使用效率提高,為城市和農(nóng)村發(fā)展提供更多的要素支撐。從可持續(xù)發(fā)展角度來看,人與地的和諧,本質(zhì)上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進一步松綁城市化過程中人與地的相互依附關(guān)系,有利于實現(xiàn)人口集中生產(chǎn)生活,生態(tài)環(huán)境休養(yǎng)保護,減少人類活動足跡對生態(tài)的破環(huán),為美麗城鄉(xiāng)提供制度保障。
因此,解放思想、改革創(chuàng)新、打開“人地死結(jié)”是當(dāng)前推進浙江城市化發(fā)展階段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亟需系統(tǒng)性制度設(shè)計。我們認為,總的思路可概括為三句話:解除依附、回歸本源、順應(yīng)規(guī)律。
——解除依附,就是要解除人地之間的制度性依附,讓人口和用地匹配起來,而不是捆綁起來,讓人回歸自然的人,作為人的人,可實現(xiàn)自主自由遷徙。
——回歸本源,就是要讓土地回歸生產(chǎn)要素的本源、人類家園的本源,讓作為資產(chǎn)的死地變?yōu)槭袌錾狭鲃拥幕畹兀屪鳛榧覉@閑置無人的地?zé)òl(fā)生機變?yōu)槌青l(xiāng)共同的家園,要素的歸要素,市場的歸市場,實現(xiàn)人地和諧。
——順應(yīng)規(guī)律,就是要尊重經(jīng)濟規(guī)律、社會規(guī)律、自然規(guī)律和城市規(guī)律,加快構(gòu)建人地和諧有利于城市化健康持續(xù)發(fā)展制度。把改革創(chuàng)新作為解除人地依附、山河重整的“金鑰匙”,一攬子改革實現(xiàn)聯(lián)動,共建美好家園,共創(chuàng)美好生活。
(四)
應(yīng)該看到,解決人與地的尖銳沖突,是需要一攬子的重大制度創(chuàng)新,但要害之處在于三個方面的制度設(shè)計。
加快農(nóng)村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借鑒省內(nèi)和國內(nèi)各地的先進經(jīng)驗,建議進一步加快以土地為承載物的農(nóng)村產(chǎn)權(quán)改革,推動“三化并舉”,變農(nóng)村土地“死資源”為“活資產(chǎn)”。其一,使用權(quán)股份化。深化“三權(quán)到人(戶),權(quán)跟人(戶)走”改革,全面完成對農(nóng)村土地的確權(quán)頒證,對于農(nóng)民集體性建設(shè)用地、承包地、林地、宅基地等集體性資產(chǎn)進行股改,探索集體經(jīng)營性建設(shè)用地出讓、租賃、入股的實現(xiàn)途徑。其二,交易市場化。建立農(nóng)村產(chǎn)權(quán)交易平臺,完善農(nóng)村產(chǎn)權(quán)交易市場,探索進城落戶農(nóng)民宅基地在試點地區(qū)探索縣域甚至更大范圍的大范圍、遠距離自愿置換、有償退出或轉(zhuǎn)讓。三是城鄉(xiāng)土地要素一體化。在前二者改革基礎(chǔ)上,加快清理不適宜的法律法規(guī),完善相關(guān)法律體系和操作細則,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建設(shè)用地市場,農(nóng)村土地實現(xiàn)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quán)同價,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在城鄉(xiāng)范圍內(nèi)市場化配置。
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以人群有序、領(lǐng)域有序、空間有序、時間有序為原則,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解除戶口以及相對應(yīng)的服務(wù)保障與城鄉(xiāng)土地的依附關(guān)系。在全面落實積分制的基礎(chǔ)上,實施浙江居民證制度,實現(xiàn)城鄉(xiāng)戶籍管理的統(tǒng)一。按照“先存量、后增量、就業(yè)優(yōu)先、服務(wù)差別”的逐步過渡原則,全面放開小城鎮(zhèn)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大中城市落戶限制,合理引導(dǎo)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進城落戶,建立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增加規(guī)模同吸納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落戶數(shù)量掛鉤機制。加快統(tǒng)籌財力資源,創(chuàng)新統(tǒng)籌方式,逐步建立覆蓋全體城鄉(xiāng),普惠可及、差異縮小、可持續(xù)的基本公共服務(wù)體系。對于發(fā)達地區(qū),在基本公共服務(wù)體系覆蓋基礎(chǔ)上,可以探索建立與居民貢獻程度相匹配的社會服務(wù)和福利供應(yīng)方式,實現(xiàn)基本公共服務(wù)追求公平,增量服務(wù)講究效率的有差別的公共服務(wù)體系。
加快財政金融體制機制改革。針對城市要地不要人的問題,合理成本分擔(dān)機制,健全財政轉(zhuǎn)移支付同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探索按照實有人口數(shù)進行中央和省級財政的分配、轉(zhuǎn)移和保障,實現(xiàn)財力保障的“費隨人轉(zhuǎn)”。按照“三權(quán)分置”的改革要求,建立農(nóng)村產(chǎn)權(quán)抵押物評估體系,全面開展農(nóng)村“三權(quán)”抵押貸款,充分賦予其擔(dān)保權(quán)能,有效拓寬農(nóng)村財產(chǎn)變現(xiàn)途徑。推進多元的城鎮(zhèn)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探索鼓勵各類投資主體共同參與市政公用事業(yè)建設(shè)、基礎(chǔ)設(shè)施、政策性住房建設(shè)的實施辦法,對于有穩(wěn)定收益的市政基礎(chǔ)設(shè)施項目建設(shè)鼓勵社會資本參與。
作者單位:浙江省發(fā)展規(guī)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