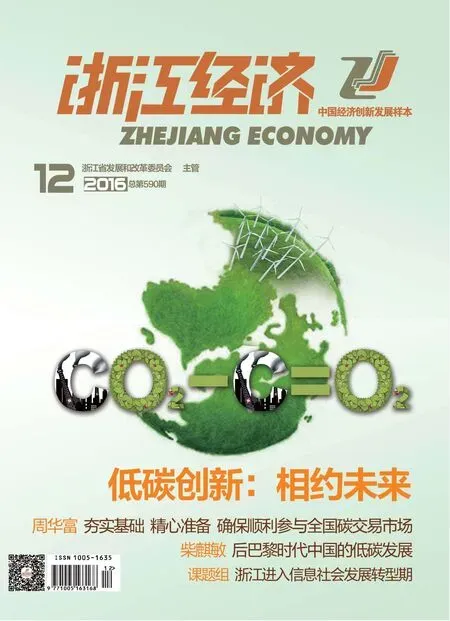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衛生經濟發展
王凌云
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衛生經濟發展
王凌云
改革開放尤其是黨中央、國務院推行新醫改以來,浙江衛生經濟工作走在全國前列,一批新模式新經驗得到推廣。新年伊始,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以人為本,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提升城市公共服務水平。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做好衛生經濟工作,保障和助推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是歷史賦予我們的重任,也是每一個衛生經濟工作者需要重視和深思的重大課題。
衛生經濟工作概況
(一)衛生投入
從總量來看,衛生總費用(THE)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通常是一年)全社會用于醫療衛生服務所消耗的資金總額。按照世衛組織的要求,發展中國家衛生總費用占GDP總費用不應低于5%。根據2015年11月國家衛計委發布的《2014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以下簡稱《公報》),2014年全國衛生總費用達35378.9億元,占GDP百分比為5.56%,高于世衛組織標準0.56個百分點。浙江省衛生總費用1977億元,占GDP的4.92%,比上年提升0.33個百分點,但不僅低于大多數省份,而且低于世衛組織標準。
從結構來看,衛生總費用是由政府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和個人衛生支出三部分構成。《公報》顯示,我國2014年政府、社會和個人衛生支出分別占29.9%、36.9%和33.2%。與上年相比,個人衛生支出占比下降0.7個百分點,但與“十二五”規劃目標(降到30%以下)相比,還差3.2個百分點。國際研究表明,個人衛生支出占比降低到15%-20%,才能基本消除災難性衛生支出和因病致貧。2014年,浙江省個人現金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為33.84%,較2010年下降近5個百分點,但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也高于周邊的上海、江蘇、江西、福建等省市。2014年浙江省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22.45%,遠低于全國的29.96%,在各省市自治區中名列倒數第四。
(二)衛生產出
從能力建設來看,浙江省基本建成了由醫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等組成的覆蓋城鄉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衛生資源總量顯著增長,主要衛生資源指標位居全國前列。2014年,每千人口床位4.46張,執業(助理)醫師2.65人、注冊護士2.63人,分別較2010年增長31.95%、26.19%和44.51%。社會辦醫療機構床位占比達22.46%,比2010年翻了一番。衛生人力資源中,本科以上學歷占比由不到50%迅速上升到59.6%。
從服務效率來看,全省2014年完成門急診5.04億人次、住院病人數756.4萬人次,較2010年分別增長了57%、51%。區域衛生發展的不平衡性逐步改善,醫療服務可及性穩步提升,“20分鐘醫療服務圈”城市、農村分別達到95.83%和92.71%。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全面覆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97.7%,住院補償率75%。醫療需求持續釋放,據第五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2013年)顯示,與上次調查(2008年)相比,兩周就診率上升24.78%,兩周未就診率下降22%。
從健康水平來看,2014年全省人均期望壽命達到78.09歲,較2010年提高0.8歲。孕產婦死亡率為5.52/10萬,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5.29‰,分別較2010年下降25.8%和35.49%,人群主要健康指標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十二五”期間,全省共創建衛生強市4個,衛生強縣(市、區)41個。
新型城鎮化建設帶來的新挑戰
新型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目前存在著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緩慢、城鎮化質量不高等問題。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拆“籬笆墻”、降“高門檻”、抹平鴻溝,解決好“三個1億人”的問題,對新型城鎮化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根據戶籍制度改革政策,除極少數超大城市外,允許農業轉移人口在就業地落戶,并保障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享有包括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在內的各種公共服務。面對新型城鎮化帶來的新任務新挑戰,浙江衛生經濟工作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亟待“補短板”。
醫療衛生資源總量不足、質量不高、布局不合理、結構不協調等問題依然突出,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不適應。在當前形勢下,地方政府面臨的投入壓力較大,應明確各級政府在衛生領域的事權財政劃分,地主政府至少應確保本地區政府衛生投入增速不低于財政支出增速。
城市大醫院資源過度利用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服務能力不足、資源利用率低等問題并存。浙江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薄弱,千人床位數、衛生人員數分別為0.4張、2人,僅為國家規劃目標的33%、58%,且呈進一步下降趨勢。2013年,全省農村人均衛生費用1717元,約為全國平均水平(2327元)的73.8%,僅相當于全省城鎮人均水平(2909元)的59%。在增長速度上,醫院擴張驚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展緩慢,“倒金字塔”現象愈發嚴重。
公立醫療機構內部資源要素結構失衡,衛生體系碎片化問題比較突出,分工協作、共建共享的機制亟待完善。政府對衛生資源配置的統籌管理、宏觀調控能力不強。譬如,“全面兩孩”政策的出臺后,據初步測算,僅在婦幼健康領域,未來五年浙江省存在近1萬張產科床位、4000多名產科護理人員的需求缺口。
社會辦醫發展空間受限,規模不大、能力不強、運行不規范。與發達的民營經濟相比,浙江社會辦醫的層次不高,低、小、散現象依然明顯。民營醫院中僅4家為三級醫院,大部分都是100張床位左右的小醫院,或是無床位的診所。在服務能力上,雖然社會辦醫院床位占比已達20%,但總診療人數和住院人數占比均不到10%。
推動衛生經濟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建設“健康中國”的重大決策部署。省委十三屆八次全會明確把健康浙江作為全面推進共享發展的重要內容,把健康產業作為七大萬億級產業之一。“十三五”時期,既是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也是全面建成衛生強省、全力打造健康浙江的關鍵時期。在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新常態下,衛生經濟工作要適應大健康、大衛生的理念,尤其是要堅持問題導向“補短板”,推動衛生經濟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加大投入。要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所確立的政府在提供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中的主導地位和投入主體責任。政府衛生投入增長幅度要高于經常性財政支出增長幅度,從而逐步提高政府衛生投入占經常性財政支出的比重和政府衛生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省、市、縣三級政府要明確事權,進而明確各自的投入責任。同時,多方籌措資金,健全以基本醫保為主體、大病保險為延伸、醫療救助為托底、社會慈善和商業保險等多種形式為補充的綜合醫療保障體系,通過政府、社會和個人三方合理分擔費用,有效減輕居民個人基本醫療衛生費用負擔,努力把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例降低到30%以下。
優化結構。在總量增長的同時,要通過醫療資源統籌,優化衛生經濟供給側結構,強化薄弱領域和薄弱環節,著力構建城鄉一體、優質均衡、多元發展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一是要落實醫院的分層管理,優化城市醫療資源布局結構。要嚴格控制城市公立醫院總體規模和單體規模。通過優化城市醫院空間布局,利用資源重組、機構拆分、合作辦醫等多種途徑,鼓勵和引導中心城區醫療資源向周邊和基層延伸、轉移。二是深化縣域醫療服務一體化發展,加強基層衛生綜合服務功能。全面推進鄉鎮衛生院標準化、規范化建設,實現村級醫療衛生服務全覆蓋。同時,加快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從資金、設施、人才以及業務協同等方面推動社區衛生服務做優做強。
搞活民營。目前對民營醫院的質疑,是對市場化的質疑,也是對規范、有序、高效市場的渴望。總體來看,民營醫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政府要從建醫院轉為管醫院,從單一的能力建設轉為規范市場,要深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進一步放寬準入條件,健全價格調整機制和政府補貼、監管機制,廣泛吸引社會資本參與衛生機構的建設和運營。在拓展社會辦醫發展空間的同時,要提升社會辦醫發展水平,積極培育醫療集團,鼓勵探索醫療機構連鎖經營。同時,支持公立醫院和社會力量通過特許經營、公建民營、民辦公助、委托管理等多種形式進行合作,基本形成功能互補、規范有序、持續發展的綜合辦醫體系。
創新模式。要實現衛生經濟領域的帕累托最優,就要積極打造主動、連續、綜合、高效的新型服務模式,從而促進醫療衛生資源的有效供給、有序利用。一是建立“雙下沉、兩提升”長效機制。加快形成醫療資源依次梯度下沉格局,深化醫療資源縱向整合。創新多層級醫療機構的管理體系,探索建設醫療聯合體。二是全面實施分級診療制度。推進基層首診,完善雙向轉診,優化急診服務和預約服務。在完善分級診療標準基礎上,實施醫保差別化支付政策,不斷完善治療-康復-長期護理服務鏈。三是鼓勵健康服務新型業態發展。培育一批檢驗檢測、影像診斷等領域的第三方服務機構,一批健康評估、咨詢專業化社會服務組織,一批醫養、醫健、醫旅等結合型服務產品,一批家庭出診、家庭病床等居家醫療衛生服務項目。
強化監管。堅持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圍繞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群眾關心的主要健康問題,通過強化綜合監督管理,優化考核評價制度,不斷提高衛生經濟的績效,增強衛生綜合實力。一是要建立健全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強化規劃、籌資和監管職能。不斷健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完善政府公共衛生服務購買機制,筑牢基層衛生網底。二是要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建立藥品短缺監測預警和低價藥供應保障機制。加強醫藥費用監管控制,采用綜合監管手段,實現醫療總費用的均次費用增幅下降,患者自付醫療費用占醫療總費用比例下降。三是要建立符合醫療衛生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和績效考核管理制度,推進信息公開,強化社會監督,探索第三方評價制度。
作者單位:杭州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