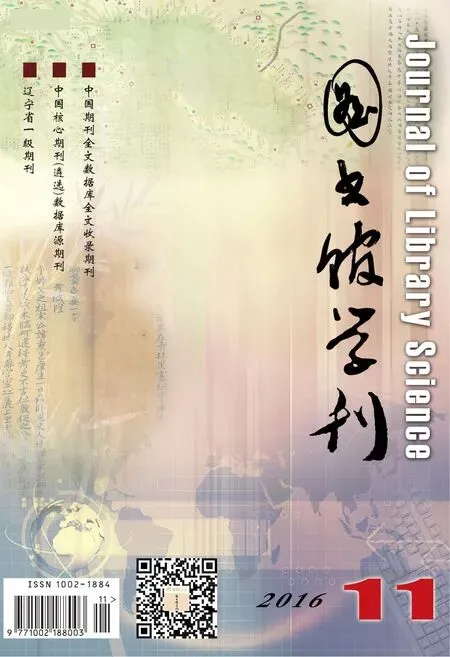基于文獻調研的廣府地域范圍研究
劉水養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圖書館,廣東 佛山 528000)
基于文獻調研的廣府地域范圍研究
劉水養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圖書館,廣東 佛山 528000)
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和討論,將有史以來廣府地域范圍的類別區分為地理含義的廣府、建置含義的廣府和文化含義的廣府,并通過古今文獻資料、正史文獻資料和現代文化研究文獻資料進行分類梳理與佐證。
廣府 廣州府 地域范圍 文獻調查
“廣府”,原指明、清時期行政建置的廣州府,后泛指廣府文化研究中以廣州為中心的廣府民系覆蓋區、廣府文化輻射區或新衍生的廣府經濟生態圈,是一個較難界定范圍的區域概念。自南朝始建廣州都督府,至明、清時期的廣州府,前后歷時一千四百余年,從政區劃分的角度,廣府地域的大小是隨著政區的設置而盈縮變化的。同時,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廣府的地域范圍也有著多種不同的說法。由此可見,廣府及其地域范圍,“是個歷史的、變化的概念”[1]。筆者在整理廣府文獻相關資料的過程中,發現相當多歷史文獻、史書和文化研究文獻中存在有關于廣府地理區域、廣府建置區域、廣府文化區域等的內容描述,經整理,可就此分類對廣府的地域范圍進行梳理考證。
1 古今文獻中的廣府地理位置確認
廣府首先是地理意義的廣府,是建立在歷史以來番禺、廣州這一固有的地理版圖上的衍化概念。秦及南越國時期,“廣州”這個名稱還沒有出現,當時稱“番禺”。廣州的前身“番禺”及后來改稱的“廣州”,是歷代廣州郡、州、府的治所所在地,是廣府的中心區域。在一些古典文獻中,能找到很多關于番禺、廣州的描述,以佐證廣府在地理范疇上的位置概念。《淮南子·人間訓》有關于秦屠睢統軍南下攻打南越的記載:“一軍處番禺之都”[2];《史記·南越列傳》任囂與趙佗語:“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3];《史記·貨殖列傳》:“番禺亦其一都會也”[4];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說番禺為“潘虞二音。今廣州。”[4]。盡管這些文獻中所提到的“番禺”,未必全部是指“番禺城”城址所在,但作為城郭的“番禺城”,按照文獻的考證和學界達成的共識,其城址均在如今的廣州舊城區內。
漢代以后,無論廣州建置名稱如何變化,廣州的城址始終固定在番禺,也就是位于現在廣州的舊城區,三國后,番禺逐漸改稱廣州,這在古今的一些文獻資料上均可查閱:《舊唐書·地理志》番禺條:“漢縣名,秦屬南海郡。后漢置交州,領郡七。吳置廣州。皆治番禺也”[5];《漢志釋地略》:“今縣”(番禺縣)[6];《讀史方輿紀要》:“南海,今廣東廣州、肇慶、南雄、韶州、潮州、惠州及高州府北境,廣西平樂府東境及梧州府東南境,皆是其地。郡治番禺,今廣州府附郭縣”[7];《史記地名考》:“秦、漢南海郡治番禺……今廣州市”[8];《中國歷史地名辭典》番禺條:“秦置,治所即今廣東廣州市。隋開皇十年(590年)廢。唐長安三年(703年)復置,治所在今廣州市珠江南岸。大歷間移治今廣州市。”[9]等。
從這些文獻資料可知,在古代,從開始的番禺,到后來的廣州,指的均是同一個地方,都是廣府地域的中心所在,是廣府文化的孕育地和發祥地。廣府首先是地理意義的廣府,以番禺、廣州為地理依托,數千年以來,嶺南首府依據廣州水陸形勝的優越位置,從荒蠻之地逐漸發展成為繁榮的嶺南商會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這與廣州作為廣府的中心地域密不可分。
2 正史文獻中的廣府由來與建置區域
2.1 秦至元代的廣州——“廣府”初地及轄區
秦至元代,雖然沒有明、清時期明確的政區建置“廣州府”,也沒有形成后來文化意義的“廣府”,但根據史書記載,“廣府”的最早來歷,可以用“孕于秦漢,起于隋唐”來概括。即經過秦、漢兩個朝代的發展孕育,廣州(番禺)已經成為嶺南的中心地區,南朝所設“廣州都督府”、隋朝所設“廣州總管府”和唐朝所設“廣州大都督府”,成為后來“廣府”稱謂可追溯的最早源頭。秦至元代各個時期的番禺、廣州,可以認為是廣府的初地,其建置地域因朝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秦
秦統一六國后,推行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10],并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首置南海郡,“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10],轄番禺、四會、龍川、博羅四縣,郡治在番禺(今廣州,下文同),稱番禺城。后人又以任囂、趙佗名之,稱任囂城或趙佗城。現在的廣州地區和珠江三角洲一帶,都屬于當時的南海郡治地。秦末漢初,龍川令趙佗建立南越國,并定都原秦南海郡,治番禺。自此之后,番禺逐步成為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2)漢
漢代建立的初期,由于沒有完成疆土統一的大業,一些荒蠻、邊遠的地區仍游離于漢朝江山的藍圖之外,其中就包括時稱南蠻的嶺南地區。直至漢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平南越,復置南海郡,屬交州,領番禺、博羅、中宿(今清遠)、龍川、四會、揭陽六縣[11],郡治仍設在番禺。
三國吳黃武五年(226年),首置廣州,“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吾、郁林、高梁四郡立為廣州,俄復舊。永安六年(263年),復分交州置廣州”[12],領南海、臨賀(今廣西賀州一帶)、始安(今廣西桂林一帶)、始興、蒼梧(今廣西蒼吾一帶,下同)、郁林(今廣西玉林一帶,下同)、桂林、高涼(今高州一帶,下同)、高興(今陽江、江門及中山西部一帶)、寧浦(今廣西橫縣一帶)十郡[12],州治在番禺。此后,晉人顧微撰《廣州記》,《南齊書·州郡志》稱“廣州,鎮南海”等,“廣州”一名開始進入文獻史冊。
(3)晉、南朝
晉朝仍沿用廣州一名,并置廣州建置,下設有南海郡,統番禺、四會、增城、博羅、龍川、平夷六縣[13],廣州州治、南海郡治均設在廣州城。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南朝先后出現南朝宋、南齊、南梁、南陳4個朝代,其中的南朝宋、南齊仍按晉朝建置,設廣州,南梁與南陳則先后改置廣州都督府[14]。這可能是史書中所能考證到與“廣府”這個稱謂有關聯的最早的建置記載。
(4)隋、唐
隋平陳后南海郡廢,置廣州總管府[14]。唐武德四年(621年),平定蕭銑而置廣州總管府,管廣州、東衡州(今韶關一帶)、洭州(今英德、佛岡一帶)、南綏州(今四會一帶)、岡州等五州,其中廣州領南海、增城、清遠、政賓(今清遠濱江一帶)、寶安(今深圳一帶)五縣。武德七年改為大都督府,又,“九年,廢南康都督,以端、封、宋、康……勤十一州隸廣府”“二年,省循州都督,以循、潮二州隸廣府”。“廣府”一詞首見于史書記載。天寶元年改南海郡,乾元元年又復為廣州[5]。
(5)宋
宋永安七年,分交州立廣州,領南海、蒼梧、晉康(今德慶、郁南、羅定一帶)、新寧(今臺山一帶,下文同)、永平(今廣西岑溪一帶)、郁林、桂林、高涼、新會、東官(今深圳一帶)、義安(今潮州一帶)、宋康(今陽西一帶)、綏建(今廣寧一帶)、海昌(今電白一帶)、宋熙(今高要一帶)、寧浦(今廣西合浦一帶)、晉興(今韶關一帶)等十七郡[15]。
(6)元
元代廣東設行中書省,廣州建置設廣州路。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廣東道宣尉使司,立總管府并錄事司,治廣州路,領南海、番禺、東莞、增城、香山(今中山市,下文同)、新會、清遠七縣[16]。
2.2 明、清建置的廣州府
公元1368年,元朝滅亡,朱元章建立明朝,改廣州路為廣州府。后明朝滅亡,清朝興起,廣州仍設廣州府。明、清廣州府的建置設立,成為“廣府”這一稱謂最為主要的歷史依據。廣州府自明清設立以來,經濟發達、商貿繁榮、文教鼎盛,廣府民系在這個地區繁衍生息,并孕育出歷史底蘊深厚的嶺南文化、廣府文化,是嶺南文化的本源之地、廣府文化的核心地帶和興盛之地。
(1)明
明代改元行中書省為布政使司,治廣州。廣州路改設廣州府,屬廣東道宜慰司,洪武元年為府,領州一、縣十五[17],分別為南海縣、番禺縣、順德縣、東莞縣、新安縣(今深圳一帶)、三水縣、增城縣、龍門縣、香山縣、新會縣、新寧縣、從化縣、清遠縣、連州、陽山縣和連山縣,府治在廣州。
(2)清
清代行政建置因明制,廣東定為省,廣州仍設廣州府,領縣十四,分別為南海縣、番禺縣、順德縣、東莞縣、從化縣、龍門縣、新寧縣、增城縣、香山縣、新會縣、三水縣、清遠縣、新安縣、花縣[18],其中花縣為康熙中期增置,省治及廣州府治均在廣州。
3 文化研究專著中的廣府地域范圍討論
3.1 方言廣府地域論
我國漢語有七大漢語方言,分別是官言、吳語、贛語、客家話、湘語、閩語、和粵語[19]。粵語就是粵方言,是指流行于廣東省內的方言,其中又包含有閩方言、客方言和廣州方言。流行于廣州地區的粵方言,書面上稱為“廣州方言”,民間多稱“廣州話”“白話”或“省城話”,也有直接稱為“廣府話”的,而外省人則籠統的稱為“廣東話”。“由于各地區之間的方言具有不同程度的歧異”,所以,“在近一百年來,廣東省省會所在地廣州的語音,成為各地的標準音。廣州話成為粵方言的代表方言”[20]。通常文字、口語中所提到的粵語、粵方言,也是通指廣州方言。
李新魁先生認為,廣東省內的粵方言分布可劃分為4個片區,那就是廣府片、高廉片、羅廣片和四邑片。其中的廣府片區主要分布在廣州、佛山、南海、番禺、順德、三水、花縣(今花都)、從化、清遠、佛岡、龍門、增城、東莞、深圳、寶安、中山、珠海、肇慶、高要、高明、英德、新興、云浮等縣市,韶關、曲江、樂昌等縣市的城區,以及香港、澳門地區[20]。
按照如上論著的描述和分析,雖然沒有明確的說明,但似乎也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廣府必須是流行粵方言或說廣府話的,廣府的地域范圍,取決于粵方言分布的范圍。
3.2 民系廣府地域論
在廣府文化研究領域,廣府民系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匯。通常認為,廣府民系的分布和延伸,是認定廣府地域最為重要的參考依據。廣府文化即廣府民系的文化,通行廣州方言[21]。討論廣府文化,歸根結底仍然離不開方言。李權時先生在論述廣府文化時,就以粵方言的分布作為廣府民系劃定的依據,他認為粵方言地域“大致包括廣東東南部珠江三角洲一帶(含今香港、澳門),整個粵中和粵西南部、湛江地區和廣西南部地區”[21]。按照這一說法,廣府的地域范圍實在是相當的廣大了,不單止在廣東省范圍內廣為分布,而且區域還延伸到了廣西省的部分地區。
徐杰舜先生則從人類族群的視角,認為“廣府人是華南漢族的主要族群之一。廣府人分布在粵中、粵西南、粵北,以及桂東南一帶,人口約有5100萬,其中廣東約有3800萬,廣西約有1300萬”[22]。按這一論述,既是“廣府人”分布的地區,那就應該算是“廣府”了。這與李權時先生認為的廣府地域大體相符。
3.3 風俗文化群落廣府地域論
司徒尚紀先生認為,廣府風俗文化群落“分布范圍與粵方言區一致,與西漢南越國疆界也大致吻合”,并將這一區域的廣府風俗文化群落“再分為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粵西嶺谷臺地和粵北山地丘陵風俗文化群落”。其中珠江三角洲風俗文化群落“包括廣州、南海、番禺、順德、中山、珠海、東莞等縣市”;西江流域風俗文化群落“東起三水,西迄廣西梧州一帶,包括以西江干流為軸線,各大小支流覆蓋的地區”;粵西嶺谷臺地風俗文化群落“東起史稱四邑(今稱五邑)西抵廣西欽州和合浦地區,包括潭江、漠陽江和鑒江流域,相當兩漢合浦郡,即六朝到隋高涼郡疆域”;粵北山地丘陵風俗文化群落“北界曲江、樂昌,南與珠江三角洲接壤,西抵懷集、廣寧,與西江風俗文化群落分界,主要包括北江中上游地區”[23]。這一說法實際上與李權時、徐杰舜先生認為的廣府地域范圍也是基本上一致的。
3.4 明、清政區廣府地域論
以明、清時期廣州府領地作為現在廣府的地域,在此基礎上展開廣府文化的研究,是廣府文化研究中廣府地域認定的其中一種觀點。陳澤泓先生在論述廣府文化時,就將廣府定義為明代始設、清代沿之的廣州府,認為“廣府文化的界定與廣府的概念有密切的關系。‘廣府’是一個歷史地名,與歷史上的行政區劃名稱有關。”之后從南北朝時期南梁、南陳二國的“廣州都督府”開始,對廣州“府”建置進行縱向的歷史考證,到明代時,“明代開始設廣州府,這一行政區劃的設定有劃時代的意義……因此,本書將‘廣府’理解為源自明代始設的廣州府”[24]。龔伯洪先生也認為,關于廣府民系中“廣府”的解釋,“這是因為唐代對廣州一帶已有‘廣府’之稱,而明清更有以廣州為治所的廣州府,廣州府人簡稱廣府人”[25]“廣府,即廣州府的簡稱。……至明代,廣州地區更明確稱為廣州府,該府轄南海、番禺、順德……等15縣及連州。清代初期,廣州府下轄南海、番禺、順德……等14縣”[1]。
4 結語
如上所述,這是古典文獻及現代文化研究中關于“廣府”地域范圍的記載和討論,廣府的地域范圍既有以廣州為中心的固定的地理范疇,歷史以來也因為政區的變動、文化的滲透,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區域空間。目前,廣府的地緣區域與社會功能與過去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發布實施、“‘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廣府煥發了新的契機,肩負了新的使命,廣府也成為了新歷史時期的新廣府。未來,如若再討論廣府的地域分布,就應該在遵循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加入現時代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的新元素,進行綜合考量、重新探討。
[1]龔伯洪.廣府華僑華人史[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
[2]淮南子·(卷18)人間訓[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485.
[3]劉起釪,等注譯.史記·(卷113)南越列傳[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4]劉起釪,等注譯.史記·(卷129)貨殖列傳[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5]舊唐書·(卷41)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
[6]汪士鐸.漢志釋地略·二十五史補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5.
[7]賀次君,施和金 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1)歷代州域形勢[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5.
[8]錢穆.史記地名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9]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中國歷史地名辭典》編委會.中國歷史地名辭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
[10]劉起釪,等注譯.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11]漢書·(卷28)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2]晉書·(卷15)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3]晉書·(卷十五)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4]隋書·(卷31)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5]宋書·(卷38)州郡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6]元史·(卷62)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7]明史·(卷45)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
[18]清史稿·(卷72)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9]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0]李新魁.廣東的方言[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21]李權時.嶺南文化[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63,64
[22]徐杰舜.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3]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24]陳澤泓.廣府文化[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25]龔伯洪.廣府文化源流[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劉水養 男,1967年生。碩士,館員。研究方向:地方文獻。
K926.5
2016-09-28;責編:姚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