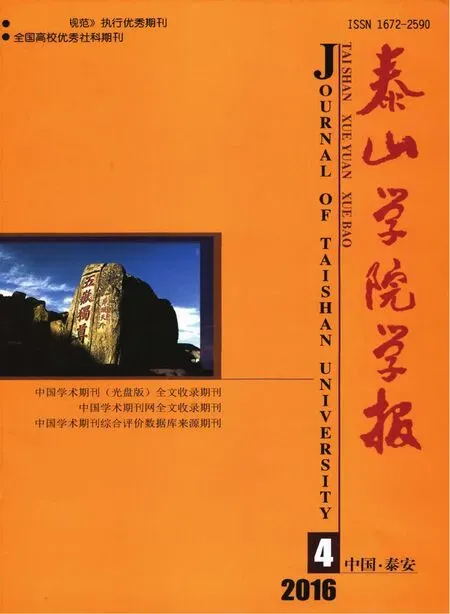30年來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李俊領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30年來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李俊領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30年來,海內外學界在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研究上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主要以“國家—社會”的視角討論了近代北京妙峰山的廟會、碧霞元君的“標準化”、碧霞元君的形象建構及其變遷、泰山信仰禮俗與民眾生活等專題。這些研究成果在新史料發掘、新視角運用、跨學科對話等方面各有優長,但也存在著視角單一等局限。未來相關研究似可以注意以下方面: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增強田野調查力度,嘗試運用“區域社會史”視角,建構以“日常生活”為觀察起點與歸宿的中層理論。
泰山信仰;禮俗;華北;區域社會史
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是指晚清民國時期華北區域社會中以東岳大帝、碧霞元君、石敢當等泰山本土神靈為信仰對象的官方典禮與民間習俗。清末,海外漢學界開始調查、研究山東泰山的信仰禮俗。20世紀20年代,大陸民俗學者開始關注和討論華北泰山信仰習俗的活動場景與文化意義。此后,民俗學、歷史學等學科的中外學者對該專題進行了多角度的討論。①尤其是近30年來,相關研究在視野拓展、方法更新、資料整理、問題意識提升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新進展。本文擬回顧30年來學界對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研究歷程,以相關的史學論著為主,在追溯該信仰禮俗研究的起源時兼顧民俗學和海外漢學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為更清楚地展示海內外相關研究在主題、路徑與風格上的差異,本文將二者的研究歷程分開進行回顧。
一、大陸學者對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討論
大陸學者在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研究上收獲了較為豐富的成果,而且形成了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專題。
其一,對民國時期泰山信仰廟會的調查與討論。妙峰山廟會是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的三處圣地(另兩處分別為山東泰山、河南大伾山)之一,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進入李景漢、顧頡剛等人的研究視野,現在成為中國民俗學興起的重要象征地。自20世紀90年代以降,民俗學界對該地廟會不斷進行研究,側重于討論近代華北泰山香會(香社)的權力秩序、心理世界與變遷特征等問題。吳效群以“國家——社會”為研究框架,從民俗學的角度梳理了北京妙峰山香會的價值理念變化歷程:追求行善和社會聲望(原初)——邀取皇寵(晚清)——經濟利益(當代)三個階段。他認為,妙峰山香會組織為保證進香的秩序性,模仿帝國政治制度建立了行香走會的制度。這些香會組織“搶洋斗勝,耗財買臉”,通過會規博弈,建構了象征意義上的“紫禁城”。在此過程中,香會組織表達了平等、互助、友愛的社會理想,發泄了長期被帝國政治象征符號壓迫而產生的憤懣。[1]王曉莉以北京地區與澗溝村的香客活動為個案,分析了清代至今妙峰山香客的進香過程和心理世界,民眾與政府等在塑造和改變碧霞元君信仰過程中各自發揮的作用。[2]葉濤簡要梳理了近代泰山香社的變遷過程,認為近代泰山的進香活動在光緒時期出現了由盛轉衰的態勢。[3]這些研究成果將近代泰山信仰禮俗視為民俗現象或民間信仰文化,著重在民俗信仰的內部觀察、討論其源流、構成與功能等要素,不僅從一個側面展示了近代華北民間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與社會運行機制,而且凸顯了民間信仰習俗的原生態價值。
其二,近代泰山信仰與王朝統治策略、民族精神建構。在“神道設教”的政治模式下,泰山神靈信仰與宋元明清的王朝統治策略密切相關。趙世瑜認為,東岳大帝崇拜更多地體現了國家信仰,而碧霞元君信仰則具有更多的民間性;明清時期北京東岳廟官方與民間的祭祀活動展示出國家與北京地方社會互相利用的一面,即前者意在控制后者,后者則借助前者壯大自己,而且二者的互相利用是一種溫和的互動。[4]周郢認為,明清時期國家對東岳大帝的祭祀衰落,而民間碧霞元君信仰興起,促使泰山之上的活動主體由廟堂轉向民間,由精英轉向草根,民間力量實際主導了這一時期泰山文化的走向。[5]李俊領、張琰認為,咸豐朝以降,晚清官方的泰山祈雨(雪)禮在國家禮儀體系中逐漸被邊緣化。一方面,由于泰山祈雨的結果不能及時如愿,清廷開始試用西方的農業灌溉技術。另一方面,泰山祈雨禮逐漸淪為地方官員借以謀取私利的工具。這從一個側面體現出“神道設教”的衰落與地方官員對朝廷的離心離德。[6]
泰山是中華民族在文化信仰意義上的一處精神家園,民國時期曾被提議賦予“國山”名號,從而參與民族精神的建構。20世紀30年代,有人提議定泰山為“國山”,由此引發了人們對于泰山象征意義的思考。周郢注意到,民國時期的許興凱、易君左、老合、芮麟等人倡“定泰山為國山”,藉以“恢復已失去之民族自信力,喚回將散而未散之國魂,驚醒國民醉生夢死之迷夢,而發揚光大中華民族之偉大精神”[7]。該社會輿論反映了時人對泰山信仰意義的新認識。泰山與“國山”、“國魂”的歷史文化關聯,值得從文化信仰與政治信仰的層面進一步討論。
其三,近代泰山信仰與華北民眾生活。泰山信仰是近代華北社會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尤其是各地泰山廟會對于民眾的信仰、娛樂與經濟等活動具有顯著的吸引力。趙世瑜分析了明清時期包括泰山神靈信仰在內的華北廟會,指出寺廟與民眾生活聯系最為密切的是廟會,“因為它涉及到民眾的經濟生活、休閑生活和各種公共生活”[8]。劉小萌發現,晚清時期外地旗人和民人在北京共同組織以東岳廟為信仰中心的香會,這是以前不曾有的“一個新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旗人與民人關系的發展;旗人與民人因為共同的信仰而密切了聯系,共享精神上的安慰與歡娛,感情上也日漸融洽。[9]蘭林友利用滿鐵調查華北社會的檔案,揭示了該地區民間香社的多種功能。他認為,華北鄉村以朝拜泰山為目的而結成的香社具有宗教、經濟與娛樂的三重功能。[10]這些討論有助于深入了解民國時期華北鄉村生活的內在邏輯與活動機制。中國農業大學的孫慶忠教授近年組織了一批本科學生深入調查了當前妙峰山香會、廟會及其對北京民間社會生活的影響。②其調查成果對于深入理解民國時期妙峰山的香會活動及當事人的生活體驗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泰山信仰禮俗下的民眾生活方式在近代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李俊領、張琰從民國時期泰山盜跖的河神化現象分析泰山民眾信仰意識的嬗變。其認為,由于泰山民間的“常門”信仰與扶乩降神的特殊因緣,作為“盜跖”化身的靈蛇“柳大王”代替了金龍四大王謝緒。這種基于“盜跖”信仰習俗的民間意識隱含著與鬼神交通的宗教情懷。“盜跖”的信眾在處于社會弱勢地位而又缺少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借用扶乩降神的傳統與儀式以應對日常生活的部分風險與困境,并積極尋求群體利益的代言人和地方共享的信仰世界。[11]李俊領還考察了近代泰山斗母宮比丘尼生活方式的嬗變。[12]其認為,近代泰山比丘尼既奉佛菩薩,也拜碧霞元君,在生活方式上不斷世俗化,主要表現為從妓和經營食宿。她們的半世俗化生活方式雖曾遭到禮教支持者的批判,但被諸多地方士紳、民眾廣泛接受。近代泰山比丘尼生活方式的“變”與“不變”,只是她們依托社會環境實現自身現實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調整,并沒有呈現出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趨勢。
近代膠東區域社會的泰山信仰習俗呈衰落趨勢,而且伴有被地方新神靈信仰取代的現象。任雙霞以清末膠東昌邑縣青山與平度大澤山的碧霞元君信仰為例,分析這一現象。她注意到,清末膠東昌邑縣青山奉祀的碧霞元君被分解成三種不同的人格神:一是作為“聰明正直”的女神“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二是作為主管斑疹的男性神——“碧霞元君之神”;三是大神天仙玉女碧霞元君。這表明當地民間的碧霞元君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模糊化的傾向。民國時期平度大澤山成為渤海——天柱山之間的地方社會信仰中心,該山日照庵主神由碧霞元君轉為無生老母和大澤山老母。[13]她分析稱,近代膠東大澤山碧霞元君信仰的衰落可能與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關。清末以降山東沿海貿易的發展以及膠濟鐵路沿線的城市開埠,促使平度、萊州、昌邑這個三角地帶形成了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區域經濟圈,也促使當地民眾在神靈信仰上更熱衷于塑造大澤山的本地神靈,同時降低了對碧霞元君的信仰熱度。[14]不過,該作者沒有呈現出近代膠東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地方信仰習俗的具體過程。另外,她還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的解釋,即清末傳入膠東地區的民間宗教九宮道主導了大澤山老母信仰的轉變過程。當地九宮道的教徒滕玉佩等人多次組織朝拜大澤山神靈的香會活動,很可能將其信奉的無生老母植入大澤山日照庵的神靈譜系。[15]誠如該作者所言,要坐實這一看法,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近代山西太古地區的泰山信仰習俗受到學界的關注。王守恩借鑒宗教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討論了清代、民國時期的山西太谷地區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他發現,民國時期山西太谷的奶奶廟(即碧霞元君廟)有38座,平均2.6個村落有1座,在當地的數百座神靈祠廟中,其數量居第7位,不如五道廟、三官廟、老爺廟、菩薩廟、真武廟與河神廟;當地民眾奉祀碧霞元君不僅因為生育之事,還為愛情、婚姻及其他事情。[16]不過,該作者在考察太谷地區的民間信仰與當地的村落自治、村際關系以及民眾生活時很少涉及泰山神靈信仰。在他看來,包括泰山神靈在內的所有神靈并不存在,只是人的創造物。不過,這種看法尚不能有效解釋至今在中國鄉村中仍廣泛存在的“巫覡”及其特異的信息攝取功能。這些“巫覡”中不乏與泰山神靈信仰深有關聯者,近代北京妙峰山香會的一些會首(如北京市朝陽區小紅門鄉紅寺村秧歌會的老會首盧德瑞)本身就有“巫”的色彩。[17]當前中西醫學、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學在此問題上尚未有圓滿的解釋。民俗學者劉道超已經注意到民間信仰背后的世界觀、思維方式與認識方式等問題,試圖由此打開中國民間信仰研究的新局面。[18]
其四,近代華北碧霞元君信仰與四大門的關系頗為密切。四大門是近代華北具有特色的民間信仰現象,20世紀30年代燕京大學社會學專業的本科生李慰祖率先對其進行了調查與研究。近30年來,學界對于近代北京四大門信仰的研究有了新收獲。或認為這是中國北方的一種民俗宗教;[19]或認為這是一種融合了儒釋道三教的北京地方性的民間秘密宗教組織;[20]或認為這是一種動物崇拜,在“近代北方民間廣泛流行”,“人們崇拜的已不再是四種動物的自然屬性,而是把它們作為巫教的神來崇拜”[21]。楊念群從民間巫與醫的角色轉換的角度出發,認為民國初年北京郊區的四大門信仰是一種難以明確把握的民間“知識系統”,與民眾的地方認同感密切相關。[22]李俊領、丁芮認為,近代北京民間信仰中的四大門在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微妙而特殊的角色。通過考察可知:在近代北京民間的視野中,四大門與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王三奶奶構成了區域化的神靈譜系;“香頭”必須經過上山朝拜碧霞元君的儀式才算完成認證;這種信仰習俗具有鮮明的倫理教化性,但并非民間宗教;四大門信仰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境遇順逆不定,由此產生了四大門信仰的正當性問題。[23]
其五,近代碧霞元君信仰與民間宗教的關系引起了學界的注意。曹春婷、邵雍注意到,北洋時期泰山岱廟的廟會出現了皈一道教徒宣講孝道的現象,而且該民間宗教與民國泰山信仰習俗都具有融合道、儒、佛三教思想的特點。[24]前面提到近代膠東地區碧霞元君信仰與無生老母信仰的關系問題。車錫倫分析了新發現的《泰山天仙圣母靈應寶卷》,認為明清民間宗教創立者將無生老母說成是觀音菩薩下凡的安龍公主,而安龍公主在泰山修煉成泰山圣母,從而造成了無生老母與碧霞元君的合體。其動機在于利用泰山香會對碧霞元君的信仰習俗,將碧霞元君嫁接到無生老母身上,組織和發展“道友”。[25]這一看法對于深入研究近代泰山信仰習俗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海外學者對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研究
晚清以降,海外學者持續關注泰山信仰禮俗。較早的是1879年馬提爾(C.W.Mateer)在《泰山之寺廟及其祭拜》中提到碧霞元君,但西方學者真正開始對泰山信仰進行研究的著作則始于1910年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泰山祭禮:中國的一種宗教信仰專論》。[26]至今,海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數量可觀,[27]他們研究的主題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碧霞元君信仰的起源與變遷,主要包括碧霞元君的身世與名號;二是碧霞元君的神格與功能;三是碧霞元君的信仰群體。這里僅其與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相關的部分進行回顧。
其一,民國時期碧霞元君的祠廟塑像與文化形象。近代泰山祠廟中供奉的碧霞元君塑像多為明清時期建造,但在海外學者的眼中,這些塑像因為俊美而容易勾起人的生理欲望。日本佛教、道教學者澤田瑞穗在民國時期親臨過泰山,他從性倫的角度推測泰山碧霞祠中那座臥于床上的碧霞元君像所展示的是仙界與人世相仿的性愛關系,似乎她正在等待男神的臨幸。他因此認為泰山香客與斗母宮尼姑的性行為意味著與泰山女神(以碧霞元君為代表)的靈肉結合。[28]彭慕蘭(KennethPomeranz)也認為,泰山上的碧霞元君雕像“性感撩人”[29]。這兩位學者對泰山碧霞元君像的觀感出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恐不能完全貼合中國本土的審美觀念。
20世紀上半葉,碧霞元君在華北民間的形象發生了轉變。彭慕蘭通過分析有關碧霞元君的民間傳說,認為這時期的碧霞元君從傳統的女神“逐漸轉變成一名好施詭計者,而她同天后、觀音菩薩之間的區別也越來越大”,其社會基礎也由精英轉變為平民;20世紀新出現的關于碧霞元君的故事則可能意味著“對真實生活中那些貶低崇拜碧霞元君的上層精英的嘲諷”[29]。這從一個側面證明民國時期諸多文化精英對泰山信仰禮俗的關注度與認可度降低了。
其二,近代碧霞元君信仰與四大門的關系。近代碧霞元君信仰和四大門的關系引起了美、法兩國學者的關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宗教系副教授康笑菲在《說狐》一書中提到,碧霞元君是狐貍精的首領,她們在地方民眾的信仰活動中都是“靈驗而危險”的,而且都具有性的曖昧意味。憑借對碧霞元君與狐仙的信仰,地方的穩婆、媒婆、藥婆、衙役等群體為自己的言行贏得了某種正當性,從而對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種威脅與制衡,因此引起了地方精英的蔑視與批判。在該書中,康笑菲重新思考了中國文化對民間神明的潛在標準化,朝廷官員和精英們自上而下對民間信仰施加的文化整合能力。[30]彭慕蘭認為,碧霞元君“乃狐貍精之首”,“這一角色也包括幫助其他狐貍精修行歸善”[29]。法國漢學家高萬桑認為,碧霞元君是四大門的管理者,而不是首領。他注意到,北京全真道與碧霞元君信仰具有密切關系,前者作為后者的制度化的侍神者,在區域社會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31]盡管這些海外學者對于碧霞元君與四大門的關系并沒有一致的認識,但他們關于碧霞元君是狐貍精的看法在泰安本地的傳說故事中也確能找到依據。
其三,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習俗的進香儀式與空間特色。前往泰山或其他地方的泰山行宮進香,是一種基于神靈信仰的儀式行為。不過,這種中國禮俗性的儀式行為是否適用西方人類學的儀式理論進行分析,還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美國學者達白安運在其《身份的反觀:中華帝國晚期的泰山朝圣》一書中運用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與民俗學的方法系統考察了平民、帝王和文人的泰山進香活動。[32]他認為,即使是平民的泰山進香之行也不符合維克多·特納的朝圣理論。沒有什么證據能夠證明,香客在朝拜泰山神靈時會進入一種閾限狀態(liminal state),即在一種“混融狀態”(communitas)中徹底顛覆日常的社會等級體系。相反,朝拜泰山的香客始終都很清醒地意識到他們自己的日常社會角色,并且以泰山進香作為謀求社會和物質利益的又一個舞臺。也就是說,泰山朝圣并不完全是對日常生活狀態的顛覆。這表明,簡單地將西方人類學的儀式理論用于中國禮俗的研究具有相當的風險。達白安運指出,帝王、文人、平民香客等各種人群是懷著不同的目的而開始泰山之旅,并且可能在“身份的反觀”中,各個集團間的沖突起了更加明顯的作用。另外,他還提到,20世紀以來的民族主義和科學技術使泰山朝圣之旅的形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晚清妙峰山從一座普通的山峰成為朝野朝拜碧霞元君的圣地,這一社會場域中充滿了復雜多樣的博弈關系。韓書瑞(Susan Naquin)關于妙峰山的兩個看法值得注意:一是妙峰山實際上就是得益于它的多重含義和香客們的千差萬別。內部的多樣化,有組織團體和個體香客的混雜,給進香之旅帶來了活力;同樣,碧霞元君崇拜和其他神靈的競爭,權貴和精英分子們的贊助或敵意都使妙峰山越來越有名。二是對16世紀以來妙峰山香會組織考察的結果并不能驗證一個設想,即“在現代的早期,中國發生了一些本質不同于以往的事情”[33]。也就是說,清代妙峰山上的碧霞元君信仰活動并沒有呈現出現代性的色彩。
其四,近代碧霞元君的神明“標準化”問題。美國人類學家華琛(James L.Watson)提出,中華帝國晚期出現了神明“標準化”現象,即在朝廷的主導下,將地方小神收編并推廣成為多區域崇拜的大神,藉以造成“大一統”的氣象或氛圍;王朝力圖倡導的是象征結構而不是信仰意義。[34]此說頗有新意,但在海內外學界引起了爭論。彭慕蘭對碧霞元君信仰的探討否認了華琛的觀點。他認為,清代碧霞元君的信徒雖然堅稱其信仰的正統性,但這一信仰卻因為碧霞元君與性的關聯而不為官方和士紳所接受,甚至被視為一種對正統社會秩序不利的力量,因而碧霞元君的“標準化”與正典化的進程遭到阻止和扭轉。[35]事實上,乾隆帝洗去了民間崇奉碧霞元君的“淫祀”嫌疑,將其納入準國家祭祀的行列。此后,士紳階層鮮有質疑碧霞元君之祀的聲音。徐天基從人類學的角度對1696—1937年間北京丫髻山的進香史進行了考察,旨在用個案形式反思并回應華琛等人開創的“標準化”議題。他認為,丫髻山進香是一個復雜的意義交流體系。皇帝、王公大臣、宮女、太監、旗人、草根階層、新興社會群體、道士、四大門的信仰者,都在其中各自建構和表達著自己的觀念。這就造成了一個將碧霞元君“標準化的帷幕”。帷幕之下,一種是朝廷權力自上而下的推廣,一種是民間自下而上的塑造,二者在連續的互動中又都“聲稱正統”,而碧霞元君“標準化”的事實卻帶有明顯的不連續性。[36]可以說,清廷對碧霞元君的“標準化”不只具有象征結構的意義,同時還具有巫術性信仰的實用意義,其派官員前往泰山祈雨(雪)以抗旱的舉措就說明了這一點。
海外學界在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研究上,基于西方的文化背景、思維方式與價值尺度,側重于建構一種像神明的“標準化”這樣的解釋模型。其在開拓新視野、提供新思路上不乏啟發意義,而且多特強調不能運用西方人類學的儀式理論分析泰山廟會進香活動的主張也確有道理。不過,他們對部分史料的分析還需要進一步體貼中國的文化語境與情感特質。
三、反思與前瞻
縱觀近30年來學界對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討論,在新史料發掘、新視角運用、跨學科對話上,各有其長,但也存在著一些局限。其一,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問題,仍是今天學界探究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難以突破的瓶頸。由于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復興較晚,迄今沒有建立自己的解釋中國社會變遷的理論框架,因此史學界對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研究仍不免借重政治史研究的解釋范式和西方社會科學的某些理論。應注意的是,西方民俗學的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于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解釋。其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運用還不夠充分。民俗學者從顧頡剛、李景漢等前輩學者開始,就十分注重田野調查。像孫慶忠等新一代學者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增加了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不過,史學界在討論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時較少運用田野調查和口述史的方法。此外,社會學的“內部觀察法”,對于討論這一禮俗而言是值得借鑒的,但學界鮮有人嘗試。③其三,大陸史學界研究該禮俗運用的“國家—社會”視角,雖可以從一個側面揭示王朝政治與社會底層群體互相利用的關系,但仍顯不夠完整。也就是說單一視角的運用,不可避免地造成觀察視野的狹隘。另外,學界對北京妙峰山、丫髻山、東岳廟與山東泰山等地泰山信仰禮俗的討論,多是就一地論一地,鮮有區域社會史的研究視野。換言之,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區域社會性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視。
未來的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可能更多在于運用新穎的理論、方法與視角,并從中獲取有益于當前社會生活轉型的歷史智慧與審美愉悅。這需要研究者在不斷拓展新領域的基礎上,積極嘗試運用新方法與新視角,不斷增強“中層理論”建構的勇氣與底氣。
學界對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探討還有廣闊的學術領域等待拓展。比如近代民間宗教如何利用了泰山信仰,泰山信仰禮俗與在華基督宗教發生了怎樣的沖突,民國時期泰山如何參與民族國家的建構,泰山神靈信仰者如何應對南京國民政府強制性的信仰習俗改造,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未來的相關研究逐一解答。
深入討論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問題,增強田野調查的力度顯得尤為需要。民俗學與人類學在這方面已經做了較好的示范,社會史的相關研究若能充分注意田野調查,常會有意外的收獲。其一,田野調查可以發現尚未公開出版的碑刻、圖像等新資料。從已經出版的三卷《山東道教碑刻集》④看,僅山東一地就有大量尚未被整理、出版的有關泰山信仰的碑刻資料。其二,田野調查可以搜集到有關泰山信仰禮俗的活著的歷史記憶。比如民國時期泰山無極廟的民間宗教信仰,賈子羽與泰山“大中至正道”,泰山斗母宮的比丘尼生活等問題,筆者曾通過在泰山當地的訪談,發現了諸多不曾載于文字資料的重要信息。這對于理解近代泰山神靈信仰的生命力確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區域社會史”研究視角的運用,將有助于深化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研究。近30年來,“區域社會史”已成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視角。以該視角討論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不僅符合泰山信仰禮俗自明清以來普遍存在于華北社會的事實,而且可以從一個相對具有文化特性的空間單位對其進行整體性的認識和把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過去相關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限。以“社會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種方法而言,探討近代泰山信仰禮俗宜有長時段意識與全局性眼光,可以借鑒年鑒學派的治學長處,將對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做出“整體史”的廣度與深度。在具體探討時,似宜將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與近代中國社會轉型聯系起來,觀察其中“變”的大脈絡、大格局,“不變”的大環境、大根源,“變”與“不變”之間的互動關聯。由此盡量避免將區域社會史做成就一地論一地的地方史,同時也盡可能克服當前中國社會史研究存在的“碎片化”現象。
在增加田野調查力度、引入“區域社會史”視角之外,不妨積極嘗試“中層理論”的建構。社會史意義上的近代泰山信仰禮俗研究容易陷入就事論事的窠臼,卻不容易做到有深度的歷史詮釋。或者說,相關的研究更多地停止在“求真”的層面,而“求智”的功夫尚有待加強,以至于屢被詰問研究的問題意識在哪里。在研究理論上突破當前的瓶頸,需要立足于中國本位,將中國社會史與西方社會史打通,積極借鑒社會學科的理論。就近代泰山信仰禮俗而言,該禮俗對于民眾的意義主要在于滿足常態社會中的去病、求子、延壽、發財等日常生活需要,很少涉及政治方面的訴求。近年來,民俗學界在努力建構以“生活世界”為基礎概念的本土化的民俗學理論體系,強調“生活世界首先是日常活動的世界”[37],由此為民俗學拓展出廣闊的學術空間。因而,可以嘗試建構一種以“日常生活”為邏輯起點與歸宿的社會史研究的中層理論,結合區域社會的特色,對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進行新的觀察和透視。時賢倡言“所謂‘歷史本體’或‘人類學歷史本體’并不是某種抽象物體,不是理式、觀念、絕對精神、意識形態等等,它只是每個活生生的人(個體)的日常生活本身”[38]。基于這樣的歷史認識,可以先將“日常生活”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的觀察視角,進而將其建構為一種解釋區域社會變遷的理論框架。這對于深化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的研究或有裨益。
可以預期,在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未來的近代華北泰山信仰禮俗研究將收獲更多的成果,也將筑起更寬廣的跨學科對話平臺,不斷為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拓展新的學術空間。
[注釋]
①已有學者綜述了海內外學界相關的部分學術成果,可參考如下文章:1.吳效群:《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研究史》,《民俗研究》2002年第3期。2.劉曉:《海外漢學家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以英語文獻為中心》,《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3.劉曉:《西方漢學家泰山信仰研究述論》,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2009年。4.李杰玲:《二十世紀日本社科界泰山研究動態》,《泰山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5.陶道強:《近三十年來碧霞元君信仰文化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泰山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6.關昕:《北京東岳廟研究綜述》,《泰山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7.邵珠峰:《近五年碧霞元君信仰文化研究綜述》,《泰山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
②孫慶忠主編:《妙峰山:香會組織的傳承與處境》,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孫慶忠主編:《妙峰山:民間文化的記憶與傳承》,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孫慶忠主編:《妙峰山:香會志與人生史》,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
③按:葉濤關于山東省鄒城市西關泰山香社的調查,在一定程度上運用了“內部觀察法”。見葉濤:《泰山后石塢元君廟與鄒城西關泰山香社——當代民間信仰組織的個案調查》,《民間文化論壇》2004年第3期。
④趙衛東主編:《山東道教碑刻集》(青州昌樂卷),齊魯書社2010年版。趙衛東主編:《山東道教碑刻集》(臨朐卷),齊魯書社2011年版。趙衛東主編:《山東道教碑刻集》(博山卷),齊魯書社2013年版。
[1]吳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間社會的歷史變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王曉莉.碧霞元君信仰與妙峰山香客村落活動的研究——以北京地區與澗溝村的香客活動為個案[D].北京師范大學,2002.
[3]葉濤.泰山香社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趙世瑜.東岳廟故事:明清北京城市的信仰、組織與街區社會[A].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C].北京:三聯書店,2006.
[5]周郢.從廟堂到民間:明清時期泰山文化之轉變[J].民俗研究,2013,(6).
[6]李俊領,張琰.除魅與離心:晚清泰山祈雨禮的變異[J].泰山學院學報,2013,(2).
[7]周郢.中華國山論——兼議泰山的“國山”地位[A].泰山與中華文化[C].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10.
[8]趙世瑜.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寺廟與民間文化——以明清時代為例[A].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C].三聯書店,2002.
[9]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10]蘭林友.廟無尋處:華北滿鐵調查村落的人類學再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7.
[11]李俊領,張琰.民國“盜跖”河神化與泰山民間意識的演變[J].泰山學院學報,2012,(2).
[12]李俊領.俗化與守舊:近代泰山比丘尼生活方式的變遷[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1).
[13]任雙霞.清末泰山信仰在海岱間的傳布——以青山碧霞宮與大澤山日照庵為中心[J].泰山學院學報,2010,(5).
[14]任雙霞.近代大澤山老母信仰與地方社會的構建——以日照庵香會碑為中心[J].民俗研究,2010,(1).
[15]任雙霞.大澤山老母信仰的轉變[D].山東大學,2010.
[16]王守恩.諸神與眾生:清代、民國山西太谷的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17]孫慶忠.妙峰山:香會組織的傳承與處境[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
[18]劉道超.筑夢民生——中國民間信仰新思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9]周星.四大門——中國北方的一種民俗宗教[A].李慰祖,周星.《四大門》[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0]方彪.九門紅塵:老北京探微述真[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
[21]陰法魯,許樹安.中國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22]楊念群.民國初年北京地區“四大門”信仰與“地方感覺”的構造——兼論京郊“巫”與“醫”的近代角色之爭[A].孫江事件·記憶·敘述[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3]李俊領,丁芮.近代北京的四大門信仰三題[J].民俗研究,2014,(1).
[24]曹春婷,邵雍.探析民國前期泰山神民間信仰的特點[J].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25]車錫倫.《泰山天仙圣母靈應寶卷》漫錄[J].民間文化論壇,2016,(1).
[26]EdouardChavannes.LeT'ai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Paris:E.Leroux,1910.
[27]劉曉.海外漢學家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以英語文獻為中心[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
[28][日]澤田瑞穗.中國の泰山[M].東京:東京講談社,1982.
[29]彭慕蘭.上下泰山:中國民間信仰政治中的碧霞元君(約公元1500年至1949年)[J].臺灣:新史學,2009,20(4).
[30]康笑菲.說狐[J].姚政志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31]Vincent Goossaert,The Taoists of Peking,1800-1949: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Harvard UniversityAsia Center,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32]Brian R.Dott,Identity Reflections:Pilgrimages to Mount Tai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
[33]韓書瑞.北京妙峰山的進香之旅:宗族組織與圣地[A].吳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間社會的歷史變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4]華琛.神明的標準化——華南沿海天后的推廣,960-1960年[A].劉永華.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5]彭慕蘭.泰山女性信仰中的權力、性別與多元文化[A].[美]韋思諦.中國大眾宗教[C].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36]徐天基.“標準化”的帷幕之下:北京丫髻山的進香史(1696-1937)[J].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4期),2014.
[37]高丙中.中國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學的路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8]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增訂本)[M].北京:三聯書店,2008.
(責任編輯 梅煥鈞)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Mount Tai Culture in Recent Three Decades
LI Jun-li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
In recent thirty years,in and out experts have made a great results with the views of Country-Society has a discussion on Miao Feng Temple of Beijing,Bixiayuanjun's Standardization,the Image-building and changes on Bixiayuanjun,belief and public,Mount Tai's belief and public life.While it cuts both ways on finding historical data,taking new views and interdisciplinary,there is the limits of single points.The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can notice to:broadening new fields,widening investigation,exerting regional social history,building daily life as a start and end's medium theory.
belief of Mount Tai,etiquette,North China,regional social history
K892
A
1672-2590(2016)04-0070-08
2016-04-12
李俊領(1978-),男,山東金鄉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