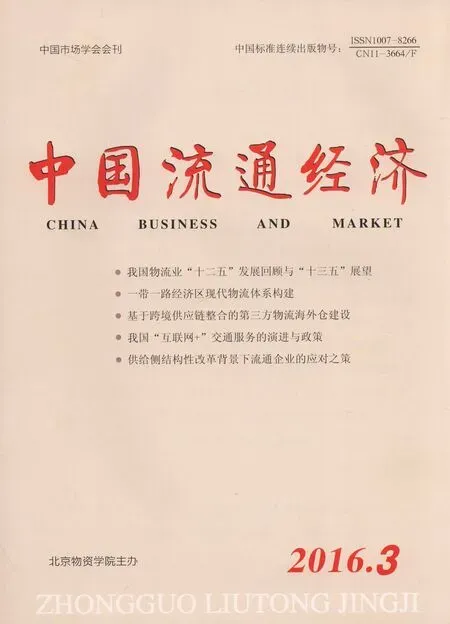快遞人員竊取快遞包裹中財物定性的法律分析
沈玉忠
(北京工業(yè)大學實驗學院,北京市101101)
快遞人員竊取快遞包裹中財物定性的法律分析
沈玉忠
(北京工業(yè)大學實驗學院,北京市101101)
摘要:快遞人員利用工作期間的便利條件,竊取快遞包裹中財物的行為屢有發(fā)生。對此應如何定性,理論界與實務界有不同觀點,爭議的焦點主要是快遞包裹歸屬以及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解。委托人將快遞包裹交付給快遞人員后,該快遞包裹的所有與占有分離,快遞企業(yè)是該快遞包裹的代為管理人即財產(chǎn)保管人。對于“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解,首先應明確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不同于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其次,職務上的便利也不等同于工作上的便利;再次,職務上的便利包括管理上的便利和勞務上的便利,但應對勞務上的便利做出合理限定。在條件成熟時,可增設業(yè)務侵占罪,因為業(yè)務侵占罪更能涵蓋此類犯罪的本質,即侵財性和破壞業(yè)務誠實信用原則。
關鍵詞:快遞人員;職務便利;封緘物;占有;業(yè)務侵占
作為新興行業(yè),快遞行業(yè)對加速貨物流通、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發(fā)揮著積極作用的同時,①由于其發(fā)展不均衡,加上內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快遞人員成為近年來刑事發(fā)案的主體之一,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司法實踐中,快遞人員利用工作期間的便利條件,竊取快遞包裹中財物的行為屢屢發(fā)生,對此行為如何定性,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著不同的觀點與看法。因此,有必要從職務侵占罪的犯罪構成出發(fā),分析職務侵占罪和盜竊罪的界限,從而為案件正確定性提供法律依據(jù)。
一、從一則典型案例說起:職務侵占抑或盜竊
被告人L系北京某速遞公司的押運員,其工作職責是押運貨物、分揀貨物。2014年11月29日5時許,其在公司分揀貨物時,把裝有“萬國”牌和“浪琴”牌手表各一塊的包裹拆開,將兩塊手表裝入自己的衣袋內,后將空的快遞包裹當成問題件交給公司操作部。經(jīng)鑒定,這兩塊手表均系仿冒,“萬國”牌手表價值人民幣2 000元、“浪琴”牌手表價值人民幣3 000元。2015年3月4日,其自動投案。
對于L的行為如何定性呢?在此案辦理過程中,辦案機關有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L行為構成詐騙罪。L將兩塊手表據(jù)為己有,卻將空包裹當成問題件交給公司操作部,使得公司因賠償客戶而遭受損失。L采用欺騙手段,使得公司利益受損而自己從中獲益,故構成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L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占單位財物,是一種職務侵占行為,此時,客戶交付公司快遞的物品被視為公司財產(chǎn)。此外,在本案中,如果不按照職務侵占罪而按照盜竊罪論處,由于盜竊罪、詐騙罪入罪數(shù)額要求低(職務侵占罪的立案標準為5 000元至2萬元,盜竊罪數(shù)額為1 000元至3 000元,另外,多次盜竊的,并未受到上述數(shù)額的限制,②詐騙罪的數(shù)額為3 000元至1萬元),對于快遞人員一律按照盜竊罪、詐騙罪論處,顯然對公司內部工作人員因職務身份不同而導致立法上的不平等。③就本案來說,L的行為因不滿足職務侵占罪的立案標準(在北京,職務侵占罪的立案標準為1萬元以上)而不構成犯罪。第三種意見認為,L的行為構成盜竊罪,因為L從事分揀工作屬于勞務性質的工作,并不是職務上的行為,另外,L竊取的財物并非快遞公司所有的財物,而是客戶所有的財物,因此,L的行為構成盜竊罪。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中,首先應排除詐騙罪之說。理由在于:L的行為并不符合詐騙罪的行為構造,即行為人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手段實施欺騙行為,財物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產(chǎn)生錯誤判斷并處分財產(chǎn),從而使行為人獲取財物而被害人財物受損。[1]在本案中,L竊取包裹中的財物后,將空的快遞包裹當成問題件交給公司操作部,此時,L的行為只是掩蓋盜竊行徑不被發(fā)現(xiàn)的事后不可罰行為。[2]因此,本案的處理主要在于L的行為構成盜竊罪還是職務侵占罪?這里需要解決三個問題:其一,在快遞行業(yè)中,客戶委托的快遞物品是否屬于快遞公司的財物?其二,快遞人員在快遞處理中的掃碼、搬運、分揀、運輸?shù)裙ぷ魇欠駥儆诼殑丈系墓ぷ鳎科淙绾螀^(qū)分經(jīng)手與接手(或過手)?為此,有必要對職務侵占罪展開探討,并結合快遞行業(yè)工作的性質與特點進行分析,從而做出合理正確的結論,為司法實踐中的具體操作提供相應的法律依據(jù)。
二、快遞中快遞物品的歸屬判斷:所有抑或占有
本單位所有的財物作為職務侵占罪的對象是毫無異議的。在快遞行業(yè)中,財物所有人將財物委托快遞企業(yè)運輸時,將財物占有轉移至快遞企業(yè),財物保管人是快遞企業(yè)。此時,快遞企業(yè)占有的快遞物品是否屬于本單位的財物呢?如果答案為“是”的話,快遞人員可以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而存在。因此,在對快遞人員竊取快遞包裹中財物的行為定性時,應首先判定快遞貨物歸屬的問題。對此,學者們存在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占有未轉移說。盡管客戶將快遞物品交付給快遞企業(yè),但是該快遞物品仍然屬于客戶占有,快遞企業(yè)并沒有占有該快遞物品,快遞物品并不屬于快遞企業(yè)的財物。因此,快遞人員竊取快遞中財物的行為不構成職務侵占罪,只能按照盜竊罪論處。其理論依據(jù)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253條的規(guī)定,即郵政工作人員私自拆開郵件從中竊取財物的,按照盜竊罪定罪處罰。該規(guī)定說明對郵件中內容物的占有并不轉移至受托人名下,委托人仍然保留對包裝中內容物的占有。[3]
第二種觀點:占有轉移說。即委托人將快遞件交付給快遞人員后,該快遞件由委托人占有轉移到快遞企業(yè),此時,該快遞件的所有與占有分離,快遞企業(yè)是該快遞件的代為管理人,即財產(chǎn)的保管人。另外,根據(jù)《刑法》第91條第2款規(guī)定,私人財產(chǎn)若在國有公司、企業(yè)等單位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被視為公共財產(chǎn)。于是,根據(jù)系統(tǒng)解釋的觀點,在本單位管理、使用或者運輸?shù)乃饺素敭a(chǎn),應以本單位財產(chǎn)論,理應屬于職務侵占罪的對象。占有轉移說又細分為全部占有轉移說和區(qū)分占有轉移說,前者是指包括包裝物和包裝物內物品隨著委托人交付快遞一并轉移到快遞企業(yè);后者是指包裝物隨著物品交付轉移到快遞企業(yè),但包裝物內的物品仍然由委托人占有。④
第三種觀點:所有與占有一并轉移說。即委托人將快遞件交付給快遞人員后,該快遞件所有權(包括占有權)由委托人轉移到快遞企業(yè)手中,在單位控制中的財物屬于單位所有。此時,該快遞件的所有權歸屬于快遞企業(yè),因為在快遞公司管理、運輸期間快遞件受損的話,快遞公司應負責賠償。[4]
在上述觀點中,第一種觀點值得推敲。占有是一種事實上的支配狀態(tài),不僅包括物理上支配的狀態(tài),也包括社會觀念上支配的狀態(tài)。[1]873根據(jù)臺灣學者的觀點,占有是對物具有事實上的管領權力,具體是指對物的事實支配,并排除他人的干涉,可以依據(jù)社會觀念,從空間與時間上加以認定。空間關系是指人與物在空間上必須有一定的結合關系,時間關系是指人與物的結合在時間上必須有相當長的持續(xù)性,如果只有短暫的結合,不能構成占有。另外,占有的成立,除了事實上對物有管領力外,還必須有占有的意思。[5]另外,占有是一種事實而非權利,但受法律保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占有制度基本功能是維持社會平和及物之秩序。[4]484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第241條規(guī)定,合同關系可以產(chǎn)生占有,由此可以得出,因合同關系可以產(chǎn)生占有的事實。刑法上的占有,是指行為人對財物現(xiàn)實的管理、支配狀態(tài),但并不以實際管領財物為必要。代為保管是指受他人委托而占有,是基于委托關系對他人財物事實上或者法律上的管理、支配狀態(tài)。委托關系包括租賃、擔保、借用、委任、寄存等關系。在快遞業(yè)務中,委托人將物品交給快遞員送到指定人手中,從性質上屬于委托運輸合同,自委托物品交付給快遞員后形成占有關系,此時,物品的所有與占有產(chǎn)生分離,所有屬于委托人,占有屬于快遞企業(yè)。此外,占有應與“得為占有的權利”區(qū)分開,即與所有權中占有權分開,所有權的占有,是本權的重要部分。
根據(jù)我國臺灣地區(qū)“民法”第941條規(guī)定:“地上權人、農(nóng)育權人、典權人、質權人、受寄人或基于其他類似之法律關系,對于他人之物為占有者,該他人為間接占有人。”直接占有是直接對于物有事實上的管領權力,間接占有是指行為人不直接占有其物,但對物享有間接管領權。間接占有人基于一定的法律關系對于直接占有物的人具有請求返還原物的權利。在委托運輸合同中,快遞企業(yè)對快遞物品占有屬于直接占有,委托人對快遞物品屬于間接占有。此時,占有與所有分屬快遞企業(yè)和財物所有人。
在快遞企業(yè)直接占有快遞物品時,快遞人員僅僅是占有輔助者。占有輔助是指具有特定從屬關系的人受指示對物事實上管領的情形。占有輔助人雖事實上管領某物,但不因此而取得占有,系以他人為占有人。輔助占有發(fā)生在受雇人、學徒、家屬或基于其他類似關系,受他人的指示而對于物有管領之力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⑤因此,在快遞人員運送快遞物品時,快遞人員和快遞企業(yè)對快遞物品并不存在共同占有的情形,僅僅為快遞企業(yè)單獨占有。
因此,在委托人將物品交付快遞公司時,物品的所有與占有發(fā)生分離,快遞件占有由委托人轉移到快遞企業(yè),在快遞期間,快遞企業(yè)對該快遞件具有事實上的管領權限,但是,委托人仍然享有該物品的所有權。因此,上述第一種觀點和第三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第二種觀點是值得肯定的。另外,我們在分析第一種觀點時應注意到,盡管快遞行業(yè)與郵政業(yè)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但是,快遞業(yè)不同于郵政業(yè),快遞人員不能認定為郵政工作人員。“郵政工作人員”是指郵電部門直接從事郵遞業(yè)務的人員,包括營業(yè)員、分揀員、發(fā)行員、投遞員、接發(fā)員、押運員、鄉(xiāng)郵員以及有關主管人員。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以下簡稱《郵政法》)的規(guī)定,郵件是指郵電部門傳遞過程中的函件(包括信函、明信片、印刷品、盲人讀物四種)和包件,而傳遞中的報紙雜志和匯票也作為“郵件”對待。因為快遞企業(yè)并不提供郵政普遍服務,快遞業(yè)不屬于《郵政法》調整范圍,因此,快遞人員竊取快遞包裹中財物的行為,不能直接依據(jù)《刑法》第253條規(guī)定,但是,對于上述情形的處理具有參考價值。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也是參考上述條文來處理快遞人員竊取快遞包裹中財物行為的。
就占有轉移說而言,筆者贊同區(qū)分占有轉移說,即包裝物隨著物品交付轉移到快遞企業(yè),但包裝物內的物品仍然由委托人占有。根據(jù)《刑法》第253條第2款的規(guī)定,犯本罪而竊取財物的,依照《刑法》第264條的規(guī)定定罪并從重處罰,說明委托人對包裹物的內容保留占有的事實。此外,占有區(qū)分說在我國臺灣地區(qū)也得到認可。⑥考慮到對包裝物封緘的事實,可以推定委托人對包裝物內的財物實際控制的事實,而包裝物本身則為受托人單獨占有。當行為人侵占整個包裝物時,是對包裝物的侵占和作為內容物的盜竊,兩者構成想象競合犯,擇一重罪處理,因盜竊罪重于職務侵占罪,因此,不管竊取包裝物內的財物還是竊取整個包裝物均構成盜竊罪。在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shù)快遞人員竊取快遞中財物的行為最終以盜竊罪定性處理,正是區(qū)分占有轉移說成立的根據(jù)之一。
三、“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解與分析:職務便利抑或工作便利
(一)“職務上的便利”理解的訟爭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職務侵占罪的客觀構成要素。職務上的便利是基于本人的職權或者因執(zhí)行職務而產(chǎn)生的主管、管理、經(jīng)手本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6]如果行為人僅僅利用在本單位工作、熟悉環(huán)境、便于接近目標等與職務無關的便利條件,不能視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對此學者們并無爭議,但是,理論界與實務界對于“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解不一,直接影響到案件的定性與處理。如何理解“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有以下四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權力便利論。認為職務上的便利應以利用行為人職務上的權力為前提。如果行為人沒有利用自己決定、辦理某一事務上的權力,而僅僅利用從事勞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產(chǎn)的,不構成職務侵占罪。
第二種觀點:權力便利與勞務便利并存論。認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不僅指利用自己職務上形成的權力的便利,而且也可以指利用自己從事勞務、持有單位財物的便利。如是,企業(yè)或者其他單位的勞務人員,利用工作中合法持有單位財物的便利,非法占有單位財產(chǎn)的行為,可以構成職務侵占罪。
第三種觀點:工作便利論。認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就是工作上的便利,公務上的便利和勞務上的便利均包括在內。[7]
第四種觀點則認為,職務上的便利,是指行為人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經(jīng)手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1]908
上述觀點中,爭議的焦點在于職務上的便利是否包括勞務上的便利。第四種觀點回避了“職務上”是否包括勞務上的便利的問題。第一種觀點將職務與權力聯(lián)系在一起,唯有主管、在管理權限內的工作人員才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這顯然縮小了職務侵占罪主體的范圍。第三種觀點將職務上的便利理解為工作上的便利,并將工作按照性質分為組織性工作、腦力勞動工作和體力勞動工作(勞務)。[4]1327由于工作上的便利界限不清,并混淆職務與工作的界限,歪曲了職務侵占罪的立法初衷。相對而言,第二種觀點對職務便利的理解并不局限于管理上的便利,同時,也避免了工作上便利的模糊性,筆者基本贊同第二種觀點。
(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之我見
1.對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解
上述第一種觀點認為職務上的便利是以利用自己職務上的權力為前提條件,這顯然深受貪污罪中“職務上的便利”的影響,從而將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解釋為管理上的便利,從而將利用勞務上的便利排除在職務上的便利之外。其理由有三:(1)根據(jù)系統(tǒng)論的觀點,在同一法律中對同一用語應做出統(tǒng)一的解釋,從而得出在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內涵與外延方面相同的結論,而貪污罪中“職務上的便利”僅指公務上的便利,并不包括勞務上的便利。(2)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構成特別與一般的法條競合關系,[1]1048相較于職務侵占罪,貪污罪除對身份與對象的要求較高以外,其他犯罪構成要素相同,這其中包括“利用職務上的便利”。(3)從兩罪侵犯的客體來分析,貪污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又侵犯公共財產(chǎn)所有權;職務侵占罪侵犯的是簡單客體,即侵犯單位財物所有權。但也有論者認為,職務侵占罪侵犯的客體除了單位的財產(chǎn)權以外,還應包括職務上的廉潔性。為此,只有職務上具有主管、管理、經(jīng)手權限的工作人員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而對勞務人員并不存在職務上的廉潔性,因此,應將勞務上的工作人員排除在職務侵占罪的主體之外。
筆者認為,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文義射程要寬于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首先,從兩罪的立法精神來分析。1979年《刑法》沒有規(guī)定職務侵占罪,僅僅規(guī)定了貪污罪。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非公有制經(jīng)濟不斷發(fā)展壯大,企業(yè)類型不斷豐富多樣,特別是隨著混合制企業(yè)的出現(xiàn),企業(yè)所有制的性質更是難以明確界定。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企業(yè)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產(chǎn)非法占為己有的情形如何處置呢?由于上述行為在客觀上的表現(xiàn)與貪污罪相似,但侵犯的客體又不同于貪污罪的保護客體,同時在行為方式上又不同于傳統(tǒng)的盜竊罪和詐騙罪。司法實踐中,對于上述行為的處置出現(xiàn)不同的方式和結果:有的按照一般民事違法行為來處置,從而削弱對非公有制經(jīng)濟的刑法保護力度;有的將貪污罪的主體進行擴大化解釋,將貪污罪的主體由國家工作人員延展到“其他經(jīng)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但是,司法實務部門對于“其他經(jīng)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界定又缺乏統(tǒng)一的判斷標準,以致將一部分從事勞務而經(jīng)手財物的人員如公交售票員、商場營業(yè)員等認定為貪污罪的主體,混淆了公務人員和勞務人員的界限,消解了貪污罪“從嚴治吏”的刑事政策思想。為此,1995年《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專門引入職務侵占罪的規(guī)定,將公司董事、監(jiān)事或者職工利用職務上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作為職務侵占罪加以處理,從而在刑法中出現(xiàn)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并存的立法格局。1997年在《刑法》修訂時,立法者重新設計職務侵占罪的罪狀,刪除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的規(guī)定。其次,從法條上分析,盡管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之間成為法條競合的關系,構成貪污罪的行為,也契合職務侵占罪的犯罪構成,反之,構成職務侵占罪的行為不一定構成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構成要素與貪污罪構成要素不盡相同,不能得出職務侵占罪與貪污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文義相同的必然結論。最后,盡管對職務侵占罪侵犯客體存在不同的觀點,但是,立法者將其歸于財產(chǎn)犯罪之中,主要考慮到職務侵占罪的侵財性,它與其他傳統(tǒng)侵財犯罪如盜竊罪、詐騙罪等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行為人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
2.“職務上的便利”與“工作上的便利”的界分
何謂職務?有學者認為,所謂職務,是指規(guī)定應該擔任的工作。既然工作包括管理性工作和勞務性工作,因此,沒有必要將勞務性工作排除在“職務之外”。[3]764于是,有論者認為,為了避免“職務上的便利”與“工作上的便利”的過分糾纏,干脆將“職務上的便利”修正為“工作上的便利”。其實,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其一,將“職務”理解為“工作”本身并不嚴謹,《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將“職務”解釋為“職位應承擔的工作”。而職位是指機關或者團體中執(zhí)行一定職務的位置,顯然,職位不同于崗位,職務不同于工作。其二,用“工作上的便利”替代“職務上的便利”的做法也不符合立法的精神。其實,1997年《刑法》對職務侵占罪進行條文設計時,正是考慮到“工作上的便利”內涵與外延的模糊性,將原先“利用職務上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中“工作上的便利”予以刪除,僅保留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種簡單化的處理顯然沒有把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真正內涵。另外,將職務理解為職權,只有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才能認定職務侵占罪,顯然對職務范圍認定過窄;而將職務理解為工作又過于寬泛。筆者認為,職務侵占是行為人將基于職務或業(yè)務所占有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因此,“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職務上形成的權力的便利,也包括利用自己從事勞務而持有單位財產(chǎn)的便利。總之,單位人員不論從事管理性的工作還是勞務性的工作,都屬于職務侵占罪之職務范疇。
3.經(jīng)手與接手、過手的界分
職務是源于工作或者崗位所生成的職責與權限,為此,有必要從實質上判斷職務的性質,即“職務”是指基于職權從事管理、控制、支配、處置單位財產(chǎn)的事務,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因處理單位事務所擁有的掌控、支配、處置單位財產(chǎn)的地位。[8]實踐中,對于行為人利用主管、管理單位財物的行為應認定為“職務行為”,并無太多的異議,在此,有必要將經(jīng)手與接手、過手做出應有的區(qū)分。經(jīng)手財物,是指因執(zhí)行職務而領取、使用、支配單位財物的行為。按照《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接手是指接替;過手是指經(jīng)手辦理。如何將經(jīng)手財物與接手、過手財物做出區(qū)分呢?筆者認為,主要看行為人對自己所接觸的財物是否具有監(jiān)督管理與獨立支配的權限。[3]929如果行為人崗位職責中包含著對所經(jīng)手的財物具有監(jiān)督管理與獨立支配的權限,且在行為人非法侵占財物時并不存在其他障礙時,可以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接手、過手財物的情況下,接手、過手僅僅是單純對財物有所接觸,行為人對財物并沒有監(jiān)管與獨立支配的權限,就不能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快遞業(yè)務中,分揀員、掃碼員、搬運工的工作僅僅在工作流水線的某一個環(huán)節(jié),不能對快遞物件具有獨立支配和控制權限,所以他們工作的性質只能認定為接手或過手。而運輸過程中快遞物品已處于駕駛員、快遞員實際占有和獨立支配范圍內,此時,駕駛員和快遞員的工作性質可以認定為經(jīng)手,若符合職務侵占罪的其他構成要件,可以構成職務侵占罪。
四、結語:業(yè)務侵占罪的設立
為了解決理論困惑和實務困境,有論者提出相應的解決途徑,即單列業(yè)務侵占罪。從國外刑法規(guī)定來看,業(yè)務侵占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侵占罪,具備侵占罪的一般特征,即“變合法持有為非法占有”,但也具有自身特征,就是基于執(zhí)行業(yè)務。業(yè)務應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業(yè)務必須是經(jīng)常、反復執(zhí)行的事務,僅偶爾從事的工作不能稱之為業(yè)務。第二,業(yè)務并不局限于在一定單位從事的工作,也包括基于社會生活地位而反復、持續(xù)進行的事務。[9]在我國刑法中,職務侵占中“侵占”手段與侵占罪的“侵占”存在區(qū)別:侵占罪中“侵占”僅僅指狹義上的侵占,是指非法占有本人業(yè)已合法持有的財物;職務侵占罪中“侵占”是指廣義上的侵占,即并不限于以合法持有為前提,侵占手段包括竊取、騙取與侵吞。因此在我國,將職務侵占罪變更為業(yè)務侵占罪并不存在立法用語的制約,更為重要的是,業(yè)務侵占罪的設立更能涵蓋此類犯罪的本質,即侵財性和破壞業(yè)務誠實信用原則。
注釋:
①2015年初,國家郵政局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至2014年,我國快遞業(yè)務量達140億件,已躍居世界第一位,年人均快遞使用量為10.3件,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公眾服務行業(yè)。
②多次盜竊是指三次以上盜竊。多次盜竊不以每次盜竊既遂為成立條件,也不要求行為人實施的每次盜竊行為均構成盜竊罪。
③一則關系到行為人是否入罪的問題,因為數(shù)額不同,可能構成盜竊罪,但不構成職務侵占罪;二則即使都構成犯罪,但同樣的數(shù)額,職務侵占罪的判刑顯然輕于盜竊罪。
④刑法學界對封緘物整體和內容物占有存在著區(qū)別說、非區(qū)別說、修正區(qū)別說等多種觀點。區(qū)別說認為,內容物為委托人占有,但封緘物整體由受托人占有;非區(qū)別說認為,封緘物中內容物與封緘物整體沒有區(qū)別,均可由受托人或者委托人占有;修正區(qū)別說認為,封緘物中內容物由受托人與委托人共同占有,但封緘物整體由受托人占有。參見張明楷所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第876-877頁。
⑤參見我國臺灣地區(qū)“民法”第942條。
⑥托運人將物品裝入箱袋,加鎖封固,委托運送人運送,在運送過程中,運送人對于整個箱袋因業(yè)務而持有,故運送人如果將整個箱袋吞沒入己,則業(yè)務侵占罪成立;若破壞封鎖而打開箱袋,僅取走箱袋中的一部分物品,而將箱袋交予托運人者,則應為盜竊罪。參見林山田所著《刑法各罪論》(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修訂第5版,第309頁。
參考文獻:
[1]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9.
[2]〔日〕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M].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93.
[3]黎宏.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42.
[4]王作富.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下)[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320.
[5]王澤鑒.民法概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481-482.
[6]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523.
[7]李希慧.刑法各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243.
[8]劉偉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司法誤區(qū)與規(guī)范性解讀[J].政治與法律,2015(1):50-59.
[9]〔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論[M].劉明祥,王昭武.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170.
責任編輯:林英澤
中圖分類號:F259.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66(2016)03-0116-06
收稿日期:2015-12-15
作者簡介:沈玉忠(1970—),男,江蘇省南通市人,北京工業(yè)大學實驗學院副教授,北京市通州區(qū)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助理(掛職),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經(jīng)濟刑法。
Legal Analysis on Qualitative Judgment of Couriers’Theft Behavior in Delivering Express Parcels
SHEN Yu-zhong
(The Pilot Colleg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101101,China)
Abstract:Frequently,there are some cases that couriers steal properties from the express parcels while delivering.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view points on how to make qualitative judgment on these behaviors among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the focuses of debates are on the ownership of the parcel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positions”.After giving the parcels to couriers,the ownership and possession of these parcels will be separated;the express enterprises become the keeper of these parcels.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position facility”,we should first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taking advantage of his position”in position embezzlement and corruption;second,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on facility and work facility;and third,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position facility”includes facility in management and laboring,and we should rationally limit the facility in laboring.When the condition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mature,we could establish the crime of business embezzlement,which can better cover the essence of this kind of crime.
Key words:courier;position facility;the seal goods;possession;business embezz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