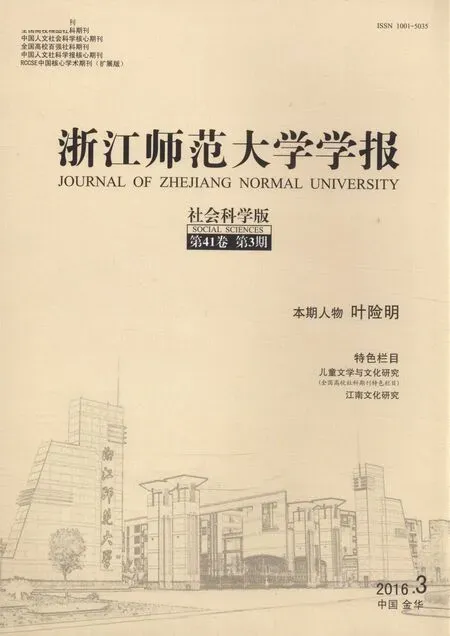“減法”盡頭,如何做文學的“加法”?
——論余華的創作歷程與癥結
黃江蘇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
“減法”盡頭,如何做文學的“加法”?
——論余華的創作歷程與癥結
黃江蘇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第七天》提供了絕佳的反觀余華創作的視角。它集中了余華在“先鋒”時期的實驗性寫作、《活著》時期的溫情寫作、《兄弟》時期的強攻現實寫作,在藝術探索、情感體驗、現實關懷方面,都維系了很高的水準。但是,在人物內在的豐富性、時代弊病的深刻透視上,卻還存在著缺陷。這是因為余華習慣的“文學的減法”的處理方式,已經不適應他日益擴大的文學視野和文學追求。余華需要學習做“文學的加法”,寫出靈魂的深度,不回避對時代精神的建構,在良知關懷的基礎上,再出大作品。
《第七天》;余華;文學的加法
余華擅長做“文學的減法”,在每一個創作階段,他都會揀定一種武藝,而砍掉其他的拖累糾纏。他會將這門武藝發揮到極致,在簡單純粹中顯現出精深博大,這讓他的每一個創作階段都特色鮮明,容易辨識,也因此而容易在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記。他一路走來足跡如此鮮明,以至于我讀到《第七天》時毫不驚訝。我覺得余華就應該有這樣一部小說,出現在他創作生涯的這個節點上。它像是一朵適時的鮮花,從余華的創作藤蔓上自然而然地開出。它攜帶著余華小說過去的優點,也延續著余華小說已經暴露的問題,但又綻放出余華小說前所未有的新質。它既確證著余華小說過去已有歷程的一貫與有效,也預示著余華小說未來將有的突破與結果。它展示了余華小說的精華,也暴露了余華小說的危機與癥結,更啟示著余華小說的出路。因著這些原因,我贊賞《第七天》的到來。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反觀視角,讓我們可以由此把余華小說的過去與現在看得更清楚,并對未來有著更明確的期待。
一、“先鋒”時期的實驗性
回顧余華的文學生涯,先鋒小說是真正繞不過的起點,但也是一個需要辨證看待的命題。先鋒小說在某些評論家那里被視為小說史上一次異軍突起的“起義”,實際上并非如此,它并非突如其來,而是歷史發展大勢中一個必然的流脈。新時期以來,文學領域似乎也在進行著步步深入的撥亂反正,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現代派”,一路走來,文學不斷尋求著對政治枷鎖的脫離,對文學自身的回歸。“純文學”“審美”“現代性”不斷尋求自己的空間與陣地,這種趨向的具體表現,在小說領域有王蒙的意識流小說,在詩歌界有朦朧詩,在話劇界有高行健等人的帶現代派色彩的先鋒戲劇,這股文學探索的浪潮一波接著一波,先鋒小說正是這股文學潮流的合理延續。有人稱它為面向文學史的寫作、形式上的實驗,認為它主要的貢獻即是拆除了文學形式上的藩籬。也有人認為形式即內容,先鋒小說用形式實驗完成了對意識形態轄制的反抗,寫出了某種世界的頹敗潰散的景象。余華身為先鋒小說的一員悍將,在這兩方面都作出了貢獻。
從《十八歲出門遠行》開始,余華創造了很多中國當代文學中自己獨有的招牌。以《現實一種》《難逃劫數》《一九八六年》等為代表的“人性即景,暴力奇觀”,將人的暴力沖動、非理性欲望,寫到了酷烈錐骨的地步。與之相伴隨的,還有所謂“零度情感敘事”,敘述者冷酷而不動聲色幾至消隱。而以《河邊的錯誤》《鮮血梅花》《古典愛情》為代表,余華完成了對偵探、武俠、“才子佳人傳”等文體形式的戲仿與顛覆,與之相伴隨的,也完成了對世界的荒誕、無因果的指認與嘲弄。可以說,在寫作生涯的起初階段,余華就迅速成為了特色鮮明、風格強烈的作家,這是他成名的法寶,也是他對文學史的貢獻。他參與了中國當代先鋒小說的創造,成為這股文學風潮的重要一翼。
但不得不說,即便如此,先鋒小說時期的余華,并不是如今這個在文學史以及讀書市場上聲名大噪、舉足輕重的余華。先鋒小說如同一個作戰團隊,余華即便是其中一員悍將,也不等于全部。如今說起先鋒小說,首先不能不提的恐怕是馬原,他才是導致80年代小說劇烈變革的關鍵樞紐;人們也不得不提李陀,他是發現并保護著先鋒小說成長的助產士。余華只是與蘇童、格非等人一起被提及,他們適逢盛會,共得風氣,聯手締造了80年代“純文學”最輝煌的一段歷史,同時也成就了各自專屬的文學面影。但這遠遠不是他們的頂峰。以余華而論,他這一時期的作品,《現實一種》也好,《鮮血梅花》也罷,它們是可以寫入文學史的“實驗”之作,但卻不是為普通讀者所喜聞樂見的作品,真正令余華風靡于世的,還是他第二個時期的作品。
二、《活著》時期的溫情主義
如果說先鋒時期的余華作品是以冷靜的暴力描寫著稱,那么轉型之后的余華小說,則是以故事中流露的人性溫情感動讀者心靈。之前的冷酷像是故意的鋪墊,為的就是讓之后的溫情更為顯著。這個翻天覆地的變化,讓人思之愕然。寫《現實一種》的余華,那么迷戀于殺戮、傷殘、暴力,或許可以解釋為他出生在醫生家庭,童年在醫院度過,在手術室外見過太多血肉模糊場景的心理折射。后來那個寫《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的余華,其溫情又何所由來呢?在傳記中,余華曾談到,是妻子陳虹教會他悲憫。[1]或許還有兒子的出生,讓他更多出舔犢的溫情?
《在細雨中呼喊》越來越被公認為是余華的轉變過渡之作。一方面,它寫父輩的頹敗,一如先鋒時期的《難逃劫數》《世事如煙》等作品;另一方面,它寫孩子們稚嫩的友情,互相扶持與相互取暖,又如同《活著》與《許三觀賣血記》。它開啟了余華的溫情主義的一個重要模式,那就是寫大人和小孩之間的情誼,包括親情與友情。余華在這上面花了大量的筆墨,也因此而成就了余華的一手絕技,他能夠將之寫得絲絲入扣,纏綿婉轉,讓人望塵莫及。《在細雨中呼喊》寫小男孩魯魯保護媽媽馮玉清的名譽,以及去勞教場找媽媽同住的經歷,實在催人淚下。后來的小說中,幾乎都有類似的情節,《活著》中福貴與有慶,《許三觀賣血記》里許三觀與孩子們,《兄弟》中的宋凡平與宋鋼和李光頭這兩個孩子,包括《第七天》里楊金彪與楊飛。余華對這個模式特別傾心,將孩子的稚嫩與熱誠、弱小與純真,與大人的成熟但落難、悲苦卻柔情,想方設法地交織在一起,將相依為命之情,寫到溫馨柔和的極致,每每要觸到人心的最柔軟處,讓人落下熱淚來。
余華的溫情還表現在對人間苦難、人性善惡的容忍與諒解上。在《活著》里,福貴遭遇了那么多家國之痛,命運之殤,可是他幾乎毫不在意,總是能輕易地與苦難和解,隨遇而安,從不呼號抗爭,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庶幾近之。他被抓壯丁,離開妻子兒女那么久,他沒有怨恨;他的兒子因為權勢者而被抽血抽死,他也沒有抗爭。《許三觀賣血記》也是這樣,他貧窮到只能賣血,賣完血還要為了討好管著兒子插隊的隊長而陪酒,直到胃如刀絞天旋地轉,他沒有怨恨;他家里窮得揭不開鍋了,他還帶著兒子們躺在床上幻想著吃紅燒肉而不怨恨。相反,福貴和許三觀都充滿了偉大的諒解與寬恕精神。福貴諒解了導致兒子死亡的間接責任人春生,許三觀諒解與寬恕了情敵何小勇。
余華不僅著力塑造這種溫情的人物,還極力塑造一個有情的世界。《活著》里面,福貴最終在一頭老牛身上找到了慰藉,在生命的盡頭依然保存了與家人相依為命的感覺,這個世界終究是充滿溫度的。《許三觀賣血記》里,余華則寫到在風雪旅途中,一路賣血的許三觀夜宿旅館,遇到一個好心人,把自己的豬崽借給他,放在被子的一頭,暖他冰冷的腳。閻連科在分析余華的成功時曾說:“余華小說中的暖意的悲憫,疼痛中的撫摸,這正符合我們傳統的閱讀習慣。”[2]實在是同為作家的犀利之見。這是余華在先鋒小說之后魅力不減、聲名日盛、占領龐大的讀書市場份額、感動無數讀者心靈的不二法寶。
三、《兄弟》時期的強攻現實與危機爆發
《兄弟》讓余華遭遇了最大的批評之聲,這大概是余華和讀者都沒有預料到的。爭論漸漸遠去之后,《兄弟》在余華創作中的位置和特質,它的特長和短處,一天比一天顯得清楚。它對余華的文學世界最大的貢獻,還是余華自己概括得最好:它讓我獲得了對現實發言的能力。[3]
有人稱《兄弟》是正面強攻現實的作品,這的確道出了一個事實。無論是先鋒小說時期,還是《活著》時期,余華小說都缺乏現實背景。雖然名為《現實一種》,可卻是出于對“虛偽的真實”的警惕,轉而挖掘內在的、暴力欲望的現實。即便是20世紀90年代貌似轉向寫實的三部長篇,實際上也是看不到社會現實的。《在細雨中呼喊》只寫父輩的墮落和孩子們憂郁的童年、殘酷的青春,卻看不到廣闊的社會背景,孫蕩小鎮像一個隱約漂浮在氤氳水汽中的舞臺,其上的人物雖各有職業,卻絲毫不見他們的社會生活牽連其中。《活著》也是一樣,那么多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幾乎都是寥寥數筆帶過,它們頂多只為人物的相遇或離別、生存或死亡做一個媒介和鋪墊。《許三觀賣血記》的情況也與之相像。
為什么會這樣呢?由這里,就可以探討到余華創作中的一個關鍵問題了。眾所周知,余華不以學問見長,他不喜歡寫得太實,為寫作去查閱資料,追求史實的精細或史詩的宏大。他是一個很親近生活的作家。可要命的是,他又是一個缺乏生活的人。他生在醫生家庭,沒有農村生活經驗,沒有體驗過底層疾苦。青年時期作為牙醫,一度除了病人的口腔之外無風景可看。此后寫作道路順利,迅速成名,成了專業作家,更由此一頭扎在文字虛構的世界里。他不像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莫言、閻連科,也不像60年代的劉震云,他的生活經歷相對單一。在某種程度上,他是個先天不足的作家。這是他的小說中現實背景模糊的重要原因,甚至也是他作品數量相對稀少的重要原因。所幸的是,余華是一個聰明的作家,懂得揚長避短,用某方面的才華掩蓋自己的先天不足,這才華,就是有評論家所稱為的“文學的減法”。[4]
所謂“文學的減法”,余華到底減去了哪些東西?結合文本來看,余華首先是減去了(弱化了)小說的歷史背景、時代環境、社會關聯等元素,其次也減去(弱化)了小說事件、故事情節的復雜性。與莫言、閻連科、格非等同行相比,余華小說不以懸念迭起、跌宕起伏、多線發展、前后呼應等特點取勝。它不像是大江大河,而像是清淺小溪;它沒有劇烈的沖突,沒有泥沙俱下,沒有支流的分叉密布,沒有峰回路轉的呼應。它在恢弘感、立體感方面稍顯欠缺。一個明顯的表現是,余華的小說總給人人物稀少的感覺。《在細雨中呼喊》還有點人物群像的意思,可是到后面,《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都只讓人記得那兩個主要人物,即便是他們的家人,家珍、許玉蘭等,也都像個陪襯,其他人則更像是跑龍套的,出場應個景。最重要的是,余華減去了人物內在的復雜性。“先鋒”時期和《活著》時期,余華小說的人物都是符號化的,是某種觀念的化身。《現實一種》中,山崗是暴力與恐懼的化身,《活著》中福貴是“忍受而活著”的化身,如此等等。余華很少正面表現他們的心理沖突,經常略去其性格發展的歷程,略去其性格的復雜性,只發揮和強調人物某一方面的特質,所以很難稱得上有對其靈魂的拷問,以及寫出其心靈的辯證法。他們好像僅供余華驅遣著,去完成各自的使命。這個問題,也得到了余華自述的確認,他認為情況是從《兄弟》開始改變的。[5]
情況真的改變了嗎?《兄弟》的確難得地寫到了當下的社會現實,寫到了當代人精神世界的浮躁景觀。比起余華以往的小說,它在篇幅、人物數量、歷史跨度、社會生活的廣闊度、故事情節的跌宕起伏、驚異離奇程度方面,都有大幅度的加強提高。但這就是真正地正面強攻現實了嗎?或者說,這就是成功地正面表現了現實嗎?
我認為,需要回到文學的古老定義,文學仍然是某種“人學”。文學作品并不會因為它表現了某種現實就自然而成為優秀的,它必須不僅僅是寫到,而是要“寫出”現實的精魂,而這就需要在寫出人物的復雜、靈魂的深度上下功夫。《兄弟》在這方面仍然是不成功的。宋凡平、宋鋼、李光頭是讓人越回想越覺得豐富深刻的人物嗎?在時代的巨大變遷面前,曾經沉靜好思的宋鋼,到底有過怎樣的思想認識與情感體驗?《兄弟》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顯然難以讓人滿意。余華得意的,不過是他控制不住李光頭這個人物了,不再是他驅遣著人物,而是人物自己管自己說話了,但是,李光頭這樣一個亂世梟雄,粗短顢頇,能說出什么有深度的話呢?所以,我對于《兄弟》的不滿,不在于它寫了偷窺屁股、處美人大賽等,因而是不道德的小說,我從來不這樣認為,我對它的不滿只是,它寫了一個病態混亂的時代,寫得很到位,但是除此之外,它沒有表現出任何更多的東西,它對這個時代的亂象缺乏足夠的抵抗力。它幾乎是一部抱著時代的亂象而與之偕老的小說。時代是這樣膚淺和浮躁,小說原封不動地把它攝取下來。這就夠了嗎?我心里總是不贊同的。在浙師大余華研究中心舉辦的活動上,我曾當面說起閱讀《兄弟》的感受,認為這樣厚厚兩本書,我一個白天就看完了,毫無閱讀障礙,毫無中途的停留與思考,說明這部作品缺乏有深度的東西。余華若有所思地聆聽著,突然冷不丁問了一句:“你說的有深度的東西到底指什么?”我一時語塞,沒想到一個成名已久的作家,突然問你作品中有深度的東西是指什么,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難道這個問題從來沒有進入過他思考的領域?現在想來,我當時說的深度,其實就是人物內在的豐富性,小說中體現出來的對人性、對時代精神的深刻獨到的發現與理解,甚至是作家超出常人、超越時代的精神建構能力。你能想象,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作家會回避這些問題嗎?一個作家如若放棄這些承擔,只滿足于做一個平凡的、等同于常人的觀察者、講述者,那他何能稱為偉大?而余華之所以對這些問題還顯得漠然,其原因和癥結,恐怕就在于他因著先天的局限,因著揚長避短的需要,過于沉浸在“文學的減法”中的緣故。通過做減法,他讓自己某方面的特長得到了極致的發揮,這成就了他的輝煌。但是,這種文學處理方式,已經與余華日益擴大的文學視野出現了不適應的癥狀,這把小刀,已經解不了大牛,再不放棄,就將成為牢籠,讓余華的文學突圍力不從心了。
四、《第七天》:集大成的特色重溫與新的出路
《第七天》像是對過去每個階段特色的重溫。首先,它寫了一個人鬼交融的世界,這像是“先鋒”時期實驗性寫作的繼續。它讓人想起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如同蘇童前幾年的《河岸》讓人想起巴西作家若昂的《河的第三條岸》,這都還有著先鋒小說時期借鑒西方現代小說的色彩,雖然已經更本土化了。其次,它延續了《活著》時期的溫情主義,這一點尤其值得細說。小說開篇就以濃霧、空虛混沌等詞營造悲涼凄怨的氛圍,并很快以胸口繡著前妻名字的睡衣,牽出一段凄惻感傷的愛戀,寫一對孤獨的男女,如何從隔閡、猜忌到融冰、相戀,并在人生的風雨中由甜蜜溫馨轉為勞燕分飛。接下來又寫到了憨厚質樸的鐵路工人,以慈心和熱誠,撫養一個棄嬰,天真的小孩與木訥的成人相依為命。前文說到,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等作品中,曾著力于描寫父親與幼子之間細微撓人的柔情,在《第七天》中,他重拾起這一武器,瞄準人心中柔弱的這一處,不斷用力,用溫婉的文字去觸碰這一點。楊金彪為著婚姻,痛苦地將年幼的楊飛遺棄,又忍不住煎熬,千里迢迢把他尋回;年老病衰,自覺人生無望的時候,他悄然出走,重訪當年的遺棄地,并在那里咽下了人世的最后一口氣。將一個質樸漢子對兒子的舔犢深情,寫得如此細膩哀婉,又如此蕩氣回腸,余華恐怕是當代作家里面最好的。書的后面還有鼠妹與男友的愛情,死無葬身之地的鬼魂們互相扶持的情義,都明顯地承襲了《活著》時期的溫情主義。
但以上這些都還不如對《兄弟》時期強攻現實這一特點的繼承力度大,這也是《第七天》最顯眼的特征。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它對大量的社會熱點事件的反映。《兄弟》其實還只是通過寫幾個人在當代的命運變遷、一個小鎮在當代的天翻地覆的變化,來寓言般地表現中國的變化,《第七天》則直接表現了“一個國家的疼痛”。舉凡過去幾年的熱點事件,暴力拆遷、群體散步、商場大火、冤假錯案、襲警、賣腎、蟻族等等,都在書中出現了。這是余華讓人側目的地方,他兌現了《兄弟》出版后的話,獲得了對現實發言的能力,寫出了一個國家的疼痛,而沒有讓這些成為大言欺世的空談。這也證明了他的創作道路之連貫與有效。看來,余華真的變了。這個“十八歲出門遠行”的孩子,走過了“現實一種”,也走過了“活著”,他開始關注更多人的活著。他想在書里一下子寫出更多的生活面相,寫出他們具體而微的難處,而不是在虛構中、在寓言般的故事中,簡單地展示一種品質或能力。余華從抽象的人性、從寓言般的存在中,走入了熱氣騰騰、喧囂雜亂的中國現實里。
但是,《兄弟》所暴露出來的余華的短板依然存在,這是因為癥結依然存在。這就是我已經提到的,余華習慣了的“文學的減法”的方式,天然地不擅長處理復雜龐大的題材。在《兄弟》里,故事的社會背景真實鮮明了,現實社會生活的素材加多了,可是它們停留于表面,人物內心與社會精神的豐富深刻性并沒有增加。《第七天》仍然是這樣。許多人詬病它是“新聞串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他們不去探究背后的原因,沒有看到是余華習慣了的文學處理方式在適應題材方面出了問題。要克服這個問題,余華需要放下自己已經得心應手的武器,改做“文學的加法”;在寫慣了校園民謠之后,要學習寫作交響樂。但這加法不是像《第七天》現在呈現的這樣,把過去已有的元素集合到一本書里,而是要在人物內在的豐富性上下功夫,在人物經歷環境與事件時其靈魂的深度反應方面下功夫。譬如《第七天》中的楊飛,當然他已經成了一個鬼魂,一定程度上可以為他的形象之模糊與單薄開脫,否則我真的要質問,他除了一點樸實(將對李青的感情埋藏在心里不敢表達)、同情心(憐憫求愛失敗成為笑料的同事)、以及柔弱(對離婚與各種挫折逆來順受)之外,他還有什么?作為一個游魂,他看到了那么多別樣的故事,他的反應有什么區別與變化?還有其他人,譬如鼠妹和男友,他們在小說中的形象也過于扁平了,除了在所有的市井故事中都會聽到的那些言行,余華為他們添加了什么?這些都需要作家去做加法,去深入了解這些人的生活和內心,真正貼近和深入他們的靈魂,而不是浮皮潦草地道聽途說,簡單轉述。要寫出這些,也需要更多的筆墨。在接受采訪時,余華說寫這部小說用幾十萬字不算本事,用十幾萬字寫出來才叫功力,[6]我覺得有點掩飾和強辯的味道了。某種程度上,這是不愿做“文學的加法”的一種遁詞。否則,余華在這部小說中還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還是前面引用過的閻連科的評語說得到位,余華滿足于做“疼痛中的撫摸”,滿足于“以情動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著力于驅遣文字,去營造骨骼們捧水為鼠妹凈身這樣的溫情畫面,而刪削了太多應有的理性思考。正是這一點,使他的文學品質缺少飽滿,平面化、符號化的癥結仍然沒有得到救治。早期在先鋒文學的旗幟下,這還是個長處,讓余華的作品特色鮮明,容易辨識。但沿襲到當下,它已成了余華創作的瓶頸,這一點不破除,余華在小說中植入再多的社會現實事件,也仍然沒有寫出時代精魂,沒有穿透現實表象,讓文學凝結為永恒堅實的時代雕像。
當然,也不能苛責余華。除了在技術層面有待商榷以外,《第七天》還是在另一個方面展示了余華可貴的新質,那就是作家的良知。寫《一九八六年》《活著》時候的余華當然也是有良知的,可是《第七天》中它表現得更加直接、迫切、別樣。《兄弟》寫偷窺女人屁股、處美人大賽,雖非不道德,但總有點嬉皮笑臉、荒唐不經的感覺,《第七天》除了有一處閑筆寫男子受拆遷驚嚇生殖器只會滑行不會起飛了顯示了一點惡趣味以外,大體上是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身,余華變得嚴肅了,有擔當了。在當代知名的純文學作家中,余華大概是第一個如此大面積地反映最近的尖銳時事的作家。這是他的獨特貢獻,他把這些都寫入了文學,并且順利出版。有人說余華是寫給西方讀者看的,我對這種說法非常氣憤,他們扭曲地揣測動機以貶損作品,遮蔽和抹黑作家可貴的良知,其害無窮。還有那種以“新聞串燒”為由而嗤笑這部小說的論調,我也不敢茍同。為什么新聞報道過了文學就不能寫?文學吸納社會新聞,不但可以,而且應當,魯迅的文章,不也是大量針對社會新聞嗎?恰恰在這一點上,能顯示出作家的勇氣與擔當。也許在技術層面上,《第七天》的寫法還存迷思,我在前文已經指出,但因此而對余華直面時弊、同情弱小的良知毫無感應,我覺得這才是大無知、大愚拙、大損失。的確,包括我在內,批評家們的心是越來越麻木了,我們在網絡上已經看過太多冠絕人寰的慘劇,練就了類似泰山崩于前而面不變色的“大心臟”。現在,有一個作家,以其悲天憫人之心、憂國傷世之情,將愚民黔首之哀苦無告、暴吏悍匪之橫行無忌、紅塵男女之辛苦恣睢、老弱婦嬰之病痛無依,一并寫進這本書,端到我們面前,他已經言人所不敢言,寫世所不敢寫,我們不但不脫帽致敬,反而壅塞心脈、死寂感覺,視仿若不見,讀仿若無思,簡單嗤之為“新聞串燒”,一笑而過。這實在是以冷血澆熱血,以懦弱鄉愿而敵視有大關懷之俠者。嗚呼,其可鄙也。我敬佩余華的《第七天》,哪怕它通篇都是憂傷,只能虛畫一個美麗的死無葬身之地來給人虛幻的慰藉,但我仍然贊美他的良知。我相信關注就是力量,當文學也來參與當下時代的記錄,當文學顯示出寬厚的關懷,它就是有出路的。我因此對余華的下一部作品充滿期待。
[1]洪治綱.余華評傳[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107.
[2]閻連科,張學昕.我的現實 我的主義:閻連科文學對話錄[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69.
[3]余華,張英.余華:我能夠對現實發言了[N].南方周末,2005-09-08(12).
[4]張清華.文學的減法——論余華[J].南方文壇,2002(4):4-8.
[5]洪治綱.余華研究資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5.
[6]夏琦,余華.余華談新書《第七天》:我會關注批評,但不是現在[N].新民晚報,2013-06-25(B08).
(責任編輯周芷汀)
When “Subtraction” Has Come to an End, How Does He Do Literary “Addition”?: On the Process of Yu Hua’s Literary Creation and Its Crux
HUANG Jiangsu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TheSeventhDayprovides an excellent contrast perspective on Yu Hua’s creation. It covers Yu Hua’s experimental writing in the avant-garde period, warmth writing inToLiveand the concern for reality inBrother, which has maintained a very high level in artistic explora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reality concern.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inherent richness of the character and the depiction of ills of the times, it is still flawed. This is due to Yu Hua’s habit of “literary subtraction” approach that no longer meets the growing of his literary vision and literary pursuits. Yu Hua needs to learn to do “literary addition” that writes the depth of the soul, does not avoi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so as to create more masterpieces based on conscientious caring.
TheSeventhDay; Yu Hua; literary addition
2016-03-15
黃江蘇(1983-),男,湖南寧遠人,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研究員,文學博士。
I206.7
A
1001-5035(2016)03-007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