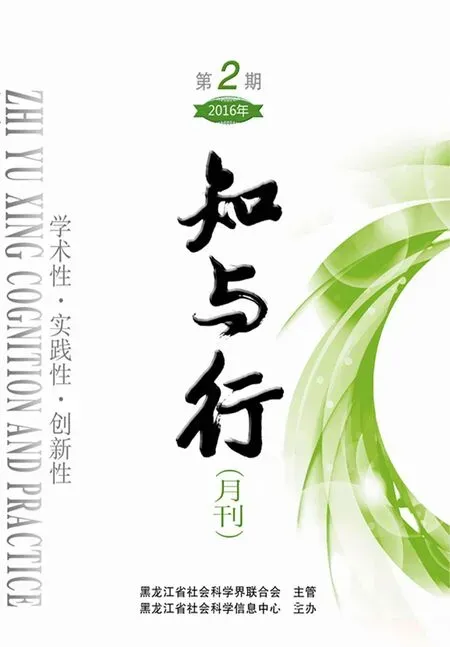對曾奇峰“三角形理論”的反思
張鑫焱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法學院,杭州 310015)
?
博士碩士論壇
對曾奇峰“三角形理論”的反思
張鑫焱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法學院,杭州 310015)
[摘要]曾奇峰將歐文·亞龍的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理論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相融合,提出了“三角形理論”:每個人的“人生舞臺”就像三角形,“生”“死”為其中兩點,決定面積的另外一點是“父母”,而“心理治療師”可以替代“父母”的位置——成為“修正父母筆誤的人”。但是,“三角形理論”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缺陷:“我的人生舞臺”沒有“我”的位置。造成“三角形理論”無法穩固的原因是兩種理論傳統無法融合,兩者之間的差異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傳統是性壓抑的決定論,而歐文·亞龍的存在心理治療則是關于存在四個基本事實的非決定論。其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傳統強調治療師對病人過去的詮釋,卻忽略了病人自身的意志。而歐文·亞龍的存在心理治療則強調病人的自我覺察。最后,弗洛伊德將治療師的功能設定為詮釋,治療師成為病人的“再造父母”。而歐文·亞龍則將病人—治療師真誠地相會作為有治愈能力的關鍵環節,治療師是病人靈魂的助產士。
[關鍵詞]“三角形理論”;精神分析;存在主義心理治療
曾奇峰先生為歐文·亞龍的著作《愛情劊子手》寫作了中譯序《學習活著》,將這位注定位列大師行列的人推薦給中國讀者。這篇文章除了具有介紹的功能之外,也融入了曾先生自己對于心理治療的思考,以及對中國當今心理學界的思考和批判。《學習活著》表現出來的對于“科學主義”的批判,以及對于人性思考的責任感深深吸引了廣大讀者,曾先生在文中提出的“三角形理論”也十分值得反思。
一、“三角形理論”的提出
曾奇峰在談到生命的局限性時說:“對于每個個體來說,生命就是在一個小小三角形平臺上的自由之舞。”三角形的面積是有限的,如何能夠稱之為“自由之舞”?好在他馬上做出了補充,“名為自由之舞,其實卻并不自由”。曾先生是從存在主義心理學的角度闡釋生命的自由與限度,“構成這個三角形舞臺的三個點是:出生、死亡和父母”。這三個因素太過稀松平常了,是每個終有一死的生命都必然存在的,為什么選擇這三個點呢,要繼續看曾先生的闡釋。“出生是之前無邊無際的黑暗的終點,也是生命的起點,在任何意義上,也是死亡的起點。”沒有前生因果,沒有后世拯救,僅有在此存在的一生,斯多葛學派的說法“每個人一出生就走向死亡”不是在“某種意義上”正確,而是“任何意義上”都為如此。死亡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生命真相,可是,每個人都在用盡辦法逃避和否定死亡,這就是歐文·亞龍“存在主義心理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假設。用形象一點的話來說就是:“每一口呼吸,都使我們暫時逃離不斷沖擊我們的死亡……但最后獲勝的,必然是死亡,因為從出生以來,死亡就是我們的命運,它只是在吞噬獵物之前玩弄一番。可是,我們卻一直對生命抱持大量的興趣和妄念,就好像竭盡所能地吹肥皂泡,希望越大越好、越久越好,但肥皂泡卻注定爆裂,化為烏有。”[1]1
可見,曾先生對于“從出生到死亡”這條邊的闡釋與歐文·亞龍關于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根本假設不謀而合,“連接出生和死亡的那條線,構成了三角舞臺不可撼動的那條邊,對于生者來說,這條邊長一點或短一點,并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因為它只會是線段,而不會是射線”。可是,如果只是這樣的話,那就還是在歐文·亞龍的理論體系下沿用引介,并無任何創新改造,少了一個點的“三角形理論”也明顯欠缺完整性。
“三角形舞臺的另一點,即父母,決定了變數最大的另外兩條邊的長短,也決定了舞臺的實際大小。”這另一點(父母這一點)成了決定性因素,生死線段之外的一點決定了距離生與死兩點的距離,也就確定了三角形舞臺的面積,“人生的千差萬別也基本由此而來”。“基本”一詞標定了人的一生,可是,“我”的人生由父母決定,這一聽起來就不那么令人舒服。曾先生如此說一定有他的道理,先是生物學方面,“父母對一個人的生物學存在的決定,已經不用說了”——我們帶著父母的基因來到這個世界,生物學上的傳承決定毋庸置疑;當然,還有精神心理方面,“父母對精神上或者人格上的決定是心理學或者至少是精神分析學關注的焦點。童年決定人格,而人格就是命運,幾乎變成了全人類的共識”——曾先生作為心理學家對人的精神和人格尤為看重,可能深恐“心理學”這個詞太大而導致論述不夠精確,特意加上了保護性的“或者至少是”來確保論證的合理性,可見,精神分析學是曾先生欣賞和研究精通的領域。
二、分析“三角形理論”:“我的人生舞臺”沒有“我”
(一)童年決定人格
一個人的性格在童年時期就已經形成并確定下來。弗洛伊德認為心理分析就是考古學,過去的心理事件從未完全消失不見,只是保存下來成為未來心理事件的地基,如“不朽之城”羅馬的建造一樣,“同一塊土地將支撐圣瑪利亞和密涅瓦教堂,以及教堂下面的古老寺廟”。于是,弗洛伊德典型的方法就是對自我感覺早期階段所建立的地層進行考古調查,發現那些生活的陰影或者被壓抑的本能。這種方法所遵循的就是弗洛伊德所建立的這個原則:“在心理生活中,過去能得到保存,這是規律,毫無例外。”[2]64新弗洛伊德派并不遵從本能—壓抑這一沖突來描述人,而是著眼于文化與環境對人的形塑。兒童需求安全感,需要得到肯定和接納,可是這些自然成長的傾向卻又不一定會得到成人環境的認可和滿足,于是形成了沖突的核心,而父母這一小型社會在兒童成長初期所起到的人際作用無疑是至關重要的。雖然新弗洛伊德派與弗洛伊德的理論有著不同(發生了從個體沖突到人際關系沖突的轉變),但是他們無不認為“過去—童年”(心理發展的早期)成了決定人生性格的關鍵始基,所有過去的東西都得到了保存,并對未來的心理建造施加著持續不斷的影響。
(二)人格就是命運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洞察到的是“性格決定命運”,這一觀點并不是讓我們服從于命運的決定論,而是強調一切都處于運動變化之中的非決定論,即便命運也可以改變,改變命運的核心就是改變人的性格。可有些人還是會覺得這句很有道理的話似乎什么也沒有講,因為性格是由什么來確定的并未得到明確的闡釋,遺傳基因、環境、模范,等等,到底哪些因素起到作用了呢?曾先生給出了一個明確的答案:父母。之所以給出這個答案,是因為“童年決定性格”,父母對于兒童早期心理的塑造和影響無疑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曾先生并不滿足于將父母具象化為家庭中具體的人格類型,而是將之泛化為“習俗環境”,“從父母往上追溯,幾代、甚至十幾代,每一代人的性格與生活都不會就那樣消失了,都會以某種方式儲存在某些地方,影響到當下的個體,影響到他或者她的現實生活”。這個判斷背后所體現出來的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決定論傳統。
(三)“我的人生舞臺”沒有“我”
在曾先生的“三角形”理論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傳統。而且曾先生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則夾雜進入歐文·亞龍的存在主義治療之中,形成了“三角形理論”。但“三角形理論”卻存在一個巨大的缺陷:三角形的兩點——“生與死”所組成的線段都是“我”之外的東西,而第三點“父母(傳統)”決定了我的性格,我的命運確定了“我”人生舞臺的面積。如果在小型社會家庭中出現了父母—子女關系的災難(那可能是無法逃避的必然)怎么辦?不必擔心,“心理治療師”可以“修正父母筆誤”,替換父母的位置,這種說法可能不像“修正上帝筆誤”的人那么狂妄,但心理治療師能夠替代上帝的位置成為我們的“再造父母”也是一種對自身從事職業極其驕傲的表述。決定我的人生舞臺大小的第三點變成了心理治療師,為什么不是哲學家?“我的人生舞臺”為什么沒有“我”存在的位置?
三、反思“三角形理論”:三重差異
三角形理論是歐文·亞龍的存在心理治療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傳統相結合的產物,但是決定三角形面積的那至關重要的第三點卻完全是弗洛伊德式的而非歐文·亞龍式的。這兩種心理治療傳統是無法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導致三角形理論不堪重負的原因是其兩個理論基礎完全無法融合。
(一)動力模式的差異:性壓抑與存在的四個基本事實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傳統的動力模式。弗洛伊德以考古學家的審慎與堅韌,深入挖掘層層累積起來的心理地層,直抵童年早期的陰影沖突。尋找到病人早期生活事件對于心理留下的那些創傷經驗,創傷所引發的原初情緒可能已經消散而使得創傷的印痕模糊不清,但是這些創傷的記憶以及所伴隨的情緒從未真正完全消失不見,只是被潛抑在了意識之外,這些創傷記憶固執地存在于潛意識之中。當預期到某種類似的危險會再度發生之時,這些潛抑的情緒就會轉化為身體的癥狀,最終在意識中得到展現,重新引發焦慮。心理治療師使用催眠或者自由聯想的方法,幫助病人回憶創傷,重現原初引發問題的記憶,再次用言語和行為釋放出被壓抑和扼殺的情感,讓那些在無意識中潛伏的受到禁錮的情感重新進入意識,得到宣泄排除。
弗洛伊德認為引發人之焦慮的根本性來源是性心理方面的不幸,最受他關注的兩種焦慮是:失去母親(分離)和失去陰莖(閹割)。這兩種焦慮的共同點是:失去(失去與母親結合的能力;失去愛的能力),失去產生無助,從而引發焦慮。從時間上來看,最早發生的應該是分離,從每個人誕生的那一刻開始,這種焦慮就已經發生了,但是,考古學家弗洛伊德并沒有執著于時間上的開端,而是堅持理論上開端的在先性,用自然的性驅力與社會的性壓抑之間產生的能量沖突來科學地構建心智機器[3]6,故而做出了復雜的設定:時間上早期的“分離”不過是為“閹割”所做的準備,在理論上“最早的焦慮經驗”是閹割焦慮[4]104。
如此一來,弗洛伊德的思考路向沿著設定好的方向行進:第一,人生早期(童年)的創傷記憶成為之后焦慮的根源。第二,創傷的本質與性心理的不幸相關,也就是與“閹割”所引發的焦慮相關。其動力模型可以概括為:性驅力——焦慮——防衛機制。
2.歐文·亞龍存在主義心理學的動力模型。歐文·亞龍的存在主義心理學的動力模型并非基于性本能的壓抑,而是依賴于對四個存在基本事實的自我覺察,只要人們反思自己在這個世界之中的生存境況,就會發現這四個基本事實。這四個存在基本事實是:死亡、自由、存在孤獨、無意義。
(1)死亡是每個人都無法逃避的基本事實,從我們一誕生就跟隨著我們,但是人們卻想盡辦法逃避死亡——相信自己是特別的(內部),或者相信有終極的拯救者(外部)。為了逃避死亡所制造的幻象可能會越吹越大,可是再美麗的肥皂泡也終究難逃破滅的命運,死亡終會來臨。
(2)自由一直是一個正向的概念,現代西方的歷史不就是為了自由歡呼吶喊嗎?可是,從存在的角度來看,自由意味著每個人都生活在偶然之中,并沒有一個已經建構好的、確定意義的宇宙,神并沒有預先設定好你的生活程式,一切都是你自己自由選擇的結果。宣稱“上帝死了”的尼采在這空前的大崩潰中看到了自由的“海洋”,“我們的航船再度起航,……海洋,我們的海洋又重新敞開了,也許從來不曾有過如此‘開闊的海洋’”[5]343。與尼采歌頌強者的生活和擁抱海洋般開闊的無限自由不同,弗洛姆則提醒我們普通人往往會“逃避自由”,因為自由意味著承擔責任,人必須要為自己的生存境況負擔起全部責任,不能將之推卸給某種超自然的力量,而這是普通人無法承受的東西。就如同亞當在伊甸園中的推諉一樣,當面對神的問責時,他說:“是你造的那個女人,叫我吃的!”亞當把自己本應當承擔的責任轉移給女人,甚至間接轉移給創造神。自由令人彷徨無措,人們渴望穩定的結構來謀劃自身的生存,出于簡單易行躲避思考的原因,人們往往會無思地臣服,或者服從于傳統習俗,或者服從于大多數人的意見,或者服從于某個權威的觀點,以此來逃避自身所應當承擔的責任。于是,一種奇怪的境況出現了,人人呼喊的自由竟然變成了人們最不想要的東西,人們逃避自由。
(3)孤獨所指的并非單純情緒性的孤獨,而是存在上的孤獨。與他人分離的人際孤獨,以及與自我脫離的內心孤獨都不是存在上的孤獨。存在孤獨是一種更徹底的孤獨,它代表著一種疏離狀態:個體從共同體中疏離出來才能看清楚自身生存的境況,只有從預先設定好的目標和價值判斷中脫離出來并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夠獲得視角上的康復。所以,尼采說真正的自由思想者必須是“‘孤獨’的發過誓的、招人嫉妒的密友”[6] 44。但是,如此出離必然會增強孤單感而引發焦慮,人們需要彼此擁抱以互相取暖,融合會驅散孤獨,但也會讓人們失去“有懷疑能力的自我覺察”[7]10。
(4)無意義是因為我們并不存在于這個已經預先規劃好意義的世界之中,為什么而活、如何活、生命的意義等問題并不是預先給定答案的,而是需要人自己去構建的,人們被拋入這個完全沒有意義的宇宙之中(海德格爾),我們尋找到的意義是否足夠支撐我們自身就成了問題。
對這四個存在的基本事實的覺察構建了歐文·亞龍的動力模型結構:對四個存在的基本事實的覺察——焦慮——防衛機制。
可見,歐文·亞龍的存在心理治療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傳統完全不同,二者的動力模型結構的起點存在著根本性差異:弗洛伊德從性壓抑(閹割)開始,而歐文·亞龍則是從個體生存現狀的覺察和反思開始。在弗洛伊德那里,病人因為受到壓抑出現了精神上的病變而需要接受治療,即病人是出現了創傷性的精神官能癥需要接受治療的人,這樣的人群并不普遍存在;而對于歐文·亞龍來說,存在的四個基本事實是每一個人包括來訪者和治療師都會面對的問題。誠然,并非每一個人都會出現精神上的疾病,但是因思考自身生存狀態而產生的痛苦焦慮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面對的事情。正常人之所以正常并不代表他沒有攜帶“病原體”(對存在基本事實的覺察),只是因為“病原體”與宿主的免疫系統達到了某種平衡的狀態,而當平衡遭到破壞之時——可能在目睹親人死亡之時,可能在與死神擦身而過之時,可能在人生出現重大變故之時(找工作、離婚等),也可能在寵物過世之時,又或者在無聊靜坐之時,身體對于“病原體”(即便病原體的毒性不變)的抵抗力在這些時刻出現了下降,于是顯現出疾病狀態。這樣一來,正常與病態之間的差異并不是絕對的,而是焦慮與防衛機制相互作用的結果。
弗洛伊德用機械模式來構建對心智的理解——“人是由化學和物理力量所活化和控制的,這些力量可以簡化為吸引力和排斥力”,將心智歸結為兩種力量相互沖突作用的結果,用性欲本能沖動和對沖動的壓抑來構建理論體系。所有人的行動都是受到原欲影響的結果,難道沒有個體自由選擇的差異嗎?弗洛伊德肯定地說:“人是靠潛意識而活的……大家深信的心靈自由和選擇是非常不符合科學的,必須讓位給掌管心智生活的決定論主張。”[4]405歐文·亞龍反問這種構建的合理性:如果所有人類的心智和身體活動是受到決定的,那“努力”呢,“堅定”和有“勇氣”呢?這些“意志”不能體現人的自由嗎?反觀歐文·亞龍的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則少了歸因于某一“本體”的獨斷,描述的人在世存在的基本狀態,更加強調人的自由和責任的擔當,那些更有覺察能力和思考能力的個體可能會承受更大的痛苦,但對于死亡的思考以及痛苦的經驗“能夠讓一個人擁有更成熟的智慧和更豐富的人生”[7]5。
(二)闡釋模式的差異:過去與未來
1.基于過去的闡釋模式。弗洛伊德的闡釋模式是基于過去的,所有行為和心理經驗都是先前事件的結果(包括環境和本能)[4]476。弗洛伊德認為童年早期的心理建構影響了之后堆疊其上的其他建筑結構,那些早期心理事件的陰影殘渣從未完全消失不見,壓抑在潛意識中等待著浮出水面的一天。因此,對于弗洛伊德來說,心理分析師如同考古學家,仔細挖掘層層堆疊的心理地層,耐心細致地尋找彌合與斷裂之處,要將精力花費在回顧過去、回憶與父母和兄弟姊妹之間的關系、檢視童年的記憶和夢之上,直到觸碰到底部的根本沖突——早期的性壓抑。因此,弗洛伊德將精神分析師比作心理的考古學家,“我們都知道,必須誘導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回憶過去被壓抑的經歷。精神分析師……的任務是什么呢?是從殘存的蛛絲馬跡辨別被遺忘的事,更準確地說是去建構……他的建構工作(或說是重新建構)就好像考古學家挖掘被毀壞、埋藏的處所。這兩種工作是相同的……”[4]476這就是弗洛伊德的闡釋模式,如果要對當前的焦慮做出解釋,那就必須深入到過去來挖掘焦慮情緒的起源,將現在的焦慮與過去的事件做出連接,用過去的生活環境來解釋個人當前行為的原因。我們也可以看出,曾奇峰的“三角形理論”用時間上的早期(童年)來決定命運、用家庭環境(父母)來決定人生舞臺的大小明顯是受到了弗洛伊德傳統的影響。
可是,弗洛伊德的基于過去的闡釋模式是有問題的。首先,就如同弗洛伊德并沒有將時間上最早的“分離”作為理論的出發點,卻將理論的開端設定為“閹割”一樣,時間上的最早發生并不一定能夠成為根本性的因素,即“并沒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假定‘根本’(也就是重要的、基本的)和‘最初’(也就是時間上最早發生)是相同的概念”[4]40。也就是說,過去的事情并不能夠成為決定當前問題的根本性事件。其次,強調過去的決定論忽略了個人自我的意志(will),這樣做會影響心理治療的效果。如果我們當下的所有問題都是基于過去無法改變的環境或者本能來決定,那么改變的能力從哪里來呢?“父母”和作為“再造父母”的心理治療師成為改變“我的人生舞臺”的關鍵性人物,為什么是心理治療師,而不是神父、教師、詩人、哲學家呢?“三角形理論”最為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我的人生舞臺”為什么完全沒有“我”的存在?這樣做僅僅樹立了治療師的優勢引領地位,卻無益于來訪者的自我成長。還有,基于過去的闡釋在方法學上也有問題,因為心理的真實并不等于歷史的真實。我們的記憶經驗只不過是真實事件的斷片,而且還會對這些斷片進行選擇性地拼接,使之組合成為我們在當前處境中能理解的事件,因此,尋找真實的事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馬克·吐溫所說,“我十七歲時相信老爸是個討厭的傻瓜,我二十一歲時卻驚訝地發現他在四年中竟然學會這么多事”。詮釋并非一次完成,而是一段不斷變化的歷史,總是與當下的處境相關聯,總是摻雜了主觀意識的構建。人的過去并非斷瓦殘垣,如文物一般深埋在地下成為不會變化的地基,過去是由現在構成的,并不斷改變內在象征來影響現在[4]478。
雖然弗洛伊德的基于過去的闡釋模式有諸多問題,但是它作為一種方法還是有效果的。第一,深入挖掘過去可以幫助治療師了解當前行為模式的早期雛形,加深治療師對病人的理解,強化治療師—病人的關系。第二,深入挖掘過去可以形成一種知性的探險,治療師和病人共同投入其中,強化治療師—病人的關系。弗洛伊德也注意到了對過去的建構很可能無法達到真實,“我們常常無法成功地使病人憶起被壓抑的事,如果正確地進行精神分析,取而代之的是在病人心里制造一種確信,相信建構的真實性,而這個建構所得到的療效和重新捕捉記憶的結果是一樣的”。治療師摻雜著主觀意識的建構并不一定能夠還原歷史的真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確信”,確信詮釋的正確性,進而確信做出詮釋者的優勢地位。詮釋最為重要的并非內容的真實性,而是詮釋的過程,詮釋的過程是對抗無知的過程,是增強人們掌控感的過程。治療師替代病人承擔了自我反思和分析的責任,病人服從了治療師對自己過去的建構,這樣來看,心理治療師確實無愧于病人的“再造父母”。可是,這個“父母”注定只是讓孩子成為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2.基于未來的闡釋模式。歐文·亞龍的存在心理治療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傳統,也承認其基于過去的闡釋方式的重要作用,他提出:過去的事件確實可能會支配當下的行為,“尚未發生之事”也會對當下的行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比如,生命如同爬山,而死亡就在另一邊的山腳靜靜等待,對死亡的覺察就會影響我們當下的行為,還有我們對自身的期許、設定的目標不也會支配當下的行為嗎?回憶過去不是為了科學式的史料收集,治療師做出重新建構的精彩詮釋不是為了鞏固治療師的權威地位,而是為了改進治療師—病人之間的關系,關系是產生治愈療效的關鍵環節,治療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病人的未來,把病人帶領到能夠自由做選擇的境界。故而,做病人的父母替代病人的思考就抹殺了病人的意志(will),will指的是強烈的決心,代表著不僅現在要做一件事,而且將要(will)做一件事,它是指向未來的。
(三)心理治療師定位的差異:再造父母與助產士
1.與理論上的設定相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傳統認為情感轉移是治療的關鍵,如果治療師不顯現出真正的自我,就會更有利于病人將自己的情感轉移到治療師身上。弗洛伊德確定了心理考古最重要的任務是對情感轉移的分析,小心經驗轉移的情感、細致分析轉移的情感與現在處境的隔閡、深入挖掘轉移的情感的嬰兒期來源,是對于病人最深層生活經驗的揭示。弗洛伊德將治療師的唯一任務定位為:做出客觀的“詮釋”分析。可是,治療師所使用的基于過去的闡釋模式是有問題的,真正能起到的作用也模糊不清。由此,歐文·亞龍認為:放棄人與人之間真誠交流的機會——隱藏自身戴著面具與人交流,只是為了本來就成問題的對病人過去進行詮釋,這就本末倒置了。也就是說,把療愈作用的關鍵環節定位在“情感轉移”是放錯了位置,治療師作為中介對病人進行并不“真實客觀”的詮釋很難達成弗洛伊德最初設想的功用,即便對病人過去的詮釋發揮了任何作用的話,那也只能是治療師—病人關系真誠互動所產生的效果[4]545。歐文·亞龍講述了弗洛伊德作為客觀的詮釋者背后做出的一些“私下的”舉動:他會給病人按摩,“病人因為月經無法接受按摩時,讓弗洛伊德感到煩惱”;他也會大膽走入病人的生活,“向病人家屬說話,澄清病人財務和物質的前景”;他甚至表現出了“獨裁而嚴厲”,“他堅定地告訴病人,他會給她二十四小時來改變想法”,否則只能離開醫院[4]547。歐文·亞龍認為這些私下的真誠互動才是廚師的私房調味料,是讓病人得到治愈的關鍵。
2.與治療師自我形象的定位相關。如果治療師向病人敞開自己,就會犧牲客觀性和治療的效力。治療師的功能是詮釋,詮釋是為了獲得“確信”,治療師保持自己無個體身份的“先知”狀態無疑更有助于獲得盲目的相信,這種相信建立在絕對地服從之上。假若治療師作為一個可能犯錯的個人出現在病人面前,那無疑會影響治療師詮釋的“正確度”和“可信度”。
在弗洛伊德那里,心理治療師戴著面具扮演了不帶感情、假裝客觀、極具權威的先知角色,心理治療師通過詮釋重新構建了病人的過去,獲得了病人盲目“確信”后的心理治療師自然成了病人的“再造父母”,通過構建過去重新制造了一個人。歐文·亞龍的心理治療師則有著完全不同的身份象征,歐文·亞龍贊同地引述了布伯的觀點:有兩種對人實現影響的方式,一種是“試圖把自己的態度和意見加諸他人身上(但是以他人覺得是自己觀點的方式進行)”;另一種是“幫助他人發現自己的性情、體驗自己的‘實現力’”。布伯將前一種方式稱為imposition(強加干預),即便再溫柔的哄騙也是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可能沒有直接的暴力實施,但思想上的暴力對人造成的禁錮比肉體的暴力更加殘酷,因為它的“甜蜜”會讓對方完全陷入而喪失反抗的意志。治療師拯救病人童年創傷成為再造病人靈魂的“再造父母”就是這種方式的典型表現,最好的狀況不過是完成一個好的復制品,沒有自由靈魂的出現;而后一種方式可以稱之為unfolding(去除遮蔽),去除制約,打開遮蔽的幕布展現出一直存在的東西,不是讓對方成為“我”的靈魂的復刻品,而是讓對方成其自身,治療師成為靈魂的助產士。治療師與來訪者相處時,要堅持agape(愛)原則——“愛他人的存有與變化”,這是一個從布伯、馬斯洛、弗洛姆的理論中演化而來的觀點,表達“無所求的愛或者無私的愛”,擁有此種愛的人更為獨立自主、較少嫉妒、更為淡然,更熱衷于幫助對方實現自身——利他、寬容,這是一種朋友之愛。“治療師以真誠關愛的方式和病人建立關系,致力于獲得真誠相會的時刻”[4]504。
四、結語
“三角形理論”并沒有像三角形一樣彼此支撐、堅固樹立,因為歐文·亞龍的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理論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無法融合的。兩種理論的差異可以描述如下:
一是弗洛伊德太過執著于創造一種可以令他獲得“不朽的名聲”[4]119的包羅萬象的心智理論體系,堅持性欲望在驅動人類行動的動機中占據核心地位,并堅持這一地基不惜與所有人(學生和朋友)決裂。這種建構誠然偉大而強力,詮釋得固然精彩絕倫,但所有詮釋如同土著人看見火山爆發時將之詮釋為火山之神的憤怒一樣,只是獲得掌控感的方法,只是人們的虛構。歐文·亞龍對“詮釋”的解構也同樣強力和精彩:“超我、本我、‘自我’;原型,理想化自我和真實自我,自尊系統;自我系統和解離系統,男性氣質的對抗;父母自我,兒童自我和成人自我狀態,這些理論沒有一樣是真正存在的,它們都是虛構的,所有心理結構都是為了語意的方便而創造的……”這些理論的“有效程度在于它們提供多少個人的掌控感”[4]471。去除了建立理論體系的宏大目標,歐文·亞龍的理論較少獨斷和強制,更多的是對人類普遍存在狀態的描述,講述在不得不面對存在的“被拋”境況下,人們如何生存如何活出人自身的意志能力,實現人自身的自由。
二是弗洛伊德認為童年對人的心理形成具有奠基的作用,而心理治療就如同考古學一樣窺看病人心理形成的早期,進而掌握其現在的行為模式。在歐文·亞龍看來,心理治療師對于病人過去的建構并不真實,病人是基于當前來重新拼湊過去的,對過去的詮釋難免與病人當前的心理狀況相關并摻雜了治療師的主觀建構,故而,在歐文·亞龍看來詮釋的作用并不是對過去客觀真實的考古,而是在于增強掌控感、增強治療師—病人的關系。而且,過分強調過去心理結構對現在行為的決定作用忽略了病人的意志,未來的事物對于病人的當前行為無疑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必須要明確的是,心理治療不是單純為了考古而去搜集病人過去的心理歷史,而是為了改變未來。
三是弗洛伊德認為治療師的詮釋是治愈的關鍵,而歐文·亞龍則認為治療師—病人之間的關系是治愈的關鍵,這直接導致了不同的治療關系。在弗洛伊德那里,治療師是決定性的人物,治療師重構病人的過去,進而創造了一個新人,治療師成為修訂父母筆誤之人,不愧為病人的“再造父母”。可是,這樣盲目地讓病人“確信”的做法卻忽略了病人的意志,治療師樹立了自身的權威,同時讓病人成為服從的、永遠長不大的“孩子”。而歐文·亞龍并不否認詮釋的重要作用,但同時強調這種做法并不是為了“考古”,不是為了讓心理治療師作為病人靈魂的工程師進而改造之。病人和治療師面對同樣的“存在的四個基本事實”,都有著不同的思考自身存在的痛苦。大家都是“存在”的病人,治療師依靠自己的專業進行愛(愛他人的存有和變化)的工作,讓病人能夠通過自我反思來認識自己,對自己靈魂進行探索,最終能夠自由做出選擇。治療師是病人靈魂的“助產士”。
雖然直面死亡、自由—責任、孤獨、無意義會產生更多的痛苦,但是否認這些也并不會令人更加健康,覺察和自省所收獲的智慧更不會讓人更瘋狂,而是會讓人獲得更多生活的經驗,也讓人生更加豐富。
[參考文獻]
[1][美]歐文·亞龍.叔本華的治療[M].易之新,譯.太原:希望出版社,2008.
[2][奧]弗洛伊德.一種幻想的未來:文明及其不滿[M].嚴志軍,張沫,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3][美]弗洛姆.逃避自由[M].劉林海,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
[4][美]歐文·亞龍.存在心理治療[M].易之新,譯.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5]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M]. Walter Kaufmann,trans.New York: Vintage, 1974.
[6]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M]. Walter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1986.
[7][美]歐文·亞龍.愛情劊子手[M]. 張美惠,譯.太原:希望出版社,2008.
〔責任編輯:屈海燕〕
[中圖分類號]B8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2-0137-07
[作者簡介]張鑫焱(1981—),男,河南洛陽人,講師,博士,從事古希臘哲學與政治哲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