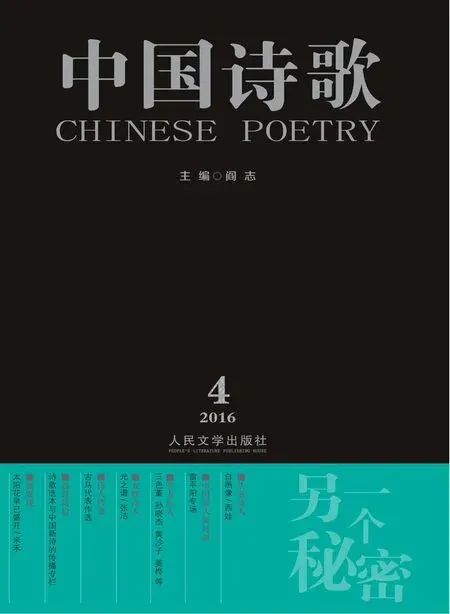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兩難處境
——現代詩歌選本的追求與問題
□李少詠
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兩難處境
——現代詩歌選本的追求與問題
□李少詠
阿諾德說:“詩歌拯救世界。”布羅茨基則認為詩人的使命就是用語言訴諸記憶,進而戰勝時間和死亡,為人類文明的積淀做出貢獻。正因為如此,古今中外的文學發展史上,詩歌選本洋洋灑灑,蔚為大觀。中國文化發展的至關重要的節點之一,就是孔夫子對于古代詩歌的選擇與編纂的成果《詩經》的出現。而《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的流布與傳播,更是讓廣大中華兒女都受益匪淺的文學奇觀。綜觀《詩經》、《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其思想性與藝術性的有機融合應該是它們流傳廣遠的主要的支撐因素。
進入現代,中國詩歌選本從數量上看不說汗牛充棟,也可以說洋洋大觀了。客觀地說,其中一些選本也可以用好,甚至優秀來評價,如陳夢家先生的《新月詩選》、藍棣之先生的《現代派詩選》、王富仁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詩歌經典》等,都是青年讀者耳熟能詳的選本。編選者對于選編對象的篩選與把握,毫無疑問都傾注了巨大的心血,選本對于人們了解和認識現代中國詩歌的發展脈絡等也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但是,如果以更高的標準來衡量,它們卻很難滿足讀者尤其是一些帶有觀摩與研究意向的讀者的心理期望。究其原因,我以為是編選者在編選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陷入了一種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兩難選擇當中。
藍棣之先生在為《現代派詩選》寫的前言中開宗明義說道:“擺在讀者面前的,是當年一批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懷著極度的苦悶、困惑和失望,徘徊歧路,在象牙塔里沉吟,在沉吟中探索人生和藝術,所留給后世的一份有爭議的詩歌遺產。”藍棣之先生也許為此一段概括性的語言費了不少心思推敲斟酌,這段話表面看來也確實很難被人抓到思想意識上可以詬病的地方。如果仔細考量,這段話卻有意無意地透射出一種隱隱約約卻足以制約藍棣之先生編選思路的因素,那就是,寧可被人批評藝術性的考慮較弱,絕不能讓人以為思想立場上不堅定。雖然他在后來的論述中用了不少筆墨為現代派詩歌的藝術性說話,但具體到選編出來的詩歌文本,僅從姓名和每個作者名下的作品數量和那些作品的具體情況來看,仍然是思想性大于藝術性的選擇。
陳夢家先生作為新月派主要詩人之一,編選新月派詩歌選本應該是差不多不二人選,那本詩選也確實顯示出相當高的詩歌眼光和藝術水準。但如果細加考量,也一樣有著思想性與藝術性不均衡的地方存在。與藍棣之先生的選本稍有不同的是,陳夢家先生的選本在編選策略上更加重了一點個人口味與感覺的色彩。他不很在意思想性方面的絕對正確與否,卻糾結于編選作品的作者與自己交往過從之疏密以及是否性情趣味更加相契合。這樣一來,讀者從選本中能夠感受到新月派的整體情況的期望就無形中打了折扣。
相形之下,王富仁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詩歌經典》更加廣博也更加豐厚一點,但卻是多了一份學者情懷的彰顯,少了一些詩歌本身的靈性的張揚。具體點說,王先生的選本更注重對現代中國詩歌傳統的梳理與節點的把握,在當下不少人已經不愿、不敢、不屑于歸根傳統,而一味地、急切地追求有別于傳統、有別于他人的個人風格的時代潮流中,這一點彌足珍貴。它代表著一種態度、一種導向、一種責任,在無形中延續著某種文化的精神。稍顯遺憾的是,這個選本由于追求博大全面,有意無意中忽略了詩歌內在精神的一些支流甚至是對于中國詩歌精神的創新與拓展相當重要的一些方面的作品,整體看來,就顯得思想性是既定的,藝術性也成了某種標簽化的東西。
就我個人的閱讀體會來說,我更喜歡幾個特點更加鮮明的詩歌選本。比如楊克主編的《中國新詩年鑒》、程光煒主編的《歲月的遺照——九十年代詩選》、廖亦武編的《沉淪的圣殿: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等。這些選本的一個共同特征,是抓住某一時期的詩歌的某一方面的主要特征集中展現,個性鮮明,讀者能夠從中各取所需,思想性與藝術性的不均衡由于某一方面的特征非常突出而被人不知不覺間感覺淡化了。也許,這也是詩歌經典選本編選者以后可以參照的一些例證吧。

——原始社會藝術性與實用性的完美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