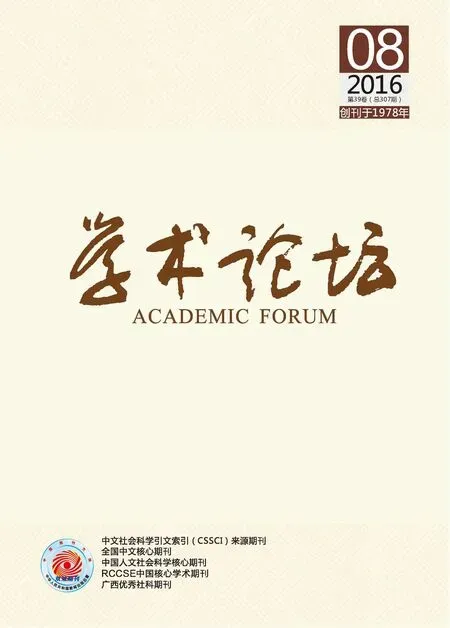胡適的媒介內容管理思想
——以管理《努力周報》內容產品為例
莊森
胡適的媒介內容管理思想
——以管理《努力周報》內容產品為例
莊森
胡適媒介管理思想高度重視管理內容產品生產。一是組建強大的撰稿群體,從源頭管理媒介的內容生產,保障內容產品的質量;二是受眾本位的議程設置,從受眾角度考慮內容產品的生產,把受眾的注意力導向某些特定的問題或爭端,通過內容產品傳播受眾最需要的信息,吸引和留住受眾;三是踐行輿論監督的傳播價值觀,聚焦負面政治事件、官員腐敗、政府以及公共機關不當決策等,為民代言,守望社會,服務受眾。
胡適;媒介管理;內容產業;內容產品;輿論監督
內容產業是融合信息服務和文化的產業群。1922年5月7日,胡適創辦的《努力周報》①《努力周報》是五四之后北方知識界一份著名的以論政議事為中心的同人刊物,發起人為胡適、丁文江等,這是他們公開談中國政治的刊物。創刊于1922年5月7日,1923年10月停刊。就是內容產業,內容定位為“談政治”——以談政治為核心組織內容生產,胡適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并承擔收稿、撰稿、編稿、付印、校對等工作,有時甚至獨自撰寫全部文章[1](P702),緊緊圍繞“談政治”生產內容產品,借助有形物質承載各種信息、文化等生產思想和資訊等內容產品。胡適強調:《努力周報》“主要是談政治問題,但并不完全排除文學和哲學的文章”[2](P144)。
一
胡適管理《努力周報》內容產品,首先組建強大的“談政治”撰稿群體,從源頭管理內容生產,保障內容產品的質量。《努力周報》注重內容生產的規范化,通過管理作者群體,規范內容產品的風格,追求內容產品的高水平,樹立內容為王的媒介形象。胡適為保證生產“談政治”的內容產品,從抓生產者——撰稿群體管理入手,“通過整合多個個體而形成一個更有價值的整體”[3](P163),組建強大陣容的“談政治”撰稿群體,從而規范管理媒介內容生產。因為知識是企業能夠取代勞動力、土地、資本變成最重要的競爭和生存的武器,管理內容實質就是管理知識。而獨立個體的知識分子能力有限,內容產業“為了完成某個具體目標只有一個人的努力是不夠的,它需要匯集眾人的智慧、知識和力量來完成這項工作”[4](P244)。
《努力周報》“談政治”的撰稿群體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個體組合而成的集體”。“個體的行為由組織目標規定,并且指向組織目標”[4](P243)。這個群體的核心成員有胡適、丁文江、高一涵、張慰慈、朱經農、任鴻雋、陳衡哲、陶孟和、徐志摩、唐鉞、楊杏佛、衛挺生等人,都是久負盛名的學者。這些人“大多曾留學歐美,不少人還獲得了博士、碩士學位;歸國后則任教于中國著名學府,因此,北京大學也成為這一群體的重要‘紐帶’。從這群人的構成還可看出,胡適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最初的聚集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實可看作是以胡適為中心,中國自由知識分子首度的匯聚。”[5](P64)這個群體中的個體作者雖有發揮的天地,但都遵從“談政治”的內容定位,使得《努力周報》的內容產品與編輯均有一貫性,形成陣容強大的“談政治”撰稿陣容。
管理學理論認為,資源的流動性決定產業的競爭力。內容產業的產品生產者——撰稿群體的資源直接影響內容產品的績效及質量水平。“如果一種生產資源要得到有效利用,那它在其所有用途中必須具有同樣的生產性——顯然,如果它在一種用途中的(邊際)產品少于另一種用途,產出就沒有最大化。因此,通常還有兩個條件成為完全競爭的一部分:資源在所有的用途中是流動的;資源的所有者知道資源在各種用途中的產出。”胡適利用資源的這種流動性組建《努力周報》撰稿群體時,充分考慮了“生產資源(其所有者擁有的數量決定其配置)的私人邊際產品必須等于其社會邊際產品(私人邊際產品加或減對其他人的效用)”[6](P8-9),注意群體成員的資源(專業知識、技能和能力),挑選擁有不同資源的專業人士組成,構成資源互補、互動,既提高從不同專業角度“談政治”的水平,更增強媒介內容產品的競爭力。“政法之稿件有一涵、慰慈等擔任(現在不是白盡義務);經濟之稿,有振飛、唐有壬等擔任;文學之稿,有志摩、陳通伯等擔任(蘇菲過于矜持,不敢預計其必有稿來);其他社會科學,有兄、叔永、擘黃、孟和(孟和來滬,當可求其作文)和我擔任,讀書雜志有頡剛、劉叔雅等擔任。”[7](P139)羅賓斯認為:“一個群體可能達到的績效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郡體中每個人給郡體帶來的資源。”“通過評估成員個體的知識、技能和能力,可以部分預測出群體績效。”[4](P249)《努力周報》這個群體成員的專業知識、技能和能力,保證了“談政治”的內容產品的高水平,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這個陣容強大的“談政治”撰稿群體以胡適為核心,胡適撰稿最多,計有107篇,其中有86篇“談政治”——關懷公共領域,盡知識分子關懷社會、守望社會的責任。這個群體“意味著在沒有形成明確黨派識見以前,知識階層為著一些共同利益暫時聯合起來。同時也可看出,現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最初的聚集,就是一個極為松散的團體,主要是一些留美的學者或技術型官僚,因暫時認同于某些政治理念,通過開茶話會、發表宣言、辦刊物的形式聚集起來”[5](P68-69)。但加入這個群體的每一個人“原因并不是惟一的。大多數人同時屬于多個群體,因此顯而易見,對個人來說,不同群體為其成員提供了不同利益”[4](P244)。丁文江是這個正式群體最積極的組織者,加入群體是為滿足實現“談政治”的“目標實現的需要”,丁文江“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8](P443)。
《努力周報》的撰稿隊伍是一個正式群體。它“之所以能夠形成和發展,往往是因為其成員擁有某種或某些共同特點”,這個“共同特點”是都不“靠政治吃飯”,但又“研究政治,討論政治”的人,多為滿足歸屬需要。群體構建在聚餐會的基礎上,“群體能夠滿足社交需要。人們往往會在群體成員的相互作用中得到滿足。對許多人來說,工作中的人際互動是滿足他們歸屬需要的最基本途徑”[4](P244)。為此,《努力周報》的撰稿群體有一個非正式的、不定期的茶話會。“參加茶話會的前后約有20多人”[5](P65),聚集成陣容強大的“談政治”撰稿群體。這個茶話會既為群體成員提供社交平臺,滿足成員的社交需要,又能在一起“討論政治”,議論切近的社會問題,決定內容產品的生產。胡適的日記這樣記載:“孑民、亮疇、少川、鈞任發起一個茶話會,邀了二十多位歐美同學在顧宅談話,討論今日切近的問題。這個意思甚好,我因與鈞任提議,繼續定期開茶話會,每次由四五個人作主人。”[1](P709)
胡適是《努力周報》撰稿群體的靈魂,全因為“不能放棄我的言論的沖動”參與創辦《努力周報》。創刊過程中,警察廳駁回申請,不予創刊,胡適一再周旋,“另擬一呈子,再請立案,措詞頗嚴厲”[1](P544)。好友高夢旦、王云五、張菊生、陳叔通等不贊成胡適辦報,胡適對此不以為然:“政府不準我辦報,我更不能不辦了。梁任公吃虧在于他放棄了他的言論事業去做總長。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棄我的言論的沖動。”[1](P522)1923年,面對“北京反動的政府”[9](P173)“取締新思想”的高壓勢態和友人勸告他“跑為上計”的好意,他公開宣稱:“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趨附時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險。封報館,坐監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調:那是恥辱!那是我決不干的!”[10]胡適把維護“談政治”的思想自由視為比生命更寶貴。胡適深刻地知道,某種思想要在現代社會中突破影響上的有限時空范圍,就必須借助媒介,所以,新聞、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成為言論自由的標志。胡適認為:“真正自由的精神在那里?出版有自由,言論也有自由。一個人只要他有種意見,在他自己總有發表出來的權利,在我們總不能禁止別人發言。”[11]胡適創辦《努力周報》就是為“談政治”,爭取思想自由,推動社會進步。
二
胡適管理《努力周報》的內容產品,遵循受眾本位的議程設置,針對社會現實問題“談政治”,服務受眾,干涉政治。《努力周報》是市場化運作的媒介,媒介間競爭激烈。《努力周報》的受眾絕大部分是固定訂閱,胡適追求每期都有受眾感興趣的內容產品吸引和留住受眾。議程設置是內容產品生產的重要藍圖,可以把受眾的注意力導向特定的問題或爭端,給受眾傳播最需要的信息。這種議程設置淡化宣傳味道,強調從受眾角度考慮內容產品生產。
《我們的政治主張》是《努力周報》重要的議程設置,最具影響力的“談政治”內容產品,不僅奠定《努力周報》“談政治”的基石,而且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成為中國現代媒介最有影響力的“談政治”內容產品,影響了中國現代政治的發展進程。
《我們的政治主張》由胡適撰寫。胡適日記記載:“做一篇《我們的主張》,是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這本是想專為《努力》做的;后來我想此文頗可用為一個公開的宣言,故半夜脫稿時,打電話與守常商議,定明日在蔡先生家會議,邀幾個‘好人’加人。知行首先贊成,并擔保王伯秋亦可加入。此文中注重和會為下手的第一步,這個意思是我今天再三考慮所得,自信這是最切實的主張。”[1](P664-665)
胡適高度重視管理“談政治”的內容產品質量,為提高《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水平,保證產品質量,胡適多次組織討論修改,管理內容生產。5月12日“七時,打電話與蔡先生,借他的家里開會,討論《我們的主張》。其余各人,也在電話上約定十一時相見”。“十一時,在蔡宅開會,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馀、湯爾和、徐伯軒(未約他,偶相值)、經農等。他們都贊成了,都列名做提議人。蔡先生留我們吃飯;飯后他們都散了,我獨與蔡先生閑談。三時,王亮疇、羅君任也來,他們略有討論,修改了幾處,也都列名。連知行、在君、王伯秋、文伯和我,共15人。下午,孟馀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1](P665)
《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五方面的政治訴求,內容極具震撼力。第一,主張全國的優秀分子放棄爭議,不再爭論各種籠統、崇高的“主義”,而把政治目標定得實實在在,以“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并倡議“我們應該同心協力地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第二,提出“好政府”的“好”標準是能“監督防止”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同時造福全社會,并“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第三,提出改革國家政治的三點要求:(1)建立一個使政治走上健康軌道的“憲政的政府”;(2)建立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考試用人的公開等,因為唯有公開才能“打破一切黑幕”;(3)實行“有計劃的政治”——有計劃才有效率,中國恰恰處于“無計劃的漂泊”狀態。第四,呼吁優秀分子“好人”不要再自命清高了,要走出來“做奮斗的好人”,“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斗”,“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需有決戰的輿論”。第五,針對緊迫的現實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反對武力統一,主張南北盡早正式議和;為保證南北不再訴諸武力,應該召集國會,并裁減軍隊;嚴定官制,裁汰冗員,改革選官辦法;廢止復選制,實行直接選舉制;實行徹底的“會計公開”,統籌國家的支出[12]。
《我們的政治主張》刊發后,社會反響非常強烈,引發各階層關注政治的熱情,《努力周報》收到大量“關于《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共得可登之文十四篇”[1](P675),取得內容產品深入人心,創造新價值空間的重大效益。這樣高的閱讀量,體現消費者對內容產品的信賴。那么多的讀者來信討論,表明消費者有溝通的強烈需求。胡適為加強內容定位管理,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增強信息交流與互通,打破單一的溝通形式,決定“另出增刊,專載”討論。《努力周報》第3期頭版頭條刊登《本報特別啟事》:“本社這幾天收到了無數關于《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文章,本期不及發表了,下期另出增刊,專載這一類的討論。”[13]胡適重視管理內容定位,費了“一天的工夫。看了這些文章之后,我頗有感觸”[1](P675),決定傳播社會各界聲音,構架編讀互通橋梁,開辟更方便、快捷的溝通渠道,不僅追求提升產品價值空間,更通過編讀互動,管理內容定位,不斷推出“談政治”內容產品。
《晨報》和《益世報》最快發表社論評論《我們的政治主張》,認為這個時候談政治不合時宜,強調改造社會是改造政治的基礎,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改造社會。胡適因忙于整理讀者來信并做答,安排高一涵撰文回應。高一涵針對《晨報》和《益世報》的社論,發表《政治與社會——答〈晨報〉〈益世報〉記者》回應,強調《我們的政治主張》“實在只是貫徹我們多年主張的一種辦法”[14]。
胡適抓住關系時代走向的“政治主張”設置議程,推動“談政治”成為文化傳播,充當文化啟蒙的社會角色。胡適“談政治”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15],在全社會構建現代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推動民眾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參與者,所以,采取“互動”方式辦媒介——編者引導讀者的視野聚焦在某個問題,消費者積極參與話題的討論,使大量社會信息進入傳播渠道,既活躍自由爭鳴的文化氣氛,又增強媒介的親和力與可讀性。這種互動還具有明顯的雙向性——編者根據內容定位設置議題,吸引讀者以來信方式參與,產品內容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為原則,改變“單向傳播”格局,不僅引發消費者的興趣,也強化消費者的主體地位。胡適因此特別重視讀者來信,展開討論《我們的政治主張》,既讓消費者參與媒介內容建構,又引導消費者注意力,提供消費者需要的內容產品。為此,《努力周報》第4期擴充為八版,討論《我們的政治主張》,構筑讀者活躍的話語空間,并決定“為節省篇幅起見,只好暫不發表”“贊成的意見”[16],胡適精選讀者質疑、補充的來信,融入大量社會信息,親自撰稿回應,管理內容定位,既搭建起互動平臺,打造品牌交流活動,又牢牢把握內容生產,擴大媒介的影響力。
王振鈞等人提出,“你們沒有明白地告訴我們的,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后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適回復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已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并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來破壞與建設都不是絕對的相反,他倆的關系也有點像你們說的雞蛋與雞的關系;有時破壞即是建設,有時建設即是破壞,有時破壞必須在先,有時破壞自然跟著建設而來,有時破壞與建設同時并進,等到雞蛋殼破裂時,小雞也已下地了。”[17]
胡適善于根據媒介的內容定位篩選讀者來信,親自撰稿耐心回答,既增加讀者信任感和敬慕情,又牢牢把握內容生產,實現編輯主體傳播的意圖,在思想上引領讀者,擴大媒介的影響力。《努力周報》第4期擴充為八版,設計為《關于〈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專號,但同時還拿出八分之一篇幅,根據內容定位的需要,安排了兩則《對本報的批評》及胡適的答復,尋求與讀者互動,經營讀者信任。
胡適的管理媒介非常重視這種編讀互動,編輯方式也相當穩定,構筑成媒介一道亮麗的文化景觀:一方面精心策劃,將社會各個層面的生活、感受和思想呈現出來;另一方面,根據讀者提供的信息,通過書信設計議題,讓知識分子精英作為意見領袖適時介入,平等討論問題,構成有趣的互動傳播,發揮了編讀主體建構媒介文化的創造潛力,使媒介成為社會的輿論空間,各個階層的人物共同參與,媒介成為聲音相對自由的“公眾論壇”,吸引讀者的目光,擴大媒介的影響力,提高了內容產品的價值。
三
胡適管理《努力周報》的內容產品,努力踐行輿論監督的傳播觀,用批判方式“談政治”,突出批評負面政治事件,追求政治平等、思想自由。官員腐敗、政府以及公共機關不當決策等是《努力周報》關注的焦點。胡適高度關注負面政治事件既與傳播的價值觀密切相關,也與《努力周報》的市場化運作密不可分。受眾關注什么樣的信息,媒介就必須為民代言,幫助受眾搜集相關信息,保住已有受眾,吸引新受眾。
胡適創辦《努力周報》就是為了進行輿論監督,決心與志同道合者“談政治”,改變輿論風氣。為管理好“談政治”的內容產品,胡適提出“談政治”必須超然黨派化和意識形態,做“監督政黨的政論家”,監督政府。這種政論家政治身份獨立,不為政黨所羈絆,表達意見時不會為一黨私利所障目,不會甘當某個政黨的喉舌,“只認是非,不論黨派;只認好人與壞人,只認好政策與壞政策,而不問這是那一黨的人與那一派的政策:他們立身在政黨之外,而影響自在政黨之中。他們不倚靠現成的勢力,而現成的勢力自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督促”[18]。
《努力周報》為踐行輿論監督,開辟專欄《這一周》,并且編排在特別突出的地位,占據第一版頭條,有時甚至占滿第一版,批評時政、守望社會、啟發民智,追求輿論監督,踐行媒介公開、正誼地監督政府,進行輿論監督,守望社會。現代政治學認為,國家(行使國家權力的政府)不是最終利益獲得者,只是公民獲得個人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保障公民獲得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政府的努力方向;保護公民的個人利益,才是政府的目的。密爾認為:“一切政府的活動,只要不是妨礙而是幫助和鼓舞個人的努力與發展,那是不厭其多的。可是,政府一到不去發揮個人和團體的活動與力量卻以它自己的活動去代替他們的活動的時候;一到不是對他們進行指教、勸導并有時指責而是叫他們在束縛之下工作,或是叫他們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們工作的時候,害處就開始了。國家的價值,從長遠看來,歸根到底還在組織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19](P125)因此,政府需要人民監督,媒介作為社會公器,監督政府,守望社會成為最重要的社會責任。正是受這種思想影響,胡適明確《努力周報》的內容定位是“談政治”,不僅密切關注現實的社會具體問題,堅守自由思想、言論自由,而且勇于批評時政,監督政府,大膽評析政府施政的優缺點,直言不諱,表揚優點,批評缺點,并提出忠告與建議。
1922年6月,直系趕走皖系“法統重光”,黎元洪再任大總統,主政北洋政府。胡適馬上提出,新政府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公開提出對“這個新政府,只有下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1)我們希望這新政府自認為一個‘事實上(De facto)的臨時政府’;他的最大任務是用公開的態度,和平的手段,做到南北的統一。(2)我們對于這次在北京自行集會的舊國會,只希望他自居于臨時的國會;缺額不得遞補,不得取消在廣州的議員的名額,免得增加統一的障礙”[20]。胡適大膽批評時政,進行輿論監督,明確提出政治建議,強調政府不統一,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就得不到發展。此外,胡適還提出采用直選制廢止復選制、制訂防止選舉舞弊的法律、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人數等等,啟發民智,批評、監督政府,進行輿論監督,守望社會。胡適堅信,媒介“就是公眾的眼睛,官員們如果要擔任公職,就必須受到報紙的監督。而且,很多誠實的官員受到不必要的審視總比一個不誠實的人可以不受懲罰地公然背叛公眾要好。與法律上的無罪推定相反,許多報紙認為,每一個擔任公職的官員都應該被假設犯有不忠誠的罪行,除非他能證明自己的無辜。只有當報紙能夠發揮作用、對公職人員的行為和動機進行調查時,民主政治的實驗才有希望獲得成功”[21](P144)。因此,胡適定下《努力周報》“這一周”的內容產品就是輿論監督,促使政府推行漸進式的改良,避免社會發生大的動亂、變化。
胡適強調輿論監督必須客觀、公允,“只討論公共事務”,杜絕任何人身攻擊。《努力周報》“嚴格遵循只討論公共事務的方針。如果一個官員不是一個好的公仆,如果他不誠實,或效率低下,或政治上腐敗,本報都會直言不諱,但從來不會對其人身進行含沙射影的攻擊”[21](P147)。因為批評時政是監督政府,進行輿論監督,守望社會,不是發泄個人私欲,而是守望社會,監督各種政治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分析評論各派政治力量及熱點事件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影響,堅守“公開的、正誼的”輿論監督。這種傳播觀直接影響到內容設計和內容管理,開了中國現代媒介輿論監督的先河。
胡適認為,他與國民黨的矛盾沖突是新舊文化、道德的碰撞。他批判國民黨的“主題是‘舊道德的死尸的復活’,而不是替什么人辯護”[22](P418),鋒芒直指國民黨組織結構,分析舊道德、舊文化對國民黨的哲學基礎、文化觀念及組織形態、組織方式的影響,認為“同盟會是一種秘密結社,國民黨是一種公開的政黨,中華革命黨和新國民黨都是政黨而帶著秘密結社的辦法”。“我們再進一步,提出一個疑問:秘密結社的儀式究竟是否適宜于大規模的政黨?秘密結社用來維系黨員的法子在現代的社會里是否可以持久?這一個‘制度’的問題似乎也有討論的價值罷。”[23]胡適指出,國民黨保留宣誓等舊幫會的舊習,不能擺脫秘密結社的幫會性質、專制傳統和黑社會習俗,不具備現代政黨的性質,陳炯明反抗這種“制度”沒有錯,值得肯定、支持。
胡適留學美國,深受美國媒介價值觀影響。美國的媒介“承認,一份真正偉大的報紙一定要比任何一名主編的良心或全體主編的集體良心都要偉大。因為當它說話時,它的言論是由那些非常明智、非常理性、非常公正、非常富有同情心、非常富有理解力以及非常誠懇的人們做出的,而不是由那些受到人類弱點和缺點腐蝕的、僅僅為了寫作而寫作的人們做出的……一份真正偉大的報紙必須擺脫任何以及全部特殊利益集團的束縛”[24](P72)。胡適無論面向任何壓力,都始終堅持“擺脫任何以及全部特殊利益集團的束縛”,堅持用認真、負責、謹慎的態度評論社會具體問題,以負責、公正的態度、強烈的民族責任心和理性的言論,守望社會,輿論監督,引導社會,積極地承擔推動國家進步,造福民族福祉的社會責任。但胡適的這種追求不僅沒有獲得輿論的贊同,還招致不少人的懷疑。
1922年,華盛頓會議通過決議,中國收回青島。北洋政府委派王正廷負責接收。山東省籍的不同利益集團群起攻之。胡適挺身而出,站在公開、正誼的媒介立場,“希望山東人士對于這件重大而帶專門性質的事件,不要全憑意氣,不要利用群眾心理,應該先把一切步驟想像出來。打倒一個人是容易的事,為事擇相當的人就不容易了。攻擊一項交易也是容易的事;根據事理,做更妥當的計劃,就不容易了”[25]。胡適這樣“談政治”,進行輿論監督,追求實現媒介“啟迪民眾。不光是向他們提供信息,而是承擔有人說的啟迪民眾的義務”[21](P320)。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胡適這種公開、正誼的媒介立場。
1922年11月12日,《時事新報》登載新猛的《胡適之與王正廷》,指責胡適幫王正廷說話:“王正廷是什么一種人,胡君還要和他說話,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卻更因此而懷疑胡適之了。”[26]胡適認為,新猛的這種言論體現了媒介社會責任的缺失。胡適強調媒介必須是“自由與責任相伴而生。位于政府之下,擁有特權地位的傳媒,在當今社會具有大眾傳播的重要功能,因此傳媒有義務對社會承擔責任”[24](P62),進行輿論監督。新猛的言論是“攻擊人”,有諱媒介的社會責任,體現了媒介的一種典型的、最時髦的病態——“攻擊人。凡是攻擊,都是超然的。我們攻擊人,從來沒有受人‘懷疑’過。我們偶然表示贊成某人,或替某人說一句公道的話,就要引起旁人的‘懷疑’了。”造成媒介的“政論者所應取之態度,只可罵人,切不可贊成人。被人罵的人,一定是該罵的,政論者應該加力幫著罵他。切不可贊成某人,切不可贊成某派,切不可贊成某事:贊成就是‘替某人某派或某事辯護’了,就不是‘超然的目光’了。”胡適的這番話很尖銳,說的雖是人,但實際指出媒介存在“小人的心理”。媒介只一味罵人,“不信天下有‘無所為’的公道話”[27],這是“運用其巨大的權力來為自己謀福利。傳媒的所有者只傳播他們自己的觀點,尤其是有關政治經濟的問題,他們同時也損害了反對者的意見”[24](P66),阻塞言論自由,失去了公開、正誼的媒介立場,完全違背了媒介的社會責任。
[1]胡適日記全編: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周質平,編譯.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3]萊斯利·W.魯,勞埃德·L.拜厄斯,等.管理學:技能與應用[M].劉松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4]斯蒂芬·P·羅賓斯.組織行為學[M].孫健敏,李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5]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喬治·J.施蒂格勒.產業組織[M].王永欽,薛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朱經農.致胡適[A].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C].北京:中華書局,1979.
[8]胡適.丁文江的傳記[A].胡適文集:第7卷[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9]胡適日記全編:第4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0]胡適.“胡適先生到底怎樣?”[N].努力周報,1923-01-07.
[11]胡適.對于滬漢事件的感想[N].晨報副鐫,1925-06-26.
[12]蔡元培,等.我們的政治主張[N].努力周報,1922-05-14.
[13]本報特別啟事[N].努力周報,1922-05-21.
[14]高一涵.政治與社會——答《晨報》《益世報》記者[N].努力周報,1922-05-21.
[15]胡適.我的自述[N].努力周報,1922-06-18.
[16]啟事[N].努力周報,1922-05-28.
[17]胡適.關于《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N].努力周報,1922-05-28.
[18]胡適.政論家與政黨[N].努力周報,1922-06-04.
[19]約翰·密爾.論自由[M].許寶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20]胡適.這一周[N].努力周報,1922-06-18.
[21]利昂·納爾遜·弗林特.報紙的良知:新聞事業的原則和問題案例講義[M].蕭嚴,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2]胡適.這一周附跋[A].胡適全集:第3卷[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3]胡適.這一周[N].努力周報,1922-08-20.
[24]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奧多·彼得森,威爾伯·施拉姆,等.傳媒的四種理論[M].戴鑫,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25]胡適.這一周[N].努力周報,1922-11-05.
[26]新猛.胡適之與王正廷[N].時事新報,1922-11-12.
[27]胡適.這一周[N].努力周報,1922-11-19.
[責任編輯:劉烜顯]
莊森,貴州民族大學傳媒學院、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研究員,博士,貴州貴陽550025
G211
A
1004-4434(2016)08-0076-06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青年》的‘新青年’元敘事研究”(13BXW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