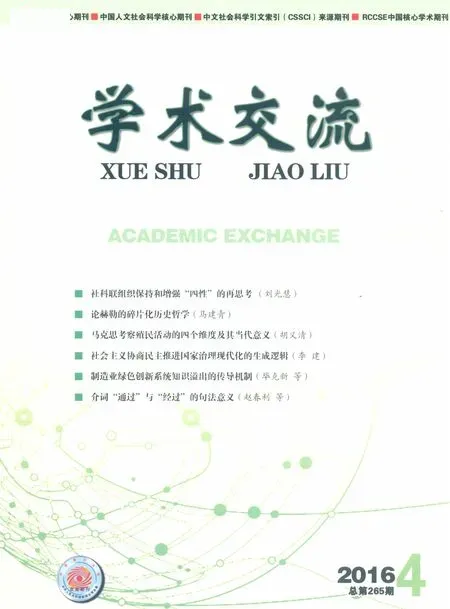赫勒的碎片化歷史哲學與年鑒學派“新史學”的比較
范 為
(中共中央編譯局 辦公廳,北京 100032)
?
赫勒的碎片化歷史哲學與年鑒學派“新史學”的比較
范為
(中共中央編譯局 辦公廳,北京 100032)
[摘要]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東歐布達佩斯學派的代表人物阿格妮絲·赫勒提出了一種后現代歷史哲學,并從社會生活的各個角度對歷史進行了深度解讀,從而對傳統歷史哲學的宏大敘事提出了挑戰。與此同時,法國的年鑒學派也在繼續著他們對傳統史學的批判,并不斷地進行史學革新,擴展歷史研究的領域和范疇。年鑒學派對于長時段重要地位的論述和其對普通個人心態及日常生活的重視,與后現代歷史哲學存在很多的相似性,年鑒學派的史學革新與赫勒的后現代歷史哲學相互影響,共同推動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碎片化為特征的史學研究的發展。
[關鍵詞]赫勒;歷史哲學;年鑒學派;新史學;碎片化;后現代;微觀視域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后現代的思潮蔓延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歷史與哲學相交叉的產物的歷史哲學研究領域,也受到了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一種以反基礎主義、反中心主義、反本質主義為特征的新的歷史哲學——后現代歷史哲學逐漸興起,持后現代歷史哲學觀點的歷史哲學家們對傳統歷史哲學進行批判。東歐布達佩斯學派的阿格妮絲·赫勒就提出了一種碎片化的歷史哲學,用以取代宏大敘事的歷史哲學。其實,早在后現代歷史哲學出現之前,1929年創立的法國年鑒學派就已經一直在致力于對傳統史學的批判。經過三代學者的共同研究探索,年鑒學派已經成為了當代西方史學中最有影響的流派,在史學研究方法的革新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比較起來,赫勒的碎片化歷史哲學與法國年鑒學派所提出的“新史學”存在著很多的相似之處。我們通過對這些相似性的分析,可以展示出歷史研究領域中方法、規則的變化。本文試通過對兩者各自發展過程及特點的分析,指出兩者在歷史研究上出現諸多相似之處的原因。
一、赫勒的碎片化歷史哲學
作為東歐布達佩斯學派的代表人物,赫勒的研究涉及激進需要、日常生活、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等。在她學術研究的后期,她將研究重點轉向了歷史哲學研究領域。1982年,她在自己歷史哲學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歷史理論》中提出了一種為取代傳統歷史哲學而建構的歷史理論。在《歷史理論》一書中,赫勒對歷史意識六階段進行了劃分,對歷史編纂學和歷史哲學進行了區分,最主要的是她表示出了對傳統宏大敘事歷史哲學的不滿,并且為取代傳統歷史哲學而提出了一種歷史理論,“歷史理論拒斥大寫的歷史的本體論建構。”[1]301她反對以往歷史研究中那種只重視帝王將相的事跡或者只以個別大陸的歷史來描述世界歷史而忽視普通平民和特殊的、所有的民族的歷史的研究方式。她認為,無論是帝王將相、個別大陸,還是普通平民,都應該被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成為歷史敘述中的要素。在她看來,“如果人們以歷史(復數的)(除了起源和我們當下的過去)來取代‘大寫的歷史’,歷史哲學的整個大廈就坍塌了。”[1]302她希望用歷史理論來代替傳統歷史哲學,但同時她也意識到,歷史理論并不是一種完整的歷史哲學,不能完成歷史哲學的全部任務,所以她知道,改造傳統宏大敘事的歷史哲學、建構一種新的歷史哲學的任務尚未完成。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后現代思潮影響到歷史哲學研究領域,后現代歷史哲學興起并不斷壯大。在1993年出版的《碎片化的歷史哲學》一書中,赫勒開始繼續她此前未竟的工作,明確提出了一種新的歷史哲學,這種歷史哲學就是為了取代傳統歷史哲學而提出的。她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后現代人繼承了歷史意識,而不是宏大敘事的自我滿足。對于世界的持續增長的透明度的信任已經不在了。這不是一個書寫體系的恰當的時代。相反,這是一個書寫碎片的恰當的時代。”[2]4這本書是圍繞著“經過反思的一般性意識也就是后現代意識”這一主題展開論述的。“它是一種宏大敘事消失之后的歷史哲學”,赫勒之所以把書命名為《碎片化的歷史哲學》,正是因為這個時代本身的特點就是碎片化。在這個時代,嚴格的范式界限已經被取消了。赫勒認為,在現代社會,以前的那種體系化的歷史哲學已經不合時宜而走向了衰落,需要由新的歷史哲學來代替,這種歷史哲學就是以反本質主義、反中心主義、反基礎主義為特征的后現代歷史哲學。赫勒從后現代的視角出發,分析了歷史中的偶然性在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且指出在后現代社會中偶然性的作用有時比必然性更為重要,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必然性在歷史中的決定作用。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的偶然性意識正在占據更重要的位置。她指出:“在現代性的開端,偶然性意識伴隨著一個沖擊而來,它不再被放在一種表面化的地位,即不再被貶至邊緣地位。曾經作為邊緣現象的偶然性意識朝著中心快速地移動。”[2]13對于理性,赫勒采取了比較中立的態度,她既不把理性當作萬能的,也不完全否定理性在治療欺騙和自我欺騙時的作用。她認為,對于理性,我們既不應該盲目地崇拜,也不應該完全地拒斥,而是要規范對理性的使用,把理性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內,以便更好地利用理性。
在其“現代性理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即1999年的《現代性理論》一書中,赫勒接著《碎片化的歷史哲學》的線索,對現代性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她指出,她的現代性理論不同于其他一些現代性的理論,因為她的現代性理論“是一種出自后現代視角的現代性理論”[3]。在正文中,她又把她所應用的后現代概念與所有其他的后現代概念區別開,認為“后現代”有兩種用法,一是“未經反思的后現代性概念”,二是“經過反思的后現代性概念”。赫勒認為這是一種態度的區分。未經反思的后現代性概念繼續了它本應該拒絕的宏大敘事和真理對應理論,經過反思的后現代性概念則在不斷地質疑自身。赫勒所采取的視角是第二種視角,她認為后現代的視角應該被描述為現代性意識本身的自我反思。在現代社會中,真理的標準是不斷變化的,現代性的合法性開始遭到懷疑。赫勒列舉了三種經典的現代性理論,包括黑格爾的、馬克思的和韋伯的現代性理論。她一邊對這三個人的思想進行分析,一邊闡釋了自己的現代性理論。她指出,人類的很多行動并不是按照計劃進行的,而是完全出于一種偶然。人類歷史也不是按照計劃來發展的一種必然,在歷史中充滿著無數的偶然,而這些偶然往往在歷史發展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接著,赫勒細致地從人生活的各個方面論述了現代性中的一些主要問題,例如現代性的動力和格局、現代性的三種邏輯、文化與文明、世界時間與生活時間,等等。這些論述表面上看起來有些凌亂,但實際上這恰恰是與赫勒的后現代的反基礎、反體系的態度相一致的。
二、年鑒學派對史學研究方法的革新
赫勒希望用碎片化的歷史哲學代替傳統宏大敘事的歷史哲學,這反映出后現代歷史哲學家對傳統歷史學研究方式的不滿。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就有一個學派對傳統宏大敘事的歷史研究方式提出了質疑。這個學派就是法國年鑒學派,其稱號來源于費弗爾和布洛赫于1929年創辦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鑒》雜志。年鑒學派是國際史學界影響最大的學派,他們一直致力于對歷史學的革新,對傳統歷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很多挑戰,對史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年鑒學派的理論逐步滲透到其他歷史學派和各個研究領域,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年鑒學派開始把心態史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形成了“新史學”運動,創新了歷史研究的方式,在歷史研究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年鑒學派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經濟與社會史年鑒》為中心,展開批判傳統史學和宣傳“新史學”的運動,倡導歷史研究應該是包括地理環境、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總體史研究;第二個階段又被稱作布羅代爾時代,同時也是年鑒學派的鼎盛期;第三個階段打出了“新史學”旗幟,因此被稱為“年鑒-新史學派”。
無論在其發展的哪個階段,年鑒學派都包含著對傳統史學的批判和反思。傳統史學也即宏觀史學,其關注的是政治史、英雄人物的歷史、斷代史、國別史等,歷史被描述為一種一直向前進步的線性發展的歷史。傳統史學對歷史進行宏大敘事,認為歷史是由上帝、理性等某一種決定性的力量推動的,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宏觀史學的最著名代表就是黑格爾。應該說,宏大敘事歷史哲學對于幫助人們認識和了解歷史有非常積極的作用;但它作為歷史研究過程的一個階段,必然不是完美的,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和擴展,隨著當代社會諸多領域中發生的變化,歷史研究的范式也必須不斷地轉變,來適應時代的需求。“年鑒學派反對那種認為歷史決定論可以用編年順序把個別偶然事件連結起來的觀念。他們提出了一種極為豐富的,關于人類時間的概念。他們借鑒了社會學、人口學和經濟學,而在這些學科中,人們談論的是結構、情勢、周期、增長等等。與此同時,歷史因果關系也不再束縛于有規則的演進概念。相反,他們設計出了一系列功能關系,而且未必遵循年代順序。”[4]
在年鑒學派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學派的創始人馬克·布洛赫提出過歷史研究的對象是總體史。他認為:“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而只有通過眾人的協作,才能接近真正的歷史。”[5]這與傳統史學只關注政治史、帝王將相的英雄史相比,極大地擴展了研究對象的范圍,不再只有國王、精英才被收錄進歷史,被統治的人、普通大眾也成為了歷史研究的對象。隨著歷史研究對象的擴大化,傳統史學研究的局限被打破了。決定歷史發展的不僅僅是某一種特定的因素,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開始被作為影響歷史發展的因素而受到同樣的重視。“為了摧毀傳統史學,年鑒學派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他們吸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地理學家入盟并非為了對歷史學進行些無關痛癢的改進。年鑒學派從其他社會科學中汲取了許多概念、方法和假設。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弗爾的策略是搜羅所有新的話語和規則,并將此作為贏得權力的手段。作為第一步,他們發出了破除學科藩籬的號召:走出你們的戰壕!這便是年鑒學派向其他人文科學發出的示好協約。”[6]46
在年鑒學派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布羅代爾成了這一學派的代名詞,這一階段也是年鑒學派的輝煌時期。布羅代爾提出了“長時段”理論,他認為可以把歷史分成三種時段: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傳統歷史學關心的是短時段、個人和事件。長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它的那種急匆匆的、戲劇性的、短促的敘述節奏。”[7]相比于短時段和中時段,長時段才是歷史時間的最深層,把握長時段中某種相對穩定的綜合結構是正確認識這段歷史的關鍵。在布羅代爾看來,經濟變化、政治變革等大多屬于短時段或中時段的歷史現象,雖然從表面上看經濟政治現象具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它們對歷史的影響并不大,真正對歷史演進構成深刻影響的是文化等長時段現象。“和其他時段相比,長時段享有特殊地位,它決定著事件和情勢的節奏,劃定了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的界限,并在一定限度內對變數進行調節。如果說事件屬于邊緣地帶,情勢屬于循環運動,那么只有長時段的結構是不可逆轉的。長時段的優勢在于它可分解為若干個不斷反復的事件系列,這些事件系列能持續顯示出被混亂事實所掩蓋的平衡和普遍規則。”[6]105-106布羅代爾對歷史上的時間作了多元化的理解,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歷史時間觀的產生。從這種歷史時間的多元性出發,布羅代爾又對整個歷史進程作了多層次的解釋。在年鑒學派兩代學者的努力下,新的歷史研究方式的影響越來越大,歷史研究再也不是線性的、單向度的圍繞政治史展開的研究,而是變成了多線索、多角度、立體式的圍繞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在內的人類社會的總體史研究。
“年鑒學派發展到第三階段,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即力圖修正‘長時段’理論的缺陷。經典年鑒學派提倡總體史學,把社會看成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而年鑒學派第三代學者卻認為歷史的間斷性是決定一切的因素,否認各種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因此,他們研究的也都是一些歷史上孤立的現象。”[8]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對心態史的研究成為了年鑒學派第三代學者的最大特征。其實早在布洛赫、費弗爾時就已經把對心態的考察列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因素來考慮,但是第三代學者與前兩代圍繞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進行總體性研究的方式不同,他們又把目光投向了更細的層面——日常生活,和更深的層次——社會心態。此時的年鑒學派學者不再局限于問題史,越來越多地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為研究的對象,“勒華拉杜里在《蒙塔尤》一書中詳細敘述了14世紀時,一些普通的牧羊人在上阿列日一個偏遠山村的日常生活。他再現了長期被歷史所忽略或無視的普通人,把日常活動納入了當時的表象領域。”[6]160尤其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失去了主體地位,不再是科學技術的主人,而是反過來變成了科學技術的附庸。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年鑒學派開始了量化的和破碎的歷史描述。“進步理念的危機促進了前工業文化的復興。因此,新史學全身投入對傳統的探尋,并更注重反復性事物和個人的曲折經歷。由于沒有集體計劃,這種研究變得更為個體化和局部化。在研究中,史學家把歷史上的重大時刻和人為的轉折拋在一邊,而唯獨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記憶。”[6]154
在三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年鑒學派成功地創立了一種新的史學研究模式,對傳統史學研究所采取的線性的、圍繞政治史進行宏大敘事的歷史解釋模式造成了極大的沖擊。綜合三代學者的研究特點可以看出,年鑒學派主張在歷史研究中把社會當作一個經濟、政治、文化、人的心態等諸多因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系統來認識,通過采取結構的、多元時空的研究方法,多角度、深層次地把握歷史。
年鑒學派對傳統史學的挑戰和革新對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年鑒學派提出對長時段的重視,促成了對線性史觀的沖擊。“長時段”理論所產生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與連續性相對的斷裂獲得歷史學家們的肯定,成為了歷史研究的起點。而斷裂同時也成為了后現代歷史哲學研究的起點。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充分肯定了“長時段”理論的重要意義,并認為它實際上完成了一種解構。福柯指出:“當代歷史中長時段的出現不意味著向歷史哲學、世界的洪荒時代或者向由各種文明的命運所規定的那些階段的返歸,它的出現是在方法論上慎重制訂序列的結果。”[9]而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后現代歷史哲學也影響了年鑒學派的歷史研究方向和主題,使之走向了碎屑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赫勒的后現代歷史哲學所提出的一些觀點與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學者所提出的觀點有很多相似之處,二者都反對以往傳統史學中所尊崇的基礎主義、本體論、中心主義,而重視日常生活中的各方面要素,用碎片化的方式來描述歷史。
三、赫勒的歷史哲學與年鑒學派“新史學”基本精神的相同
通過上述對赫勒的歷史哲學和法國年鑒學派的“新史學”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赫勒還是法國年鑒學派,他們所進行的史學革新都是源自對傳統史學的不滿。正是由于這種目的上的同一性,使得我們能夠通過分析,探尋出他們兩者之間存在的一些相似之處,比如:兩者都明確反對以往宏大敘事的歷史敘述方式,反對“大寫的歷史”而重視“小寫的歷史”;兩者都反對以某種單一的因素作為決定歷史發展的原因,都認為歷史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兩者都注重對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個人日常生活等在內的各個方面的考察。
總體而言,赫勒的后現代歷史哲學與年鑒學派的史學革新有兩個相同之處:
第一,兩者都對傳統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質疑,擴展了史學研究的范圍。無論是赫勒所提出的碎片化的后現代歷史哲學,還是法國年鑒學派的“新史學”,都明確反對傳統的歷史學研究中只重視政治史的方式,主張歷史研究和歷史敘述都應該把視野擴大,對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等諸多方面進行研究;二者都在承認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主張把關注的對象從帝王將相擴展到普通人。“年鑒群體三代人突出的成就,在于開拓了廣袤的史學領域。這一群體已將史學家的領域,拓展至出人意表的人類活動領域及傳統史學家忽視的社會群體。與這一史學領域的拓展密切聯系的,是對新史料的發掘及對相應所需新方法的開發。與之密切相關的還有與研究人類的其他學科——從地理學到語言學,從經濟學到心理學——的合作。”[10]赫勒和法國年鑒學派在史學研究對象的問題上對傳統史學的挑戰,為更加全面、客觀、準確地研究歷史、敘述歷史真相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兩者采用了相同的歷史學研究視域,即微觀視域。傳統史學之所以能夠長期在歷史學研究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就是因為這種傳統史學提出的宏大敘事的歷史學研究模式為史學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只不過,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無論是社會生活還是人的思維都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態勢,傳統史學那種“找出一個單一的要素來作為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的歷史解釋模式已經難以令人信服了。在宏觀史學中備受關注的“大寫的歷史”,即那些政治史、英雄史、國別史、民族史等,已經無法反映出歷史的全部面貌,無法為歷史發展提供解釋,因而備受爭議,并失去了信徒。人們已經注意到,那些在宏大敘事中被遮蔽了的所謂微不足道的人物、事件,在歷史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不但并非微不足道,甚至有時還是極其重要的,或者可以說是決定性的。為了避免宏大敘事研究方式在歷史研究中出現的片面性和不足,赫勒和法國年鑒學派都以一種微觀的視域開展了歷史研究,將社會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涉及人的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納入到歷史研究和敘述的范圍之中,摒棄了對整體的“單數的人”的重視,轉向對個體的“單數的人”的注意和研究。正是因為研究范式從宏觀到微觀的轉變,赫勒和年鑒學派得以沖破傳統史學研究在范式上的限制。“年鑒學派的新史學對政治軍事等大事件背后的日常生活、生產方式、文化等長時段歷史要素的分析,在研究范式上與20世紀的生活世界理論,特別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有著深刻的一致性。把日常生活世界從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線上,使理性自覺地向生活世界回歸,是20世紀哲學的重大發現之一,胡塞爾、維特根斯坦、許茨、海德格爾、列斐伏爾、哈貝馬斯、赫勒等許多理論家從不同層面推動了這一哲學轉向。”[11]赫勒也在《歷史理論》《碎片化的歷史哲學》《現代性理論》這“三部曲”中,通過微觀視域的運用,把自己的歷史哲學從一種不完整的歷史哲學,即歷史理論,發展為碎片化的歷史哲學,并對現代社會中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了細致的分析。
當然,赫勒的后現代歷史哲學與年鑒學派的史學革新之間也有一些區別。一個最明顯的區別就是,相比而言,赫勒的后現代歷史哲學有著更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批判性。法國年鑒學派的學者們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提出總體史、長時段、心態史等觀點,并批判了傳統史學。他們的這種批判主要針對的是史學研究的方法,而非社會現實。而赫勒的后現代歷史哲學深受馬克思社會歷史理論的影響,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是一種批判理論。因此,赫勒在對傳統宏大敘事進行批判的同時,也對現實進行了批判,并嘗試著通過這種批判而為人從現代性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尋找道路。
總之,無論是赫勒的后現代歷史哲學還是法國年鑒學派所進行的史學革新,其目的都是更加全面、準確、客觀地研究和解釋歷史。二者所主張的從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各個角度來進行歷史研究的方式,對傳統史學形成了挑戰,為人們認識歷史、把握現在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也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人從帝王將相的陰影中解放出來而真正地成為了歷史的主體。
[參考文獻]
[1][匈]阿格妮絲·赫勒.歷史理論[M].李西祥,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
[2][匈]阿格妮絲·赫勒.碎片化的歷史哲學[M].趙海峰,高來源,范為,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
[3][匈]阿格尼絲·赫勒.現代性理論[M].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5.
[4][法]保羅·利科.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M].王建華,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38.
[5][法]馬克·布洛赫.為歷史學辯護[M].張和聲,程郁,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8.
[6][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M].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7][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M].劉北成,周立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9.
[8]張正明.年鑒學派史學范式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41.
[9][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M].謝強,馬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7.
[10][英]彼得·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M].劉永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04.
[11]衣俊卿.社會歷史理論的微觀視域(上)[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58-59.
〔責任編輯:余明全〕
[中圖分類號]B515;K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4-0016-05
[作者簡介]范為(1982-),男,黑龍江哈爾濱人,助理研究員,博士,從事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研究。
[收稿日期]2016-03-03
中東歐思想文化研究
·布達佩斯學派歷史哲學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