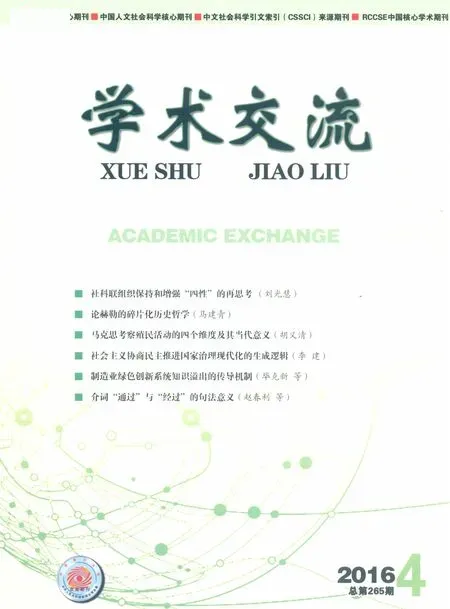論似真推理的價值證成
杜文靜
(華東政法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1620)
?
法學研究
論似真推理的價值證成
杜文靜
(華東政法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1620)
[摘要]在傳統邏輯中,演繹推理要求前提真結論必然為真,歸納推理要求前提真結論可能為真。似真推理則要求命題似真結論也似真,其結論是非決定性的,這是一種可廢止的推理。因此,似真推理被認為是不同于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的第三種推理類型。似真推理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雖先后遭到柏拉圖的抨擊、邏輯學家和宗教勢力的壓制,以及帕斯卡的批評,但在卡爾尼德斯(卡涅阿德斯)提出似真推理的系統理論之后,洛克和邊沁將其發展,似真推理在推理體系中的地位逐漸得以牢固確立。威格莫爾將其作為法律證據的核心,波利亞闡述了其在數學領域的重要地位。如今,似真推理在人工智能、法律論證、法律證據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在人工智能領域,似真推理可處理不一致信息推理,可基于不相容數據資料而進行推論。在法律論證領域,似真推理是證據推理概念的基礎,是法律論證中最重要的推理。
[關鍵詞]演繹推理;歸納推理;似真推理;法律論證
縱觀古希臘時期以來的邏輯發展,在亞里士多德三段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演繹邏輯和以培根三表法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歸納邏輯傳統上被認為是邏輯學的兩種主要類型。二者分別以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為研究對象。而似真推理一直處于邏輯的邊緣地帶,甚至有學者認為似真推理不是邏輯知識體系的一部分,而是一種論辯的手段。通過梳理似真推理的發展脈絡,本文認為似真推理是不同于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的第三種推理。這種類型的推理在法律論證理論和人工智能領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應用價值。
一、似真推理及其基本特征
在古希臘時期,學者們經常提及“弱者與強者打架”的案例,案中雙方互相指斥對方是爭斗的挑起者:弱者說他非常清楚自己沒有任何優勢,所以不可能首先攻擊如此強壯的對方;強者辯稱自己不可能襲擊比其瘦弱的對方,因為他明白自己在法庭上不會得到任何支持。他們是通過怎樣的推理過程得到各自結論的呢?顯然既非演繹推理也非歸納推理,他們的推理過程建立在表象(appearance)、可能性(likelihood)、蓋然性(probability)和似真性(plausibility)的基礎上。雙方從各自角度出發,通過解釋案件發生的情形而建立起兩個不同的推理。雙方都使用了人們(包括陪審團)所熟知的“可能性”概念,因此其推理與陪審團如何評價這兩個競爭性解釋的似真性也有聯系。我們把這種訴諸可能性、蓋然性或似真性的推理或論證稱為似真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或似真論證(plausible argument)。
歷史上,這種推理又被稱為蓋然主義。然而,蓋然主義這一術語的運用導致了諸多關于似真推理的誤解。許多學者認為,古希臘懷疑主義哲學家倡導的似真推理只不過是現代概率推理的一種過時的、錯誤的版本。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似真推理不同于演繹推理,也不同于歸納推理。古希臘時期,似真推理的名稱是希臘語eikós,該詞語具有相似性(similarity)、貌似真實(verisimilitude)、類似真實(truth-likeness)、可能性、蓋然性、似真性等多種含義。經過文獻研究,筆者提出,基于eikós的推理實質上就是現代的似真推理。有學者將probability翻譯為概然性、或然性,將likelihood翻譯為似然性。為了避免今后術語使用的混亂,我們約定:基于eikós、古代蓋然性、似真性的推理統一翻譯為似真推理,似真性對應的英文可以是plausibility(plausible)、possibility(possible)、verisimilitude(verisimilar)、true-likeness(likely to be true);而訴諸蓋然性的推理稱為概率推理,它是以現代統計概率為基礎的推理,蓋然性對應的英文可以是probability(probable, probabilistic)、likelihood。
沃爾頓主張,似真推理的結論被作為一種假設而暫時接受,故其結論是非決定性的。因此,似真推理是不同于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的第三種推理。沃爾頓等人提出,似真推理具有11個特征:(1)似真推理的過程是從一個似真性較強的前提推出一個進行似真論證之前似真性較弱的結論;(2)聽眾對聽到的事情比較熟悉或自己的腦海里有相關實例時,會認為這個事情是似真的;(3)似真推理基于共同擁有的知識(common knowledge)之上;(4)似真推理是可廢止的;(5)似真推理基于熟悉環境下事物通常的發展方式;(6)在不完全論證中,似真推理可用于填補隱含的前提;(7)似真推理通常建立在通過感知獲得的表象之上;(8)穩定性是似真推理的一個重要特征;(9)似真推理可付諸檢驗,并以此得到確證或反駁;(10)在對話中探究似真推理是檢驗它的一種方法;(11)似真推理可以用似真度來衡量,但度量方式不同于帕斯卡概率理論中的標準概率值和貝葉斯規則(Bayesian rules)。[1]114
二、似真推理的歷史演進
(一)似真推理的古代起源
似真推理起源于古希臘時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為了能夠給一些沒有目擊證人、書面證明或其他無懈可擊的直接證據的案子進行成功辯護,古希臘西西里島的司法演說家們設計了一套完美的論證方法,將論證建立在陳述的內在或外在的似真性基礎之上。這種新的論證方式在實踐中經常被演說家們使用,在理論中也常常被學者們探討,并被冠以希臘語eikós的名稱。對于演說家們來說,這種基于似真性的論證有一個最大優點,即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論辯技巧。亞里士多德稱之為技巧性的(technical)、狡猾的(artful)論證。但不可否認,在直接證據不具有決定性且證人證言有疑問或不可獲得時,似真論證作為一種最有用的主觀論證類型,在理性說服未實現時仍具有證明力。
似真推理的創立與古希臘修辭學的興起有著密切聯系。克拉克斯(Corax,前500?—前400?)和提西阿斯(Tisias,前500?—前400?)被認為是修辭學的創始人,似真推理也歸功于他們兩人的成果。著名詭辯家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前481—前411?)和高爾吉亞(Gorgias,前483?—前375?)也運用過似真推理。在公元前500—前400年期間,似真推理盛行,在古希臘論辯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安提豐(Antiphon,前426?—前373?)、利西阿斯(Lysias,前450?—前380?)、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皮浪(Pyrrhon,前365?—前270?),以及其他的早期阿提卡論辯家(Attic orators),都在演說中廣泛使用似真推理方法,甚至希羅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前400?)這樣的歷史學家也頻繁運用過似真推理。[2]1-2
(二)柏拉圖的批判
似真推理建立在個人基于自己熟知的、能理解的常識經驗而對當時情形形成的認知的基礎之上,其結論是非決定性的。一個命題對某個觀察者來說似乎是真的,但對另一觀察者來說又可能是假的。對同一個有爭議的案件,很有可能構造兩個互逆的似真論證,它們指向不同的案件結果。正因如此,似真論證被指責為具有欺騙性、詭辯性和非真實性。例如上述“弱者與強者打架”的案例中,強者論證就是弱者論證的逆論證,它抵消了先前弱者論證的證明力,恢復了似真性的平衡狀態。柏拉圖一度攻擊似真推理,作為對懷疑主義哲學家的批判。例如柏拉圖評論道:“讓提西阿斯和高爾吉亞安息吧!他們認為似真性比真理更值得推崇,他們借助演講的力量使得一些很小的東西變得看起來很大。”[2]3這一攻擊導致似真推理在整個哲學史上遭到學者們的強烈排斥。
但以現代視角分析,柏拉圖曲解了eikós論證的原本含義。基于eikós的推理并沒有欺騙性,因為在證據不足以得出決定性結論時,似真推理作為一種最有用的主觀論證仍然是有證明力的。似真推理的結論只是暫時性地被接受,當有新的反對證據被證實時,該結論可以被推翻,甚至廢止。正如加加林所指出:柏拉圖的評論是不公正的,提西阿斯、高爾吉亞和安提豐等人并不認為似真性比真理更好、更強、更有價值,他們只是在沒有書證、目擊證人證言等可靠直接證據的那類案件中,以似真論證作為權宜之計,此時“真理”要么不可獲得,要么是非決定性的。[3]
(三)卡爾尼德斯的似真推理
時隔大約200年后,柏拉圖學院的第三任領袖卡爾尼德斯(Carneades,前214?—前129?。通譯為“卡涅阿德斯”)發展并完善了似真推理的概念,并提出一套較為系統的似真推理理論。卡爾尼德斯創立似真理論,是為了反對斯多葛學派(Stoics)的如下認識論主張,即:認知印象是對明顯被感知的事物的準確捕捉,因此可以提供一種確定印象內容為真的可靠標準。對此,卡爾尼德斯舉出一些基于欺騙性表象例子的、大家所熟悉的懷疑論論證,對斯多葛學派的主張進行了攻擊。然而,這一攻擊也使學院派遭到如下反駁:他們缺乏任何引導智者決策的可接受性標準。為了回應這個反駁,卡爾尼德斯提出其似真推理理論,允許智者暫時接受似真的印象。即使不能確定這種印象達到排除了合理懷疑而為真的程度,只要智者意識到這種接受是可廢止的,他也就可以合理接受這種似真印象。在卡爾尼德斯的似真理論中,初始印象需要得到檢驗,例如通過與其他印象進行對比。如果初始印象沒有通過檢驗,則撤回接受;如果通過檢驗,則可以確認它比先前更似真,進而為接受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
卡爾尼德斯的理論認為,如果一種表征滿足三個標準,則可以暫時接受它具有似真性。第一,如果它看來為真,則具有似真性;第二,如果它看來為真并且穩定,也就是說它與其他看來為真的命題相容,則它更加具有似真性;第三,如果它可付諸檢驗且通過檢驗,則它具有更進一步的似真性。
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160?—210)通過“繩子和蛇”的故事來闡釋卡爾尼德斯的三重標準理論:一個人在昏暗的屋子里看到一卷繩子,急忙從上面跳了過去,當時他猜想這是一條蛇;但隨后他轉過身去探究事實,當看到它并未移動時,他已經開始認為它不是蛇;盡管如此,他心中還是揣測道,冬天里被冰霜凍僵的蛇也一動不動,于是他用棍子撥了一下這圈東西,得出這樣的結論——呈現在他面前的東西是繩子,而不是蛇。此人在昏暗的屋子里看到一圈類似于繩子的東西,基于其表征,他提出一個假設:這個東西是繩子。這是第一個標準,即“這個東西是繩子”看來為真。但由于昏暗看不清,他心中琢磨:這東西也可能是蛇。基于這一假設,并出于安全考慮,他從這個東西上跳了過去,隨后轉身觀察,看到它沒有動。基于這個新的表征,他轉向了一個新的假設:此東西是繩子。這是第二個標準,即“這個東西是繩子”看來為真并且穩定。隨后他又想到凍僵的蛇也不會動,所以用棍子撥了撥這個東西,感覺不是蛇。該檢驗確證了此東西是繩子,而不像他一度認為的那樣是蛇,這就是第三個標準。因此,人們暫時接受“這個東西是繩子”為真。但當引入新證據,該假設可以推翻,例如屋內亮燈后發現這是條死蛇,就可以推翻“這個東西是繩子”的假設。
(四)中世紀和啟蒙運動時期的似真推理
雖然似真推理在卡爾尼德斯時期進入一個新的活躍階段,但對于其與邏輯之間的關系,大家莫衷一是。在古希臘,似真推理有時被歸為修辭學或說服藝術一類,有時被歸為邏輯的一部分。然而,古希臘及中世紀學者普遍認為,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比起似真推理更具有基礎地位。在中世紀,似真理論受到邏輯學家和宗教勢力的批判。一方面,邏輯學家認為,似真推理不是邏輯的一部分,而是一種論辯手段。三段論是邏輯學的基礎,在邏輯中占據主導地位,學者們把研究焦點集中在基于三段論的演繹推理上。另一方面,在當時的社會,宗教占統治地位,人們強調教條信仰,認為似真推理雖早于基督教但與基督教教條相悖,故稱之為異端。因此,似真推理理論的發展在中世紀受到了嚴重的壓制。
在啟蒙運動時期,似真推理的思想遭到了帕斯卡的嚴厲批評。帕斯卡嘲笑似真推理是一種關于道德推理和決策推理的主觀的、有偏見的嘗試。他把以歐幾里得幾何學為典型代表的幾何推理看成通達真理的唯一客觀方法,而把其他所有推理都看成是主觀的,看成“內心問題”,因而對其置之不理。到此,似真推理被認為是一種不科學的推理,是不道德的人所使用的具有欺騙性和詭辯性的伎倆。帕斯卡的抨擊致使似真推理的思想在啟蒙運動時期消失殆盡。
(五)洛克、邊沁和威格莫爾的似真推理
似真推理思想在帕斯卡時代處于逐漸消亡的境地,但比帕斯卡稍晚的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重新提起這種古老的思想,并以之作為其哲學體系的核心。洛克提出演繹推理與似真推理的區別。他以三段論作為演繹推理的例子指出,雖然三段論推理在科學領域和基于知識的推理中很重要,但在法律推理和日常論證這類缺乏完整或確定性知識的情形下則“很少或根本沒有用”。根據洛克的評價,演繹推理缺乏靈活性,不能像似真推理那樣應用于包含不確定事實的論證之中。洛克甚至認為,很多情況下似真推理是比演繹推理及評價論證更好的工具。
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沿用了洛克的思想,并把它作為核心成分并入其“證據自然理論”之中。在洛克和邊沁之后,似真推理作為威格莫爾(John Henry Wigmore,1863—1943)證據理論的基礎,再次活躍起來。威格莫爾要求所有法律證據都必須建立在“日常邏輯的理性根基”之上,而這種根基主要就是似真推理。在威格莫爾的證據理論中,案件的所有證據被表示為一個與推理相關的命題網絡,命題之間的推理關系都以命題的似真性為基礎。[4]115-122
(六)波利亞的似真推理
20世紀50年代晚期,在人工智能來臨前夕,符號邏輯支持者認為符號邏輯可以滿足人類對推理工具的需要。然而,符號邏輯是演繹推理的形式化,而演繹推理只不過是推理的一部分,我們還需要其他推理模式。波利亞主張,即使在演繹推理占絕對優勢的數學領域,也需要以似真推理作為補充。他撰寫了兩卷巨著《數學和似真推理》,以闡明似真推理是產生新數學猜想的方法。[5-6]在第一卷中,波利亞為了讓學生能夠掌握猜想新數學結果的方法,把歸納法和類比法都作為似真推理的主要來源。波利亞勸告學生:誠然,我們要學會證明,但我們也要學會猜想。哈爾莫斯在評論此卷時說:“好的猜想跟好的證明同樣重要”[7]。在第二卷中,波利亞構建了多種似真推理的模式,也討論了這些似真推理模式與概率演算的關系。波利亞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的例子,以此說明如何通過確定性的規則運用似真推理。
波利亞指出,很顯然,在任意長的演繹推理鏈中,結論具有和前提一樣的確定性。而在其他類型的推理中,結論的可靠性將隨著推理鏈的延伸而逐漸變弱。波利亞指出,即使是純數學家,大多數時候實際使用的也是那些較弱類型的推理,而不是演繹推理。當然,數學家要提出一個新定理,還是要非常仔細地使用演繹推理給出證明。但引導數學家發現定理的過程,幾乎總是那些較弱類型的推理。在波利亞看來,推理只有兩種類型,一是演繹推理,二是似真推理(數學中又譯為“合情推理”),而歸納推理僅是似真推理的一個特殊情況。波利亞認為數學的證明是演繹推理,而物理學家使用的歸納證據、律師使用的情況證據、歷史學家使用的文獻證據及經濟學家使用的統計證據統統屬于似真推理。
三、似真推理的應用價值
如上,似真推理理論經歷了“興起—遭受歧視—發展并形成理論雛形—長期被邏輯和科學界忽略—在法律論證、數學、人工智能中活躍”的發展歷程。目前,它在法律論證、人工智能、科學領域中蓬勃發展。似真推理的應用研究受到艾倫(J. Allen)、霍其森(D. Hodgson)、約瑟夫森夫婦(J. Josephson and S. Josephson)及沃爾頓等許多知名學者關注,相關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展現出廣闊的發展前景。
(一)人工智能中的似真推理模型
論證的邏輯建模是當代人工智能領域的一大熱點。該領域已開發出許多著名的軟件,如英國敦提大學計算機系里德(Chris Reed)等人研發的阿拉卡利亞系統(Araucaria)、荷蘭格羅寧根大學人工智能系維赫雅(Bart Verheij)研發的論證仲裁系統(ArguMed 3)、德國弗勞思霍夫協會開放通訊研究所(Fraunhofer FOKUS)戈登(Thomas Gordon)和加拿大溫莎大學沃爾頓共同研發的卡爾尼德斯論證系統(CAS)等。其中,卡爾尼德斯系統的核心推理模式就是似真推理。該系統是一個由定義和數學結構組成的數學模型,也是一個計算模型,每個數學結構的函數都是可計算的。該系統通過定義論證的數學結構來識別、分析和可視化論證案例,利用論證規則和論證畫圖工具建立論證結構和應用的模型。基于這個系統,沃爾頓等人分析了“繩子和蛇”的案例。[1]106-110
人工智能中需要處理不一致信息推理,也就是要消解問題。在這方面,雷斯切提出的似真推理理論[8]給出了很好的解決方案。他把似真理論表述為進行“沖突消解”(inconsistency-resolution)的一般原則,即面臨認知沖突時運用的一種“極小化最大潛在損失”(minimax-potential-loss)的策略。雷斯切認為似真推理是非概率的,他沒有將概率理論作為似真推理的基礎,而是以概率為參考,以傳統的模態原則為基礎,根據最弱的前提而確定推理的結論。這樣就只需綜合使用演繹推理和排序比較,不需要使用復雜的概率演算。這種似真理論比概率理論簡單。基于這種似真推理方法,我們處理似真性時只需進行比較、排序,不需要涉及融合各種數量關系的演算。雷斯切以命題來源的可靠性衡量命題的似真性,命題來源可以是人、組織機構、人類的能力、智力活動和一些基本原則(如簡潔性、一致性)。似真性的度量僅涉及量化、可比、相對的排序,其排序分析只需使用1、(n-1)/n、(n-2)/n……1/n這些標尺來計算。似真性和蓋然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一方面,似真性不是最大時,一個命題和其否命題都可以有很高的似真性,如90%;另一方面,合取命題的似真性等于最不似真的合取支的似真性,這就是雷斯切提出的“最小似真前提規則”,即結論至少應與似真性最小的前提同樣似真。
在雷斯切看來,似真推理可基于不相容數據資料而進行推論。這種情況下,演繹形式邏輯是不夠充分的,因為它規定任何結論必須從相容的前提中推得。而歸納概率邏輯也是不相關的,因為它把歸納論證的概率定義為前提的概率“合取”結論的概率“除以”前提的概率,如果前提不相容,前提的概率為零,即這個除法的分母為零,這樣的定義就失去了意義。證據資料不完整甚至互相沖突時,演繹邏輯和概率理論無法告訴我們什么東西應該被合理接受,似真推理的方法卻可以為該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它可以將命題來源的可靠性轉移到結論的似真性。
(二)法律領域中的似真證據推理
在法律論證領域,似真推理是證據推理概念的基礎。傳統上研究證據推理,要么從演繹推理模式出發,要么從歸納邏輯模式出發。但沃爾頓在《法律論證與證據》一書中基于似真推理而提出了證據理論的一種新方法,即似真證據理論。在他看來,推理有三種類型,即演繹推理、歸納推理和似真推理。在傳統邏輯學界,似真推理被邏輯學家當作謬誤加以排斥;但沃爾頓認為,它恰恰是法律中證據推理的邏輯基礎。沃爾頓的基本思想是:通過似真推理,從一個(可信的)人的初始印象(從表面上看似乎是誠實的),推出某事物,且它被理性地接受,那么它就是證據。[4]204演繹推理的分析和評價建立在(邏輯)語義與語形維度之上,歸納推理的分析和評價建立在經驗事實基礎之上;而似真推理的分析和評價建立在語用維度之上,恰恰反映了法律證據推理的語用本質。當代非形式邏輯學家熱衷于把論證分為三種類型,即演繹論證、歸納論證和協同論證(conductive argument)。其中,協同論證本質上就是一種語用論證,因為其分析、評價和建構總是與作為另一個論證者的聽眾密切相關。因此,法律證據推理與協同論證具有高度契合性。協同論證與似真推理模式本質上是一致的。在證據法學中,傳統上并不區分間接證據(indirect evidence)和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但基于似真證據推理,沃爾頓把二者嚴格區分開來。我國已有學者關注到沃爾頓的這種證據理論。例如,唐世齊等人根據似真證據理論批判了我國法定證據概念理論中的“事實說”和“材料說”,并提出:證據是通過似真推理推出、被用于說服訴訟主體理性地接受訴訟結論的命題。[9-10]
似真推理的概念還是證據證明力概念的基礎,而證明力概念又是理解法律論證如何運用于證據法的基礎,因此似真推理是法律論證中最重要的推理。例如,在邊沁的“證據自然理論”系統中,證據推理不受人工規則的約束,而是建立在法庭之外日常推理所使用的似真性和證明力等概念的基礎之上。邊沁認為,一個命題的似真性程度可用一個公式計算,即似真程度等于支持似真命題證據的初始證明力減去每個反面證據的證明力。
[參考文獻]
[1]Walton Douglas,Tindale Christopher W,Gordon Thomas F.Applying Recent Argumentation Methods to Some Ancient Examples of Plausible Reasoning[J].Argumentation,2014,28(1).
[2]Kraus Manfred.Early Greek Probability Arguments and Common Ground in Dissensus[C/OL]//Ontari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University of Windsor,Windsor,June 6-9, 2007:Dissensus & The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2016-02-25]. http://scholar.uwindsor.ca/ossaarchive/OSSA7/papersandcommentaries/92.
[3]Gagarin Michael.Probability and Persuasion: Plato and Early Greek Rhetoric[M]//Worthington I.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London:Routledge,1994:46-68.
[4][加拿大]道格拉斯·沃爾頓.法律論證與證據[M].梁慶寅,熊明輝,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
[5]Pólya George.Mathematics and Plausible Reasoning(Volume I. Induction and Analogy in Mathematic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
[6]Pólya George.Mathematics and Plausible Reasoning(Volume II. Patterns of Plausible Reasoning)[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7]Halmos Paul R.Review: G. Polya, Mathematics and Plausible Reasoning[J].Bulletin of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1955,61(3):243-245.
[8]Rescher Nicholas.Plausible Reason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lausibilistic Inference[M].Assen:Van Gorcum,1976.
[9]唐世齊,焦俊峰.法定證據概念的誤區:基于似真性證據理論的批判[J].求索,2012,(1):144.
[10]唐世齊,李英山.似真證據理論對證據概念界定的價值[J].人民檢察,2011,(23):67.
〔責任編輯:余明全〕
[中圖分類號]D90-051;B8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4-0106-05
[作者簡介]杜文靜(1979-),女,河南新鄉人,講師,博士,從事法律證據推理、法律方法、法律邏輯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法律證據推理的歸納概率邏輯研究”(15BZX084);上海市社科規劃課題青年項目“法律證據推理的貝葉斯模型”(2014EZX002)
[收稿日期]2016-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