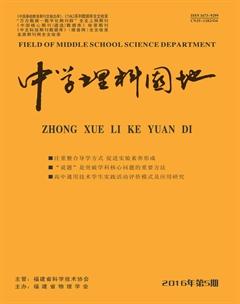實(shí)驗(yàn)構(gòu)建的“生態(tài)課堂”
黃瑞香
摘 要:生態(tài)課堂是學(xué)生積極學(xué)習(xí)的課堂,它以實(shí)驗(yàn)為基礎(chǔ),開展健康、富有活力的學(xué)習(xí)活動(dòng),借助獨(dú)立思考與合作交流的學(xué)習(xí)形式,營造有自信、相互尊重的學(xué)習(xí)氛圍,讓學(xué)生有自由、主動(dòng)、全面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空間。本文以“向心力的實(shí)例分析”這節(jié)課為例,把實(shí)驗(yàn)作為每個(gè)知識(shí)點(diǎn)的背景,結(jié)合學(xué)生的知識(shí)水平,教師逐步引導(dǎo),突破重點(diǎn)和難點(diǎn)。利用實(shí)驗(yàn)使學(xué)生在愉快的氣氛中獲取知識(shí),增加自信;通過展示實(shí)驗(yàn)和學(xué)生動(dòng)手、表演實(shí)驗(yàn),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探究和創(chuàng)新精神,從而建立生態(tài)課堂。
關(guān)鍵詞:物理實(shí)驗(yàn);向心力;生態(tài)課堂
引言
盧梭說:“教育必須順著自然——也就是順其天性而為,否則必然產(chǎn)生本性斷傷的結(jié)果。”教育家烏申斯基也指出:“沒有絲毫興趣的強(qiáng)制性學(xué)習(xí),將會(huì)扼殺學(xué)生探索真理的欲望 [1 ]。”當(dāng)前中學(xué)物理教學(xué)存在一些問題,如理論教學(xué)過度,抽象性大,許多學(xué)生難以適應(yīng)。物理教學(xué)雖然可以結(jié)合學(xué)生的生活經(jīng)驗(yàn),但是許多物理知識(shí)又超越了學(xué)生的經(jīng)驗(yàn),依靠生活經(jīng)驗(yàn)構(gòu)建物理情境往往不深刻,實(shí)效不大。據(jù)此筆者嘗試借助物理實(shí)驗(yàn)來構(gòu)建新的課堂教學(xué)情境,營造新的課堂生態(tài)。
生態(tài)課堂是學(xué)生積極學(xué)習(xí)的課堂,它以實(shí)驗(yàn)為基礎(chǔ),開展健康、富有活力的學(xué)習(xí)活動(dòng),借助獨(dú)立思考與合作交流的學(xué)習(xí)形式,營造有自信、相互尊重的學(xué)習(xí)氛圍,讓學(xué)生有自由、主動(dòng)、全面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空間。這種課堂需教師激情引入,點(diǎn)拔智慧技巧,愛心責(zé)任育人;學(xué)生學(xué)會(huì)自信參與,主動(dòng)交流、合作探究。
1 《向心力的實(shí)例分析》課例 生態(tài)課堂的建構(gòu)
“向心力的實(shí)例分析”這節(jié)課是在學(xué)生學(xué)習(xí)了向心力的概念、大小以及方向之后的一節(jié),該節(jié)要求學(xué)生會(huì)掌握在具體問題中分析向心力的來源的方法,以及繩球和桿球兩類模型在最高點(diǎn)的臨界狀態(tài)的速度分析;應(yīng)用向心力公式計(jì)算相關(guān)的物理量,分析在豎直平面內(nèi)做圓周運(yùn)動(dòng)的物體在最高(低)點(diǎn)的受力特點(diǎn)。下面是《向心力的實(shí)例分析》這節(jié)課的生態(tài)課堂的建構(gòu)。
1.1 播放實(shí)驗(yàn),展開教學(xué),提出問題引思考
首先通過多媒體播放飛行中的鳥或飛機(jī)轉(zhuǎn)彎時(shí),身體要傾斜,來吸引學(xué)生的注意力并激發(fā)學(xué)生的興趣。根據(jù)教學(xué)要求,結(jié)合學(xué)生的知識(shí)基礎(chǔ),提出問題。
師:大家知道為什么鳥或飛機(jī)轉(zhuǎn)彎時(shí)身體要傾斜嗎?
生:只有傾斜才能轉(zhuǎn)彎
師:轉(zhuǎn)彎時(shí)做圓周運(yùn)動(dòng),向心力由誰提供呢?
生:(通過受力分析)重力和浮力的合力提供做圓周運(yùn)動(dòng)的向心力。
師:如果轉(zhuǎn)彎時(shí)不傾斜,受力情況又是如何呢?
生:重力和浮力會(huì)相互抵消,沒有力提供做圓周運(yùn)動(dòng)的向心力,則無法轉(zhuǎn)彎。
師:是否所有的物體要轉(zhuǎn)彎都要傾斜身體呢?
生:想。
評(píng)析:通過視頻中自然現(xiàn)象,吸引學(xué)生注意力,提出問題,引發(fā)學(xué)生思考,訓(xùn)練學(xué)生分析向心力來源的方法,解決提出的問題,鞏固知識(shí),獲得成就感,從而調(diào)動(dòng)了學(xué)習(xí)的情緒,為接下來的學(xué)習(xí)奠定基礎(chǔ),營造氣氛。
1.2 演示實(shí)驗(yàn),推進(jìn)教學(xué),激疑解惑練思維
汽車水平路面轉(zhuǎn)彎時(shí)的向心力實(shí)例分析。
實(shí)驗(yàn):把一輛玩具小汽車放在桌面上的光盤上,轉(zhuǎn)動(dòng)光盤可模擬汽車在水平面上轉(zhuǎn)彎,實(shí)驗(yàn)?zāi)P腿鐖D1所示。
師:請(qǐng)同學(xué)們分析汽車做圓周運(yùn)動(dòng)時(shí)受力情況?
生:(通過受力分析)汽車受重力、支持力、靜摩擦力。
師:靜摩擦力的方向呢?
生:跟線速度的方向一致。
師:既然汽車會(huì)隨著光盤做圓周運(yùn)動(dòng),那么向心力由誰提供呢?
(學(xué)生這時(shí)會(huì)發(fā)現(xiàn)沒有力提供做圓周運(yùn)動(dòng)的向心力)
師:向心力的特點(diǎn)是要指向圓心,哪個(gè)力最有可能指向圓心呢?
生:靜摩擦力。
師:對(duì)。所以汽車轉(zhuǎn)彎時(shí)受到了兩個(gè)方向摩擦力的作用。指向圓心的靜摩擦力提供做圓周運(yùn)動(dòng)的向心力。
演示實(shí)驗(yàn):快速轉(zhuǎn)動(dòng)光盤,使得光盤上的玩具汽車向外甩出
師:為什么汽車會(huì)被甩出?
生:速度變大。
師:為了不讓汽車被甩出,速度最大為多少?最大的速度受什么因素制約呢?
通過列出向心力的表達(dá)式F=m,引導(dǎo)學(xué)生分析得出。
生:受最大靜摩擦力制約。
師:賽車的速度一般都會(huì)遠(yuǎn)大于普通汽車的速度,那么為什么賽車在轉(zhuǎn)彎時(shí)速度可以很大呢?
通過多媒體展示賽車轉(zhuǎn)彎軌道,引導(dǎo)學(xué)生觀察軌道的特點(diǎn),分析賽車轉(zhuǎn)彎時(shí)的受力情況,從而得出向心力的來源。
生:傾斜的軌道,使得提供賽車轉(zhuǎn)彎時(shí)向心力變大,所以允許的最大速度也變大。
評(píng)價(jià):通過模擬汽車在水平面轉(zhuǎn)彎的實(shí)驗(yàn),有助于學(xué)生找出向心力的來源,理解汽車轉(zhuǎn)彎時(shí)的受力情況,同時(shí)知道為什么轉(zhuǎn)彎時(shí)速度不能太大的原因。再加上對(duì)賽車轉(zhuǎn)彎軌道的認(rèn)識(shí),為后續(xù)的火車轉(zhuǎn)彎墊基礎(chǔ)。這樣設(shè)計(jì)可以逐步引導(dǎo)學(xué)生觀察思考,刺激學(xué)生的思維。
1.3 對(duì)比實(shí)驗(yàn),深化教學(xué),深入思考獲成就
火車在內(nèi)低外高的軌道面上轉(zhuǎn)彎。
展示火車和鐵軌模型(圖2),引導(dǎo)學(xué)生觀察火車車輪,教師提出問題。
師:火車在水平軌道轉(zhuǎn)彎時(shí),向心力由誰提供?
生:指向圓心的靜摩擦力提供。
師:火車車輪與鐵軌接觸面粗糙度不大,靜摩擦力小,不足提供做圓周運(yùn)動(dòng)需要的向心力。那么是誰提供的呢?
(學(xué)生紛紛討論,開始再次觀察火車模型,重新對(duì)火車受力分析)
生:外軌對(duì)輪緣的彈力提供火車轉(zhuǎn)彎的向心力。
師:火車質(zhì)量大,若僅靠外軌對(duì)輪緣的彈力提供向心力,則輪緣與外軌間的作用力很大,鐵軌很容易損壞,造成火車傾覆。那么有沒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決這個(gè)問題呢?
生:建個(gè)傾斜的軌道
評(píng)價(jià):火車轉(zhuǎn)彎時(shí)向心力來源對(duì)學(xué)生來說是個(gè)難點(diǎn),先通過對(duì)比實(shí)驗(yàn)讓學(xué)生觀察鐵軌,發(fā)現(xiàn)實(shí)際中的鐵軌跟他們?cè)O(shè)想的一樣,這時(shí)學(xué)生會(huì)很興奮,體會(huì)到鐵軌設(shè)計(jì)的思想,獲得成就感;教師再通過板書,逐步引導(dǎo)學(xué)生得出火車在傾斜軌道轉(zhuǎn)彎時(shí)的向心力表達(dá)式:mgtanθ=m,并分析得出規(guī)定速度取決于彎道半徑和傾角。
1.4 動(dòng)手實(shí)驗(yàn),拓展教學(xué),手腦并用探究實(shí)驗(yàn)
汽車過拱形橋——豎直面的圓周運(yùn)動(dòng)“向心力實(shí)驗(yàn)分析” [2 ]
演示實(shí)驗(yàn):利用書本以及紙張搭建一座凹形橋,如圖3所示。首先讓玩具小汽車靜止于凹形橋最低點(diǎn),再讓玩具小汽車有速度的駛過凹形橋,結(jié)果橋變形或斷了。
師:為什么會(huì)斷呢?
生:有速度,對(duì)橋的作用力變大。
師:這又是為什么?(引導(dǎo)學(xué)生對(duì)小汽車在凹形橋最低點(diǎn)處受力分析,找出過橋的向心力來源,從而得到汽車靜止與運(yùn)動(dòng)時(shí),對(duì)橋作用力的變化。)
教師演示實(shí)驗(yàn):把圖中的紙張改成軟紙板,搭建一座凸形橋,如圖4所示;先讓玩具小汽車靜止于橋頂,橋頂會(huì)有明顯的凹陷;當(dāng)小汽車駛過橋頂時(shí),橋頂沒有明顯的凹陷。
評(píng)價(jià):通過該實(shí)驗(yàn)引導(dǎo)學(xué)生思考小汽車在橋頂時(shí)的受力情況,找出向心力,分析實(shí)驗(yàn)現(xiàn)象,得出結(jié)論:小汽車過凸形橋受到的支持力小于重力。上述兩個(gè)實(shí)驗(yàn)所用材料簡單,學(xué)生可以自己動(dòng)手搭建,模擬實(shí)驗(yàn),培養(yǎng)探究精神。
1.5 表演實(shí)驗(yàn),升華教學(xué),體驗(yàn)表演釋樂趣
過山車向心力實(shí)驗(yàn)分析
師:大家看過水流星表演嗎?
生:看過
師:下面我們請(qǐng)一位同學(xué)來表演下水流星。
(同學(xué)利用如圖5所示的儀器表演,表演的很順利)
師:能否告訴同學(xué)們,水流星表演的技巧在哪里?
生:速度要夠快。
師:為什么呢?
生:想。
評(píng)價(jià):通過這樣一個(gè)有趣的表演,學(xué)生的積極性又再次被調(diào)動(dòng)起來,都急于想知道原因。這時(shí)教師再講解水流星在最高點(diǎn)、最低點(diǎn)的受力情況,引導(dǎo)學(xué)生找出向心力的來源,分析水不流出來所需要的速度。同時(shí)該實(shí)驗(yàn)也可讓學(xué)生體會(huì)到我們生活中充滿了物理知識(shí),物理知識(shí)又是來源于生活,鼓勵(lì)學(xué)生多觀察,多思考,多動(dòng)手。
2 討論
本節(jié)課通過播放實(shí)驗(yàn)、演示實(shí)驗(yàn)、對(duì)比實(shí)驗(yàn)、動(dòng)手實(shí)驗(yàn)、表演實(shí)驗(yàn)等多種實(shí)驗(yàn)形式,逐漸將“向心力實(shí)例分析”這節(jié)課開展深入,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興趣、解答學(xué)生的疑惑,使得學(xué)生獲得成就感等等。課例中模擬生活中做圓周運(yùn)動(dòng)的例子,有助于學(xué)生找出向心力的來源,同時(shí)使學(xué)生體會(huì)到物理知識(shí)不僅來源于生活,又可指導(dǎo)生活,體會(huì)物理的思想。鼓勵(lì)學(xué)生利用身邊的材料來制作模型,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動(dòng)手能力,探究精神。每個(gè)實(shí)驗(yàn)都能使學(xué)生的感官受到刺激,激發(fā)學(xué)生的探究欲望。教師再通過合理的發(fā)問和引導(dǎo),刺激學(xué)生的思維,讓學(xué)生自己逐步地找到答案,體驗(yàn)探索的樂趣,獲得成就感,增加了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自信,達(dá)到了建立生態(tài)課堂的教學(xué)目標(biāo)。
參考文獻(xiàn):
[1]吳蘭紅.“實(shí)驗(yàn)建構(gòu)式生態(tài)課堂”的構(gòu)建策略[J].中學(xué)物理教學(xué)參考,2014(3).
[2]黃正玉.物理習(xí)題實(shí)驗(yàn)化的案例分析[J].中學(xué)物理教學(xué)參考,20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