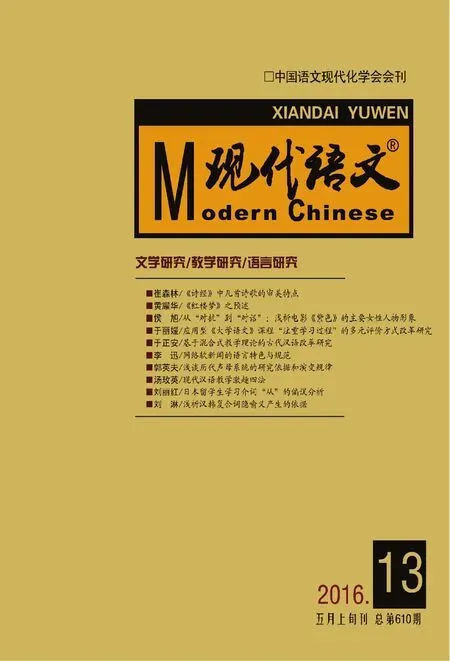語文作業權的回歸與重構
○陳 妍
語文作業權的回歸與重構
○陳 妍
作業的發展歷程從受教育者的義務走向受教育者的權利、從教師的權力走向教師的責任。回歸學生的作業自主權是基于學生心理、作業本質以及課改精神的。因此,學生在作業目標的決策與安排、作業內容的選擇與建構、作業過程的認可與尊重、作業評價的公正與參與中都應當享有廣泛的權利。本文以語文科作業權利的回歸與重構為例,探討為作業“爭權賦能”的必要性。
作業權 回歸 重構
作業是學生和教師溝通的紐帶,更是反映認知獲得的參照,衡量自身學業能力的指標。通過作業,教師可以細致觀測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適時調整教學重點,合理調控教學方向;學生則在鞏固知識、查找不足的基礎上形成獨特的作業觀。根據學生個性化的作業心理和作業觀,教師需要將傳統的學生權力觀引申至“作業權”的賦予與維護。學生受教育權主要包括教育起點上的權利,教育過程中的權利以及教育結果的公平對待權,其中實質性的權利主要是教育過程中的權利,語文作業正是學生的一種學習過程和生活方式,只有重視學生在作業中體現出的學習需要、生活需要和人生需要,語文作業才能發揮出它的最大功效,才能達到新課程標準下高中語文作業要培養學生的能力和素養的要求。
一、回歸作業權力的合理性
(一)語文作業的心理向度.
學生是作業的主體,是作業的主人,是作業目的本身,是不可忽視的對象。每個學生的作業觀不盡相同,有的認為是學習的需要,是獲取知識的路徑,產生一種愉快的內心體驗;也有的認為是一種負擔,是強加的任務,產生一種無形的壓力如作業倦怠。提倡“作業權利觀”是將學生的人權、受教育權以及話語權具體到為作業“爭權賦能”,學生會認識到:無論是筆記、作業本、練習冊、卷面或是板書、演示、觀點等都是我自己開發的領域,自主打造的成果,可以被質疑,不容被侵犯!這種維權意識能極大的提高學生自信,獲取積極的自我效能感,形成健全完善的人格。
(二)語文作業的價值取向
教師作業單一性與學生多方需求存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基于過程取向的作業,其過程性和可操作性決定了作業實施的民主性。教師布置的作業與學生可操作之間存在差異。馬克斯·韋伯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區分為工具的理性和價值的理性,工具理性即“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者‘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1],這種目的合理性更關注目的實現的結果和過程的可操作性,更關注手段的功效作用及現實可能性。語文作業則應緊扣“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學習過程,圍繞中心話題,展開協商,作業內容則根據需要拓展延伸,研發生成,做到始終追求語文核心素養的全面提高。
(三)課程改革的內在要求
基于新課程倡導全面、個性化發展的指導思想,針對教師和學生在作業問題上存在的差異,教師在設計任務難度、作業量乃至作業形式時就應特別注意到個別化特征,作業的設計也應當堅持新課改“民主參與,科學決策”的方針。從我國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三級課程管理體制來看,必修課程中綜合實踐活動就為學生提供了充分發揮主動性,充分實踐、自主學習、自由探究世界的作業空間;選修課程則提供了人性化、個人化的選擇機會;校本課程設置的邏輯起點就是基于學校情境和學生經驗、需要與興趣,充分發展學生的興趣。學生的權利不僅是接受前人的既定文化,完成教師日常的作業任務,更是作業意義生成的反思者和革新者,來實現學校文化傳遞、批判、創造與更新的使命,充分發揮學校教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重構作業權力的著力點
(一)作業目標的決策與安排
作業通常依據教學計劃蘊含著統一的目標與利益標準,要使這種“合作事業”普遍適用于個人,就需要師生統籌協商,集中智慧。傳統作業目標作為一種預設、一種集體事業,“人們已經自愿地接受了這種安排的利益,或者為了促進自己的利益已經自愿地利用了這種安排所提供的機會。并因此而按照為產生所有人的利益所必須的方式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權。”[2]不論作業權如何歸屬,作業目的都是要促進學習內容的保持與遷移,基于整體目標與個別發展,蘇霍姆林斯基指出應特別重視作業個別化,“如果教師不給某些學生布置一些個別性的作業,那就說明他沒有研究過每一個學生的力量、可能性和能力。”[3]
(二)作業內容的選擇與建構
受教育者通過作業積累的經驗價值體現在作業內容的個體意向性和生成性,這就要求學生有自主選擇與建構作業內容的權利。首先,學生對作業內容的選擇權,魏書生在《教師上課“十條”》中第八條認為一堂課要留有三種不同類型的作業題,讓學生按照自己的學習情況選擇完成。其次,學生對作業內容的建構與生成取決于學生這個特殊群體的個性化人格與多學科視角,如用副學科知識來分析主學科作業,以小說或戲劇的語言鑒賞為例,通過對人物對話的語義語調等語法點進行分析從而捕捉到人物性格及文本主題的深刻意義;如滲透跨學科知識,借鑒歷史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平行的學科知識來解讀文學現象,如用邏輯學的知識來理解閱讀題干與選項之間的演繹與推理,這不僅延伸了作業答案,更培養了多元智能與發散思維的能力。
(三)作業過程的認可與尊重
作業自主權利的獲得源自于師生之間的相互認可與尊重,表現為教師對學生作業過程的充分信任與尊重,學生對教師評價的認真接納與反思。當不尊重差異、強制橫向比較、關注少數學生、評價關系對立、評價語言缺乏正當性和深層次互動等倫理缺失充斥在作業系統中時,權利就會惡變為精神的負擔。只有在相互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學生才能掌握他們所能掌握的最大限度分量和深度的作業意義,使得“學習負擔最優化,并且不會超出科學規定的課內學習和家庭作業的實踐量。”[4]以錢夢龍“導讀語文”教學模式為例,在“自讀式-教讀式-復讀式”導讀流程中,自讀作為學生感知理解課文的實踐形式,是課內培養學生獨立閱讀能力的實踐性課堂作業。自讀在課堂教學中進行的時機靈活多樣,學生被賦予充分的作業權:“可以是嘗試性的教前自讀;可以是點撥性的教中自讀;可以是類比性的教后自讀。”[5]
(四)作業評價的公正與參與
教師的作業批改、評價方式與學生認可度之間存在差異。當教師被禁錮在作業批改任務中,就會不自覺地傾向于標準答案,形成單一化思維,無法抽出來時間更多地關注學生、指導學生,評價結果難以得到認同。運用“讓渡作業批改權利、加強對學生自批互批的培訓、引導小組成員互幫互學、師生對作業問題雙重跟蹤、對學生加強個別指導”[6]式的批改策略,做到權利交接,尊重、賞識、不控制學生,則有利于關注過程、體現公平、激勵學生積極參與到科學的精細的作業評價過程中。
結語
作業權利實際上就是教師或作業設計者通過與學生協商交流,從作業設計到作業反思的實施過程中重構作業意義的權利。語文學科有其外延廣、生活性和對話性等獨特的規律和特點,更容易使學生形成建議、質疑、批駁、感化的交流機制,更有利于作業權利的運行和實施。“如果我們打算在課程過程中授權給教師,那么我們也要在與學生年齡相適應的程序上授權給他們,使其能控制自己的學習,如果課程的確是衍生于參與者的對話之中的,我們就不能將學生拒絕于這場對話之外。”[7]這就要求教師在作業過程中真正實現“民主作業”,消解不合理的教師權威、消解在作業目標和內容選擇上的專斷以及行為認可與作業評價中的偏頗,真正實現權利在對話中回歸,意義在革新中重構。
注釋:
[1]林榮遠譯,[德]馬克斯·韋伯著:《經濟與社會》(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6頁。
[2]謝延光譯,[美]羅爾斯著:《正義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頁。
[3]杜殿坤編譯,[蘇]瓦·阿·蘇霍姆林斯基著:《給教師的建議》,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頁。
[4]吳文侃譯,[蘇]Ю.К.巴班斯基著:《教學教育過程最優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頁。
[5]陳寶祥:《“三主四式”,圓“夢”之路》,中學語文,2009年,第9期。
[6]劉瑩:《中學教師“零作業批改”實踐研究——基于“零作業批改”實驗學校的調查》,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7]柯森譯,[美]艾倫·C.奧恩斯坦,費明西斯·P.漢金斯著:《課程:基礎、原理和問題》,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頁。
(陳妍 安徽淮北 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23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