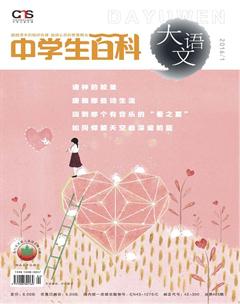卷耳
張定浩
能有力量長久跟隨我們的
是刺,不是花瓣
這是多么悲哀的想法。
當滿頭大汗的少年從灌木叢中跑出,
細小的卷耳沾滿他的全身,
他才不會這么煩惱。
他將像收集子彈一樣,收集這帶刺的卷耳,
預謀著在來日的課堂上
發動一場針對長頭發的戰爭。
他這么想著就笑了。
不遠處,采野菜的婦人
仍低著頭
薦詩/媛的春秋
這首詩的第一小節把我們迅速拉進一個有關生命預言的暗影之中,“悲哀的想法”猝不及防地將我們擊中。那令我們傾慕的花瓣,原來只是一個個脆弱、美麗、稍縱即逝的幻象;而令我們討厭和懼怕的刺,卻有著執拗的力量,能“長久跟隨我們”。過去歲月的荒謬和種種痛苦,不就是根根暗伏的刺?在一個人得意忘形時,冷不丁地再次刺出,提醒他自身的不完美和命運的不可測。
然而我們還未來得及發出成年人慣常的悲嘆,一個滿頭大汗的少年就從灌木叢里跑出,闖入我們的視野。第二小節的節奏明快,意象活潑,一掃第一小節帶來的陰郁之氣;虛詞“才”用得極妙,把青春少年那種毫無顧忌,頑皮灑脫的性情全然呈現。
這位少年所鐘情的,并非是荒原上的野玫瑰。他將像“收集子彈”一樣搜集細小的卷耳。那么,卷耳是什么東西?
兩年前,在家鄉一位朋友的果園里,我第一次見識“蒼耳”,在此之前只模糊記得這個名字代表一味中藥。只見它隨意地長在一條土堤壩上,葉子寬大如南瓜葉,隱藏在葉子下的蒼耳子綠茸茸毛刺刺,像蜷縮起來的小毛毛蟲。7歲的云裳和4歲的小表弟羽飛像發現了寶貝一般興奮,爭先恐后把“小毛毛蟲”摘下來,粘到大人的衣衫和裸露的胳膊上,大人假裝害怕,發出哇哇的尖叫。“其實并不疼啊!”云裳后來說。確實,蒼耳只會引起輕微的癢癢,絕不像玫瑰刺傷人,害得歌德筆下的輕佻少年手指流血,更害得多情的里爾克得了敗血癥,繼而丟了性命。
而卷耳就是蒼耳的別名。“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那丟下半筐卷耳,思念征夫的女子和她的馬匹還在苦苦攀爬遠古的山崗呢,這位現代少年就已急不可待地等著明日去捉弄同班女生了。帶刺的卷耳似乎在影射青春期懵懂莽撞的情欲。少年也許自己也未曾意識到,這小小的惡作劇的念頭竟起源于一種難以名狀的情緒。倘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發動這場針對長發女孩的戰爭,是少年不知如何向女孩表達愛慕,竟用笨拙荒唐的,帶有侵犯意味的游戲來引起女孩的關注。這樣的伎倆,你是否似曾相識?
第三小節制造了緊張的戲劇性效果:子彈,刺,預謀,發動,針對,長頭發,戰爭。但詩人并沒有把詩歌推向一個高潮的結尾。
正當讀者沉浸于對來日課堂鬧劇的想象中,詩人的視線轉向不遠處采野菜的婦人。她(們)仍低著頭,專注于手中勞動。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什么也沒有撞見過,世界安靜如初。田野山川的廣闊寂寥,釋放了少年所攜帶的蓬勃旺盛的,不無破壞性的生命能量;沉默勞作的婦人作為對莽撞少年形象的平衡,抵消了詩歌畫面里的躁動不安。這首“少年情詩”結束于一種具有永恒意義的靜謐之中。
“采野菜”這一從《詩經》時代就延續下來的詩歌場景,讓我回憶起在鄉村度過的七年光陰,常食腥膻的口舌向往起野菜的甘甜或清苦。我仿佛聽到鄉野的呼喚之音,也恍惚看到那低頭摘野菜的農婦直起腰身,手搭涼棚,朝我望過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