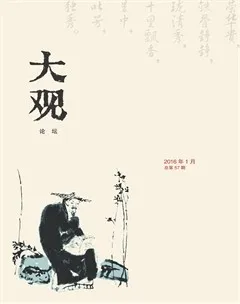武平客家山歌的形成根源及題材類別
李鳳英
摘要:作為新時期時代人類活動的早期遺址地,漢初南海國故都所在地的武平,在當時的南中國無疑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宋元南遷的漢人又把中原帶來的古漢族文化與之相結合,因而形成了獨特的武平客家文化。武平客家山歌,便是這種文化的一個典型代表。對于武平客家山歌的形成根源及類別,不同時期和地區有不同的見解,可以從不同的方面進行分類。筆者在對武平客家山歌充分調研后,根據山歌的主線,對武平客家山歌在形成根源及題材類別上進行進一步分類,有助于大家進一步了解武平客家山歌,感受武平客家山歌的魅力。
關鍵詞:客家山歌;根源;題材內容;類別
武平客家山歌,是武平人民的口頭詩歌,是能歌唱或能吟誦的韻文,是民間文學的形式之一。它蘊量豐富,多姿多彩,唱出了武平人民的心聲、民俗的風彩、時代的韻味。它形成時間長,已有千百年的歷史,分布廣泛,分別流布在武平十七個鄉鎮,二百一十余個行政村,是武平客家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武平客家山歌的形成,考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源于武平客家先民的組成部分——當地土著即古老畬族的一種文學文藝傳統。客家醞釀地區閩粵贛邊界,恰好是漢初南海國(介于閩越國和南越國之間)的轄區,而武平,正是南海國的王城所在地。據考,南海國封于漢高祖時期,滅于漢武帝,存在只有短短的幾十年,后被滅國遷民,貴族北遷,而留下的平民則廣布于廣袤山區丘陵地帶,這些平民,就是今天畬族的祖先。雖然畬族的語言和文學藝術形式沒有被傳承下來,但學者們認為,自東晉開始到宋元時期形成的客家人,是南遷漢族與當地土著畬族融合的一個民系,即漢族客家民系。客家人創造的歌唱山歌的文學藝術形式,部分傳承于畬族的民俗風情。
二是源于南遷漢民從中原帶來的文學藝術傳統。考各地客家山歌,包括閩浙各地的畬族山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山歌其實就是對中原古代七言詩或五言詩的傳承。如黃遵憲所言,《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即為婦人女子等普通百姓的歌詠,漢民族這種民間文學藝術的傳承,在西北地區便被演繹成信天游,在元末明初便被演繹成山歌詠嘆。如成書于該時代的《水滸》第十五回“智取生辰綱”中白日鼠白勝唱的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這既是七言詩,也是當時典型的山歌。
三是源于武平客家人的居住環境。武平屬丘陵地帶,山地盆地遍布縣境各地,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三十多座,其山多林密的自然環境,讓它以山歌為主要形式的情形創造了特有的條件。一個人進入深不可測的大山,難免會有一種對大自然的恐懼,對毒蛇猛獸的恐懼。于是,他們先是用“噢嗬”之類的長高音來呼喚同類,或嚇跑獸類,或為自己壯膽,繼而便發展到唱山歌。加之四面群山往往回應或放大這種聲音或歌唱,猶如一個天然大音箱,使這種聲音或歌唱音色更美、更具魅力,因而激勵著人們對歌唱的愛好,這也是大江大海和平原上少有歌唱的原因。
四是源于武平客家的勞動習俗。在客家社會里,舊禮教束縛很嚴,平常在家庭中或鄉村里,男女之間保持嚴格的界限,而迫于生計的客家男女又必須終日作業于田野山嶺之間。在長期的山間共同勞作中男女互相傾訴衷曲是預料中事。由于在家里拘束過嚴,到了山間其精神得到了解放,會自然地唱起山歌來。再加上舊時客家因沒有其他較為完備而普遍的民俗娛樂,而山歌有音韻的言詞比一般語言更能表達情意,所以男女對它都有共同的喜愛,一旦走到山上或原野谷中,不免唱幾首歌來發泄自己的感情。
五是源于武平特殊的地理位置。武平是閩粵贛三省交界的“金三角”,臨近江西的尋烏,會昌,廣東的蕉嶺、梅縣、平遠,福建的長汀、上杭、永定等縣,與鄰縣鄰省的經濟、文化、婚遷等交往尤為密切,作為民間口頭文學的輕騎兵——山歌,就相互滲透、傳播,經“過濾”、吸收或融合,就成為本地山歌。
此外,武平很多山歌也是本地居民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及其它活動中所產生的。
武平客家山歌,按題材內容來分,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是情歌。在浩如煙海的武平客家山歌中,愛情山歌始終是最主要的表現內容,也是山歌中最常見,占篇幅最大的部分。情歌或溫婉、癡情,或痛苦、酸澀,或大膽、濃烈,有表達對愛情的期待和憧憬,有對美滿婚姻的渴望和追求,有表達對封建婚姻制度的憤怒和不滿,有婉拒對方的追求等等,不一而足。愛情歌感情之真摯,愛情之鮮明,主題之突出,結構之嚴整,生動形象、淋漓盡致地展示歌者內心世界豐富復雜的愛情感受。情歌有慕情、戀情、迷情、思情、勸情,也有苦情、離情、別情、怨情、憤情,寥寥四句,形隨聲現,情共聲生。如:“見妹挑擔百二三,阿哥心頭著一驚;心想同你分多少,又見人多唔敢聲。”歌中敘述了客家妹子勤勞能干,長途能挑擔一百二三十斤,使男的為之吃驚同時心疼,細致刻畫了男青年對情人既關心又怕羞的復雜心情,抒情敘事,渾然一體。
作為男女傳情和抒發個人情感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情歌又可分為戀歌、怨歌、悲歌、勸歌、對歌和長歌共六個部分。情歌在武平的中部、南部地區流布為密,東部和西部地區為次密,北部地區(特別是大禾、湘店地帶)流布教稀,這與當地“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世俗偏見嚴重有關。
二是生活山歌。生活山歌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用山歌來敘述生活,講述自己的故事。生活山歌主要分苦恨歌、童養媳苦歌、寡婦苦歌、光棍苦歌、罵媒歌、后母虐待苦歌、勸世歌、唱山歌的歌、世態新歌、其他歌等類目。如“十八姐嫁個三歲郎,朝朝夜夜擦尿床;床上好比牛欄桿,床下好比養魚塘。十八姐嫁個三歲郎,等得花開葉又黃,等得結果樹又老,等得郎大妹老娘。郎阿郎,不是看你爺娘面,腳尖一踢見閻王。”講述了童養媳的痛苦生活。還有其他如《百歲歌》《知足歌》等。生活山歌伴隨武平客家人的勞動生活、民俗活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達內心世界的情感,回應時代的風云變幻。
三是勞動歌。勞動歌是描繪勞動場景,訴說勞動感受的。勞動歌即編即唱,內容豐富多彩,有樵夫山歌、挑擔山歌,礦工歌、漁歌、牧歌、田頭歌、采茶歌等。上山割燒斫樵,入坑種田勞動,都可能觸景生情,歌隨口出,吟唱自如。如“心靈手快篾刀舞,雙手巧似繡花姑;日編竹笪曬金谷,夜補新籮裝珍珠。”歌中的“舞、巧、金谷、珍珠”等詞,把篾匠勞動的樂觀主義精神表現出來。勞動是辛苦的,可武平客家人卻善于用歌謠來描繪勞動情景,抒發內心感受,激勵情緒、驅除疲勞,還可協調動作,提高生產效率,鼓舞情緒,苦中作樂,讓辛苦的勞作變得輕松而愉快。
四是時政歌。時政歌分為時事世態歌、紅軍歌、頌世歌三類,這類歌人心向背最明顯,愛憎也最分明。武平是著名的革命老區,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武平兒女為新中國的解放事業前赴后繼,譜寫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因此建國前的時政歌中有相當數量的革命歌謠和紅色歌謠被廣為流傳。如“大家報名當紅軍,當起紅軍鬧翻身;打到土豪分田地,撥開烏云見青天。”紅軍歌體現了當地群眾對紅軍的無限熱愛。經受嚴寒的小草倍愛陽光,在這塊閩粵贛三省交界的紅色土地上,建國后又產生了為數可觀的歌頌黨、歌頌人民政府及其它各項事業進展的成就的新時政歌,這類歌多是歌唱新生活。如“年年種樹樹滿坡,歲歲養魚魚滿河;肚里裝了蜜罐罐,時時頌黨有新歌。”
五是儀式歌。儀式歌的存在與生活中舉行的一定典禮儀式是分不開的。武平縣流傳的儀式歌主要有訣術歌、節令歌、禮俗歌、祭典歌、酒宴歌等。它的形式是固定的,很少即興之作,內容上大多是反應人民生活的良好愿望及生活習俗。如“手拎梁米袋袋紅,今日拿來掛梁中;梁頭掛出好丞相,梁尾掛出狀元公。”這是掛梁米歌,在客家傳統習俗中,新蓋房梁上好后,兩端要掛裝有精米的小紅布袋和筆墨,三字經之類,稱“掛梁米”,由掛梁時木匠師傅演唱的歌謠。有些祭奠山歌,尤其是喪葬山歌如《十月懷胎》《拜血盆歌》,它們在那樣一種悲痛至極的氣氛下,用唱歌的形式,抒發自己對作古親人的感謝和思念,歌頌了人間至善至愛的孝道,深刻地體現了“百善孝為先”的道德標準。
六是歷史傳說歌。歷史傳說歌屬于敘事山歌,它多見于歷史傳說歌,歌詞較一般山歌長,大部分都有手抄本。篇目有《趙玉麟與梁四珍》、《十二月古人》、《十里亭》等,這些山歌流傳于全縣、尤其以平川、城廂、中山、中堡、永平一帶為盛。
武平客家山歌流傳了千百年,內容廣泛,旋律優美,保留了很多古語的成分,具有很高的鑒賞價值。雖然有些山歌如情歌敘述難免不夠含蓄,甚至有些太俚俗率真,但放在那個時代,也是對封建禮教的一種反抗,一種否定,從時代發展的角度看還是有進步意義和藝術價值的。因為真正的藝術來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真實寫照,但它又對生活進行了提煉,已遠遠高于生活。
武平客家山歌作為客家民系優秀文化遺產寶貴的一部分,我們應當要振興和傳承,既要整理和保存原腔原板的山歌資料,又要鼓勵創作具有時代氣息的新山歌,把傳統和時代的東西糅在一起,使傳統山歌煥發出新時代的藝術魅力。
【參考文獻】
[1]福鼎縣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中國歌謠集成[M].福建省武平縣分卷,1994
[2]何志溪.閩西山歌.歌謠選[M].海峽出版發行集團-鷺江出版社,2011
[3]王民發,林善珂.武平客家山歌選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