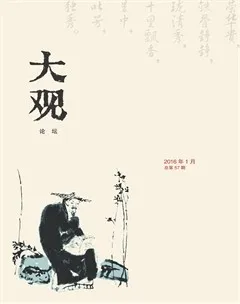生態文化視域下論努爾人與中國人牛文化的區別
摘要:世界上許多地區、許多國家都存在著牛文化或者由于牛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產生了對牛的敬重與崇拜。努爾人被稱為“牛背上的寄生者”,把牛當成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他們支配牛,但不奴役,他們敬重牛,卻不崇拜。而在中國人的眼中,雖然也有把牛當成是圖騰崇拜的民族,但由于中國水稻的種植,牛在中國人的生活與精神兩個領域卻呈現出了不同的地位,這與努爾人的牛文化有著值得令人深思的區別。
關鍵詞:中國人;努爾人;牛
一、生態角度下的依賴與半依賴性
造成世界各地的文化差異以及習俗異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態的多樣性。文化習俗雖然是精神領域的概念,但是人作為文化的創造者,卻是實實在在的生物,人擺脫不了生態對自己的影響,以至于把這種生態的多樣性與差異帶進了我們所創造的文化當中。
努爾人生活在東部非洲,承受著雨季與旱季兩個季節的循環交替,雨季時他們居住在高地的村落上,旱季時則為了牛能吃到草而搬遷到暫居的營地上。生態平衡是自然界的一個基本準則,在炎熱的努爾地區,當地民眾為了達到生態平衡,適應自然界,形成了努爾地區的混合經濟,將游牧、園藝和捕魚結合在一起。但是努爾人在自我認知中卻把自己當成了游牧人,他們主要的食品有奶制品、黍米制成的粥與啤酒、少量的玉米、魚以及肉。然而,少量的黍米收入并不能夠完全支撐起努爾人的生活,并且努爾人把種植園藝工作認為是倒霉的勞動,捕魚也只是為了應付牛瘟或者奶牛產小牛時牛產品銳減的情況。因此,努爾人首先在意識上就已經偏向了牧牛生活。其次,努爾地區的環境特征也證實了努爾人在意識上的選擇不是空穴來風。牛群所必需的青草要靠適宜的土壤和水的條件而生長,努爾地區的土壤是高粘性的粘土,在干旱季節被太陽曬出深深的裂縫,在雨季又會被雨水浸透。它們能夠保持水分,因而能使某些草類在干旱的月份存活下來,使牛有牧草可吃。[1]所以,努爾人的意識偏向是與生存環境有必然聯系的,故被稱為“牛背上的寄生者”。
而在中國,水稻是首要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和產量均占糧食作物的第一位。因此,稻谷生產在中國糧食生產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水稻在中國的分布很廣,最主要的產區是南方稻谷集中產區,在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的長江流域和華南各省,稻谷播種面積合計約占全國的95%以上,其余的5%分布在北方稻谷分散產區。而在中國東部季風區,雨熱同期,土壤肥沃,生產力高,集中了全國90%左右的耕地和林地。中國南方又屬于熱帶、亞熱帶氣候區,多丘陵、山地,但熱量高,降水豐沛。正是這樣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水稻在中國人民生活中的首要地位,而水稻的地位則直接決定了老百姓的生活離不開牛。在中國,尤其是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耕牛可以說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實用主義的影響,中國人民對于牛的感情是建立在勞作的基礎上,所以更多的是主人與耕牛的主仆關系。
綜合兩地民眾對于牛的使用方式和依賴程度,我們可以看出努爾人和中國人對于牛的感情有著實質性的區別。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明,那就是中國人可以找到其他農產工具來代替牛,但是努爾人卻無法脫離牛而獨立生活。這不僅是意識上的認同的區別,還是生態環境的特點所間接決定的特征。
二、精神認同下的崇拜與非崇拜
在精神認同方面,雖然二者各自在寄生和奴役的基礎上都與牛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但是究其實質仍有很大的區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人把牛上升到了圖騰崇拜或者牛神信仰的層面,而努爾人則把牛當成是情感的紐帶。
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南方的諸多少數民族,有把牛當成是圖騰崇拜的文化現象,究其起源仍然無法脫離生態環境來獨立考證。在科技落后的古代,自然災害是中國農民最大的擔憂,他們對于自然的利用被限制于他們對自然征服的能力上。于是,他們開始借助各種自然界的動植物,展開想象,希望能夠通過這些動植物來解釋并解決一些超自然的現象。基于這個基礎,牛神和其他類似風神、雨神之類的自然信仰一起應運而生。所以,在中國人民的心中,基于現實因素把各類由自然崇拜衍生出來的神都做了相應的歸類,并賦予了他們相應的職能。中國人民的牛神崇拜依然是不能擺脫牛在人民生活的作用的。可以簡單地認為,中國人民是認為牛有用,所以才把牛供奉為神,顯示出中國人對于農作物生產的重視,寄托著豐收的期望。
努爾人對牛的高度認同感,不僅表現在奶牛可以生產他們作為主要食物的奶制品,而且牛在當地民眾幾乎所有的重大事項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婚禮、葬禮、節日祭祀都離不開牛,而且一般情況下不輕易屠殺牛作為食物。在他們的眼中,沒有牛不僅是貧窮落后的象征,還是遭人鄙夷的主要原因,他們會為了牛而戰,為了牛而豁出自己的生命。對于他們來說,牛并沒有庇佑他們的能力,相反,他們還要保護好自己的牛。在努爾地區,人們常常用牛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他們的語言系統里,有許許多多描述牛的詞匯。他們用牛糞來洗澡,用牛尿來制作酸奶,晚上還和牛睡在一起。在特定的時期里,他們還會把營地的牛集中到一起來圈養,可見,牛在努爾人的生活中不僅是生活重心、精神寄托、情感紐帶而且還是一種自我身份的認定以及部落向心力的關鍵所在。
對比來看,中國人對于牛的精神認同存在著一種實用主義影響下的信仰傾向,在現實生活中牛的地位是為輔助主人耕作而被奴役的位置,但是在面對自然災難時,在中國人的精神層面,又把牛上升到牛神的地位,替百姓解決農作物生產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而努爾人則不同,努爾人把牛融入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認為牛就是自己,雖然也有把牛當成是圣物的傾向,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生活中的表現,他們把牛提升到了跟人一樣的地位,這不是一種神化而是一種感情的實質化的體現。
【參考文獻】
[1]埃文思—普理查德.努爾人[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67
作者簡介:林信煒:男,福建福州人,1992年9月出生,系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14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民間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