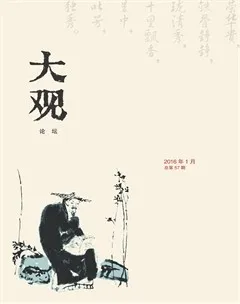文獻記載所見商周生活
蘇靜 趙娜
摘要:中國古人的意識中,早已有關注社會生活的傳統心態。文獻記載中涉及聚落分布遷移、衣食住行、祭祀、婚娶等各個領域,本文主要介紹商周生活的飲食篇。
關鍵詞:文獻記載;商周生活;飲食
商代的食物中,谷物有粟、黍、麥、稻等。肉類食物有兩類,一類是家畜,有牛、羊、豕、犬、馬、雞;一類是野生動物。夏商時期的飲食用器有炊器、飲器、食器三大類。炊器主要有鬲、鼎、飌、罐、甑等,用于煮蒸食物;飲器有蒝、爵、繹、觚、杯等,多數為飲酒之器;食器主要有簋、豆、缽等。夏代多為陶器,商代則主要是青銅器。當時人們主要的進食方式是抓食,匕、勺、箸是比較常見的餐具。
一、文獻記載所見商周食物
(一)文獻記載所見飲食價值觀
《漢書·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文獻記載:
《淮南子·主術訓》:食者,民之本也。
《論語·顏淵》: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尚書·益稷》:蒸民乃粒,萬邦作乂(治)。
《禮記·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毛詩·小雅·天保》:“君能下下,以成其政”,需順乎“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釋名·釋飲食》: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食以體政”和“寓禮于食”的飲食價值觀,并對飲食賦于“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得后嗣(《左傳》隱公十一年)”和“明貴賤,辨等列(《左傳》隱公五年)”的禮的內容。
《呂氏春秋·本味》: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于東海。菜之美者:昆侖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余暓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蕓,云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姜,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鳣鮪之醢,大夏之鹽 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侖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水,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云夢之柚,漢上石耳。
(二)文獻記載所見商周食物
《尚書·酒誥》: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詩經·商頌·玄鳥》稱商人:大糦是承。毛傳云:糦,黍、稷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述商滅國后,箕子傷感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禾,即谷子,或稱粟。
從文獻可見,商人主要的植物食物有:黍、稷、麥和粟。但甲骨文中記載的品種更多,主要有禾(粟)、麥(大麥)、來(小麥)、稻等九大品類。從考古發掘看,自史前至夏商時期,不少遺址中都出土了粟、黍、大麥、小麥、稻、高粱、大豆等。殷墟發掘中所見的也不外乎這些品種。另外,還有各種各樣蔬菜和水果。
《夏書·益稷》:“奏庶根食、鮮食。”所謂“鮮食”,指的是鳥獸新殺為“鮮”,凡指動物類的肉質食品。文獻記載所見商周食器
二、文獻記載商人飲食器物
(一)文獻記載商人如何烹飪
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膻,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咸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呂氏春秋·本味》
(二)文獻記載所見商周飲食具
1.食器
商代很長時間仍抓食,還產生了相關禮節。《禮記·曲禮上》云:“共飯不澤手。”鄭注:“為汗手不潔也。”孔疏:“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既與人共飯,手宜潔凈。”古人注意到抓食時手應干凈,故飯前盥洗手的衛生細禮也就產生。《禮記·喪大記》云:“食粥于盛不盥,食于篹者盥。”孔疏:“食粥于盛不盥者,以其粥不用手,故不盥;食于者盥者,謂竹筥飯盛于篹,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喝粥不洗手而抓飯洗手,也仍是出于衛生的變宜考慮。
不過,與抓食吃法并行的,是夏商人采用餐具將食物或飲料直送口中的進食方式,也在逐漸推而廣之,有關餐具主要為匕、柶、勺、斗、瓚、刀、削、叉、箸等。
“匕,所以載鼎實。”《儀禮·士昏禮》“匕俎從設”,鄭注:“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可知匕可以把肉類食物從容器中擗取出。又用于批取飯食,《儀禮·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賈疏:“匕,所以匕黍稷者也”。可見匕主要是為批取飯食或擗取肉食或撈取羹食的進食餐具。
2.飲酒器
據《墨子·非樂上》云: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磐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偽尚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纏子》云:桀為天下,酒濁殺人。《大戴禮記·少閑》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作宮高臺,污池土察,以為民虐,粒食之民,焉幾亡。有夏一代,貴族統治階級飲酒之風漸開,青銅禮器爵、盉、斝、觚、角等酒器的出現與此是相應的,唯因生產水平的制約,數量有限,最先通常為陶、漆制品,青銅禮器實承襲陶禮器及漆禮器而來。
【參考文獻】
[1]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