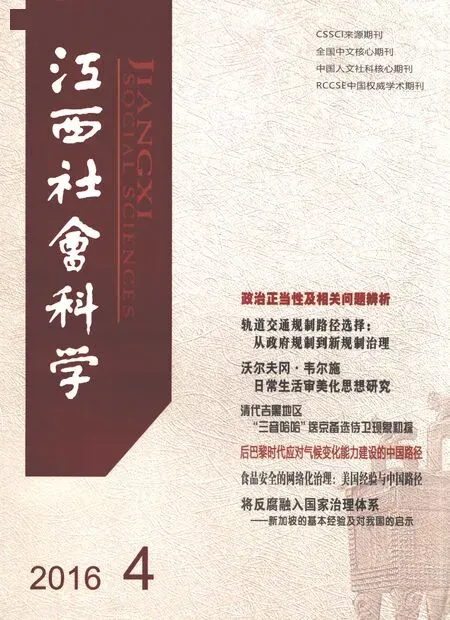我國耕地休養(yǎng)生態(tài)補(bǔ)償機(jī)制的構(gòu)建
■吳 萍
我國耕地休養(yǎng)生態(tài)補(bǔ)償機(jī)制的構(gòu)建
■吳 萍
耕地休養(yǎng)有助于提高耕地質(zhì)量,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生態(tài)補(bǔ)償是實(shí)現(xiàn)耕地休養(yǎng)的重要途徑和手段,能實(shí)現(xiàn)利益衡平,體現(xiàn)公平、正義,促使農(nóng)民自覺養(yǎng)成良好的資源利用習(xí)慣。西方國家大都有相對(duì)完善的農(nóng)田休耕制度和生態(tài)補(bǔ)償(補(bǔ)貼)制度,美國環(huán)保休耕計(jì)劃的生態(tài)補(bǔ)償理念及方式值得我國學(xué)習(xí)。我國應(yīng)在借鑒國外土地休耕生態(tài)補(bǔ)償制度及國內(nèi)森林、流域等生態(tài)補(bǔ)償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上下銜接、相互配套和運(yùn)行靈活的耕地休養(yǎng)生態(tài)補(bǔ)償制度,包括完善耕地休養(yǎng)生態(tài)補(bǔ)償主體、引進(jìn)國外機(jī)會(huì)成本法提高補(bǔ)償水平、多渠道構(gòu)建補(bǔ)償資金來源等。
耕地休養(yǎng);生態(tài)補(bǔ)償;制度構(gòu)建;機(jī)會(huì)成本法;利益引導(dǎo)
吳 萍,東華理工大學(xué)文法學(xué)院,江西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制度研究中心教授。(江西南昌 330013)
我國糧食生產(chǎn)取得了“十二連增”的歷史性成就,但輝煌成就的背后,是土地資源利用已近極限和環(huán)境承載的超負(fù)荷運(yùn)行。對(duì)此,2016年中央一號(hào)文件指出我國農(nóng)業(yè)資源短缺、開發(fā)過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資源環(huán)境硬約束下保障農(nóng)產(chǎn)品有效供給和質(zhì)量安全,提升農(nóng)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是一個(gè)必須應(yīng)對(duì)的重大挑戰(zhàn)。統(tǒng)籌實(shí)施全國高標(biāo)準(zhǔn)農(nóng)田建設(shè)總體規(guī)劃,實(shí)施耕地質(zhì)量保護(hù)與提升行動(dòng),推進(jìn)受損害土地休養(yǎng)生息是應(yīng)對(duì)辦法之一,但應(yīng)該如何推進(jìn)落實(shí)這項(xiàng)工作?從既往經(jīng)驗(yàn)來看,自上而下地依靠行政管制來強(qiáng)行推進(jìn)的效果并不理想,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已給現(xiàn)階段我國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指明了道路,提出“實(shí)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tài)補(bǔ)償制度,改革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管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