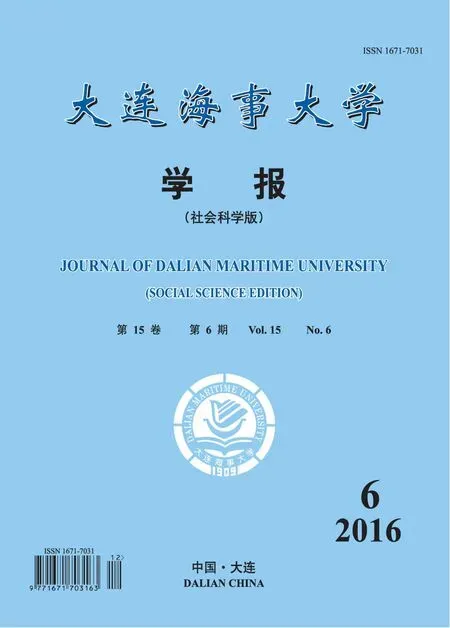論中國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的性質(zhì)及制度發(fā)展
張昕宇,呂明偉
(1.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重慶 400031; 2.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重慶 401120)
?
論中國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的性質(zhì)及制度發(fā)展
張昕宇1,呂明偉2
(1.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重慶 400031; 2.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重慶 401120)
實踐中,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廣泛存在,但是在中國立法和執(zhí)法層面上如何處理這一問題尚未有一致意見和做法。從協(xié)議控制的基本理論出發(fā),結(jié)合中國實際情況,尤其是2015年商務(wù)部公布的《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及《關(guān)于〈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的說明》,對目前理論界和實務(wù)界對于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的三種處理意見進行比較分析,認為申報制方案跨度過大,風險較高,不符合目前中國實際,申請準入許可方式又有過度監(jiān)管之嫌,而申請認定制的“申請認定(準則設(shè)立)+隱性自由裁量權(quán)”架構(gòu)能夠較好處理協(xié)議控制的問題。
協(xié)議控制;《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申請認定制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容忍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而未宣布其非法。[1]1962015年1月19日,中國商務(wù)部公布了《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以及《關(guān)于〈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但是該草案至今尚未被提交全國人大審議,足見其所涉內(nèi)容之復雜。按照《說明》所賦予該法的定位,《外國投資法》定位于“統(tǒng)一的管理和促進外國投資的基礎(chǔ)性法律”*參見商務(wù)部《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的說明》。。《征求意見稿》在許多方面相較于現(xiàn)今施行的“外資三法”*即《中外合資經(jīng)營企業(yè)法》《中外合作經(jīng)營企業(yè)法》和《外資企業(yè)法》。均有明顯的調(diào)整,第一次試圖將協(xié)議控制的問題納入調(diào)整范圍,但是關(guān)于協(xié)議控制的第158條是《征求意見稿》中唯一一條沒有形成確定表述的條文,只是在《說明》中列出了現(xiàn)今學術(shù)界和實務(wù)界的三種處理意見。本文擬結(jié)合中國實際,以比較分析的路徑就協(xié)議控制的基本問題嘗試給出法律回應。
一、協(xié)議控制的性質(zhì)界定
(一)概念界分
協(xié)議控制是與股權(quán)控制相對的概念,不同于《公司法》等商事法律制度中以股權(quán)作為連接因素從而實現(xiàn)不同的實體之間的控制與被控制的關(guān)系,在協(xié)議控制的語境下,這個連接點不是股權(quán)而是一束合同或者可稱之為合同群,即是通過合同安排來確立控制實體與被控制實體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主要表現(xiàn)為控制實體通過合同群實現(xiàn)對被控制實體的經(jīng)營、管理和決策的實際掌控,相應地,該合同群的另一效果是壓縮甚至排除股東對于被控制實體的經(jīng)營管理和決策空間。鑒于此,有學者將協(xié)議控制定義為“通過合同的安排,境外上市主體獲得境內(nèi)運營主體的大部分經(jīng)濟利益,形成‘人、財、物’全面、有效的控制,間接實現(xiàn)境外殼公司對境內(nèi)企業(yè)的控制”[2]。因此,實際上在這兩個實體之間存在的是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而非股權(quán)關(guān)系。
與協(xié)議控制緊密相關(guān)的另一個概念是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VIE)。在部分文獻中,對于協(xié)議控制和VIE未加區(qū)分而等同使用,實際上嚴格來講,二者屬于不同的范疇,但在某些方面具有很大相關(guān)性和相似性,因此本文擬不對二者做過度區(qū)分。VIE是源自于美國財務(wù)會計準則委員會在安然事件后為加強對公司財務(wù)會計真實狀況的審查和監(jiān)管,改變原有的僅以股權(quán)作為標準的審查和監(jiān)管依據(jù)的弊端而創(chuàng)設(shè)的新概念。對于這一概念的屬性,有的學者認為它僅僅是一個財務(wù)會計概念而非法律概念[3],然而,對于何為法律概念,卻并未有一個清晰的解釋和說明。筆者查閱了當代各種法律詞典*筆者所檢索的詞典包括《布萊克法律詞典》(第八版)、《(加拿大)基礎(chǔ)法律詞典》、《劍橋法律詞典》(第五版)以及《柯林斯法律詞典》(第二版)。,均沒有關(guān)于何為法律概念的詞條。實際上,法律概念是人類語言活動的產(chǎn)物而非其他自然客體的產(chǎn)物,因此,法律概念與使用者的主觀意圖以及長期由此而形成的使用習慣密切相關(guān)。因此,“法律概念可以被視為是用來以一種簡略的方式辨識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的工作性工具”[4]501。故而,筆者認為,僅從“工作性工具”這一層面而言,爭執(zhí)這一概念到底是財務(wù)會計概念抑或是法律概念的意義并不大,況且,協(xié)議控制和VIE本身就是與財務(wù)會計和法律規(guī)范緊密相關(guān)的概念,非要分出其屬性似乎對于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并無多大助益,并且進一步講,使用這一結(jié)構(gòu)“既有法律目的,也有會計目的”[1]202。但是,需要明確的是,協(xié)議控制和VIE是兩個不同向度的概念,協(xié)議控制表現(xiàn)為平等商事主體之間的橫向合同安排,而VIE則是監(jiān)管者對市場主體進行監(jiān)管時所使用的一種標準,更多地體現(xiàn)為縱向的經(jīng)濟管理關(guān)系,這一點不可不察。
(二)產(chǎn)生原因
對于協(xié)議控制的產(chǎn)生原因,目前學界和實務(wù)界基本沒有分歧。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內(nèi)外資“雙軌制”管理模式以及國內(nèi)金融市場發(fā)育和發(fā)展尚未完成,同時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進一步推進,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代表的新興產(chǎn)業(yè)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潮中異軍突起,它們的發(fā)展急需資金和智力支持,但是國內(nèi)的金融市場門檻高,手續(xù)繁雜,無形之中將這些新興產(chǎn)業(yè)阻擋在了融資的門外,但是諷刺的是,國家明確表態(tài)支持其發(fā)展,政策配套卻遠未滿足這些市場主體的需求;另一方面,對于這些行業(yè),外資被限制或者禁止進入,所以盡管國外投資者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shù)卻苦于無處投資。因此,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分析,造成這一現(xiàn)象發(fā)生的直接原因是國內(nèi)這些新興產(chǎn)業(yè)對資金和管理的“需求”和國外投資者的資金和技術(shù)的“供給”出現(xiàn)了失衡,這種供需失衡致使雙方不得不采取迂回的辦法以實現(xiàn)各自的目標。
如若再做進一步的分析,產(chǎn)生這一“供給”和“需求”失衡的背后的原因?qū)嶋H上是中國國內(nèi)的經(jīng)濟發(fā)展(或者可以說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與法律秩序之間的內(nèi)生型的矛盾。改革開放至今已近40年,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也已經(jīng)進入了新常態(tài),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型升級面臨著迫切的壓力,經(jīng)濟增長動力正在從傳統(tǒng)的國內(nèi)投資驅(qū)動轉(zhuǎn)向創(chuàng)新驅(qū)動,經(jīng)濟增長的多面性正在凸顯,而正是這種多面性對原有的制度體系造成沖擊和挑戰(zhàn)。另一方面,毋庸置疑的是,法律具有內(nèi)生的穩(wěn)定性與滯后性的特征,如果某一個規(guī)則體系僅為應付某些一時凸顯的社會問題臨時創(chuàng)設(shè)而不具備其應有的穩(wěn)定性內(nèi)涵,那么它是無法真正地確立其權(quán)威并為大眾所認可和遵守的。雖然說曾有古代先賢指出“法律必須是穩(wěn)定的,但不可一成不變”[5],但是這種變動通常是被動的和緩慢的,“法律中的許多變化都是緩慢而又漸進發(fā)生的”[4]340。我們姑且把法律的以上特性稱之為保守性。因此,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創(chuàng)新性和多面性對于法律的保守性而言構(gòu)成了“制度性的挑戰(zhàn)(institutional challenge)”。[6]1061故而,筆者認為,這才是協(xié)議控制這一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協(xié)議控制本身又可以看做是對于這一“制度性挑戰(zhàn)”所作出的非官方的抑或是非正式的回應。
(三)協(xié)議控制的結(jié)構(gòu)和特征
簡單來說,協(xié)議控制的結(jié)構(gòu)一般包括三方,即境外上市主體(offshore holding company)、境內(nèi)殼公司以及境內(nèi)經(jīng)營實體(PRC-domiciled operating business entity),也有外國學者將境內(nèi)經(jīng)營實體直接表示為VIE。[1]203其中,境內(nèi)經(jīng)營實體的股東僅有內(nèi)資,而境外上市主體的股東則包括境內(nèi)經(jīng)營實體的股東和外國投資者,這里的外國投資者就是上文所述的有資金和技術(shù)“供給”愿望的外國投資者,他們將成為境外上市主體的股東作為進軍中國相關(guān)行業(yè)的第一步。再由這個境外上市主體設(shè)立一家境內(nèi)殼公司,即外商獨資企業(yè),這個境內(nèi)殼公司是該境外上市主體的全資子公司(wholly foreign owned entity, WFOE)。最后由這個境內(nèi)殼公司與境內(nèi)經(jīng)營實體發(fā)生合同關(guān)系,并且由此而產(chǎn)生的合同收益通過WFOE傳送到境外上市主體賬下,境外上市主體再依據(jù)股權(quán)關(guān)系分區(qū)各自的“利潤”,其中內(nèi)資獲取到了進一步經(jīng)營發(fā)展的資金(即成功融資),外國投資者也獲得了其投資利益,可謂實現(xiàn)雙贏結(jié)局。
如上文所述,在協(xié)議控制的語境下,控制實體與被控制實體之間的這種控制與被控制關(guān)系是通過合同群(或曰協(xié)議群)來實現(xiàn)的,同時,最終的利益分配也依靠這個合同群來實現(xiàn)。這是協(xié)議控制最大的特征。這些合同或協(xié)議通常包括借款合同、股權(quán)質(zhì)押合同、獨家咨詢和服務(wù)合同、資產(chǎn)運營控制合同等。如前所述,這一系列的合同關(guān)系發(fā)生在同為境內(nèi)企業(yè)的境內(nèi)殼公司和境內(nèi)經(jīng)營實體之間,所以,就單個合同關(guān)系而言,只要其滿足合同法等法律法規(guī)的要求,一般不會存在問題。但是,當這些合同組合在一起構(gòu)成了這里所說的合同群以后,就可能會產(chǎn)生問題,如有可能被境內(nèi)實體所在國認定為無效,從而危及整個協(xié)議控制和VIE架構(gòu)所形成的結(jié)構(gòu),不僅于外資不利,同樣會傷及內(nèi)資。所以,由合同群這一最為顯著的特征派生出的合同效力的不確定性的風險是協(xié)議控制的另一大特征。
二、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在中國的發(fā)展及相關(guān)制度的演進
(一)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及相關(guān)制度在中國的發(fā)展
從上文可得知,在改革發(fā)展型的國家中最容易出現(xiàn)協(xié)議控制現(xiàn)象,因為在這樣的國家中,產(chǎn)生這一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即經(jīng)濟發(fā)展與法律秩序之間的內(nèi)生型的矛盾最容易出現(xiàn)也最為突出。在當前的中國,正好處在變革的大時代,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的分析范式出發(fā),作為改革領(lǐng)頭羊和切入點的經(jīng)濟改革與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改革已經(jīng)形成了矛盾和不協(xié)調(diào),后二者的步調(diào)整體上慢于前者,而且就其本質(zhì)而言,后二者的改革屬于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的外生型改革。所以,這使得這一矛盾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變得十分突出。在這樣的困境中,在21世紀之初,當時中國的新型網(wǎng)絡(luò)公司新浪在成立僅僅不到兩年的時間就通過“協(xié)議控制+VIE”的方式成功在美國納斯達克(NASDAQ)股票市場正式掛牌交易。在此后十年間,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yè)使用協(xié)議控制模式的比例呈上升態(tài)勢,此后相繼有搜狐網(wǎng)、百度、人人、騰訊、阿里巴巴、當當以及新東方教育采取這種方式。2011年P(guān)aul Gillis教授在對在美三大交易所(紐交所、納斯達克和美交所)上市的230家中國企業(yè)進行分析之后得出數(shù)據(jù),總體而言,超過42%的在美上市中國企業(yè)采用了協(xié)議控制這一方式,而在2010年一年中紐交所和納斯達克各自的這一比例分別是47%和65%。[7]而在此之前的2006年,商務(wù)部、國資委、國家稅務(wù)總局、國家工商總局、證監(jiān)會、外管局六個部委聯(lián)合出臺《關(guān)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nèi)企業(yè)的規(guī)定》(2006年第10號)(也即業(yè)界所稱“10號文”),對此后的外資并購和協(xié)議控制問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有學者和實務(wù)界人士在分析了該文件之后,發(fā)現(xiàn)該文件只針對“股權(quán)并購”和“資產(chǎn)并購”問題,并不涉及協(xié)議控制的問題,這為有的企業(yè)采取協(xié)議控制的方式去海外上市以謀求融資提供了所謂法律支持。如2009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國秦發(fā)在其招股說明書中說,“……不涉及收購于中國成立的任何公司的股本收益或資產(chǎn),故此……本集團的上市無須中國證監(jiān)會批準”[8]。此后不久,國務(wù)院辦公廳發(fā)布《關(guān)于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nèi)企業(yè)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國辦發(fā)〔2011〕6號)(以下簡稱“6號文”),雖未直接寫明“協(xié)議控制”落入規(guī)制范圍,但在對實際控制權(quán)的一條中有一兜底條款,即“其他導致境內(nèi)企業(yè)的經(jīng)營決策、財務(wù)、人事、技術(shù)等實際控制權(quán)轉(zhuǎn)移給外國投資者的情形”*參見國務(wù)院辦公廳《關(guān)于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nèi)企業(yè)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第1條第3項。。這被認為是隱含了對協(xié)議控制的規(guī)制。緊接著商務(wù)部《實施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nèi)企業(yè)安全審查制度的規(guī)定》(商務(wù)部公告2011年第53號)(以下簡稱“商務(wù)部53號文”)中第9條則是明確提到了“對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nèi)企業(yè),應從交易的實質(zhì)內(nèi)容和實際影響來判斷并購交易是否屬于并購安全審查的范圍;外國投資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實質(zhì)規(guī)避并購安全審查,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信托、多層次再投資、租賃、貸款、協(xié)議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雖然“6號文”和“商務(wù)部53號文”是僅針對外資并購的國家安全審查這一特定事項,但是,“鑒于協(xié)議控制和并購在功能上的相似性”[1]224,這其中反映的監(jiān)管層的思路傾向還是值得注意的。而在2013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紙判決又掀起了對這一問題的關(guān)注熱潮。[9]在該案中,法院判定原告A公司(為一內(nèi)資公司)和被告B公司(外商獨資企業(yè),即上文所述WFOE)之間簽訂的《獨家商務(wù)咨詢服務(wù)協(xié)議》與《獨家技術(shù)服務(wù)與咨詢協(xié)議》及其4份補充協(xié)議違反了《合同法》第52條第3款,即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因而無效,由此再次激起了社會的疑慮。從這一線索來看,中國政府似乎在協(xié)議控制問題上采取了收緊的思路。
(二)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在中國面臨的制度挑戰(zhàn)
關(guān)于這個問題,依循筆者在前文對協(xié)議控制問題的原因分析,因為經(jīng)濟發(fā)展同法律秩序之間的內(nèi)生型矛盾產(chǎn)生了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的失衡,失衡即意味著制度缺位,也就意味著標準缺失,相關(guān)主體之行為的法律性質(zhì)和法律效果就是不確定的。因此,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在中國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其結(jié)構(gòu)本身的合法性問題和其項下合同群的強制力(或可稱之為執(zhí)行力)問題。[10]但是,這些問題都是表象的,抑或從一定程度上說,這些并不是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本身的問題,而是在立法層面上的制度缺位的問題,同時也是部分外國學者所稱的在執(zhí)法層面上“選擇性管理”或“選擇性執(zhí)法”[1]230[6]1072的問題,也即中國在一些產(chǎn)業(yè),如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秉持實用主義的觀點,對這些行業(yè)所存在的VIE結(jié)構(gòu)“睜一只眼閉一只眼”[1]231,因為他們對中國經(jīng)濟(至少就目前來講)有著重要的促進意義,而“正是這種‘選擇性管理’增加了中國投資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和危險性”[1]232-233。筆者認為,這兩個層面的問題才是根本性的問題。
三、中國外資法體系中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的立法建構(gòu)
(一)《征求意見稿》第158條的立法困境
2015年1月19日商務(wù)部公布的《征求意見稿》關(guān)于協(xié)議控制的內(nèi)容是在第158條,而這也是該意見稿中唯一一條沒有形成確定表述的條文,可見目前政策層對于這個問題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同時也反映出協(xié)議控制背后的復雜的利益考量,一方面既要考慮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求,另一方面還要考慮法律秩序的穩(wěn)定與變革。如果立法承認或允許協(xié)議控制模式(盡管幾乎沒有可能),則必須考慮其可能會對現(xiàn)有法律秩序和結(jié)構(gòu)的潛在的巨大沖突(制度性挑戰(zhàn)),還要考慮這可能對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及國家安全的現(xiàn)實威脅;如果立法禁止協(xié)議控制模式,則必須慎重研究在此之前的十幾年中已經(jīng)通過該方式在海外上市并成功融資的這些企業(yè)的尷尬境地,畢竟這些企業(yè)代表著中國新興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前景,其本身的成敗對于中國經(jīng)濟的轉(zhuǎn)型升級亦具有重大的意義。
對于《外國投資法》生效后仍屬于禁止或限制外國投資的領(lǐng)域應當如何處理,《說明》第三部分(即“若干問題的說明”)“協(xié)議控制的處理”部分列出了理論界和實務(wù)界的三種觀點:
(1)實施協(xié)議控制的外國投資企業(yè),向國務(wù)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申報其受中國投資者實際控制的,可繼續(xù)保留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相關(guān)主體可繼續(xù)開展經(jīng)營活動,也即申報制。
(2)實施協(xié)議控制的外國投資企業(yè),應當向國務(wù)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申請認定其受中國投資者實際控制,在國務(wù)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認定其受中國投資者實際控制后,可繼續(xù)保留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相關(guān)主體可繼續(xù)開展經(jīng)營活動,也即申請認定制。
(3)實施協(xié)議控制的外國投資企業(yè),應當向國務(wù)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申請準入許可,國務(wù)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會同有關(guān)部門綜合考慮外國投資企業(yè)的實際控制人等因素作出決定,也即申請批準制。
下文將嘗試對這三種處理意見進行比較分析。
(二)協(xié)議控制三種立法方案比較分析
1.申報制
在上文所述的第一種方案中,在存在協(xié)議控制的情形下,該外國投資企業(yè)只需要向外國投資主管部門申報表明其是受中國投資者實際控制,則可以繼續(xù)保留協(xié)議控制結(jié)構(gòu),也就意味著該結(jié)構(gòu)項下的一系列合同是有效的并且受到法律保護,外國投資企業(yè)也可以繼續(xù)通過該結(jié)構(gòu)獲取合同利益。
這里需要明確的是什么是申報。一般而言,申報是指向上級或有關(guān)部門提出(提交)相關(guān)事宜的書面報告(多用于法令文件),可看成是“申請報批”之縮寫,其后一般伴隨著該上級或主管部門的批復。也就是說,最終的實質(zhì)決定權(quán)仍在該上級或主管部門手中。但是,結(jié)合后兩種意見,筆者認為,此處的申報不應按照一般理解,而應近似理解為“備案”,即向主管機關(guān)報告事由存案以備查考,既為“以備查考”,則在備案當時不需要“查考”,也就不需要上級或主管機關(guān)來決定。
由此看來,這種方式實際上對于協(xié)議控制沒有任何的限制,也是對目前經(jīng)濟秩序和結(jié)構(gòu)影響最小的一種方式,自然,這種方式也就對內(nèi)資和外資都最有利,因為他們唯一的“麻煩”是提交一份陳述(file a statement)以表明其受中國投資者控制。因此,許多外國學者支持這一種方案,他們認為這種方案將會使中國經(jīng)濟整體受益[11]。筆者認為,此種方式固然能夠滿足進一步建立經(jīng)濟新體制的要求和體現(xiàn)改革開放的精神,但是,對于此處的核心問題——受中國投資者控制——這一問題完全由申報人進行拿捏并不十分妥當,不能排除申報人弄虛作假、欺報瞞報現(xiàn)象的發(fā)生,而這一旦發(fā)生,將對中國經(jīng)濟埋下極大的隱患。中國經(jīng)濟正處于深度調(diào)整當中,目前的協(xié)議控制多集中于高成長性的行業(yè)當中,而這些行業(yè)對于中國經(jīng)濟的轉(zhuǎn)型升級所具有的意義是極端重大的,甚至將其升級為國家安全戰(zhàn)略也不為過。故此,筆者認為,這一方案跨度過大,風險較高,不符合目前中國實際。
2.申請認定制
相較于第一種方案,這種方案在措辭上有所變化,即由申報改為了申請認定,并且作為其邏輯結(jié)果,相關(guān)主體繼續(xù)在協(xié)議控制的框架下開展經(jīng)營活動多了一個前提條件,即“在國務(wù)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認定其受中國投資者實際控制后”。同樣,遵循上述分析邏輯,筆者認為,此處的申請認定當理解為類似于“準則設(shè)立主義”,即只要符合規(guī)定條件,認定機關(guān)(具體而言就是國務(wù)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就應當予以認定。相比而言,這種方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第一種方式中的實際控制判別風險。同時,對于控制的標準,《征求意見稿》在第18條予以明確,其將控制標準做了股權(quán)控制和實際控制兩種類分,在其第3款明確規(guī)定:通過合同、信托等方式能夠?qū)υ撈髽I(yè)的經(jīng)營、財務(wù)、人事或技術(shù)等施加決定性影響的。這被認為是對協(xié)議控制的直接規(guī)制。筆者認為,在該條所確立的控制標準中,“有權(quán)”、“有能力”、“重大影響”、“決定性影響”等用語賦予了認定機構(gòu)足夠的自由裁量空間,也可以稱為隱性自由裁量權(quán),故而,“申請認定(準則設(shè)立)+隱性自由裁量權(quán)”的架構(gòu)一方面不至于過于影響外國投資者對于中國投資環(huán)境的疑慮,另一方面也可以確保中國主管機構(gòu)對相關(guān)問題的管控,因而能夠克服第一種方案所可能產(chǎn)生的問題。
3.申請準入許可制
相較于前兩種方案,這種方案賦予了主管機關(guān)完全的控制權(quán)。一方面該種方案的措辭是“準入許可”,即類似于“核準登記主義”,主管機關(guān)將有權(quán)對所涉材料進行實質(zhì)性審查,并最終決定是否予以批準,并且,由于這種方式涉及諸多部門,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多方利益,造成效率低下,同時還涉及不同的標準,不同標準之間的協(xié)調(diào)又將是一大問題,這可能會對中國整體投資環(huán)境造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這種方案恐與《說明》中列明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不符,《說明》明確表示將“創(chuàng)新外資管理模式。取消現(xiàn)行對外商投資的逐案審批制……”“切實轉(zhuǎn)變政府職能。從重事前審批向提供公共服務(wù)和加強事中事后監(jiān)管轉(zhuǎn)變……”因此,筆者認為,這種方式有過度監(jiān)管之嫌,當慎用。
此外,關(guān)于設(shè)立過渡期(grace period)的建議值得考慮[11]。可借鑒《說明》中關(guān)于給予在《外國投資法》生效以前依法存續(xù)的外國投資企業(yè)的組織形式和組織機構(gòu)三年的過渡期的做法,給予協(xié)議控制架構(gòu)下的相關(guān)主體一年到三年的過渡期以進行調(diào)整或拆除協(xié)議控制架構(gòu)而退出市場,避免引起過大的市場反應和震蕩,影響整體經(jīng)濟運行,確保平穩(wěn)過渡。
四、結(jié) 語
不可否認,協(xié)議控制的模式在這十幾年中給中國經(jīng)濟確實帶來了很多好處[12],這也是很多外國學者認為中國不太可能全盤否定協(xié)議控制的重要原因。如Paul Gillis教授就認為“中國政府目前不大可能否定全部在中國通過VIE結(jié)構(gòu)運行的公司”[13]。還有學者認為中國政府目前似乎并不急于澄清協(xié)議控制的相關(guān)問題[1]227,而且中國政府是故意這么做的[1]197。同時,我們也看到,《征求意見稿》已經(jīng)將這個問題納入規(guī)制范圍,盡管還存在諸多困難,甚至意見都還不能統(tǒng)一,但是作為“一部深化體制改革的法,擴大對外開放的法,促進外商投資的法,規(guī)范外資管理的法”,*參見《說明》“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部分。其大的方向是已經(jīng)大致確定了的,現(xiàn)今比較務(wù)實的做法是緊跟立法動態(tài),(相關(guān)主體)最好提前做好準備[14],因為“to V[IE] or not to V[IE]”[15]的問題終歸是要解決的。
[1]SCHINDELHEIM D.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struc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uncertainty for foreign investors par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J].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12, 21: 195-232.
[2]伏軍.境外間接上市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07.
[3]劉燕.企業(yè)境外間接上市的監(jiān)管困境及其突破路徑——以協(xié)議控制模式為分析對象[J].法商研究,2012(5):13-15.
[4]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
[5]龐德.法律史解釋[M].鄧正來,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3:1.
[6]MENGWEI M. Perils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Unraveling the murky rul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posed[J]. Hong Kong Law Journal, 2013, 43: 1061-1072.
[7]GILLIS P. Statistics on VIE usage[EB/OL].[2016-03-02].http://www.chinaaccountingblog.com/weblog/statistics-on-vie-usage.html.
[8]李壽雙,蘇龍飛.紅籌博弈:十號文時代的民企境外上市[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57.
[9]ZIEGLER S. China’s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problem: How Americans have illegally invested billions in China and How to fix it[J].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2016, 84(2): 548-549.
[10]SHI S. Dragon’s house of cards: Perils of investing in 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domicil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l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J].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4, 37(4): 1268.
[11]SIU W, SHENG J, LIVDAHL D. China issues draft foreign investment law[EB/OL].(2015-02-12)[2016-03-03].http://www.pillsburylaw.conVsiteFiles/Publications/AlertFeb2015ChinaChinalssuesDraftForeign investmentLaw.pdf.
[12]JOHNSON K. 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Alibaba’s regulatory work-around to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restrictions[J].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015, 12(2): 249-266.
[13]GILLIS P. Placing the VIE story in history[EB/OL].(2011-10-13)[2016-03-03].http://www.chinaaccountingblog.com/weblog/placing-the-vie-story-in.html.
[14]OUYANG E. China redefines its foreign investment laws[EB/OL].(2015-02-15)[2016-03-03]. http://globalriskinsights.com/2015/02/china-redefining-foreign-investment-laws/.
[15]HARRIS D, TIGER C, FRAUD H. Clear speaking on VIEs[EB/OL].(2011-07-16)[2016-03-03]. http://www.chinalawblog.com/?s=Clear+Speaking+on+VIEs.
2016-07-21
張昕宇(1976-),男,博士,副教授,E-mail:584698377@qq.com
1671-7031(2016)06-0049-06
D923.9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