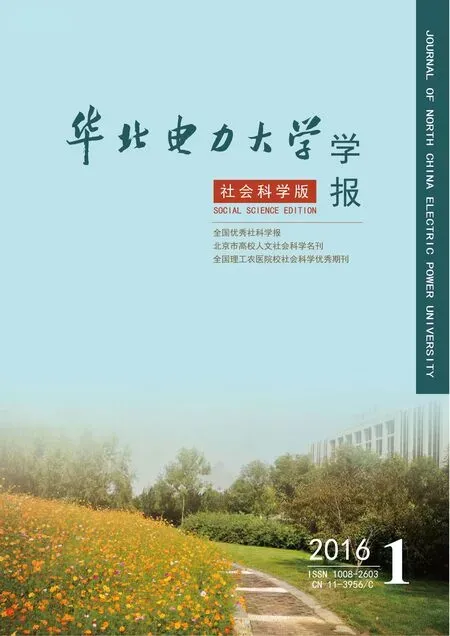大數據時代文學出版的審美維度
郝 丹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
大數據時代文學出版的審美維度
郝 丹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大數據時代是一個海量信息的漫游時代。大數據時代的中國文學出版存在著嚴重的“審美”缺陷。文學出版的“審美”內涵包括文學出版的文化理性和文學出版的裝幀藝術兩個層面的內容。出版從業人員應充分利用大數據資源應對當下文學出版的“審美危機”,其具體策略一是要努力規范和開拓文學暢銷書市場,二是要加大對嚴肅文學的出版和宣傳力度,三是要優化文學圖書的裝幀設計,四是要挖掘文學新人和文學精品。
大數據時代;文學出版;審美維度
文學出版是圖書出版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出版的審美維度不僅直接作用于讀者的文學閱讀,而且對社會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大數據時代”(Big Data)是一個承載著海量信息的時代,中國的文學出版應該充分利用“大數據”不斷提升自身的審美內涵和文化品質,以推動人類社會文明朝著更多元、更高遠的方向前行。大數據時代文學出版的審美維度主要包含是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大數據時代的文學出版在通向審美的道路上存在著哪些問題和缺陷,具體到中國的文學出版就表現為一種“弱文化”出版現象;二是大數據時代文學出版的審美內涵,這里所要探討的是文學出版與文化理性、文學出版與裝幀藝術兩個方面的問題;三是中國的文學出版應該怎樣充分利用大數據來豐富和充盈自身的審美內涵。
一、 大數據時代中國文學的出版圖景
上世紀八十年代,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中明確指出了計算機“能夠記憶和把大量的起因互相聯系起來”[1]的偉大功能,他認為計算機“能篩選大量資料,并找到微妙的解決方案。它能夠把‘瞬息即逝的’因素組合成比較大的更有意義的整體。在固定設想和模式下,它能探索出各種可供選擇的決定可能造成的后果,而且比一般的分析更為系統,更為完整。它甚至能夠通過識別新的和迄今尚不為人們注意的人與資源之間的關系,對某個問題的解決,提出富于想象力的建議。”[1]從表面上看,托夫勒的論述針對的是計算機在第三次浪潮中的應用效能,而實際上我們從中不難看出,計算機所提供的大量信息資料對于預測結果和解決問題是具有巨大作用的。那么計算機提供的海量信息資料是否等同于“數據”呢?數據在傳統意義上常被理解為數值,它似乎必須是一種經過統計、運算、實驗或者論證才能得出的數字結果。然而這種理解顯然已經脫離了當下社會的發展節奏——現今的“數據”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它的呈現方式已經隨著媒介的發展而日益多元化,文字、數字、聲音、圖像、視頻等等都可以被作為數據來看待。海量信息完全構成了一個“數據大”的現實,當然它并不能因此而等于“大數據”。“大數據”是一個新近的概念,“數據大”只是它的特征之一,它的內涵遠比字面意義豐富得多。率先對這一概念進行明確分析和闡釋的是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2011年5月該公司公布了一份極具世界影響力的報告——《大數據:下一個競爭、創新和生產力的前沿領域》(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該報告從美國的醫療保健、歐洲的國有經濟管理、美國零售業、制造業和全球個人位置數據這五個領域對大數據做了考察,而這實際上是對海量數據分析的潛在商業價值的一次科學性評估。從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和麥肯錫商業技術辦公室(McKinsey’s Business Technology Office)聯合進行的這次調研來看,對大量數據集的分析將成為未來競爭的重要依據,這種數據分析會支撐著生產率增長、商業技術創新和消費者盈余的新浪潮。
2013年一本關于大數據的扛鼎之作《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and Think)問世,該書以大量的大數據應用案例為基礎,對大數據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巨大變革做了生動的闡述。其作者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和肯尼思·庫克耶(Kenneth Cukier)認為,大數據的應用“是當今社會獨有的一種新型能力: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通過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獲得巨大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或深刻的洞見”[2]。在他們看來,預測是大數據的心臟,大數據時代的預測面向的是三種轉變:其一是可供分析的數據是海量的,甚至一些時候與某一特定現象有關的所有數據我們都可以獲得,所以隨機采樣的方式將不再為我們所依賴;其二是對以往的狂熱追求精確度的冷卻,這種“冷卻”是基于海量數據本身就能夠根據我們的不同需要提供針對性極強的預測依據;其三是不再注重因果聯系,因為海量數據形成的是一個巨大的數據網,數據自己就可以說話,每一個數據集之間的聯系已經足以幫助人們了解世界,那么現象背后的原因自然就不必通過我們“追根究底式”的挖掘來找尋了。與這三個轉變相應,大數據具備了四個突出特征,也就是所謂的“4V”,即數據量(Volume)、時效性(Velocity)、多樣性(Variety)和可靠性(Veracity)。以出版業為例,數據量體現為一切與出版相關的數據的累積和疊合,而這個“相關”數據實際上是跨行業、跨領域的,比如某一部文學作品的銷售量數據信息和根據這部作品改編的電視劇的收視率數據信息就是密切關聯的。時效性體現為數據商業價值的利用效率,出版人所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最新的數據財富,而面對這些數據,出版人無需追問過多的“為什么”,只是要關注其“是什么”就可以了。多樣性表現為數據呈現形式的多樣化,傳統的數據信息需要統計成具體的數字或形成規范的表格,而在大數據時代,文字、圖像、個人信息等等都是數據,比如我們在一個網絡搜索引擎中敲入“文化”二字,那么與之相關的一切信息就會在網頁上呈現出來,這些信息的條目數就是數據,而每條信息的具體內容又會提供相關數據,再如手機用戶可以在發布新浪微博時使用定位功能明確自己當時的位置,而這些定位信息匯聚起來,就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數據信息——如某一城市的哪家書店最受歡迎,某一年度哪家百貨商店的新品服裝最受關注,或是某一季節全國哪個旅游景點最熱門等等。可靠性以大數據的數據量和數據本身的質量為基礎,一本圖書如果在十個權威暢銷書排行榜上都位居前列,我們才說它是暢銷書,一個出版社如果連續五到十年都有健康的業績增長,我們才會把它作為成功的經營案例進行分析,而榜單和業績實際上都是數據,只有榜單公平權威、業績準確詳實,它們所構成的大數據才會既有量又有質。
單看文學出版,它所能夠提供的信息量是極其龐大的,但若將其匯入浩瀚的數據之洋,它又只是一個分流般的存在。當然,文學出版領域所貢獻的“數據集”在這樣一個大數據時代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單獨存在的,它可以隨時拆解,亦可以隨時融合,甚至它可以滲透到與之相關聯的一切領域并由此而發生意想不到的“化學反應”。那么文學出版以哪些信息呼應了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呢?其實只要從國內文學出版的現狀以及存在的相關問題入手即可找到答案。目前我國的文學出版尚處于一個以讀者的閱讀興趣為唯一導向的“弱文化”出版階段,這種“弱文化”出版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首先,從整體上看,文學類暢銷書的文化品質不高,且在內容題材上有趨同的傾向。以開卷2014年第三季度暢銷書排行榜為例,在虛構類前十五名中,張嘉佳的《從你的全世界路過:讓所有人心動的故事》和《讓我留在你身邊》分列第三位和第七位;而在非虛構類前十五名中,劉同的《你的孤獨,雖敗猶榮》和《誰的青春不迷茫》分列第一位和第九位,盧思浩的《愿有人陪你顛沛流離》也排在了第十五名的位置。此外,在開卷2014年50周(12.08-12.14)暢銷書排行榜上,九夜茴的《匆匆那年》(全二冊)和《匆匆那年》(完美紀念版)亦進入了前十名。以上的這些暢銷書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隨筆,都是圍繞著青春、愛情、友情、現實生活創痛等一系列相關內容展開的。不可否認的是,對年輕一代讀者而言,這些作品既是觸動人心的,也是發人深省的,但是題材和表達的雷同化帶來的是審美藝術價值的降低和深層文化內蘊的削弱。其次,出版人對嚴肅文學作品的重視不夠。和通俗文學相比,嚴肅文學的市場的確狹小了一些,因為嚴肅文學通常在內容、思想以及藝術表現手法上對讀者的閱讀水平和理解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是作為文化傳播鏈條上重要把關人的圖書出版人,有責任也有義務引導讀者去追求具有更高文化層次的閱讀體驗。然而遺憾的是,目前大多數的出版從業人員優先考慮的還是作品的商業價值,他們更愿意為那些能夠迅速占領市場并幫助他們獲得最大利潤的通俗文學作品做宣傳,這樣一來嚴肅文學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嚴肅文學作品在當下的出路就是依靠影視改編、國內外獎項和傳統的口碑,而大部分出版人于此都是被動的,也就是說只有當嚴肅文學作品與以上三個因素相掛鉤時,出版人才愿意為其“費些心思”。第三,從嚴肅文學作品內部來看,外國文學作品銷量較高,而中國文學經典特別是古典文學精品受關注度明顯偏低。在開卷2014年上半年虛構類暢銷書排行榜前二十名中,外國嚴肅文學作品有四本,中國嚴肅文學作品有五本*外國嚴肅文學作品分別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風箏的人》以及艾麗絲·門羅的《逃離》,中國嚴肅文學作品分別是余華的《活著》、錢鐘書的《圍城》、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精)、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共三部)、羅廣斌和楊益言的《紅巖》。;在2014年亞馬遜上半年圖書分類榜——小說圖書前二十名當中,外國嚴肅文學作品有五本,中國嚴肅文學作品有三本*[5] 外國嚴肅文學作品分別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艾麗絲·門羅的《逃離》、村上春樹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以及杰羅姆·大衛·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紀念版),中國嚴肅文學作品分別是余華的《活著》和《第七天》、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精)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共三部)。;在2013年當當網小說類暢銷書排行榜前二十名當中,外國嚴肅文學作品有四本,中國嚴肅文學作品有五本*外國嚴肅文學作品分別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風箏的人》、艾麗絲·門羅的《逃離》,中國嚴肅文學作品分別是余華的《活著》和《第七天》、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共三部)、莫言的《蛙》和《豐乳肥臀》。。雖然從以上數據看來,嚴肅文學內部外國文學和中國文學算是平分秋色,但實際上其中還潛藏著三個更深層的問題:一是讀者對中國文學作品的閱讀是純粹的母語閱讀,而對外國文學作品的閱讀屬于譯介閱讀,前者無論從語言表達還是文化根基上都更具有適應性優勢,但這種優勢卻并沒有體現在具體的圖書購買和閱讀行為上;二是縱然在“所占席位”上,中外作品顯得旗鼓相當,但從實際排名看,外國嚴肅文學作品還是更勝一籌,在前面所提到的三個榜單中,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風箏的人》一直都盤踞在前五名的位置,而中國嚴肅文學作品排名則相對靠后;三是在上述上榜的中國嚴肅文學作品當中,沒有一本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這就從另一個層面上證實了大數據時代中國“弱文化”出版現象的存在。當然,許多出版人認為他們在文化傳播上盡了全力,他們已經將各種類型的圖書投放到市場中去,讀者選擇購買和閱讀哪些作品是讀者的自由,他們無權干涉。可他們真的在文化傳播上竭盡全力了嗎?或者說,作為文化把關人的出版人只要把所謂的多樣性文化隨意地拋給讀者就正確了嗎?這其實就涉及到了文學出版的審美內涵問題。
二、 大數據時代文學出版的審美內涵
文學出版首先應具有文化理性。文化理性要求出版人既要遵循出版倫理,正當競爭,合理經營,傳播有益或者至少是無害的價值觀念,同時又要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文化為本,努力提升自身的審美品位,利用有意義的出版行為和出版物來引導讀者向更高的文化層面行進。“所謂出版倫理,是指關于出版業道德的、在出版從業者之中促進理性的自我指導或決定的一種社會規范體系。制定出版倫理規范,主要目的在于調節人類出版活動中的關系,以保障出版業健康有序發展。”[3]“文學和藝術欣賞是一種審美體驗過程,文學和藝術的審美形態主要體現在藝術形式審美和道德倫理審美兩個層面。出版作為紙面媒介,一方面被動地記錄和反映文學藝術的創作成果,受益于各種藝術形態的既有影響,是傳播者和收獲者;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選擇影響和決定文學藝術的審美取向,所以它又是伯樂和守門人。”[4]對出版倫理的強調實際上是對出版人從業之道的警示。在大數據時代,出版單位或出版企業的任何商業行為都可能成為數據的一部分,因此這些數據的內容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負面的。我們希冀出版人能夠以健康的出版姿態為大數據提供更多具有積極意義的信息,當然一些不良出版行為最終也會作為數據的一部分服務于未來的相關預測。就文學出版而言,對出版倫理的違背既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顯性的很好理解,比如為了以低成本獲得高利潤,一些無良出版從業人員和書商無視版權,把盜版書籍投到市場上去賣,又如某些競爭力薄弱的民營出版社為了能在圖書市場立足,完全復制其他出版社的經營理念和品牌文化,甚至抄襲他人選題等等。但隱性的違背則埋藏得較深,有的時候是出版人的集體無意識行為,其對文化理性的損害常常是慢性的、滲透式的,甚至在讀者那里這種損害因不易被察覺而并不值得一提,比如當下的文學出版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圖書的定價和作品的價值并不相符。于此我們不妨拿兩本書來進行一下比對,由韓寒監制、一個工作室主編的《所有人問所有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的定價是36.00元,全書269頁,字數不超過十五萬,它是電子雜志《一個》的“所有人問所有人”欄目中部分內容的集結,107個問題和回答的確展現了當下社會流行的諸種問題,且趣味性較強,但實際上整部書只是以一種“侃”的態度來探討時下熱點,文化價值備受時間局限,談不上有什么深遠影響;而米蘭·昆德拉的經典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的定價是35.00元,全書294頁,字數超過二十萬,從表面上看作品講述的是一男兩女的三角感情故事,但實際上卻蘊含了極深的哲學意味,作者試圖探討的是輕與重、靈與肉之于生命的關系問題,且他以文學的方式對“媚俗”做了哲理性的思考,而這些質素都決定了這部作品的文化生命長度和強度。既然兩本書的內容含量和文化價值相差如此之大,那為什么在價錢上卻沒有體現出來呢?原因就是出版人違背了出版倫理,忽略了文化理性,將圖書的價格與作者的市場影響力、圖書的紙張費用和印刷費用以及相關的宣傳支出直接掛鉤。“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文化、信息才是最值錢的,文化附加值應該是決定圖書價格的根本決定性因素,出版物的價值是靠其所含的文化含量來提升的,可目前的圖書定價比較重視其載體的價值,而相對輕視其所承載的文化的價值,這不能不說是出版業的悲哀。”[5]
文化理性除了號召出版人遵循出版倫理,也呼喚其提升自身的文化品味。出版人是文化傳播者。文化傳播者的身份決定了出版人要兼具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要將出版作為一項具有廣泛文化影響力和導向作用的事業來做,而事實上所有從事出版工作的人都應該如此。出版單位或出版企業的領導層成員作為領頭人和決策人,在企業經營當中必須高瞻遠矚,切勿為眼前的蠅頭小利和一時輝煌而犧牲單位或企業的社會價值,他們既要樹立品牌文化意識,突出企業經營特色,明確市場定位,同時也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引領團隊出版具有較高文化品質的讀物,把出版事業當作一項真正的文化事業來做。編輯和發行人員的文化品位同樣非常重要,其實許多編輯都有著較高的審美水準,在入行伊始也都有著崇高的文化理想,但面對現實的市場環境和來自出版單位或企業上層的壓力,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做出讓步,其實好的編輯不僅要在選題、選稿上具有獨特的審美眼光,還要了解出版單位或企業的經營目標以及廣大讀者的需求,甚至要懂得如何說服出版決策人做出明智的選擇。發行人員是出版產業鏈條上最了解市場的人,但他們大多提供給出版單位或企業的信息是“什么樣的書能賣得好”,實際上發行人員最要堅守文化理性,因為他們完全可以在與實體書店、電商、圖書館、學校進行接洽的過程中傳達和接收有關圖書出版、流通以及消費的一切有利于文化傳播與發展的信息。
裝幀藝術是文學出版審美內涵的另外一維。從審美的角度看,圖書的裝幀藝術實際上應該以滿足讀者的觸感需求和觀感需求為宗旨,但具體到某一類書或者某一本書,裝幀藝術風格也應與圖書內容氣質相符。通常情況下,出版人比較在意讀者對書籍的觀感,特別是注重圖書封面的設計,因為在實際的購買當中確實有一部分圖書消費者是隸屬于“外貌協會”的,有的時候他們就是會因為一本書的封面圖案或者腰封推薦而選擇掏腰包。但是,真正具有審美文化意義的圖書裝幀藝術不能僅僅以博人眼球為旨歸。文學圖書的裝幀首先要追求“表里如一”,即內容與封面設計要和諧統一,比如一本詩歌集或散文集,它的封面設計應力求簡約詩意,而不是漫天的濃墨重彩加上幾個“腰封王子”和“腰封公主”沒完沒了的推薦;其次要照顧讀者的眼睛,這就不僅要求編輯們注意正文的字體、字號、行間距、頁邊距等排版問題,還應考慮紙張的顏色、亮度及其對眼睛的適應性;第三是要關注讀者的觸感需求,現在已經有一部分編輯意識到了這一點,其實觸感所強調的也是舒適度的問題,只不過它面向的是讀者的手而不是眼。觸感需求實際上還是細節需求,比如我們在閱讀一本書時,首先是要翻頁,如果圖書紙張的舒適度高,讀者就能避免至少三個問題的發生:一是兩頁紙貼合太緊導致的翻單頁困難,二是新書紙張邊角鋒利劃破手指,三是手容易出汗的讀者在翻頁時可能會破壞圖書原本的質地。就觸感而言,圖書的大小、輕重也很重要,口袋書于此就是一種比較成功的實踐,但是就文學出版而言,口袋書的市場還是有待開拓。
腰封泛濫是當前圖書出版市場的一種病象,它既反映了出版人文化理性的缺失,也體現出圖書裝幀藝術的文化缺陷。“腰封們”除了色彩醒目,名人的推薦語和奪人眼球的廣告宣傳語更是無處不在,在新近上架的新書中就不乏這樣的例子。如王海鸰的《新守婚時代》的腰封上就寫著:“著名編劇/作家王海鸰繼《新戀愛時代》、《新結婚時代》后/婚戀力作華美來襲/首次探討轉型期中國式守婚難題/再度喚起都市男女十年青春記憶。”這算是比較中規中矩的一類,而像亨利·梭羅著、鮑榮與何栓鵬譯的《瓦爾登湖·論公民的不服從義務》的腰封內容就極為“豐富多彩”了,上面除了印著“哈佛史上最年輕的畢業生之一/托爾斯泰、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的靈魂導師”以及“首度收錄作者遺作/可讀性最高漢譯本/三億美國人必讀課程”外,還有李銀河、柴靜、張德芬、李開復等八位“大咖”“推崇備至”的字樣,更為重要的是英語教育屆的權威“笨蘋果”的推薦語,即“這個譯本很不錯。在2012年以前,讀懂梭羅譯著恐怕只有一個半中國人吧,海子算一個,他辭世時手里就拿著,其他人都算半個吧。但是,從此以后,能夠讀懂梭羅的中國人,也許就多出兩個來,一個是你,一個是我”。有了這段話,無疑就證明了這個譯本的可讀性和可收藏價值。這個腰封文案算是比較典型的,有夠夸張的“噱頭”,有“大腕兒”,有煽情的推薦語,并且圖書內容本身有一定的口碑基礎。但實際上鋪天蓋地的腰封已經引起了許多讀者的不滿,2009年5月豆瓣“恨腰封”小組的成立無疑證明了讀者對“妖封”的厭倦,小組中最熱門的幾個討論話題就是“你所見過的最惡心的腰封”、“大家都把腰封拿來干什么”、“腰封小王子列舉”等。而關于腰封的用途通常有兩種回應,一是被當做垃圾扔掉,另一種就是當做書簽。可見,文學出版召喚文化理性、提升裝幀藝術格調已是迫在眉睫。
三、 審美立場下文學出版的“大數據”應用策略
既然文學出版在當下正面臨著嚴重的“審美危機”,那么出版人應該怎樣利用“大數據”緩解和改善這種現狀呢?事實上,“面對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出版行業認知大數據技術的戰略意義不在于掌握龐大的出版數據信息,而在于對這些數據進行專業化的處理,從而挖掘出數據背后的意義和價值”[6]。所謂“進行專業化的處理”其實就是要求出版人對大數據的使用具有針對性,而這種針對性既要“明顯”,又要“明確”。“明顯”意味著文學出版從業人員要全力挖掘出可被利用的數據信息,把數據的潛在價值轉變成出版的文化價值和單位或企業的社會價值,譬如一部獲得國際獎項的文學作品,它在世界各國的發行量、零售銷量、圖書館館藏量以及書評人的評價、讀者的閱讀反饋等一系列信息都能構成一個極富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的數據庫,中國的出版人是否能夠發現這些數據的存在價值和應用價值呢?“明確”就是在挖掘、發現大數據的基礎上分門別類地使用數據,例如由各種文學暢銷書排行榜、文學暢銷書搜索關鍵詞、文學暢銷書作者的受關注信息以及不同文學暢銷書的定價、字數、頁數、出版發行單位、印刷單位、版次印次、裝幀特點、讀者反響、專家品評等一切相關信息組成的大數據集應被出版人利用在文學暢銷書的出版預測上,如果將這些數據用在預測經濟類圖書或者歷史類圖書的出版上,那肯定是驢唇對不上馬嘴。在明晰了“針對性”問題之后,審美立場下文學出版的“大數據”應用策略就可以具體而談了。
首先,出版從業人員應充分利用大數據來規范和拓展文學暢銷書的出版市場,充盈文學暢銷書的審美文化內涵。“營銷策略與發行組織控制著零售圖書和消費者的選擇機會,所依賴的途徑是,它們促進編審與大眾趣味直接接觸,不僅僅從經濟角度增強主要由低下的社會階層組成的消費者的文化購買力,而且更多的從心理角度降低文學作品的‘獲取條件’,使人們得以在低弱的前提條件和后果之下,舒舒服服地接受文學。”[7]其實,出版單位或企業愿意更多地給通俗文學作品投資就是因為它們更有市場,更有可能成為暢銷書,為此它們不惜以遠遠超出作品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價錢去爭奪作者和版權,它們也樂于在出版發行上加大投入,因為它們清楚利潤是會不斷上漲的。實際上,目前中國的出版從業人員非常了解中國讀者的閱讀興趣點,對于哪些文學作品會暢銷他們只需要憑借自己的出版經驗和市場眼光就能做出不錯的預測和判斷。但是,前面已經分析過,文學類暢銷書出版的問題并不在銷量,而在文化品位。如何利用大數據提高文學暢銷書的文化品位呢?就規范文學暢銷書出版市場而言,出版從業人員應該通過搜集整理各大暢銷書排行榜提供的所有相關信息來發掘當下文學類暢銷書在文化層面存在的弊病,比如哪些文學暢銷書在內容和題材上是近乎相同的,哪些作品的表現手法和敘事風格是過分雷同的,哪些作者的寫作是模式化的、缺少個性和創造力的,哪些暢銷書所傳遞的價值觀是消極的、陰暗的等等。一旦出版從業者通過數據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十分清楚今后的文學出版需要規避和剔除哪些作品了。就拓展文學暢銷書出版市場而言,出版從業人員也應該利用大數據來革新自己的慣有眼光。文學出版于此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一是文學作品是否一定要與青春回眸、玄幻武俠、大眾言情、古裝穿越之類相聯系才有資格被重點出版并成為暢銷書,二是一些暢銷作品縱然在題材和主題上相近,但是否在情節設置和藝術表現上也難于做個性化的探索和創新。當然,第二個問題更像是面向作者而提的,但出版從業人員其實只要利用相關數據就能發掘哪些作品是雷同化、模式化甚至有抄襲嫌疑的,而這類作品即便再有市場,出版方也應堅決拒絕出版。
其次,出版從業人員應充分利用大數據來加大對嚴肅文學的出版和宣傳力度。我們都很清楚嚴肅文學的市場競爭力很難與通俗文學相比,但這并不以為著嚴肅文學不能成為暢銷作品,比如像《百年孤獨》這樣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在中國的累積銷量就已經超過了二百五十萬冊。出版業是文化產業,作為產業自然要盈利,或者至少要不賠本,而在商言商也是天經地義,所以加大嚴肅文學的出版和宣傳力度絕不是讓出版單位或出版企業背上傳播高層次文化的精神枷鎖去做賠本買賣,而是鼓勵每一個出版從業人員去利用便捷而充實的海量數據挖掘優秀嚴肅文學作品的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谷歌的數據圖書館(Goolge Ngram Viewer)的應用在此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策略借鑒。谷歌公司的信息優勢在業界是不言自明的,其互聯網搜索所能提供的數據量更是難于用數字來形容。谷歌數據圖書館是建立在谷歌擁有的全部圖書的數據資源基礎之上的,數據需求者可以在這里找到單詞和短語的使用次數,并由此發掘某一時期哪些話題更受人們關注或者寫作者們對哪些用詞青睞最多等等。中國的嚴肅文學出版同樣可以開發大數據的這項潛能,比如每天都有數以億計的人在使用谷歌、百度、搜搜、搜狗、有道等搜索引擎,這些搜索引擎一定儲備了相當數量的數據信息,這些信息自然是龐雜而混亂的,但是從中提取與嚴肅文學相關的內容也不是不可能,像與嚴肅文學相關的名字類搜索關鍵詞就可以構成一個巨大的數據集,具體可包括作家名字、作品名字、作品所獲獎項的名字、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作品中地理位置的名字、作品不同版本的出版單位的名字、作品其他語種譯本的名字、作品各譯介本譯者的名字、改編后的影視作品的名字、影視作品的導演和演員的名字等等。出版從業人員可以根據這些“名字”搜索所提供的數據信息來豐富嚴肅文學的出版,如哪些作者的受關注度高,讀者對哪些作品的期待值高,哪些導演改編的影視作品的原著本更有市場,哪些文學獎項的獲獎作品更容易引起讀者的購買欲……此外,出版從業人員完全可以通過對搜索引擎中熱門詞匯的統計來從內容上定位式地尋找讀者喜歡或期待的嚴肅文學作品,這實際上非常有利于編輯的征稿、選稿和選題工作的進行。
第三,出版從業人員還可以利用大數據資源來優化文學類圖書的裝幀藝術。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對精神文化消費的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如果說十幾年前作為精神消費主體的讀者們還只是關注書的內容的話,那么新世紀以來在“讀書”這件事情上讀者們的要求就不再那么簡單了。書的“舒適度”對當下的讀者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前所述,圖書的裝幀藝術其實是一門審美含量極高的藝術,圖書的裝幀設計一方面要力求與文本的內容氣質相契合,另一方面也要努力讓讀者在捧書閱讀時有一種舒適感和滿足感。如何獲知讀者對文學圖書裝幀設計的需求呢?出版人于此完全可以通過讀者的反饋信息來實現這一目標。在大數據時代,讀者的反饋信息更多地是通過網絡媒介直接呈現出來,亞馬遜、當當、京東等電商在他們每本圖書的銷售頁面上設都有“商品評論”一項,已購書讀者可以通過留言的方式對圖書的內容、裝幀、性價比等作出評價,當當圖書還專門在商品評論中設置了一個名為“買過的人覺得”的版塊來對消費者的評價進行分類,分類項包括“包裝不錯哦”、“整體感覺不錯”、“性價比很高”、“印刷很正”、“紙質好”、“排版不錯”、“包裝一般”、“折痕變形”、“紙質一般”。其實這樣的例子只是出版大數據的冰山一角,出版人若是能有效地掌握和利用這些數據,就能夠了解讀者對于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圖書有哪些裝幀設計上的需求。在腰封泛濫問題的整治上,大數據同樣具有極大的利用價值。除了從讀者的反饋信息中來獲知讀者對“妖封”有哪些具體的不滿之外,中國出版人還可以通過搜索和整合世界大數據來學習如何設計令人喜愛和滿意的腰封,比如日本出版界對于圖書裝幀就有許多可供借鑒的心得,他們十分精通于如何將圖書制作成一個藝術品,也自然在腰封的文案設計和美術設計上更有發言權,出版從業人員可以通過網羅世界性數據來挖掘“什么樣的腰封能夠兼具宣傳效果和藝術美感”。
最后,出版從業人員應該充分利用大數據的預測功能來挖掘文學新人和文學精品,務必以文學價值和文化價值論英雄,力求做“不看出身”的出版。文學出版,往往更看重作者的名氣,除去像魯迅、張愛玲這樣的已故文學大家之外,當下作者的名氣有可能是各種國際國內大獎捧出來的,有可能是網絡點擊率造就的,有可能是影視作品推出后連帶而來的,也有可能是其他領域的名人跨界跨出來的,但很少有是出版人直接推薦出來的。當然,出版人有出版人的難處,畢竟在中國圖書出版市場中,讀者并不關心出版人的眼光,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信賴體系。然而我們之所以呼吁文學出版的文化理性,就在于期待出版從業者能夠發揮其文化傳播者和文化把關人的作用來打破當下讀者并不健全也不健康的圖書選購習慣。作為生產一方,出版人有責任也有義務向讀者提供具有較高文化內涵和審美品質的文學作品,而這其中就包含許多尚未被發現的好的作品。于此,利用大數據資源來選稿既是一個風險性的項目,同時也是一種可靠性的作為。事實上,出版從業者要想達到商業價值和文化價值的雙豐收,就要既知道讀者愛什么,也知道讀者缺什么,有的時候讀者愛得越多就會缺得越多,比如前幾年玄幻類和仙俠類文學作品大熱,造成了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市場收縮,于是最近一兩年讀者又開始尋求貼近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非虛構類小說就搖身成為了消費熱點。想要找尋到有品質且有市場的文學新品,第一步就是要做好預測,出版人其實可以比較輕松地通過對讀者近三年到五年的購買數據信息來預測未來一到兩年之內讀者的購買需求。知道了讀者想要什么,知道了讀者缺乏什么,出版人就要拿出些態度和魄力來,畢竟數據再龐大、再有效,也只有被轉化成出版實踐行為才有意義。文學新人哪里尋,文學精品哪里找?傳統的推薦方式(人際推薦、期刊推薦、媒體推薦等)始終存在“看出身”甚至“看人情”的弊端,出版從業人員倒不妨利用大數據來為某一選題定位所需作品,比如編輯們在確定了一個有關女性詩歌的出版選題后,完全可以根據團隊設定的關鍵詞進行數據搜索,看一看哪些期刊雜志上有更多符合選題的作品,或者找一找哪些類型的博客和個人主頁上有切合這一選題的詩歌作品的發布。
從全球的范圍來看,大數據時代已經撲面而來,在這一背景環境當中,中國的文學出版能否在審美內涵上有所豐富關鍵還是在出版人。當然,出版業對于大數據的有效利用在目前看來也有相應的難度,因為漫天的數據信息還有待被篩選和整理,而國內還鮮有像谷歌數據圖書館這樣比較成體系、成規模的海量信息數據集庫,所以出版從業人員在大數據的搜尋和使用上還須待更多地實踐性探索。不過,不足正意味著巨大的商機和提升空間,誰能夠提供文學出版所需的大數據或者說整個出版行業所需的大數據呢?IT領域的企業可以嘗試,風險評估領域的企業可以嘗試,電子商務領域的企業可以嘗試,出版發行領域的企業和單位更可以嘗試。事實就是,出版單位或企業一旦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大數據資源庫,就等于擁有了一種新形式的資本,而這種資本所能夠帶來的“產值”(經濟價值、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等)是不可估量的。
[1] (美)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潘琪,張焱,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192.
[2] (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M].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4.
[3] 蔣志臻.當代中國出版問題的倫理審視[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4:36.
[4] 孔則吾.千年的跨越:世紀之交的中國出版現象研究[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253.
[5] 郝振省.出版文化理性研究[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99.
[6] 周煜.大數據時代出版行業發展趨勢分析[J].中國出版,2014(7).
[7]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193.
(責任編輯:王 荻)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 Literary Publishing in the Age of Big Data
HAO Dan
(School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The age of Big Data is an age full of massiv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There is a serious aesthetic defect in literary publishing in the age of Big Data.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literary publishing includes two aspects: the cultural rationality of literary publishing and the art of the book of literary publishing. Publication practitioners should make the best of the big data resources to cope with the aesthetic crisis of literary publishing. There are four concrete strategies. Firstly, it needs to resulate and expand the market of literary best-sellers. Secondly, in needs to increase the publishing and propaganda of the serious literature. Thirdly, it is to optimize the graphic design of the literary books. Lastly, it needs to find for new authors and elaborate works.
age of big data;literary publishing;aesthetic dimension
2015-09-21
郝丹,女,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G239.1
A
1008-2603(2016)01-01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