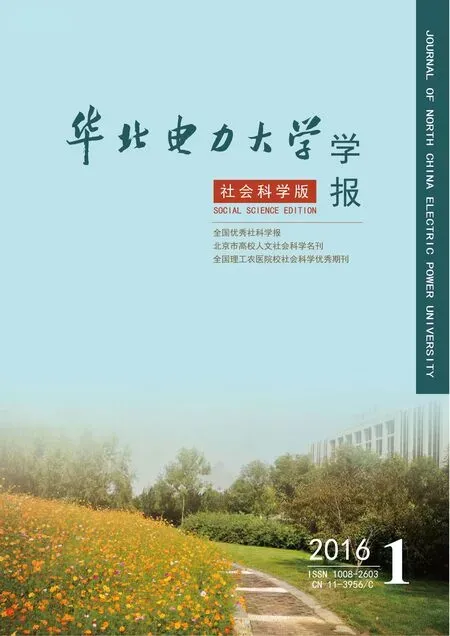茅于美的李清照詞英譯及啟示
葛文峰
(1.北京外國語大學 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2.淮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GE Wen-feng1,2
(1.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China;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China)
?
茅于美的李清照詞英譯及啟示
葛文峰1,2
(1.北京外國語大學 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2.淮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茅于美的《漱玉擷英:李清照詞英譯》是易安詞英譯歷程中的一個重要譯本。譯者堅持詩詞翻譯是創造性工作,更是一種跨文化的文學移植事業。因此,茅于美發揮主體性,使得李清照詞譯文彰顯出深受讀者認可的創造性。《漱玉擷英》成功的背后,凝結著茅于美的詞人、學者與譯家三重文化身份動因,故而使得她的李清照詞英譯克服文化障礙,呼應讀者閱讀視野,而更加將原詞的情感傳譯出來。
茅于美;李清照詞;英譯;譯者文化身份
GE Wen-feng1,2
(1.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China;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China)
1867年,法國譯者朱笛特·葛諦靄(Judith Gautier)的漢詩譯集《玉書》(LeLivredeJade)選譯了六首李清照詞,開啟了李清照詞的外譯西傳之路。一個半世紀以來,數十位譯者或選譯,或全譯過李清照的易安詞。他們的譯事經歷、翻譯特點及影響廣受學界關注。遺憾的是,有一位李清照詞的譯者卻始終沒有走進學界的研究視野。她的翻譯與異域著名譯者——肯尼斯·雷克思羅斯(Kenneth Rexroth)、詹姆斯·克萊爾(James Cryer)——的譯本一樣深受海外讀者歡迎,而她卻是中國本土譯者;與其他李清照詞譯者單一文化身份不同,她又是兼具詞人、學者、文學評論家等多重背景的綜合型翻譯家。首部探討易安詞翻譯的著作《李清照詞英譯對比研究》的作者酈青女士,曾失望地坦誠,“無論筆者怎樣努力,至今都未能見著這一珍貴的譯本”[1]24。
這位李清照詞譯者究竟是誰,她是如何英譯的,又有何啟示?
她就是《漱玉擷英:李清照詞英譯》的譯者——茅于美。
一、茅于美與《漱玉擷英:李清照詞英譯》
茅于美(1920-1998),江蘇鎮江人,系著名橋梁工程科學家茅以升的長女。幼年的茅于美曾跟隨曾虛白學習外文,為畢生的中外文學、文化對比研究與交流打下堅實基礎。抗戰全面爆發后,茅于美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昆明),兼習法、德、拉丁等多種外語。她后因病輟學,痊愈后轉入浙江大學外文系,期間受教于詞學家繆鉞先生,填詞技法日益精進。畢業后,茅于美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研究生,專攻英國文學,業師為吳宓教授。1947至1948年,茅于美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48年秋,她又開始在伊利諾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旋即欣聞新中國成立,茅于美放棄學業,于1950年與丈夫徐璇歸國。回國后,茅于美先后經歷幾番政治運動,無法繼續跨文化、文學研究的專業工作,先后供職于北京文學研究所、出版總署編譯局、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1962年,茅氏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任比較文學教授,著譯頗豐。晚年的茅氏數次赴美探親、訪學,1998年初夏,茅于美于美國學術交流期間,因癌癥病故于加州。
早年留學美國時,茅于美即開始中國文學的譯介工作。她曾英譯《四書》、《五經》,結集為《移植集》,意在將中國文化典籍“移植”到美國。也正在此時,“她還把中國古代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詩詞譯成英文……為中西文化交流嘔心瀝血”[2]1718。這證明茅氏的李清照詞英譯工作至少在1940年代末期便已經開始了。筆者所持《漱玉擷英》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2003年版本。但是,根據譯者“李清照《漱玉詞》英譯卷成感賦”自述,譯畢時間為“1978年10月”。由此可見,茅氏英譯李清照詞的時間跨度長達30年之久。趙樸初曾填詞《浣溪沙》,贊嘆茅氏的這項偉大翻譯工作,上闋為“譯著功同創作深,幾多覓覓與尋尋,誰知煉石補天心”[3]44。茅氏傾情李清照詞的翻譯,中間經歷過多少“尋尋覓覓”的思索、推敲與修訂已不得而知。但是,最終出版的譯本無疑是譯者字斟句酌的滿意成果,是成熟完善的譯作。她的好友馮至先生祝賀道,“你多年的工作成果——英譯李清照詞——能與讀者見面,正如看見自己的孩子長大成人一樣令人愉快”[4]387。《漱玉擷英》共英譯李清照詞32首,未譯存疑詞,底本為王學初注疏的《李清照集校注》。該集附有“譯者簡介”、“致謝”、繆鉞與趙樸初的“賀詞”《點絳唇》與《浣溪沙》、“引言”以及美國普渡大學桑·休斯教授(Prof. Shaun F. D. Hughes)的“序言”。
二、茅于美英譯李清照詞的思想與方法
在國內譯者崇尚古典詩歌“形神兼備”翻譯傳統的大趨勢下,茅于美反其道而行之,傾向于采用國外譯者的“自由體”翻譯策略。晚年的茅氏在其論文《譯詩瑣談》(《中國翻譯》1992年第1期)中總結了她的詩詞翻譯思想。她堅持“以詩譯詩”,“詩歌翻譯要譯得忠實之外,還要傳達原文風格,展現出美感。譯出來的詩本身也應該是詩”[5]22-23。難能可貴的是,在1990年代初期,在言必稱“信達雅”、“忠實”文學翻譯觀念深入人心的年代,茅于美卓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創造性翻譯”的思想:
我認為,“信”和“達”體現著語言的精通,而“雅”卻顯現出“再創造”的功夫,正是最見功力和水平的地方。……整個翻譯勞動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第一步,譯者須進入原作的“角色”,達到忘乎自我、出神入化的程度,與作者憂喜與共,心魄和一;第二步,譯者須返回自我,使出渾身解數,用所熟諳的外語重新譜寫原作;第三步,譯者須進行譯文的藝術加工,重現原作詩意,貼切原作形式,格律、音韻盡量自然而合轍。……上乘的譯者并不是由原作者牽線的木偶,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5]22-23。
茅氏的詩歌翻譯思想雖然也基于“信達雅”的傳統譯論,但是她的獨創性在于對“雅”的闡釋。以往的論者將“雅”詮釋為“爾雅”、“文雅”,而茅于美則將其深入地闡釋為一種譯者為追求“深層忠實”翻譯而進行的主體性、能動性的發揮。她提出的“創造性翻譯”的三個步驟具體闡明了譯者如何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翻譯的過程:譯者首先要信任原作才能真正理解原始文本,理解之后需要將原作融匯于心,將其“據為己有”,然后在藝術加工的層面進行大膽的增、刪、改、編,旨在還原、甚至增強譯文的文藝美學特質。茅于美的翻譯思想彰顯了譯者主體地位,對當時國內盛行的翻譯理論與實踐中的“原作中心論”與“譯文中心論”是一種挑戰。這也契合了當時英國闡釋翻譯學派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的“翻譯四步論”,即“信任”、“入侵”、“吸納”與“補償”。茅氏與喬氏的翻譯思想“對于翻譯實例的分析,尤其是分析翻譯闡釋這一相對隱蔽的過程,具有特殊的解釋力”[6]81-87。
茅于美的創造性詩詞翻譯思想主要是在她的李清照詞英譯實踐中形成的,她的李清照詞“自由體”英譯方法又踐行著她的翻譯思想,翻譯思想與翻譯實踐交互影響,相互促進,互為因果。
李清照作為一代詞宗,倡導作詞“別是一家”,她本人更是嫻熟地運用各種詞牌進行創作。相應地,詞牌也成為“詞”作為中國古典詩歌中一種特殊文體的象征,而與詞作的內容幾乎沒有必然聯系,僅僅作為篇幅、韻律、平仄的文學規范。這也是李清照詞英譯過程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茅于美采用創造性的“增譯+音譯”方法。譯者將每一首易安詞的內容加以提煉,賦予譯作新的標題,然后在副標題中注明詞牌。譬如,膾炙人口的《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的詞牌譯為“RowingaBoat——tothetuneofRumengling”,《點絳唇(寂寞深閨)》的詞牌譯為“Lovesickness——tothetuneofDianjiangchun”。茅氏的這種譯法既方便了英語讀者對譯作的理解,又讓他們從“to the tune of”(諧律)中明白,譯作源自一種獨特的、與音樂相關的文體。這種譯法的優勢在于“既讓譯語讀者在順暢的閱讀中感受審美體驗,又保留了原作的語言和文化內涵”[7]49-53。
李清照詞以“情發于中”、“情真意切”著稱。李詞中的愛情詞自不必言,其閨怨、離別、傷逝等詞作更是感人至深。茅于美認為,“李詞的主要題材是抒寫對愛情失去的愁苦和悲哀。生離死別形成她抒情詞的特殊內容”[8]344。易安詞的感情抒發與翻譯傳遞也是譯者一直努力的方向,例如《訴衷情》的翻譯。
訴衷情ASleeplessNight——tothetuneofSuzhongqing
夜來沉醉卸妝遲,Deeply drunk tonight,
梅萼插殘枝。I remove my hair-wear late.
酒醒熏破春睡,The mume-calyx withers on my hairpin,
夢遠不成歸。I awoke from my spring dream, recovered from wine.
My dream of your return was cut short.
——Far, far away are you.
人悄悄,All is quiet on earth,
月依依,The moon shines with love.
翠簾垂。Green curtains are drawn low.
更挼殘蕊,So: I rub gently the withered mume-calyx.
更捻馀香,So: I pick up the incense ash,
更得些時[3]73。 So: I pass the time in this way[3]72.
這首詞作于晚年詞人故國滅亡、南渡浙江之時。詞人詠梅卻意不在梅花,而是抒發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一腔幽怨之情。茅于美沒有模仿中國傳統詩歌注疏一樣,取名《詠梅》,而是基于個人的解讀,在譯詞中新擬題目《不眠之夜》(ASleeplessNight),這避免了英語讀者對譯詞內容的誤解,以“不眠之夜”點明了譯詞的內容基調。原詞中多用“無主語句”,以達到中國傳統詩詞中“無我之境”的審美傾向。而譯者深諳英詩中“有我之境”的傳統,更以規范的英文譯出原詞中潛在的主語“我”(I、My),運用了主人公與景物描寫相結合的抒情模式。上闋末句寫詞人酒醒,離愁別緒更濃。譯者在此將其中深意外化、顯化,具體改寫為“丈夫的歸來無非夢一場”(My dream of your return was cut short),而現實的情況卻是“你在那遙遠的地方”(Far, far away are you)。在譯詞中,譯者用第一人稱“我”(I)與第二人稱“你”(You)形成一種詞人與丈夫直接交流的口吻,娓娓道來,有利于情感的抒發。下闋的前三句寫環境的寂靜,以襯托詞人的寂寥。“人悄悄”的“人”既可以指詞人,也可以范指其他人,作為第三人稱使用。譯者此處譯為“All is quiet on earth”,意在與下文的景物描寫融為一體,達到借景抒情。末尾三個排比句將詞人的悲傷情緒表達的淋漓盡致。譯者匠心獨具,分別以三個“So”起句,傳達詞人的無奈心情,更以三次重復使用第一人稱主語“我”(I)來強化孤獨寂寞的場景。茅于美的創造性譯詞寓情于景,情景渾然一體。
茅于美堅持的創造性翻譯的“第三步”認為詩歌翻譯要“格律、音韻盡量自然而合轍”。李清照詞慣用疊詞疊韻,音樂性極強。盡管譯者承認韻律翻譯的困難,但是她仍舊盡力而為。茅氏認為,“李清照在韻腳的選擇和安排方面千古獨步,《聲聲慢》運用了許多雙聲疊韻,強化了凄婉柔和的音樂美感”[8]352。例如《聲聲慢》開篇七對疊詞是為千古絕唱,茅氏的譯文如下。
尋尋覓覓、Seek, seek. Search, search.
冷冷清清、Cold, cold. Empty, emprty.
凄凄慘慘戚戚[3]98。Misery, misery. Sorrow, sorrow. Sadness, sadness[3]99.
譯者忠實地譯出了十四個疊詞,表面上來看,是“字對字”的翻譯。然而,譯者巧妙地運用了英詩中的韻律表現手法。在譯文中,七對疊詞有四對押“頭韻” (Alliteration),兩對押尾韻(End Rhyme)。例如頭韻的/S/音為齒齦音、清輔音,原本在英詩中表達憂傷、苦悶的心情,在譯詞中可以將原詞的類似情感傳達出來。同樣的還有《聲聲慢》下闋中的“點點滴滴”,茅氏譯為“Drip, drip, drop, drop”[3]99,是為英詩中著名的類尾韻(Pararhyme),創造性地再現了原詞的音樂性。
三、茅于美英譯李清照詞的啟示與意義
對于《漱玉擷英》,繆鉞先生填詞《點絳唇·題于美英譯李清照詞》盛贊道:“彩筆凌云,能傳千載芳馨意。仙葩奇卉,移植新園地。九畹滋蘭,應記當年事。鵬飛萬里,天半紅霞起”[3]42。休斯教授更是贊美有加,茅氏譯文“讓李清照在美國也發出了清澈明晰而又活力四射的聲音”[3]32。那么,茅于美的李清照詞英譯緣何得到如此的贊揚與認可?究其原因,可以從她詞人、學者、翻譯家的文化身份中找到確切答案。
(一)詞人譯詞,感悟深刻
茅于美從17歲開始填詞,畢生有《夜珠詞》與《海貝詞》二集傳世,包括326首詞、29首詩,二集后來合刊行世,名為《茅于美詞集》。茅氏出身書香門第,早年適逢亂世,輾轉求學;青年留學海外,幸遇佳偶,一生感情甚篤;中年遭遇各種運動,親人離散;晚年學術輝煌,步涉海內外各地。她的人生經歷與李清照頗為相似,甚至其居所也取名“歸來堂”。茅氏詞風深受易安詞影響。馮至認為,“論者多以茅于美詞來比漱玉詞。茅于美早期受李清照影響較多,她近年又曾將李詞譯為英文詩,這比擬是有一定道理的”[4]146。細讀茅于美不同時期的詞作,從中可以發現她綿延不絕的愁情、纏綿悱惻的戀情、篤念天倫的親情與報效祖國的豪情。
正因與李清照的詞風的極似,茅于美在英譯易安詞時,才能較其他譯者更加深入的體悟原詞的內容與情感。尤其是“茅氏詞風接近李清照的婉約,這是不言而喻的”[9]178。因此,在翻譯過程的第一、二步,茅于美既可以如同閱讀“自己”的詞作一樣去理解李清照詞,又可以像“自譯”“夜珠詞”、“海貝詞”一樣譯出李清照詞。譯者的詞人身份使得她在研讀、理解、體會李清照詞方面,具有了其他譯者無法比擬的優勢。
(二)學者譯詞,中西會通
我們著名翻譯家曹靖華的觀點是“翻譯什么就研究什么,換而言之,研究什么就翻譯什么”[10]139-140,將翻譯與研究的對象統一起來,可以相互促進,是學者型翻譯家的一種工作路徑。茅于美也正是如此。她既是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者,又是中西文學對比研究的教授。她著有《中西詩歌對比研究》、《易卜生和他的戲劇》等專著,另有《十四行詩與中國詞》、《莎士比亞和他的作品》、《英國桂冠詩人》、《中西隱逸詩人》、《中西詩人筆下的愛情主題》、《中西詩人的憂患意識》等學術論文。由此可見,茅于美在中西詩歌比讀與研究方面取得的豐碩成果。
在跨文化的視野中,茅于美將李清照詞與英國女詩人白朗寧夫人(Mrs. Elizabeth Browning)的詩歌進行對比研究,發掘出她們詩歌中共有的鮮明愛情主題。與西方詩歌進行比較后,茅氏發現,李清照的愛情詞多為幽怨哀傷、缺乏現實生活的描寫。在對憂患意識的解讀中,茅于美的結論是,李詞“遣詞造句,綺麗典雅,倚重紅綠繽紛的色彩,體現出濃郁的畫意”[11]96-100。譯者對李清照詞與國外詩人詩歌的研究,其學術性洞見有利于她從學理與文學審美等角度深刻地理解、翻譯易安詞,也能藉此把握英文讀者的詩歌閱讀習慣與心理,更加注重譯文的可讀性。
(三)譯家譯詞,注重接受
茅于美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除了《漱玉擷英》、《移植集》之外,她的翻譯文集還有《濟慈書信選譯》與匈牙利劇作家莫里茲(Móricz Zsigmond)的四幕劇《親戚》。茅于美的翻譯目標明確,即文學的跨文化“移植”。她在論詩歌翻譯時談到,“譯詩好比是移植的任務。這種移植工作常因氣候、土壤和栽培技術等條件的限制而屢遭失敗。但若各種基因湊巧,也能栽培出鮮艷的花朵。因其帶有重新栽種的那片泥土的芬芳,使觀賞者認為它比在故土開得更好”[5]22-23。在此,茅于美深刻感悟到作為“移植”的翻譯工作的困難。但是,在“基因湊巧”——創造性的翻譯——的情況下,同樣可以產生比原作更優美的譯本——“比在故土開得更好”。事實上,這種“翻譯移植論”與英國文化翻譯學派領秀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關于詩歌翻譯的“種子移植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她們均“強調詩歌的生命力可以憑借翻譯而得以延續,提倡詩歌翻譯的創造性”[12]88-95。
通過上述茅氏李清照詞譯文的解讀可以發現,其譯詞內容重于形式,力圖把譯詞與原詞盡最大限度地融合無間。也正是為了李清照詞譯文在美國的生命力得以重新煥發,能夠被異域讀者順利接受。茅于美趁旅美訪學的機會,邀請休斯教授與中國留學生王吉輝對《漱玉擷英》的譯稿進行修改,適應讀者的理解與接納,以期李清照詞的譯文之花,在美國“開得更加美麗”。
五、結語
茅于美的《漱玉擷英》是李清照詞翻譯史上的一個成功個案。在譯者創造性詩詞翻譯思想的指導下,茅氏譯文不但傳遞了李清照詞的文學美感,更適應了英語讀者的閱讀規范。茅于美的成功譯事得益于她“移樹植花甘譯匠,采珠拾貝樂詞人”[13]9的綜合譯者文化身份。詞人、學者與譯家的文化背景使得茅于美的李清照詞翻譯更加傳情,從而克服文化差異,深受讀者歡迎。
[1] 酈青.李清照詞英譯對比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09:24.
[2] 孫小金.名人后代大追蹤(第四卷)[M].北京:中國古籍出版社,2009:1718.
[3] 茅于美.漱玉擷英:李清照詞英譯[M].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03:44、72、73、98、99、42、32.
[4] 馮至.馮至全集(第十二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87,146.
[5] 茅于美.譯詩瑣談[J].中國翻譯,1992(1).
[6] 夏天.斯坦納闡釋運作理論的應用:問題與方法[J].外語研究,2009(3).
[7] 酈青.李清照詞牌英譯方法探微[J].民族論壇,2005(3).
[8] 茅于美.中西詩歌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334.
[9] 陳雪軍.論女詞人茅於美的創作歷程和藝術成就[J].詞學,2012(1).
[10] 曹靖華.曹靖華譯著文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139-140.
[11] 茅于美.中西詩人的憂患意識[J].國外文學,1995(6).
[12] 侯建.也談詩歌翻譯的“種子移植”[J].外文研究,2013(4).
[13] 茅于美.茅于美詞集[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9.
(責任編輯:王 荻)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Qingzhao′s Ci-poems by Mao Yumei and its Enlightenments
PickingtheBestCi-poemsfromtheWashingJadeby Mao Yumei is an important ren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Li Qingzhao′s poetry. The translator Mao believes poetry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 creative task, but an intercultural deed of transplanting literature. Therefore, Mao′s English version of Li′ works takes on the well-received creativity from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Beyond the success of the rendered masterpiece, it owes much to Mao′s cultural identity of ci-poetess, scholar and translator. Accordingly, the rendered work conveys its original emotion by overcoming cultural block and catering to readers′ reading horizon.
Mao Yumei; Li Qingzhao′s Ci-poems;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2015-08-27
安徽省高等學校省級優秀青年人才基金項目“詞宗遠游:美國李清照詞英譯研究”(項目編號:2012SQRW214);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旅行與賦形:美國李清照詞英譯研究”(項目編號:12YJC740038)。
葛文峰,男,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淮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H059
A
1008-2603(2016)01-01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