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預(yù)警,抑或?yàn)榇蟮睾盎?br/>——論閻真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路向
鄭國(guó)友
(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長(zhǎng)沙 410205)
?
精神預(yù)警,抑或?yàn)榇蟮睾盎?br/>——論閻真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路向
鄭國(guó)友
(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長(zhǎng)沙410205)
閻真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創(chuàng)作從多個(gè)側(cè)面呈現(xiàn)了20、21世紀(jì)之交“世界”的真實(shí),表達(dá)了對(duì)世界的關(guān)切和憂思。在世俗文化浪潮中,精神的旗幟被降下,人們處在對(duì)權(quán)和錢的深度迷戀之中。閻真的小說直面世界性難題、整體性危機(jī)和人類共同的生存困境。閻真對(duì)世界的這樣一種表達(dá)方式,讓人生出一種絕望,其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路向的價(jià)值正是從反向,甚至不惜以一種放大后果的表達(dá)方式,警醒人們?cè)谛碌氖兰o(jì)和新的文化語境中,通過借鑒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資源,完善這個(gè)時(shí)代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人格,重新找回那種傳統(tǒng)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氣魄,以激活民族的精神血脈,重新張揚(yáng)民族的精神文化,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
閻真;現(xiàn)實(shí)主義;世俗化;精神預(yù)警
一
20、21世紀(jì)之交,大約不到三十年的時(shí)間,中國(guó)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精神格局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1992年,中共中央作出“全面建設(shè)有中國(guó)特色的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重大決策,市場(chǎng)的觀念和經(jīng)濟(jì)利益的考量成了這個(gè)時(shí)代普遍性的共識(shí),一種新的政治邏輯和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呈席卷之勢(sh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顯示出的一種“霸權(quán)”,顛覆幾千年來中國(guó)人“重義輕利”的價(jià)值認(rèn)同,一種新型的財(cái)富觀全面侵入人們的生活,并重構(gòu)了人們對(duì)世界的認(rèn)知方式。政治爭(zhēng)議可以擱置,經(jīng)濟(jì)與世界接軌被“優(yōu)先”,全球化時(shí)代也正在這種經(jīng)濟(jì)的一體化中日漸成型。市場(chǎng)作為一種價(jià)值準(zhǔn)則和意識(shí)形態(tài),它猶如一場(chǎng)風(fēng)暴,迅速地掀起和促動(dòng)了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領(lǐng)域的大變革、大調(diào)整、大轉(zhuǎn)型。“后革命時(shí)代”與“革命時(shí)代”猶如“兩重天”,經(jīng)濟(jì)思維取代了政治折騰,“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取代了“階級(jí)斗爭(zhēng)”,“市場(chǎng)”取代了“計(jì)劃”,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留給人們一個(gè)暗淡的背影,個(gè)體的合理欲求得到法律保障。精神降下了旗幟,理想主義萎縮,世俗時(shí)代來臨了,人們邁步跨進(jìn)了消費(fèi)社會(huì)。但人們?nèi)找嬲J(rèn)識(shí)到,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卻并沒有為人們帶來期望中的幸福。資源枯竭、生態(tài)破壞、倫理道德失范、人際交往恐懼,欲望化時(shí)代物質(zhì)追求至上和精神的放逐,使人們陷入精神危機(jī)和生存困局之中。任何一位真正的知識(shí)分子,面對(duì)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的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他不可能不關(guān)切,不可能不焦灼,不可能不苦痛。1993年,《上海文學(xué)》發(fā)表王曉明、陳思和等學(xué)者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xué)和人文精神的危機(jī)》一文,以對(duì)話體記錄了當(dāng)時(shí)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王曉明、張宏、徐麟、崔宜明、張檸的討論,從而在思想文化界引發(fā)了一場(chǎng)關(guān)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大論辯。這次大討論、大論辯中雖然有識(shí)之士意識(shí)到了精神的危機(jī)并激發(fā)了巨大的思想擔(dān)憂,但它難以阻止時(shí)代的步伐,世俗化的征程一經(jīng)開啟,其摧枯拉朽之勢(shì)不可阻擋。世俗化是一個(gè)意義重大的歷史性事件,它對(duì)世界的存在方式和人們心理結(jié)構(gòu)及生活方式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而這種影響還在繼續(xù)和深化,且其后續(xù)影響還不可估量。然而,面對(duì)這種歷史性的變革,文壇風(fēng)潮中的文學(xué)依然陶醉在小小的“自己的園地”里,做著可憐的“薔薇色的夢(mèng)”。中國(guó)文壇需要一種理性、深刻現(xiàn)實(shí)表達(dá)。正如有學(xué)者認(rèn)識(shí)到的,“中國(guó)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為文學(xué)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jī)遇,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反映和揭示這個(gè)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為作家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天地。文學(xué)應(yīng)該有充分理由說出它對(duì)當(dāng)代中國(guó)的理解和表達(dá),建構(gòu)一種歷史性的文學(xué)想象和敘述”[1]。文學(xué)不能“與大地的苦難擦肩而過”,現(xiàn)實(shí)主義作為一種精神姿態(tài)和敘事方式自古便活躍在中國(guó)文學(xué)血脈之中,構(gòu)成了中國(guó)文學(xué)的“風(fēng)骨”。作為一位深具現(xiàn)實(shí)情結(jié)的作家,自1996年發(fā)表第一部長(zhǎng)篇小說《曾在天涯》以來,閻真共創(chuàng)作了四部長(zhǎng)篇小說。當(dāng)把這四部小說放在一起考察時(shí)可以發(fā)現(xiàn),閻真一直在對(duì)20世紀(jì)90年代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密切關(guān)注和深度審視,而且這種關(guān)注和審視,顯示出一個(gè)作家獨(dú)特的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賦予了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以新的世紀(jì)姿態(tài)和藝術(shù)表達(dá)。
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來說,“世界到底是一個(gè)什么樣子”應(yīng)該是作家面向現(xiàn)實(shí)發(fā)言時(shí)需要廓清的首要問題。因此,可以說,現(xiàn)實(shí)主義首先是一種思維方式,然后才是一種文學(xué)手段。然而,回眸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歷程便可以發(fā)現(xiàn),它承擔(dān)了大多道德訓(xùn)誡的說教任務(wù),添加了太多政治教科書的內(nèi)容。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這種小說“不是再現(xiàn)現(xiàn)實(shí),更不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力求精確的復(fù)制。同樣,它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構(gòu)成對(duì)歷史的直接記敘”[2]。為了道德“拔高”,現(xiàn)實(shí)在這里已經(jīng)“走樣”,偏離了“真實(shí)”。特別是在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主導(dǎo)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十七年時(shí)期”,那些以“宏大敘事”表達(dá)階級(jí)意識(shí)的所謂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讓人感覺更像是浪漫主義文學(xué)。閻真的小說選擇了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創(chuàng)造路向,但他在作品中不摻雜半點(diǎn)道德“水分”,僅僅是把小說當(dāng)作一種“敘事”,真切地呈現(xiàn)世界的本來面目。正如米蘭·昆德拉所指出的:“小說家既非歷史學(xué)家,又非預(yù)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3]56閻真醉心于對(duì)存在的勘探和發(fā)現(xiàn),特別可貴的是,他的小說在表達(dá)“世界的真實(shí)樣子”的同時(shí),更是“不得不從看得見的行動(dòng)世界中掉過頭,去關(guān)注看不見的內(nèi)心生活”[3]31。從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進(jìn)入心理現(xiàn)實(shí),表現(xiàn)出一種“內(nèi)向性”,成為閻真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的一種獨(dú)特文學(xué)方式和藝術(shù)氣質(zhì)。正如榮格所說的:“一切直接經(jīng)驗(yàn)都是心理經(jīng)驗(yàn),因而直接的現(xiàn)實(shí)只能是心理的現(xiàn)實(shí)。”[4]這種現(xiàn)實(shí)主義敘事路線是閻真小說一個(gè)普遍的藝術(shù)特征。這顯然與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另一種影響巨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新寫實(shí)”小說,有著明顯的差異。“新寫實(shí)”小說追求以“零度情感”進(jìn)行“世相描摹”,從而放棄了作家對(duì)于世界的情感體驗(yàn)表達(dá),同時(shí)也拒絕了精神探尋,小說中幾乎不表達(dá)和反思終極價(jià)值。這種敘事姿態(tài)恰好走向了“宏大敘事”的反面,激情淡出,關(guān)懷退場(chǎng)。與“新寫實(shí)”小說一樣,閻真的小說寫的也是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與“新寫實(shí)”小說“小事小說”的語調(diào)和方式不同,閻真小說中的“小事”是“以小見大”,是“大事小說”。正是從這些“小事”之中,照見出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中國(guó)社會(huì)的變局。雖然也是“激情淡出”,但這些“小事”卻逼迫人們不得不對(duì)“存在”進(jìn)行反思和質(zhì)詢,對(duì)“自我”進(jìn)行沉思和追問。這無疑又使閻真的小說仍然具有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的精神深度。
二
世界到底是什么樣子?這是閻真小說所著力探究和描摹的地方。在消費(fèi)主義大潮中,在市場(chǎng)的“神龕”上,世界越來越簡(jiǎn)單,也越來越殘酷。閻真從多個(gè)視角和層面表達(dá)了對(duì)這種現(xiàn)象的憂思。這仿佛是一場(chǎng)全球性的危機(jī)、世界性的難題,也是世紀(jì)性錯(cuò)誤。對(duì)西方的“想象”和向往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zhēng)打開國(guó)門以來便一直成為國(guó)人的精神事實(shí)。然而,在《曾在天涯》中,高力偉所面對(duì)的“西方”卻是另外一樣更加真實(shí)的天地。在這里,“這是商業(yè)社會(huì),除了錢有溫度,燙手,其它都是冷冰冰的”[5]461,高力偉“一踏上這塊土地那模糊的目標(biāo)馬上鮮明急切起來:賺錢”[5]14。“名和利會(huì)像木偶后面的提線人,用蒼白的雙手操縱了人世間的一切。”[5]126西方世界的世俗化和對(duì)金錢的迷戀似乎比東方世界走得更早、更快。留學(xué)生們開始認(rèn)為:“事業(yè)是什么,說到底不就是活得好點(diǎn)嗎?活得好不就是錢嗎?”[5]64為了錢,高力偉放下人格尊嚴(yán),騙獎(jiǎng)學(xué)金,發(fā)豆芽賣錢,到餐館洗碗,可謂不擇手段瘋狂追求。在一種秩序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高力偉“沒料到在加拿大自己變成了錢迷”[5]171。把5萬塊錢的目標(biāo),當(dāng)成了“神圣的召喚”,“生命變成了追求數(shù)字的游戲”,錢成了高力偉“與這個(gè)社會(huì)的唯一聯(lián)系”。這讓高力偉感到了痛苦,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看到了世界的殘酷和荒誕。他努力掙扎,最終,高力偉感到“這個(gè)世界不是為我這樣的人安排的”[5]460,終于強(qiáng)烈地要回國(guó),覺得“盼望回國(guó)比兩年多前盼望出國(guó)更加熱切”[5]344。連讓人羨慕的綠卡和刻骨銘心的愛情也不要了,回國(guó)成了最明確和強(qiáng)烈的要求。
高力偉終于回國(guó)了,當(dāng)閻真將關(guān)切的鏡頭切換到國(guó)內(nèi),高力偉換成了池大為,我們看到,中國(guó)的世俗文化景觀同樣觸目驚心。這個(gè)世界功利主義甚囂塵上。傳統(tǒng)文化在這里遭到毀滅性顛覆,官場(chǎng)潛規(guī)則大行其道,權(quán)力意志逼人就范,享樂主義、個(gè)人主義高奏凱歌。小說中池大為感到了驚慌,“世界變了,一切都顛倒了”[6]179,無奈哀嘆道:“權(quán)和錢,這是世界的主宰,是怎么也繞不過去的硬道理。”[6]179面對(duì)世俗化大潮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巨型話語,知識(shí)分子只能繳械投降,“世界在變,它不是哪一點(diǎn),它是一個(gè)系統(tǒng)工程,所以對(duì)抗它是沒有意義的”[6]205。池大為身不由己地陷入官場(chǎng)之中,在這里,官場(chǎng)文化以其“潛規(guī)則”控制著整個(gè)社會(huì)政治運(yùn)行,并造成了人的“異化”和人格的矮化。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矛盾成了橫亙?cè)诔卮鬄槊媲耙粋€(gè)巨大障礙。他發(fā)現(xiàn):“這個(gè)世界呀,宣傳的時(shí)候講道理,操作起來講功利,會(huì)上講道理,會(huì)后講功利,沒錢沒權(quán)的人到哪里都免開尊口。”[6]282世界是如此的光怪陸離,他明白:“這是一個(gè)操作的年代,操作的過程非常繁復(fù),動(dòng)機(jī)卻很單純。操作的目標(biāo)就是要讓別人出局自己入局,最后出局的就是那些弱者。”“操作只講結(jié)果,而不能講原則講公正,也不能講人格講良心。”[6]320池大為最終放棄了人格堅(jiān)守,投身到污濁的現(xiàn)實(shí)中同流合污,他終于得到了世俗中的各種好處,得到世俗世界的認(rèn)同。“我看透了這個(gè)世界在用怎樣的眼光看人,我沒辦法!沒辦法怎么辦?這一輩子就算了?人能有兩輩子嗎?世事如此,我也只能如此。”[6]281他似乎獲得了一種無奈但堅(jiān)硬的理由。他高升之后確認(rèn)了自己的高升“離開了權(quán)和錢就根本不可能發(fā)生”[6]326。你只能變壞,才能被認(rèn)可和獲得成功,這似乎是一種運(yùn)行邏輯。曾經(jīng)的“烏托邦”被解構(gòu)了,世界露出了它的猙獰面目。
有人說,一個(gè)社會(huì)最不應(yīng)該腐敗的領(lǐng)域是醫(yī)療和教育系統(tǒng)。但《滄浪之水》和《活著之上》則分別直指這兩個(gè)領(lǐng)域的亂象。假如說閻真通過池大為的人生經(jīng)歷呈現(xiàn)了世紀(jì)末中國(guó)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tǒng)“真實(shí)的樣子”,那么在《活著之上》中聶致遠(yuǎn)的高校生活以及通過他自己和趙平平串起的中學(xué)、小學(xué)生活則讓人們看到了中國(guó)教育系統(tǒng)在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的混亂而荒誕狀態(tài)。而它們共同的歷史語境則是商品經(jīng)濟(jì)時(shí)代新的價(jià)值準(zhǔn)則。小說中寫道:“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前提,就是承認(rèn)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追求那個(gè)的合理性。這是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巨型話語,它如水銀瀉地,以自身的邏輯即功利主義,在很大程度上統(tǒng)攝了我們的價(jià)值觀,對(duì)精神的價(jià)值發(fā)出了嚴(yán)峻的挑戰(zhàn)。”[7]125于是,小說中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成了一種裝點(diǎn),“活動(dòng)”才是關(guān)鍵:“坐在家里搞學(xué)問就成了大師,那個(gè)時(shí)代已經(jīng)過去了。”[7]59“象牙塔”同樣陷入對(duì)金錢的迷戀之中,“每天應(yīng)該想著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錢了。錢,錢,錢。錢這個(gè)東西決定了我……這個(gè)事實(shí)沒有討論的余地”[7]279。人們?cè)僖膊活櫠Y義廉恥:“這個(gè)世界的生存哲學(xué),全部的要義就是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要‘搞到’,手段是無需計(jì)較的。”[7]70因?yàn)樗麄兿嘈牛骸笆虑閬砹耍愀鷦e人說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都沒有用,只有票子這個(gè)‘子’才是真正管用的子。”[7]113他們理由看起來似乎十分正當(dāng):“錢和權(quán),這是時(shí)代的巨型話語,它們不動(dòng)聲色,但都堅(jiān)定地展示著自身那巨輪般的力量。我能螳臂當(dāng)車嗎?”[7]224
伴隨著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世界露出了它殘酷的一面,權(quán)力和金錢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重要標(biāo)準(zhǔn),它使過去幾千年所形成的倫理道德和價(jià)值認(rèn)同變得曖昧。“世界翻轉(zhuǎn)過來了,從世界看個(gè)人的時(shí)代一去不復(fù)返了。”[6]408而理由似乎十分正當(dāng):“我們?cè)谑兰o(jì)之交遭遇了相對(duì)主義,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變成一種說法,一種含糊其詞模棱兩可的說法……歷史決定了我們是必然的庸人,別無選擇。”[6]407
三
世界的殘酷不只是男人的殘酷,它同時(shí)也是女人的悲慘。假如說在《曾在天涯》《滄浪之水》《活著之上》中,閻真讓人們主要從男性生存的一面看到“世界的真相”,那么《因?yàn)榕恕穭t讓人們從性別的另一面看到了同處一個(gè)“穹頂之下”的女性生存的艱難。消費(fèi)社會(huì)來臨了,女性解放了,她們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目標(biāo)和職業(yè)前景,社會(huì)看起來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寬容。但金錢社會(huì)使欲望被充分調(diào)動(dòng)起來,然而“講欲望講身體,女人必然是輸家,因?yàn)榍啻翰粫?huì)永久”[8]352。欲望社會(huì)的思維方式使女人變?yōu)槟腥说囊环N消費(fèi)品,因此,“在這個(gè)年代,你不年輕不漂亮,那不但是有錯(cuò),簡(jiǎn)直就是有罪”[8]3。這顯然又導(dǎo)致了另外一個(gè)“世紀(jì)性錯(cuò)誤”:“欲望優(yōu)先,這是一個(gè)世紀(jì)性的錯(cuò)誤,也是一個(gè)世界性的錯(cuò)誤。”[8]352社會(huì)的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進(jìn)步以及女權(quán)主義運(yùn)動(dòng)并沒有使女性實(shí)現(xiàn)真正的“身體解放”,身體的解放使她們陷入另一種身體的“陷阱”之中。愛情作為一種信仰,一直以來都是女性的人生主題,這種美好也一直在文學(xué)中得到表現(xiàn),成為文學(xué)的一個(gè)母題。但是,隨著消費(fèi)社會(huì)的來臨,女人的這一信仰同樣遭到了顛覆。正如小說中寫道的:“女人的悲劇就在于在一個(gè)欲望的時(shí)代向往愛情。”[8]157因?yàn)椤笆袌?chǎng)使愛情功利,自由使愛情淺薄”[8] 261,“愛作為女人的生命主題真的已經(jīng)發(fā)生歷史性改變”,“我們已經(jīng)來到一個(gè)重新定義愛情的時(shí)代”[8]342。男人的欲望似乎仍然主導(dǎo)了女人,而女人只能用盡金錢來與時(shí)間抗?fàn)帲珪r(shí)間是殘忍的,誰也不能阻止它的前行。在這個(gè)社會(huì)中女性生存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場(chǎng)敗局。柳依依曾經(jīng)也信仰愛情,但在《因?yàn)榕恕分校S著故事的展開,她越來越不相信愛情了,甚至在女人那里,愛情也逐漸變成了欲望,她不但性生活隨意,做了“小三”,而且竟然也忍不住想去找一個(gè)“自己有感覺的男人”,這就是現(xiàn)實(shí),這就是這個(gè)時(shí)代女性的真實(shí)生存圖景。從一個(gè)純情少女,到成長(zhǎng)為一位曠世怨婦,一個(gè)女人開始不再相信愛情,因?yàn)樗谶@樣一個(gè)“欲望優(yōu)先”的消費(fèi)時(shí)代找不到一位與他談情說愛的人了。一個(gè)女孩,她“對(duì)男人的絕望其實(shí)就是對(duì)世界的絕望”[8]89,她“對(duì)愛情的灰心,其實(shí)就是對(duì)世界的灰心”[8]32。小說中的柳依依從此絕望了,生活由此呈現(xiàn)出一種敗相。
《因?yàn)榕恕肥菑那閻鄣囊暯牵憩F(xiàn)出一位女性對(duì)于世界的絕望。然而在閻真的其他小說中,可以看到幾位幾乎同為小說主角的女性形象,比如《曾在天涯》中的林思文、《滄浪之水》中的董柳、《活著之上》中的趙平平,她們本為社會(huì)的“弱者”,她們也以愛情的名義與高力偉、池大為、聶致遠(yuǎn)走在了一起,但她們似乎都越來越不相信愛情,而糾纏于俗世中的權(quán)與錢。正如小說中寫道的,“這個(gè)社會(huì)愛情姓錢,現(xiàn)實(shí)得很”[5]321。她們開始變得“不談愛情”,生活中的她們更多的是教導(dǎo)和逼迫她們的男人“活在這個(gè)世界上只能按達(dá)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說自己想怎么做”[5]90。這些女人在小說中都比她們的男人更早和更加世俗化,她們更真切更敏感地意識(shí)到權(quán)和錢的魅力,于是以生存的理由,以自我為中心,強(qiáng)令她們的男人降下精神的旗幟,唆使他們墜入對(duì)金錢的追逐中。而這也是從女性的視角——從一個(gè)單純、弱小、美麗的群體——表現(xiàn)出這個(gè)世界“不再天真”。
不得不承認(rèn),在閻真的四部小說中,小說主人公幾乎都是“一個(gè)人在戰(zhàn)斗”,高力偉、池大為、聶致遠(yuǎn)他們?cè)谛≌f中往往處于勢(shì)單力敵的狀況,他們?cè)谏钪猩踔炼颊也坏叫撵`傾訴的對(duì)象,而只能獨(dú)自躲在角落里咀嚼自己的內(nèi)心苦痛,時(shí)時(shí)陷入與自己對(duì)話的心靈苦悶之中。他們是這個(gè)世界最后的知識(shí)分子,歷史似乎要在他們這里“另起一頁(yè)”。這是最后的掙扎。在小說中,除了女人放棄了掙扎,一個(gè)更大的群體正招搖“襲來”,他們與俗世共舞,毫不感到別扭。在《曾在天涯》中,畢竟回國(guó)的只有一個(gè)高力偉,甚至他的朋友們還賭下一桌酒席,堅(jiān)信他還會(huì)回來。而在《滄浪之水》中,小孔、小魏、小龔、小蔡,他們已經(jīng)順應(yīng)了這個(gè)時(shí)代,他們對(duì)權(quán)力的順從不再如池大為般拘束、猶疑和苦痛,他們自然而然地融入俗世,正如小說中寫道的,“市場(chǎng)是現(xiàn)世主義的課堂,它時(shí)刻在教育人們”[6]490。在他們看來,這種對(duì)俗世的遷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不值得糾結(jié),而糾結(jié)是愚蠢的、可笑的。相似的邏輯同樣出現(xiàn)在《活著之上》中,聶致遠(yuǎn)的學(xué)生范曉敏、馬濱、武斌、劉沙他們,同樣表現(xiàn)出對(duì)這個(gè)世界規(guī)則操作的熟練。而更有意味的是,閻真的小說幾乎都設(shè)置了一組甚至多組人物關(guān)系,如高力偉與林思文、池大為與丁小槐、池大為與任志強(qiáng)、柳依依與苗小慧、聶致遠(yuǎn)與蒙天舒等,這些人物關(guān)系是作為對(duì)比性的存在被布局在文本中的,他們各自代表了人生選擇和行動(dòng)的兩極。在這里,堅(jiān)守與屈服、抗拒與順應(yīng)、成功與失敗、尊嚴(yán)與屈辱、義與利等二元命題既在各自的平面展開,又互相糾纏、沖撞、對(duì)峙。現(xiàn)實(shí)的復(fù)雜性和豐富性在閻真的筆下得以生動(dòng)呈現(xiàn)。
從西方到東方,從男人到女人,一種世界性的難題、整體性的危機(jī)、無性別差異的人類共同的生存困境,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時(shí)代成為世紀(jì)之交一個(gè)共同的景觀。權(quán)和錢的“魔戒”效應(yīng),使人性的丑惡不斷放大。“天使在哭泣,魔鬼在狂笑”的精神局面恍如世紀(jì)之交的現(xiàn)實(shí)圖景。世界注定在這里拐彎,歷史必將在這里改寫。閻真對(duì)世界的這樣一種表達(dá)方式,讓人生出一種絕望。
四
知識(shí)分子被視為社會(huì)的良心,他們處在人類精神的前沿。在這樣一個(gè)社會(huì)轉(zhuǎn)型、文化“裂變”的時(shí)代,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選擇及其靈魂處境最能反映這個(gè)時(shí)代的道德標(biāo)高。一個(gè)突出的特征是,閻真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有著知識(shí)分子的身份。這是閻真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創(chuàng)作路向中對(duì)一個(gè)群體的特別觀照和靈魂審視。可以這樣說,一個(gè)時(shí)代的危機(jī)就是知識(shí)分子的危機(jī),而知識(shí)分子的危機(jī)也就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危機(jī)。
“我們”該怎么辦?這是閻真小說中的人物最焦灼、煎熬最深的精神苦痛。閻真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有著堂吉訶德似的精神理想,但與堂吉訶德帶有浪漫主義認(rèn)識(shí)不同的是,他們對(duì)混濁的現(xiàn)實(shí)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只不過由于“先在”的文化認(rèn)同,使他們難以適應(yīng)現(xiàn)實(shí)對(duì)他們的生存提出的種種難題。因此,高力偉、池大為、柳依依、聶致遠(yuǎn)們又有時(shí)呈現(xiàn)出魯迅筆下“孤獨(dú)者”的精神底色,在信仰和現(xiàn)實(shí)的雙重夾擊中,他們時(shí)時(shí)陷入左右為難、舉步維艱、進(jìn)退失措的兩難困局而無力自拔。他們仿佛陷入了“無物之陣”,面對(duì)整個(gè)秩序而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虛弱,無法與整個(gè)體制對(duì)抗,只能沉入自己的內(nèi)心悲嘆、自責(zé)。這樣一種寫作上的向內(nèi)“傾斜”,又使人們常常看到“零余者”對(duì)生命的詠嘆。在“世紀(jì)性的錯(cuò)誤”面前,世界是殘忍的。正如司湯達(dá)在《紅與黑》中寫道的:“在錯(cuò)誤面前,個(gè)體是那么渺小和無力。”閻真小說中的人物在現(xiàn)實(shí)逼迫面前,總是心情沉重地反問自己:“世界已經(jīng)走到這一步了,我們還認(rèn)什么真?”[6]205在現(xiàn)實(shí)逼迫中,人物要作出選擇,于是,高力偉選擇了“回國(guó)”,他還有權(quán)利、有機(jī)遇逃避一種生活方式對(duì)他的規(guī)約。然而在《滄浪之水》中,閻真對(duì)權(quán)利“霸權(quán)”作了一種無法抗拒的絕對(duì)性的理解。權(quán)利無可置疑地要求人對(duì)它順從,池大為最終被“規(guī)訓(xùn)”了。他說:“我越來越不相信這個(gè)世界了。”[6]403在他“功成名就”后,他反問道:“我有了今天,是公正在時(shí)間的路口等待嗎?”[6]342這似乎是放棄堅(jiān)守傳統(tǒng)價(jià)值觀一個(gè)不容置疑的巨大理由。也許,真如聶致遠(yuǎn)所言:“在市場(chǎng)之中,一個(gè)人的世俗化是多么合情合理啊。”[7]103“也許,凡俗就是這一代人的宿命。”“好好活著,活在當(dāng)下,一切與此無關(guān)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不必上心。這是生活給我們的啟示。”[7]309
知識(shí)分子群體繳械投降,最不應(yīng)該腐敗的中國(guó)醫(yī)療和教育系統(tǒng)腐敗叢生,消費(fèi)社會(huì)對(duì)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的解構(gòu),“精神的廢墟”已經(jīng)顯現(xiàn),世俗化潮流勢(shì)不可擋。按照閻真在小說中的敘事邏輯和表達(dá)的歷史趨向,悲劇已經(jīng)難以避免。“市場(chǎng)它是一種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又是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它消解了終極,消解了知識(shí)分子。”[7]405在世紀(jì)之交的精神荒原上,最后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終將隨風(fēng)飄逝。
五
尼采在 1882年出版的 《快樂的科學(xué)》 第三卷第125 節(jié)中講到:一個(gè)瘋子大白天打著燈籠 ,在市場(chǎng)上不停地叫喊 “我找上帝”, 正好那里聚集著許多不信上帝的人。于是, 這個(gè)瘋子闖入了人群中:“上帝去哪兒了?” 他大聲喊道,“我要對(duì)你們說!我們已經(jīng)殺死了他——你們和我!我們都是謀殺犯!”于是,上帝就被歷史性地宣告死亡。而在閻真的小說中,被宣告死亡的其實(shí)又何止只是上帝。“市場(chǎng)只承認(rèn)眼前的利益,不承認(rèn)萬古千秋,這就摧毀了全部的神圣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經(jīng)死去,在這一代人心中也已經(jīng)死去,因此我說知識(shí)分子也已經(jīng)死去。”[6]406“我說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卻也看到這是歷史的必然。”[6]407
不僅孔子被宣告死了,知識(shí)分子已經(jīng)死去,閻真在小說中還寫了池大為的父親死了,聶致遠(yuǎn)的爺爺死了。他們的死去,更多地隱喻著一種精神的熄滅。在中國(guó)這片古老的大地上,除了孔子,這里曾經(jīng)還出現(xiàn)過屈原,出現(xiàn)過司馬遷,出現(xiàn)過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文天祥、王陽明、曹雪芹、魯迅……如果說上帝是人們虛構(gòu)的精神幻象,那么這片土地上“生長(zhǎng)”出來的孔子、屈原、司馬遷等絕對(duì)就是精神的“實(shí)存”,幾千年來,這些文人志士身上體現(xiàn)出來的精神文化從來沒有斷絕過。然而,這種歷史中的“實(shí)存”卻也被今天的人們視為一種“幻象”,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guó)的大地上四處游蕩,他們無所敬畏,無所恐懼,肆無忌憚,將對(duì)權(quán)和錢的瘋狂追求視作生命的最終本質(zhì)和終極目標(biāo),將欲望的無限放大當(dāng)作生命存在的最終指向。照這樣的發(fā)展邏輯和心理趨勢(shì),人類是不是在走向一條“不歸路”,而上帝死了,孔子死了,屈原死了,司馬遷死了……“父親”死了,“爺爺”死了,在“上帝”、“圣人”、“先輩”一個(gè)接一個(gè)先后被宣布死亡,精神的“幻象”和精神的“實(shí)存”一概被今天的人們拒之門外、不予承認(rèn)和接受,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依托將最終失去可靠支撐,精神的“斷崖”必將導(dǎo)致人類精神走向死亡,人類從此成為這個(gè)世界沒有靈魂的漂浮物,正如閻真在小說中通過池大為之口表達(dá)的“中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失去了根基,他們解放了自己,卻陷入了萬劫不復(fù)的精神絕地”[6]409。如此,這片古老的土地也終將熄滅其綿延了幾千年的精神之火,從此“板結(jié)”,不再生長(zhǎng)“圣人”,不再傳播精神。由此前瞻,人類正步入深淵,在前頭招手的必將是大災(zāi)難、大消亡。
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詠嘆:“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而屈原在《楚辭·招魂》中也抒發(fā)了其“魂兮歸來”的精神隱痛和沉吟,表達(dá)了其對(duì)這片土地的深情和熱愛。閻真對(duì)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的“絕地”、“絕境”描寫,正如陶淵明對(duì)“田園將蕪”的悲嘆,其小說的價(jià)值也許在于它提供給正在世俗化浪潮中一路狂奔的人們一種精神警醒,通過吟唱“挽歌”的極端方式,提醒人們放慢腳步,“仰望星空”。正如閻真談到的:“我并不想以古代文化名人的名義,以精神價(jià)值的名義,否定物質(zhì)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也是否定不了的。我想說的是,在一種物質(zhì)化的生活氛圍中,人們是不是同時(shí)也要珍視精神的重量,給精神價(jià)值一定的空間?”[9]知識(shí)分子作為社會(huì)的精英,這個(gè)群體在這個(gè)時(shí)代遭遇到極大的挑戰(zhàn)和巨大的危機(jī),閻真通過其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將這種挑戰(zhàn)和危機(jī)暴露出來,其用意和價(jià)值顯然在于喚起人們重新思考在消費(fèi)時(shí)代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語境中知識(shí)分子應(yīng)該如何重鑄這一文化身份,擔(dān)負(fù)社會(huì)責(zé)任、文化使命,提升精神境界,以彌補(bǔ)欲望化時(shí)代日益嚴(yán)重的精神缺失。除了表達(dá)一種精神預(yù)警,閻真抑或通過四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為這個(gè)日漸空空蕩蕩的精神荒原呼喊著一種迷失掉了的魂魄。而這,卻也是這片土地自古就在頑強(qiáng)“生長(zhǎng)”的精神實(shí)存。自古以來,中國(guó)這片土地就是一塊多災(zāi)多難的土地。但是,只要精神不死,這片土地便注定興旺也必將興旺。今天,閻真以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筆觸,對(duì)這片土地表達(dá)了一種失望、一種悲觀,寫出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最后的掙扎,寫出了世俗文化在當(dāng)今時(shí)代的至高無上、暢通無阻的憂思。這顯然表達(dá)的是一種生存困境,這無疑也是當(dāng)下有識(shí)之士最為苦痛不已但同時(shí)又“回天乏力”的狀況,同時(shí)也是政治上層在大抓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時(shí)刻不忘強(qiáng)調(diào)實(shí)施“一手抓物質(zhì)文明建設(shè),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shè)”政治方針的癥結(jié)所在。2014年10月15日,習(xí)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強(qiáng)調(diào):“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yuǎn)健康向上、永遠(yuǎn)充滿希望。”習(xí)近平同時(shí)還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yǎng)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cè)谑澜缥幕な幹姓痉€(wěn)腳跟的堅(jiān)實(shí)根基。”[10]現(xiàn)實(shí)中的閻真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命運(yùn)及其危機(jī)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在一篇學(xué)術(shù)文章中,他寫道:“弘揚(yáng)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對(duì)今日中國(guó)而言,不是一個(gè)理論問題,學(xué)術(shù)問題,而是一種歷史要求,利益訴求,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fā)展要求。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在大國(guó)崛起進(jìn)程中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源泉,是國(guó)家軟實(shí)力的重要構(gòu)成,是中國(guó)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標(biāo)記,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礎(chǔ)。弘揚(yáng)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生存發(fā)展的必然歷史要求。”[11]可以發(fā)現(xiàn),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的學(xué)者閻真和從事小說寫作的作家閻真,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認(rèn)識(shí)是契合的。只不過,閻真的這種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創(chuàng)作路向的價(jià)值是從反向,甚至不惜以一種極端、片面、放大后果的表達(dá)方式,讓人們警醒,為大地喊魂。其作品喚起人們?cè)谛碌氖兰o(jì)和新的文化語境之中,通過借鑒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資源,完善這個(gè)時(shí)代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人格,真正重新找回那種傳統(tǒng)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氣魄,以此激活民族的精神血脈,重新張揚(yáng)民族的精神文化,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
[1]張伯存,盧衍鵬.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文學(xué)轉(zhuǎn)向與社會(huì)轉(zhuǎn)型研究[M].北京: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2014:3.
[2]格非.小說敘事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2:4.
[3]昆德拉.小說的藝術(shù)[M].董強(qiáng),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4]榮格.心理學(xué)與文學(xué)[M].馮川,蘇克,譯.南京:意林出版社,2014:17.
[5]閻真.曾在天涯[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
[6]閻真.滄浪之水[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1.
[7]閻真.活著之上[M].長(zhǎng)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
[8]閻真.因?yàn)榕薣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7.
[9]閻真.精神的重量[J].創(chuàng)作與評(píng)論,2013(4):5-8.
[10]習(xí)近平.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EB/OL].(2014-10-15)[2016-03-1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11]閻真.歷史要求: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命運(yùn)之逆轉(zhuǎn)[J].求索,2015(12):155-159.
2016-05-12
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2015年科研資助項(xiàng)目(XYS15S04)
鄭國(guó)友(1974-),男,講師;E-mail: zhengguoyou2003@126.com
1671-7031(2016)05-0105-06
I207.42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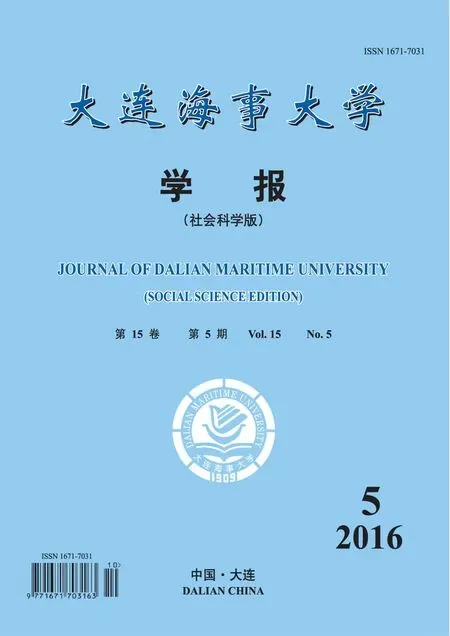 大連海事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5期
大連海事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5期
- 大連海事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語言服務(wù)行業(yè)視域下翻譯項(xiàng)目管理研究
- 跨文化語境政治演講中“自由”的話語建構(gòu)
——批評(píng)話語分析視角 - 政府背景風(fēng)險(xiǎn)投資對(duì)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績(jī)效的影響
- 英語動(dòng)詞時(shí)態(tài)的認(rèn)知研究
- 海事行業(yè)含元音字母英語縮寫詞和縮略語之英漢讀音規(guī)律
- 中國(guó)供給側(cè)改革下的財(cái)稅難點(diǎn)與政策建議
——基于協(xié)整檢驗(yàn)與ECM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