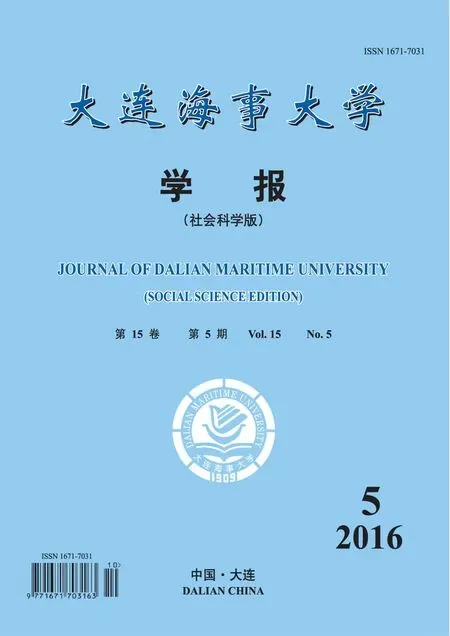論海子存在主義詩學觀之流變
萬孝獻
(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寧德分校,福建寧德 352100)
?
論海子存在主義詩學觀之流變
萬孝獻
(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寧德分校,福建寧德352100)
存在主義是以人的生存狀態、生命意義為前提的價值學說,關注的是人的生存及存在的根本問題。海子是詩歌領域存在主題的先行者,開創性地在現代漢語詩歌中引入神性維度,通過在實體與幻象中分別植入不同的神性因子,體驗在經驗與超驗兩種不同生存狀態中生命的意義與感受,試圖從中尋找生命的終極意義。他的方式和其他人都不同,但結論卻是相同的。他的詩歌創作是一個生命能量的消耗過程,當實體與幻象都無法證明存在價值時,詩人陷入徹底的絕望。
海子;存在主義;神性維度;實體;幻象
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開篇就說:“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其余的都是無足輕重的事情。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回答了這個問題等于回答了哲學的根本問題。”[1]面對存在的荒誕,人要避免自殺就必須要依靠某種可靠的價值信念來說服自己人生值得經歷。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關于自殺原因說法有多種,有的說直接的導火索是失戀,自殺前幾天海子因為在酒后說了關于初戀女友的話自責不已,導致了其輕生。也有的說是練氣功走火入魔,從遺書中可以看出其精神已崩潰。這些說法都不無道理,但其實都只是外在推力,真正的原因是他一直苦苦追尋的價值信念出了問題。閱讀海子的詩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詩人是如何從憧憬詩意與神性的生存一步步滑落到被存在的深淵吞噬的痛苦歷程,體驗到生命中那種不可承受之輕。詩人將自己生命價值的實現完全托付給了詩歌,并且用它來追問存在的意義與真相,不幸的是,生活最后依然還是只有茍且,詩和遠方背后站立的永遠是存在虛無的本質,發現之后的深刻絕望最終吞噬了詩人年輕的生命。
一、有神論存在主題的先行者
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是海子詩歌的核心問題。海子詩歌對存在的高度關注和當時流行于中國文壇的西方存在主義思潮有著直接的關系。存在主義是以人的生存狀態、生命意義為前提的價值學說,關注的是人的生存及存在的根本問題,它為異化狀態下的現代人指出了一條自由之路。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偶像破滅、價值重估的時代,以存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在與國家主流話語形態和新啟蒙話語形態的較量中事實上處于支配地位,在重塑青年人的價值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先鋒小說執著于表現存在的荒誕性,如劉索拉、徐星對生活無聊感的表現,余華對暴力、死亡的恐怖敘事,殘雪對人與人之間非理性關系的描述,都深入至所謂的“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的存在主題。
第三代詩歌對生命意識的張揚也是深受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生命意識是第三代詩歌的重要美學特征,主要由兩個方面構成,即對待“性”的態度和對待“死亡”的態度。第三代詩人普遍突破對性的禁錮與壓抑,在詩歌中大力張揚人類生命的原始本能,借此表達對生命的肯定。對待死亡的態度則有多種,認識到人對改變自己生命結局的無能為力,有的詩人采取無動于衷的態度,不對死亡追根究底,但也有的詩人對死亡采取歌頌甚至渴望的態度。“借肯定死亡來否定現實的生命,從人生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病態的、非理性的抉擇,但是如果從審美的角度來看,它又意味著對生命意識一個新的層面的拓展。”[2]海子無疑屬于后一類的詩人。海子是第三代詩人中“存在主題的先行者”[3],但他的詩歌寫作和別人截然不同。他從不涉及“性”的領域,關心的永遠是形而上的終極問題。他的詩歌寫作主要從有神論的角度對存在展開追問。
存在主題寫作,主要有有神論和無神論兩個向度。無神論者認為宗教與信仰是人類用來自欺和欺人的騙局,唯有揭穿與否定它,才能從精神上擺脫它,擁抱自由。有神論者認為,現代科技與理性精神只能解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不能解決人們的精神出路問題。唯有無形的、廣義的宗教,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的精神生活問題。無神論存在寫作因為存在意義的荒誕性一開始就陷入絕望,有神論者試圖跳出這種荒誕性,為生存尋找終極意義。這兩種主張,無論哪一種,研究的都是人的存在問題。海子的寫作是有神論的,他開創性地在現代漢語詩歌中引入神性維度,通過在實體與幻象中分別植入不同的神性因子,體驗在經驗與超驗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態中生命的意義與感受,試圖從中尋找生命的終極意義。無論是無神論還是有神論,別人仿佛生來就是絕望的,生命缺少發展與變化的軌跡,生硬而空洞。海子則不然,從早期的“尋找對實體的接觸”到后期的太陽史詩夢想,海子始終自覺以神性的光芒為存在去蔽。無論是麥地時期的短詩,還是太陽史詩時期的長詩,無不充滿著海子企圖窺視存在真相的渴望。
二、尋找對實體的接觸
“觸摸實體”是海子早期的詩歌選擇。長詩《河流》原序的標題就是“尋找對實體的接觸”。實體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首創的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也譯為本體,其含義一般是指能夠獨立存在的、作為一切屬性的基礎和萬物本源的東西。尋找對實體的接觸,目的就在于重返萬物的本源。海子認為土地和河流是最大的實體。土地是一種總體的關系,它包含、生產,像女人的身體一樣不可思議,而河流中則蘊含著寂靜而內含的東方精神。海子要通過它們,走向民族的心靈深處,為東方人的生存作證,為在塵世生活的靈魂唱歌。“當前,有一小批年輕的詩人開始走向我們民族的心靈深處,揭開黃色的皮膚,看一看古老的沉積著流水和暗紅色血塊的心臟,看一看河流的含沙量和沖擊力。我決心用自己的詩的方式加入這支隊伍。我希望能找到對土地和河流——這些巨大實體的觸摸方式。”[4]1017這種尋根意識明顯受到當時江河、楊煉等人首倡的文化史詩的影響。
如何通過實體來發現生存的秘密?海德格爾認為“存在是一個自身顯現、自身敞開、自身領悟的過程”[5]。傳統美學把人作為思維和實踐的主體,把物作為認識的客體,這種主客體分離的二元論構成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與對抗,打碎了人與世界的統一。海德格爾超越了這種二元論,從存在自身來理解藝術,認為“藝術就是真理在作品中的自行置入”[6],這種理論啟發了海子對存在的思考,“詩不是詩人的陳述。更多的時候是實體在傾訴”[4]1018。“詩應是一種主體和實體間面對面的解體和重新誕生。”[4]1017“實體永遠只能被表達,不能被創造。”[4]1018海子認為詩人的任務主要是聆聽實體的傾訴。早期長詩《河流》《傳說》《但是水,水》以及麥地組詩是這個階段的代表作。尤其是麥地主題詩歌,在中國新詩中首創性地引入神性維度,重建天地人神四維空間,呈現出和傳統詩歌不同的風貌。
神性維度是解讀海子詩歌的關鍵詞。這是一個來自西方的詩學概念。海德格爾認為人的居住擁有大地、天空、神圣者、短暫者,即天地人神四重性,但是這種完整性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喪失了。時代的貧乏不僅在于神的蹤跡無法確認,也不僅在于上帝之死,更在于短暫者幾乎不知道自己的短暫。海子從神性維度切入,展開對中國傳統文化及生存方式的思考,認為中國文人隱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把一切都變成趣味,蒼白孱弱,令人難以忍受。同樣是歸隱,梭羅通過歸隱來表達對生命和存在本身的珍惜和關注,陶淵明卻把歸隱變成個人的趣味。詩歌自新之路在于要拋棄這種文人趣味,直接關注生命本身。
從神性維度出發觀察存在的詩學理念主要受到荷爾德林的啟發。荷爾德林是德國浪漫派詩人,生活的時代(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工業化革命剛剛興起的時期,人類在漫長農耕時期形成的長期穩定的生活狀態受到工業文明的沖擊開始出現劇烈變化。荷爾德林敏感地發現了這一點,用詩歌進行反思,認為技術的白晝就是世界的黑夜,諸神的缺席不在于有沒有教堂和信仰,而在于諸神已經不再將人和物聚集于其自身,人處于被拋的狀態。人類要找回自己,只有重新返回神祇庇護的時代。詩人的使命在于自覺成為神的兒子,在暗夜中尋訪神的蹤跡。西方文學有悠久的宗教傳統和豐富的神話資源,本身就有神性維度。中國文學則不然,“子不語怪力亂神”,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學已經徹底世俗化,進則經世濟用,退則修身養性,已經完全失去了神性維度,海子要創造一個神性時空出來,不僅艱巨而且充滿危險。
實體世界的神性天空在哪里?“把宇宙當做一個神殿和一種秩序來愛。”[4]1071“做一個熱愛‘人類秘密’的詩人,這秘密既包括人獸之間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間的秘密。”[4]1071從神秘文化角度去觀察河流、土地等這些巨大的實體,把自己融入其中,從中發現一些傳統的二元認識論下發現不了的秘密,這是海子神性思維的方式。“麥地/別人看見你/覺得你溫暖,美麗/我則站在你痛苦質問的中心/被你灼傷”(《答復》)。以谷物和大地為主題的詩歌,傳統上都是歌頌勞動贊美大地,目的是凸顯人的偉大,人與自然其實是分離甚至對立的。海子的麥地詩歌打破了這種二元論,麥地作為一個神秘的質問者,拷問人類的心靈,麥子成為主體,人反而成為客體。質問之后,讓詩人覺得“詩人,你無力償還/麥地和光芒的情義”(《麥地與詩人》)。在這里,人和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一切不僅是平等的,而且人還要感恩自然的恩賜。人其實和大地孕育出來的谷物是一樣的,也只是一顆麥粒。從麥子的角度看世界,產生了不一樣的詩意,帶給人神圣的感覺。
生存的受難因為神性的附麗產生了詩意棲居的感覺,但這只是暫時的,畢竟物欲世界的丑陋無法靠這一層輕紗而得以掩飾。現代文明已使實體世界遍體鱗傷,幻想通過重構神性來重建文明史詩顯然已經不可能。神性思維還讓海子產生了宿命的思想,命運無可遁逃,只能逆來順受,即使有神的看護,人還是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這種無力感讓海子深感挫敗。從太陽史詩時期開始,海子詩風大變。“如果說我以前寫的是‘她’,人類之母,詩經中的‘伊人’,一種北方的土地和水,寂靜的勞作,那么,現在,我要寫‘他’,一個大男人,人類之父,我要寫楚辭中的‘東皇太一’,甚至奧義書中的‘大梵’,但歸根結底,他只是一個失敗的英雄,和我一樣。”[4]1034海子開始謀求將拯救之路掌握在自己手中,對存在萬物從仰視的姿態走向平視與審視,不愿再做四維結構中安靜的自然之子。
三、幻象的死亡是真正的死亡
幻象是對海子后期詩歌寫作對象的一個統稱。海子是個悲劇詩人,具有濃厚的悲劇意識。尼采認為,希臘悲劇之所以美,是因為它融合了日神與酒神兩種精神,日神精神代表著理智、冷靜的靜穆之美,酒神精神代表著旺盛的生命力,力與美的結合才誕生了悲劇這種最高的藝術形態。海子詩歌充斥著日神與酒神的沖突,就是這種悲劇精神的體現。日神精神體現為他精心構筑的農耕文明的詩意棲居之夢和在當代中國成就偉大史詩的夢想,酒神精神體現為日神幻滅之后的強力意志以及由醉入魔的狂躁狀態。當兩者完美結合的時候,他的詩歌華美而絢麗,如太陽史詩中最完整的作品《弒》,“在《弒》里,酒神精神的表達建基于對日神必要的敬意基礎之上。這也許是其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7]213。還有早期的麥地系列詩歌。但是當兩者分離,酒神殺死日神,陷入幻象式的生存方式之后,詩人開始分裂,內心深處的原始欲望開始主宰詩人的心靈。以詩歌的名義詩人頻繁發起暴動,妄圖一舉登上幻想中神授的詩歌王座。當發現最后都是一場虛無之后,徹底陷入絕望,存在最后的真相刺瞎了詩人的眼睛。
農耕文明的詩意棲居之夢是海子早期的詩歌理想,他創造性地引入西方的神性維度,反省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受現代文明的影響,農耕文明早已失去詩意棲居的可能。在土地、河流等實體中,海子發現更多是迫害力,而不是慰藉,是疾病,而不是收獲,家園的詩意面紗被詩人親手扯下。“過去的詩歌是永久的炊煙升起在親切的泥土上/如今的詩歌是饑餓的節奏”,“故鄉和家園是我們唯一的病 不治之癥啊/我們應乘一切酒精之馬情欲之馬一切閃電/離開這片果園/這條河流這座房舍這本詩集/快快離開故鄉跑得越遠越好!”
海子轉而謀求在當代中國創作一部偉大史詩,在他看來,詩歌的勝利已經足夠,只要詩歌之王的詩萬世長存,任何犧牲都不足惜。這種理想本身是日神性質的。現實中海子生活頗為潦倒,詩歌發表渠道并不順暢,“新浪漫主義”詩歌風格和長詩寫作方式在圈子內備受質疑,連最珍惜的初戀也失敗了,這些都讓他感覺自己是個多余的負擔,要改變命運唯有借助詩歌。日神精神幫助個體活在夢境世界中,實現對痛苦的超越。海子把全部的生命力都投入到史詩的創作中,但從寫作方式來看,表現出來的卻是酒神的迷狂狀態。
海子眼中的詩歌分為大詩和小詩,大詩就是他所說的史詩。他認為史詩中最偉大的是舊約、荷馬史詩、印度史詩,它們是人類早期的集體回憶。其次是一些浪漫主義王子如荷爾德林、普希金等人的創作。為了實現史詩夢想,詩人主體開始無限膨脹,由實體階段的通靈者逐步上升為人類集體命運的祭司、太陽神王子,直至太陽本身。早期那個克制、冷靜、擁有一定反省意識的詩人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躁動、迷狂的主體。海子先是引荷爾德林等浪漫主義詩歌王子為同類,將他們視為自己的孿生兄弟,認為自己也是神授的王子。短篇小說《神秘故事六篇》中的故事主人公都有一個神秘的身份,如《龜王》中的石匠、《木船》中的男孩,都是受上天的派遣來到人間,經歷無數苦難最終修成正果。這種關于詩人形象的描述,既包含東方的宿命觀念,也包含西方的天命神授觀念,兩者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海子關于詩人使命的特殊認識。海子認為浪漫主義詩歌王子來到人間的使命就是要用詩歌來尋找被隱匿、被遮蔽的存在真相,像荷爾德林一樣,在神圣的暗夜尋找神性的蹤跡。但是隨著實體世界的破碎,這種理想很快也被自己否決了。海子產生了要創作類似于荷馬史詩、印度史詩等這類代表著人類早期集體回憶的詩歌的想法,這些在他看來是屬于最高境界的詩歌。“人類經歷了個人巨匠的創造之手以后,是否又會在20世紀以后重回集體創造?”[4]1052海子自問自答,在他心目中,答案是肯定的,并且認為自己責無旁貸。他要做沙漠里的指路人,通過太陽史詩的幻象世界,“提高生存的深度與生存的深刻”[4]1052。幻象是真實的對立面,也是實體世界的對立面。既然在實體世界里,已經找不到存在的真實感,只能從它的對立面來尋找。
海子說“我要做第一個擦亮燈火的詩歌皇帝”,王者之夢的實現方式是營造一座多神共居的太陽神神殿,神殿里東西方神祇都有,但核心的神只有一個,就是太陽自身,實際上就是海子自己。他手握對蕓蕓眾生甚至眾神的生殺予奪大權,在類似于氣功的幻覺中成為一個自我感覺真實的王(海子沉迷氣功,每天除了寫詩就是練功,自言已開通小周天)。“你們要么成為我,要么成為我的奴隸”,這和他的實際生活形成極大反差。短時間內,詩人自我身份認同不斷提升,《斷頭篇》里化身為人類集體命運的祭司。《弒》中是命定的詩歌王子,《太陽·詩劇》中是擦亮詩歌燈火的皇帝。身份的變化說明海子已經開始不相信神,只相信自我和藝術。主體無限放大,自我成為一切的中心,不僅凌駕于自然之上,也凌駕于萬人之上。一方面透露出實體失敗后詩人內心的焦慮,另一方面也加重了詩歌整體的虛幻色彩。“太陽七部書”的抒情主體,都處于一種極度瘋狂的狀態,詩歌節奏迅疾,內容恍惚迷離。主體的狂躁與虛弱使海子喪失了對文本的控制力,很多作品都處于未完成狀態,殘稿斷章很多。
王者之夢主要靠強力意志來實現。尼采的超人說和強力意志在海子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王者之夢的驅使下,海子發現唯有忘掉日神的清規戒律,才能徹底進入忘我之境,體驗到生命的原始與本真,與世界融為一體。海子嗜酒,耽于氣功,這些外力也都在幫助他體驗生命之醉。海子后期大部分的作品都帶著明顯的酒神精神影響的蹤跡。酒神精神的力量源泉是各種非理性的本能之力,體現在詩歌內容上就是對暴力意象和暴力修辭的依賴。原始的本能之力包含性的放縱和對暴力的膜拜。海子相信純潔的愛情,性解放在那個年代也遠未到來,所以全部的原始性都向暴力方向泛濫。海子似乎把暴力當成了生命力本身,把破壞和毀滅等同于創造。在他的詩歌中,天空是血紅的,空中飛馳著各種殺人的兵器和被砍斷的殘肢斷臂。由暴力傾向還衍生出了濃厚的死亡情結和黑夜情結。語言上,狂歡化色彩濃厚。如《弒》中,運用了散文、童謠、民謠、自由詩、頌詩、啞劇、鬧劇等多種體裁和形式,俗語、成語、俚語、行話、黑話、官話等紛紛登場,互相交融在一起,把酒神式的狂喜成功地轉化為語言的狂歡。
詩歌氣質上,由原來如水的母性氣質轉為如火的父性氣質。實體階段的詩歌,“東方佛的真理不是新鮮而痛苦的征服,而是一種對話,一種人與萬物的永恒的包容與交流”[4]1025。總體呈現出靜謐、包容的氣質。到了幻象階段,暴烈的父性氣質壓倒一切,“我要把糧食和水、大地和愛情這匯集一切的青春統統投入太陽和火,讓它們沖突、戰斗、燃燒、混沌、盲目、殘忍甚至黑暗”[4]1032。“我要首先成為群龍之首,然后我要殺死這群龍之首,讓他進入更高的生命形式。”[4]1032太陽史詩的核心意象是火,是燃燒。火焰的中心是黑暗,是盲目,燃燒的背后是灰燼,是虛無。
詩歌空間上,由原來南方的河流、西部的黃土高原逐漸轉移到神秘的青藏高原,甚至印度、兩河流域。時間上,由現代文明轉向古代文明,甚至原始文明。“越遠的地方我越虔誠”,呈現出一個越蠻荒越好、越原始越好的特點,走上了一條與現代文明相背離的逆行之旅。
詩歌整體沿用的還是傳統的革命思維方式,“在一個衰竭實利的時代,我要為英雄主義作證”[4]1035。在崇高使命的旗幟下,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打倒、屠殺。生命的戰爭無處不在,不是和對手的戰爭,就是和自己的戰爭。殺人如麻、虐己成癖,革命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烏托邦式的人神共居的神殿。人借此擺脫被設定的命運,得以永生,存在由此轉變荒謬的處境而獲得意義。在這種思維模式中,人已不再是自然的產物,而成為主人,和自然萬物也不是對等的關系,而是它們命運的主宰者,人自然就變成了神。這和實體階段的神性思維是不一樣的。這種對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的思考,和啟蒙時代以來對人的主體性認識是相同的,盲目自信,妄自尊大,割裂了與自然萬物的平衡關系,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更深層次的迷失。
四、生命不可承受之輕
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對存在的認識主要有三方面:存在先于本質、存在是自由的、存在是荒謬的。海子的存在之思和薩特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對存在是否先于本質的認識,其余兩點是一致的。對存在認識的出發點不同,探索與追問的內容不同,得出的結論卻一致,甚至更為絕望,這一點頗讓人深思。
存在先于本質是薩特存在主義第一原理。薩特認為存在分為兩種:自在的存在和自為的存在。世界是自在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純屬偶然。人是自為的存在,人出生時無所謂善惡好壞,任何內容也沒有,究竟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完全是后天決定的。因為人的存在,外部世界才獲得意義。人的個體差異也造就了存在的繽紛萬象。人是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志來創造世界的,而不是按照神的授意,薩特推翻了有神論關于上帝按照自己概念造人的說法,認為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上帝造人,人的本質就必然先于人的存在。薩特也否定了普遍人性的存在,認為人性論是有神論的殘余。以薩特為代表的這種觀點,否定上帝,否定普遍人性,使人類在精神上自由得無所適從,這種“輕”是人的生命所不能承受的。
在對人的主體性認識上,海子和薩特有著明顯的區別。薩特認為人到這個世界純屬偶然,海子則不然,依然秉持那個時代特有的英雄敘事情結,認為作為一個詩人,在這神圣的暗夜,使命就是要拯救人類的靈魂。海子詩歌的一切出發點,都是從詩人的這種神圣使命感出發,從這種主體定位來說,是本質先于存在。海子認為可以通過詩歌搭建起一座通向存在的神性之思的橋梁。詩歌有著天然的語言通道,它的飛躍能力能夠使那些在哲學和邏輯中都無從言說的東西獲得神妙的自明。這是一種完全個人化的寫作,用個人性的價值和私人化的敘事實現對傳統詩歌的背叛與超越。這和當時的先鋒文學精神是一致的。
存在的本質如此悲觀,自為存在的人如何拯救?薩特從悲觀的深層本質中引出了樂觀的行動,樹立積極入世的世界觀,讓個體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在薩特看來,人的本質不是上帝賦予的,也不是環境決定的,而是在人的“自由選擇”、自我創造的過程中不斷獲得的。只有自由選擇、自我創造、敢于沖破環境束縛的人才會有真正的“存在”。存在即自由。在人被判定是自由的認識上,海子的態度很矛盾。一方面,海子相信“自由選擇”,太陽史詩中,他的身份認同不斷變化,從通靈者到命運祭司再到詩歌王子最后到王,即是其不斷自由選擇的結果,但另一方面他認為,無論如何選擇,最終都擺脫不了命運的安排。“永恒輪回”是世間萬物的集體命運。這一點上,海子受到尼采和中國傳統宿命論的雙重影響。從永恒輪回的角度來說,自由選擇其實是無用的,無論如何選擇,最終的結果都是早已注定的,就像人之必死一樣,無論過程如何精彩,到死神降臨的時候,一切都將毫無意義。
存在主義通過各種形式得出存在是荒謬的、他人即地獄等結論。海子的方式和其他人都不同,但結論卻是相同的。實體階段,詩人初窺存在的秘密,通過神性維度使沒落的農耕文明在現代社會重煥生機,但詩人覺得這秘密只是存在真相的一小部分,而且在現代文明的語境下,存在早已失去了原來的本真狀態。虛構出來的詩意棲居的生活是不真實的,要找回生命的本真,唯有退回到更為原始、更為遙遠的狩獵時代,返回文明的源頭才有可能。這是一種文明的逆行之旅,具有鮮明的反現代性特征。體現在海子詩歌中,就是越原始越好,越遙遠越好。“海子的原始崇拜最終把原初和原始變成了價值的來源。”[7]239原始力量成為主體力量。海子認為,更高等級的秘密是人和神之間的秘密,它關系到命運、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等,只有獲悉這些秘密之后,存在的真相才能被徹底揭開。在這種思想引導下,海子拋棄了實體,將目光投向象征更高等級秘密的“宇宙的神殿”。
在現實中海子是一個封閉性的人格,和其他詩人不同,對現實中發生的、正在進行中的歷史視而不見,同時也拒絕世界走向他。這種自我封閉、拒絕成長的性格也直接導致其自我膨脹,他對主體的各種自我期許正是源于此。但一旦遭遇現實的擠壓,又極易在相反的方向引發自我貶損與放逐。他的原始主義是對現在的逃避,遠方膜拜是對此在的逃避。海子早期的原始主義傾向還含有一些理性的成分,在向文明源頭的追溯中發現了神性的和諧之美,但在接觸尼采后他的詩歌開始從和平母親轉向原始母親,反理性的立場成為一種自覺。“古典理性主義攜帶一把盲目的斧子,在失明狀態下斫砍生命之樹。”[4]1039他在《詩學:一份提綱》中這樣說。海子詩歌拒絕接納現實,其實是對現代文明代表的理性文化的恐懼,認為理性文化是對人的生命力的抑制。
要體驗生命之美,尼采的方式是夢與醉的結合。日神的克制、靜觀、勿過度的要求使人回避生存的真實。藝術之美的追求也是對人生意義的一種逃避。但尼采認為只有日神是不夠的,酒神的迷醉才能讓我們與內心深處的原始力量,以及宇宙的神秘本質合二為一,體驗到生命的狂喜。只有將兩者完美結合,這樣的藝術或人生才是完美的。海子早期是“以夢為馬”的日神性質的詩人,但到后期完全蛻變為“以醉為馬”的酒神性質的詩人,無法將兩者融合為一體,是其走向絕望的主要原因。由醉入魔也證明了詩人主體的虛弱。虛弱的根源在于對存在虛無本質的無限恐懼。海子對生命與存在終極意義的追尋,早期充滿信心,繼而苦悶、懷疑,最后瘋狂、絕望。在徹底絕望之前,他內心經歷了多場曲折而慘烈的戰爭。這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熾熱的心靈與虛無世界之間的戰爭,就像魯迅《野草》中的戰士,陷入無物之陣,最后的勝者卻是無物之物。
主體的虛弱導致了詩人對文本控制能力的喪失,出現了碎片化的現象,以及對暴力修辭的依賴,最后只能走向死亡。海子肯定死亡,認為死亡不是毀滅和深淵,而是幫助生命脫離苦難,在另一時空獲得永生。這種對死亡的贊美態度,其實是對自己的安慰,但所有妄圖借戰勝死亡來延續生命的努力都是無效的,注定失敗。存在最終的結果如果擺脫不了虛無的結局,所有的價值追求都將失去重量。幻象破滅后必然陷入深深的絕望。如果不愿茍活,像日神藝術家一樣,用藝術來安慰人生,就只有擁抱死神這條路了。
“存在主義注重研究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處境。因此,文學在它那里也具有更多的‘人學’特征。帶有存在主義特點的作家和以往的或一般別的作家的一個明顯區別是,他不再把創作當作單獨的功利追求或審美游戲,而是當作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或者說生命能量消耗的一個過程。這類作家對存在有一種深切體驗。他們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力作都是從內心深處發出的呼叫、呻吟、歡唱、傾訴……不管是痛苦的,歡欣的,狂怒的,抒情的。里爾克就是屬于這樣的作家。”[8]里爾克是這樣的詩人,海子也是這樣的詩人,在深刻性上比里爾克走得更遠。詩歌既是他個人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他用來求證生命價值的實驗,當實體與幻象、經驗與超驗都無法證明存在價值的時候,只有用毅然決然的死亡方式為人生之虛無劃上最后一個句號了。
[1]加繆.西西弗斯神話[M].閻正坤,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1.
[2]溫宗軍.論第三代詩歌的生命意識[J].湛江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4):73.
[3]張清華.在幻象和流放中創造了偉大的詩歌[M]//崔衛平.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172.
[4]西川.海子詩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5]海德格爾.詩 語言 思[M].彭富春,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2.
[6]海德格爾.林中路[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50.
[7]西渡.壯烈風景——駱一禾海子比較論[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2.
[8]葉延芳.永不枯竭的話題——里爾克藝術隨想錄[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3.
2016-05-20
福建廣播電視大學2014年科研課題(KY14064)
萬孝獻(1969-)男,副教授;E-mail: 365029397@qq.com
1671-7031(2016)05-0111-07
I207.2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