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 ———近年來(lái)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趨勢(shì)掃描
劉 大 先
流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 ———近年來(lái)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趨勢(shì)掃描
劉 大 先
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回歸是近幾年來(lái)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突出特征,通過(guò)對(duì)當(dāng)下少數(shù)民族小說(shuō)、詩(shī)歌、散文的掃描,我們發(fā)現(xiàn)回歸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既包含19世紀(jì)經(jīng)典現(xiàn)實(shí)主義手法,也有著自然主義書(shū)寫(xiě),更有吸收了先鋒文學(xué)營(yíng)養(yǎng)的日常寫(xiě)作,更涵蓋了以“真實(shí)性”為旨?xì)w的非虛構(gòu)寫(xiě)作,這種現(xiàn)實(shí)主義是因應(yīng)現(xiàn)實(shí)而不斷以不同面貌呈現(xiàn)的“流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盡管在當(dāng)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中,現(xiàn)實(shí)主義及其不同變體取得了一定的實(shí)績(jī),但存在著平面化、狹隘化和窄化的風(fēng)險(xiǎn),需要結(jié)合盧卡契的總體性與布萊希特的現(xiàn)實(shí)感,倡導(dǎo)一種全面、立體、完整地呈現(xiàn)、再現(xiàn)與表現(xiàn)的創(chuàng)作自覺(jué)。
無(wú)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平面化;自動(dòng)寫(xiě)作;素樸的詩(shī);非虛構(gòu)
作者劉大先,男,漢族,安徽六安人,文學(xué)博士,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民族文學(xué)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 100732)。
正如羅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1913~2012)所說(shuō):“一切真正的藝術(shù)品都表現(xiàn)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種形式”,因而“沒(méi)有非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即不參照在它之外并獨(dú)立于它的現(xiàn)實(shí)的藝術(shù)”[1]P171。現(xiàn)實(shí)主義作為一種特定方法和觀念,源于18世紀(jì)的德國(guó)與法國(guó)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在19世紀(jì)成熟并達(dá)至其美學(xué)意義上的頂峰并延至20世紀(jì),經(jīng)過(guò)司湯達(dá)、巴爾扎克、福樓拜到托爾斯泰、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由寫(xiě)實(shí)主義到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再到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它自身獲得了歷史性的發(fā)展與演變,但總體而言都建基于作家主體對(duì)外部世界的摹寫(xiě)、提煉與洞察之上。這種歷史變遷之中蘊(yùn)含的意味是:現(xiàn)實(shí)主義不僅是方法論,也是世界觀,它始終包含了客觀認(rèn)識(shí)與主觀創(chuàng)造的結(jié)合,而不是脫離實(shí)際的臆想與獨(dú)斷。在特定的時(shí)代與社會(huì)中,現(xiàn)實(shí)主義總是作家、藝術(shù)家用一個(gè)民族的語(yǔ)言與方式表達(dá)具體生產(chǎn)條件、生活方式、制度體系中最為核心的思想觀點(diǎn)、現(xiàn)實(shí)狀態(tài)和未來(lái)趨勢(shì)。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最重要的一脈,現(xiàn)實(shí)主義也體現(xiàn)在新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歷次潮流之中,無(wú)論從早期的“為人生”、革命文學(xué)、革命英雄傳奇、社會(huì)主義創(chuàng)業(yè)史,還是到80年代具有啟蒙精神的各種文學(xué)思潮,以及90年代的新寫(xiě)實(shí)主義甚至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的探索之中,它們可能在形式、語(yǔ)言、風(fēng)格、技法上各有不同,但總是貫穿著現(xiàn)實(shí)的精神。新世紀(jì)以來(lái)隨著“純文學(xué)”與先鋒文藝的落幕,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回歸”成為近年來(lái)現(xiàn)象型的事件。
這種回歸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是一種“流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即它可能既包含現(xiàn)實(shí)主義經(jīng)典定義所界說(shuō)的特質(zhì),也涵括了那些被后來(lái)的文學(xué)批評(píng)者稱(chēng)之為現(xiàn)代主義或后現(xiàn)代主義式的寫(xiě)作。本文以2015年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為中心,結(jié)合近些年來(lái)相關(guān)作品的掃描,期望對(duì)此種趨勢(shì)進(jìn)行概括,以裨補(bǔ)整個(gè)中國(guó)當(dāng)下文學(xué)現(xiàn)場(chǎng)的觀察,立此存照。
一、平面現(xiàn)實(shí)主義
所謂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回歸,并不是說(shuō)它一度消失,而是呈現(xiàn)形式有別于經(jīng)典的19世紀(jì)現(xiàn)實(shí)主義手法。此類(lèi)手法其實(shí)一直是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流,無(wú)論是現(xiàn)實(shí)題材還是歷史題材,只是在更注重形式求新求變的“新時(shí)期”以來(lái),被批評(píng)家和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者有意淡化。但現(xiàn)實(shí)主義有著巨大的自我更新的能力,我們可以看到新世紀(jì)以來(lái)的“回歸”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也已經(jīng)不同于原先印象中已經(jīng)較為定型的形象。一個(gè)世紀(jì)以來(lái)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到當(dāng)代文學(xué)諸多立場(chǎng)、理論、流派、潮流已經(jīng)改造了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筆法,九卷本葉廣芩(滿族)文集最典型的體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無(wú)論是《采桑子》、《全家福》、《青木川》、《狀元媒》等主要以京城家族史和地方史為主題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還是以現(xiàn)實(shí)生活為對(duì)象的《黃連厚樸》、《山鬼木客》等中短篇小說(shuō)集,還是《老縣城》、《琢玉記》等散文集,葉廣芩都以一種抒情化的現(xiàn)實(shí)筆法呈現(xiàn)出來(lái),將個(gè)體與社會(huì)連接起來(lái),通過(guò)人物與特定環(huán)境的鋪寫(xiě)描摹,形成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比照性敘事。顯然她已經(jīng)不再試圖塑造一個(gè)能夠涵括時(shí)代精神的典型人物,而是平視地展示,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表現(xiàn)為:一、細(xì)致逼真的描摹。葉廣芩的作品,大多涉及北京地方的民風(fēng)民俗尤其是滿族家庭的各種生活習(xí)慣、禮儀制度等等。她對(duì)旗人貴族的那一套禮儀、習(xí)俗,描寫(xiě)細(xì)致,于中把玩品味,并有一種流連和忘情。閑筆式的細(xì)節(jié)描寫(xiě)作為一種藝術(shù)表達(dá)的需要,有時(shí)候因其精雕細(xì)刻而帶有民俗學(xué)的文獻(xiàn)意義和認(rèn)識(shí)價(jià)值。比如對(duì)貴族的繁文縟節(jié)的描寫(xiě),使她的作品不僅豐滿真實(shí),并且可以幫助人們了解當(dāng)時(shí)的特定社會(huì)生活實(shí)況。這些知識(shí)在客觀上體現(xiàn)了作家深厚的文化修養(yǎng)。二、真摯自然的風(fēng)格。葉廣芩的作品風(fēng)格真摯自然,凝重老辣,頗見(jiàn)工夫,語(yǔ)言尤其幽默與優(yōu)美并重,這是典型的旗人文化修養(yǎng)沉淀下來(lái)的結(jié)果。更重要的是葉廣芩的作品以“真實(shí)”為生命基調(diào)的散文化特質(zhì),是對(duì)古典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一種當(dāng)下變革。三、對(duì)于族群氣質(zhì)秉性冷靜考察達(dá)到人性的深度。葉廣芩的小說(shuō),如同她自己坦言的:“其中自然有不少我的情感和我的生活的東西”[2],許多是以自己的家族興衰和親朋故舊作為原型,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跟現(xiàn)實(shí)生活可以相互對(duì)照。其敘述格局采取的是一種否定的敘述視角,抱著冷靜而又溫情的態(tài)度,有分寸地打開(kāi)班駁陸離的往事與現(xiàn)實(shí)之門(mén),上演貴族家庭和其一群末世子弟的故事。石玉賜(侗族)的《逃漢》也是歷史題材,講述的是紅六軍團(tuán)在長(zhǎng)征過(guò)程中在黔東的錦屏縣路過(guò)一個(gè)叫高壩的侗寨,逃漢石金果參加紅軍并獻(xiàn)計(jì)立功的故事。“逃漢”是對(duì)高壩方言“蹇嘎”的翻譯。因?yàn)榇说匾恢遍]塞愚昧,那個(gè)時(shí)候侗族自稱(chēng)“臘更”,而稱(chēng)呼苗漢同胞為“臘嘎”。歷史上“臘更”落后,遇到強(qiáng)盜或戰(zhàn)亂只有逃匿。紅軍到來(lái)時(shí),村民不明究里,誤信國(guó)民黨關(guān)于“赤匪”的謠傳,所以很多人就逃入深山躲藏。從恐懼懷疑到加入紅軍,勝利到達(dá)延安,石金果經(jīng)歷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認(rèn)識(shí)到“我們不可能連國(guó)家都不要”[3]P138。在個(gè)人融入集體的洪流之中,邊緣少數(shù)民族與主導(dǎo)性意識(shí)形態(tài)之間形成了溝通和融合,這也是絕大多數(shù)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普遍書(shū)寫(xiě)模式。
同為散淡的敘事,石舒清(回族)的小說(shuō)則加強(qiáng)了主體自身的反思與感悟。他淡化情節(jié)和人物性格而刻意營(yíng)造一種舒緩的“講故事”式的松散筆法,幾乎都是通過(guò)敘述人“我”的講述與回憶,以及與情節(jié)內(nèi)部人物之間的對(duì)話構(gòu)成,從而形成一種言說(shuō)的閉合圈,這樣就使他的小說(shuō)有一種敘述者自我反芻的色彩。在涉及到宗教信仰題材的作品中,這種特點(diǎn)尤為明顯。比如《灰袍子》里寫(xiě)到三個(gè)與信仰有關(guān)的人物,我的叔叔、村里面的一個(gè)老人以及努爾舅爺?shù)钠瑪嘟?jīng)歷與言詞,他們之間并沒(méi)有特殊的聯(lián)系,而是通過(guò)對(duì)宗教、信仰以及迷信的態(tài)度,將他們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充滿了內(nèi)部的對(duì)話和比照,從而使得小說(shuō)顯得哲思悠長(zhǎng)。這是一種外在型的講述,很少描寫(xiě)與刻畫(huà),敘述人是一個(gè)耽于外部的觀察者,因而形成了一種間離效果,敦促讀者像作者一樣進(jìn)入到對(duì)平常事物的體味和感悟之中。《韭菜坪》寫(xiě)的就是“我”在韭菜坪拱北住的幾天經(jīng)歷、觀看、體會(huì)以及反思的內(nèi)容。“我”已經(jīng)是世俗化了的教徒,所以并沒(méi)有以一個(gè)伊斯蘭教的局內(nèi)人去進(jìn)行描繪,而是采取了與外來(lái)旅行者、普通游客類(lèi)似的觀察視角,有種與普通讀者的貼近性。因?yàn)檫@個(gè)觀察者有著優(yōu)裕紆徐的時(shí)間和空間去反思,因而他的句子往往精雕細(xì)鑿,并且時(shí)有充滿靈性與機(jī)智的想法蹦出。《賀家堡》通過(guò)楊萬(wàn)山老人和他兒子之間對(duì)于將小孫子出散到拱北去的不同態(tài)度,可以看出民間日常中復(fù)雜的宗教態(tài)度,顯示了世俗化時(shí)代的信仰景觀。
無(wú)論在零散的故事,還是在寫(xiě)法上,石舒清世俗生活題材的作品都更多體現(xiàn)了日常化的特點(diǎn),但又不同于九十年代盛行一時(shí)的凡庸“新寫(xiě)實(shí)主義”,而可以稱(chēng)之為“抒情現(xiàn)實(shí)主義”。《果院》里的心理描寫(xiě)堪比“新感覺(jué)派”,耶爾古拜的女人在年輕男人剪果枝時(shí)候的春心萌動(dòng)細(xì)致入微。《遺物》里面寫(xiě)到二爺家的姨奶奶,一個(gè)沒(méi)有子嗣的寡婦的平凡人生,她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道德觀和倫理觀,體現(xiàn)了自尊又自卑的鄉(xiāng)土中國(guó)婦女代表性的形象。《黃昏》里通過(guò)姑舅爺?shù)倪€錢(qián)和克里木的借錢(qián),折射出時(shí)代變遷當(dāng)中道德、信譽(yù)和情義的變遷,也正暗示了姨奶奶、姑舅爺這代人彌足珍貴品質(zhì)的逝去。《尕嘴女人》中寫(xiě)到尕嘴女人對(duì)患有老年癡呆癥的母親的愛(ài)恨交織,在自責(zé)與怨恨中的自我反思,并沒(méi)有過(guò)于高蹈的超脫性,而就是蕓蕓眾生所面臨的常見(jiàn)情感處境,卻于平淡中見(jiàn)出愛(ài)的聯(lián)系與傳承。《遷徙》也是一個(gè)小品式的小說(shuō),寫(xiě)到爾薩爸與大舅爺從新疆到寧夏的來(lái)回遷徙,情節(jié)平淡,其中透露出的許多敘述者的議論倒值得一提。比如他寫(xiě)道:“有時(shí)候甚至可以說(shuō)人是活在不同的世上,但終歸是同一個(gè)世界。終歸都是人在活著。回村里的時(shí)候,村里人眼神已有些變化,好像我已是一個(gè)客人。他們觀察并探究著,要是我顯得熱情他們就很熱情。我覺(jué)得村子的老舊,就像一壇子腌菜,多少年來(lái)也是那個(gè)味道。其實(shí)村子是變化了不少的,只是在外面游逛的人不容易看出來(lái)。當(dāng)看到兩個(gè)年輕、健碩的女人騎了摩托車(chē)由村巷里一掠而過(guò);看到一個(gè)除草的人突然停住勞動(dòng),取出別在腰里的手機(jī)嗚嗚哇哇講著時(shí),心里還是很有些異樣的。但同時(shí)就看到高天下面的塬上,幾只烏鴉在緩緩盤(pán)旋,忽然的一個(gè)俯沖,像被什么擊中似的掉到塬下面去,你就覺(jué)得眼前情景,真是和兒時(shí)所見(jiàn)沒(méi)有兩樣”。[4]P102在這樣的文字當(dāng)中可以看到,時(shí)代的變遷與更久遠(yuǎn)、永恒的自然山川相比,凸現(xiàn)出人在轉(zhuǎn)型時(shí)代的存在感。《眼喜歡》寫(xiě)幾個(gè)揀枸杞子女人之間的閑話,那些家長(zhǎng)里短、人間細(xì)碎,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村莊的聲調(diào)、速度、氣息,既傷感又無(wú)奈,也有著對(duì)生命的達(dá)觀,令人不禁想起另一位“農(nóng)民哲學(xué)家”劉亮程的風(fēng)格——就是在村莊里、在最普通平凡的人們的閑話中,發(fā)現(xiàn)一些頗具哲理意味的鄉(xiāng)土智慧。《阿舍》寫(xiě)的是“我”家十幾歲的保姆的生活,她的生活當(dāng)然也只是“我”零碎的觀察與猜測(cè),顯示出濃郁的中年況味。《二爺》中畢業(yè)于蘭州大學(xué)歷史系的二爺,曾經(jīng)在固原地區(qū)法院工作,又被打成右派,命運(yùn)顛簸起伏,又成為廚師,最后給人糊頂棚為生,直到最后平反。但是無(wú)論什么樣的生活處境和態(tài)度,他都保持了一種處變不驚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不僅是回族,也是中國(guó)最廣泛民眾樂(lè)天知命或者說(shuō)在艱難時(shí)世中的無(wú)奈選擇。《低保》是一個(gè)非常有意思的小說(shuō),老鴉村村長(zhǎng)王國(guó)才需要平整果園,通過(guò)吃低保的人們和希望吃低保的人們的不同反應(yīng),王爪爪、王尖頭、呱啦啦、馬建文、脫書(shū)記、王國(guó)才的漫畫(huà)式群像,顯示出基層鄉(xiāng)村里面的微觀政治,而對(duì)權(quán)力的毛細(xì)血管及其背后更為宏大的體制與結(jié)構(gòu)進(jìn)行反思。
在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似乎無(wú)力進(jìn)行復(fù)雜結(jié)構(gòu)的處理,往往都是一種筆記式的寫(xiě)法。這種散文化的小說(shuō)從正面而言滲透著“修辭立其誠(chéng)”的真實(shí)感,從反面而言則失之于清淺。石舒清的小說(shuō)就像一個(gè)百無(wú)聊賴(lài)的中年人在閑適的午后說(shuō)閑話,已經(jīng)沒(méi)有了“為賦新詞強(qiáng)說(shuō)愁”的矯情,也沒(méi)有“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的歡快,這些是少年心性;當(dāng)然他更沒(méi)有“僵臥孤村不自哀”的凄涼,或者“死去元知萬(wàn)事空”的絕望,那是老年人的心境:他用那不疾不徐的語(yǔ)調(diào)講述村巷閑談和家族往事,其中浸潤(rùn)著一種心事濃如酒卻又逐漸趨向于達(dá)觀和平靜的態(tài)度。因而他的小說(shuō)就有一種自然天成的氣質(zhì),有時(shí)候甚至顯得有些絮叨,但正是在這些細(xì)密、瑣碎甚至無(wú)聊的講述中,顯示出了鄉(xiāng)土中國(guó)的日常生活的肌理。這些故事就是一些家長(zhǎng)里短,人物顯得面目模糊,卻給人一種地老天荒的感覺(jué),仿佛那是亙古不變的人間常道。這種感覺(jué)來(lái)自于他那舒緩從容的講述語(yǔ)調(diào),但更重要的是一種非性格式、非典型性的散點(diǎn)敘事——它們不是被虛構(gòu)和創(chuàng)造出來(lái),而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每個(gè)人所經(jīng)歷的家長(zhǎng)里短、飛短流長(zhǎng)和驚艷傳奇。石舒清是個(gè)很好的觀察者,比如他在一個(gè)短篇小說(shuō)《剪掉的嘴》當(dāng)中寫(xiě)到母雞抱窩,其細(xì)致入微簡(jiǎn)直堪稱(chēng)文學(xué)史上少有的華彩段落。更多的時(shí)候他很少進(jìn)行描繪性的刻畫(huà),而更傾向于平淡地講述,人物的性格、外貌、服飾等都被模糊化,他要傳達(dá)的是一種人生況味,比如《果核——記鄰村的幾個(gè)人》里面寫(xiě)到的望天子、懶漢、啞巴、大姑父,《雜拌》里面寫(xiě)到的陳太太、小朋友、爺爺、祖太太、太太、太爺、父親,這些小人物的生活史、家族史構(gòu)成了一個(gè)微觀村莊史,與大時(shí)代遙相呼應(yīng),在漫長(zhǎng)而又起伏變幻的人生經(jīng)歷當(dāng)中體現(xiàn)出一種變中不變的人生厚道,構(gòu)成了一個(gè)微觀的中國(guó)現(xiàn)代史,但這個(gè)現(xiàn)代史并沒(méi)有傳達(dá)出任何一種史觀,而是一種抒情式的人生體驗(yàn)。
人生體驗(yàn)的書(shū)寫(xiě)賦予了經(jīng)驗(yàn)以共情的可能。馬金蓮(回族)《賽麥的院子》從兒童的視角,寫(xiě)出了消逝的童真和希望的幻滅,以其密實(shí)的生活質(zhì)感和強(qiáng)烈的性別意識(shí),令人印象深刻。《念書(shū)》則有著強(qiáng)烈的自敘傳色彩,12歲的“我”到北山回民小學(xué)念書(shū)的苦難經(jīng)歷,沒(méi)有親身體驗(yàn)很難寫(xiě)出那種殘酷中的自我成長(zhǎng):“12歲的日子過(guò)得緊繃繃的,干澀,枯燥,又孤獨(dú),矜持。”[5]P86這種寫(xiě)青春期的小說(shuō)與時(shí)尚中流行的“青春文學(xué)”做比較,有著令人恍如隔世、判若鴻溝的感覺(jué)。其可貴之處正在這里,這些艱苦的青春是“中國(guó)故事”的另一種側(cè)面,其中有著底層少年的掙扎和冉阿讓般的道德命題。《柳葉哨》里困境中的少女梅梅每天都陷入繁重不堪的勞動(dòng)之中,又被饑餓所折磨,鄰居少年馬仁的念經(jīng)聲和他的微笑,是這種陰郁悲慘青春中的一縷難得的陽(yáng)光。這是一個(gè)少女成長(zhǎng)的心靈史,烙下了時(shí)代的背景,最后少女朦朧的愛(ài)情在時(shí)空與身份的隔閡中漸行漸遠(yuǎn)。在必然性與惆悵當(dāng)中,少女的人生經(jīng)驗(yàn)貫通了所有人的人生經(jīng)驗(yàn),因而這個(gè)童年記憶就超越了故事本身,而具有了普遍的人類(lèi)性。《暗傷》寫(xiě)的是父與子之間幾十年的愛(ài)恨交織,直到父親的死亡,父親才獲得最終的安寧和兒子最終的救贖。最終,兒子的心頭也安靜下來(lái):“他想,交給時(shí)間吧,就像過(guò)去這幾十年里經(jīng)歷的一樣,隨著時(shí)間推移,所有的傷口都會(huì)痊愈,包括那些長(zhǎng)久以來(lái)難以彌合的暗傷。”
馬金蓮的作品,以樸實(shí)自然的敘述風(fēng)格,細(xì)膩單純的藝術(shù)手法,生動(dòng)地展現(xiàn)了西北地區(qū)的鄉(xiāng)村故事,揭示了現(xiàn)實(shí)的沉重和命運(yùn)的無(wú)常。在書(shū)寫(xiě)特有的生命體驗(yàn)和文化記憶、生存、成長(zhǎng)、蛻變以及對(duì)人性的觀照時(shí),她的小說(shuō)形成了三個(gè)突出的特點(diǎn):第一、兒童視角的自敘傳,孩童從懵懂無(wú)知到明白事理的過(guò)程,就像太陽(yáng)升起,光芒逐漸驅(qū)散早晨的濃霧,袒露出清白而復(fù)雜的大地景色,因而這樣的小說(shuō)總是帶有成長(zhǎng)小說(shuō)的意味。第二、性別意識(shí)的不自覺(jué)的流露,比如在《賽麥的院子》里寫(xiě)到的那個(gè)生了七個(gè)女兒的悲苦的母親,《念書(shū)》中在學(xué)校里經(jīng)歷月經(jīng)初潮的女孩那種惶恐的心理,《鮮花與蛇》里懷孕少婦的微妙的心理悸動(dòng)。她以一個(gè)女性作家細(xì)膩的經(jīng)驗(yàn)與體驗(yàn),書(shū)寫(xiě)出為很多男性作家所忽略的女性那幽暗曲折的生理與心理過(guò)程。第三、細(xì)致而富有質(zhì)感的底層生活日常描寫(xiě),充滿了種種真實(shí)可信的細(xì)節(ji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關(guān)于饑餓和勞累的辛苦的精雕細(xì)刻。她的小說(shuō)就像在西北貧瘠山地上生長(zhǎng)著的豌豆花,清新、流麗又有著堅(jiān)韌而頑強(qiáng)的內(nèi)在生命力。這是一種經(jīng)驗(yàn)性的寫(xiě)作,作家依靠著厚著密實(shí)的人生經(jīng)歷,以樸素而直觀的文字娓娓道來(lái),因而獲得了接地氣的感人力量。但是這樣的寫(xiě)作缺點(diǎn)也是明顯的,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作家的個(gè)人經(jīng)歷寫(xiě)完了之后,她如何進(jìn)一步開(kāi)掘自己的寫(xiě)作潛力,她如何從一種個(gè)性的經(jīng)驗(yàn)諸如親情、友誼、村莊、信仰中超越出來(lái),使這種獨(dú)特性獲得它的普遍性。在這條道路上,馬金蓮還有很長(zhǎng)的路要走。
與上述諸位的“自敘傳”式小說(shuō)不同的是,虛構(gòu)性寫(xiě)實(shí)所帶有的旁觀者理性色彩。木妮(回族)的小說(shuō)以都市女性的家庭與情感生活為核心,而常常涉及到死亡。《花兒與少年》通過(guò)一個(gè)懵懂的賣(mài)書(shū)少年的眼光切入,進(jìn)入到一個(gè)他無(wú)法理解、不可詮釋?zhuān)部赡苡肋h(yuǎn)沒(méi)有答案的秘密當(dāng)中。那個(gè)自始至終沒(méi)有透露出姓名與身份的神秘女人自殺的原因,她經(jīng)歷了什么,她背后的故事和人生,一切都隱藏在都市的喧囂與雜亂當(dāng)中。《雙魚(yú)星座》則是一個(gè)啼笑皆非的網(wǎng)戀故事,因?yàn)殛幉铌?yáng)錯(cuò)的誤會(huì),自視甚高的女教師潘朵拉與陌生網(wǎng)友發(fā)生了一夜情。當(dāng)他們彼此都發(fā)現(xiàn)這一點(diǎn)的時(shí)候,出現(xiàn)了詭異的一幕:男人在網(wǎng)上建立的刻骨銘心甚至自己都以為可以克服外表、身份等世俗差距的愛(ài)情,在遇到這個(gè)美艷而又知書(shū)達(dá)理的女人后迅速瓦解。即便在兩人去開(kāi)房的路上他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真相,卻也沒(méi)有揭破;蒙在鼓里的潘朵拉也同樣,第二天在知道真相后,對(duì)在網(wǎng)上苦心經(jīng)營(yíng)的情感也產(chǎn)生懷疑,因?yàn)樗查_(kāi)始喜歡這個(gè)男人,但是她還要裝模作樣地離開(kāi),“其實(shí)他不知道,雙魚(yú)星座是天下最柔軟的星座。只要他再叫聲朵拉,朵拉”[6]P159。這個(gè)結(jié)尾相當(dāng)有力地揭示了當(dāng)代情感最為深刻也最為淺薄的一面。《愛(ài)人同志》將都市愛(ài)情當(dāng)中冷漠、理性、蒼白的一面推到了極致。舒拉與格恩兩個(gè)相戀十年、結(jié)婚六年、分居二年的“愛(ài)人同志”,“既不愿打破一個(gè)舊世界也不愿建立一個(gè)新世界”,以名義上的夫妻身份生活在一起,又各自有著性愛(ài)對(duì)象與情感生活。這種非常規(guī)的婚姻與家庭形態(tài),顯示了當(dāng)代社會(huì)中情感結(jié)構(gòu)的重大變革。這些都市中的男女都是患有世紀(jì)末頹廢式的懈怠癥人物,軟弱而又自閉,都沒(méi)有建立其自己的主體性,而在輕糜的時(shí)風(fēng)中載浮載沉。倒是《彼岸燈火》中的女電臺(tái)主持人獲得了精神上的成長(zhǎng):她在發(fā)現(xiàn)丈夫出軌之后,準(zhǔn)備自殺過(guò)程中的一系列心理活動(dòng)與行動(dòng),逐漸讓自己擺脫了情感的狹隘桎梏。在這個(gè)從憤怒、怨恨、憂愁,到沉思、解脫的過(guò)程當(dāng)中,女人獲得了自己的精神上的重生,重新建立其自主的主體性。
曹海英(回族)的小說(shuō)同樣聚焦于城市里的家庭與情感故事,但題材更為開(kāi)闊與豐富。《半杯水》當(dāng)中,馬杰與李小紅進(jìn)入婚姻疲倦期的中年心態(tài),在一地雞毛的生活狀態(tài)中面臨著蠢蠢欲動(dòng)的誘惑。小說(shuō)在馬杰接到仰慕自己的女實(shí)習(xí)生的短信后戛然而止:“馬杰看著短信,張了張嘴,卻什么也沒(méi)說(shuō)。心里面突然虛飄飄的,好像有一縷煙,就在他的面前,但他只能遠(yuǎn)遠(yuǎn)地看著。一伸手,就算了。”[7]P14這個(gè)結(jié)尾預(yù)示了多種可能性,而很大的可能是他會(huì)重復(fù)李小紅父親的出軌覆轍,這也正應(yīng)和了“半杯水”的寓意。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國(guó)無(wú)政府主義者那里,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guò)“杯水主義”的理論,其實(shí)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指摒棄了傳統(tǒng)女性應(yīng)有的道德觀,追求性的享受,在生理需要的情況下,與人發(fā)生性關(guān)系,就如口渴了就應(yīng)該喝水一樣,是應(yīng)該得以滿足,而且很平常的一件事。但“半杯水”恰恰表明了這些當(dāng)代都市人的尷尬、糾結(jié)與不徹底。《忙音》則關(guān)注城市里空巢老人的心理與情感狀態(tài),老人接到一個(gè)兒童誤打進(jìn)來(lái)的電話,亦真亦幻,體現(xiàn)了一種喧囂中的刻骨孤獨(dú)。《私生活》則是以貓咪的角度,以寵物的遭遇暗喻了人受困而又沒(méi)有出路的境遇。馬麗華(回族)對(duì)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令人印象深刻。《浪花》寫(xiě)底層女性在艱辛日常中與丈夫的患難相恤。《筏子客的女人》可以視為其姊妹篇,進(jìn)一步凸顯了女性自我欲望的覺(jué)醒和情義觀念的信守,而最終不得不在命運(yùn)之前走向了輪回式的人生困境。《風(fēng)之浴》別有不同,寫(xiě)?yīng)氉缘奖本で笮律畹膹V播電臺(tái)主持人司葉的“北漂”生涯,這個(gè)小說(shuō)有著更為強(qiáng)烈和明確的女性共同體意識(shí)。司葉是由單身養(yǎng)母教養(yǎng)成人,在漂泊中時(shí)時(shí)有著探曉身世秘密的愿望——她在自己主持的節(jié)目影像里自己的形象中想象母親的形象,正是一種女性尋找自我主體的隱喻。而主任徐麗君同樣是一位獨(dú)立自強(qiáng)的女性,在司葉遭受挫折的時(shí)候給予鼓勵(lì)與支持:“兩個(gè)人一起站在陽(yáng)臺(tái)上看遠(yuǎn)處。這時(shí)看去,景物全變了,變得像模型。這一種凌空俯視的視野,給人一種傲視一切也藐視一切的感覺(jué)”[8]P17。木妮、曹海英和馬麗華,顯示了回族文學(xué)在鄉(xiāng)土題材之外都市題材開(kāi)掘的極大空間,她們更多局限在個(gè)人的情感與個(gè)體之內(nèi),但也顯示了向更廣領(lǐng)域開(kāi)拓的可能,尤其是性別自覺(jué)維度的發(fā)掘有著極大的發(fā)展空間。
了一容(東鄉(xiāng)族)的小說(shuō)顯示了他掌控多樣題材的能力。《命途》通過(guò)一個(gè)年輕人和撒拉族老頭,在青海路途中的遭遇,通過(guò)抽象化的極端情境與意象象征了人性內(nèi)在的自我掙扎與搏斗,正如小說(shuō)所要表達(dá)的主題:“在生命的旅途中人的信念是壓不垮的”[9]P4。《立木》則是一個(gè)充滿民俗風(fēng)情韻味的小說(shuō),對(duì)上房梁和檁木的鄉(xiāng)村習(xí)俗進(jìn)行了饒有趣味的描寫(xiě)。《襤褸王》是一篇寓言化的小說(shuō),老實(shí)巴交甚至有些愚昧的村民尕細(xì)目,在青年勞教所的兒子出獄的時(shí)候,因?yàn)樾偶舆t的緣故,趕到水城監(jiān)獄卻沒(méi)有接到。漂泊在水城的尕細(xì)目受盡冷漠,像乞丐一樣流浪回家,一路上飽受饑餓、歧視甚至毆打的苦楚,而在村里也沒(méi)有人把他當(dāng)人看。這是一個(gè)觸目驚心的悲慘世界,苦難像揮之不去的霧霾,一層一層籠罩著這個(gè)可憐的底層人。“尕細(xì)目這樣的農(nóng)民在水村確乎有一大批,他們的內(nèi)心與靈魂多是復(fù)雜的,難說(shuō)清的,也可以說(shuō)是扭曲了的。他們的內(nèi)心和靈魂一直在一種奔突中進(jìn)行較量,尋找平和寧?kù)o的理由。他們的復(fù)雜在于平時(shí)看起來(lái)顯得低三下四和自我作賤卑微的樣子,甚至是無(wú)限的忍耐和順從有余。但是他們的內(nèi)心和靈魂里卻暗暗隱藏著一種激情,甚至是一種強(qiáng)大而熾熱的激情,這就像是引燃的木炭或者地火,外表上總是覆蓋著一層灰燼,但里面卻熾烈的暗地燃著,一旦突然的爆發(fā),就會(huì)令你感到震驚和匪夷所思,乃至覺(jué)得后悔得不可收拾。” 不出所料,尕細(xì)目最終走向了無(wú)可挽回的境地,將村主任一家全部殺死。小說(shuō)成功地塑造了一種讓人忍無(wú)可忍的絕望處境,并在這種極端的情境當(dāng)中細(xì)致入微地刻畫(huà)了犯罪的發(fā)生學(xué)。正如在小說(shuō)的結(jié)尾,作者借尕細(xì)目妻子的哥哥感嘆道:“人活著就是為了呼吸,呼是為了出這一口氣,吸——卻是為了爭(zhēng)這口氣啊!”小說(shuō)在批判現(xiàn)實(shí)之外,更有一層現(xiàn)實(shí)關(guān)注,那就是對(duì)于底層宗教信仰的探討,正如馬克思所說(shuō)“宗教是被壓迫眾生的嘆息,是無(wú)情世界的感情,同樣也是精神喪失狀態(tài)中的精神。它是人民的鴉片。”[10]P4尕細(xì)目正是到了走投無(wú)路的時(shí)候,在他人即地獄般的場(chǎng)景當(dāng)中,只能投向宗教的懷抱,而最終導(dǎo)向了一個(gè)不可避免的悲慘結(jié)局。小說(shuō)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在于,提醒了我們一種社會(huì)的暴力、戾氣和極端行動(dòng)的起源。
《紅山羊》以兒童的眼見(jiàn)證了金錢(qián)給世道人心所帶來(lái)的變化:“這世道,就連我這么個(gè)涉世未深的娃娃,竟也這么喜歡錢(qián),對(duì)花花綠綠的票子竟也這么感興趣!”在這種世道下,曾經(jīng)本本份份、一心為公的牧場(chǎng)場(chǎng)主父親,就變得不合時(shí)宜。他抱怨“現(xiàn)在這些羊把式,私心太重了,把這個(gè)公家的牧場(chǎng)當(dāng)成了一臺(tái)發(fā)家致富的機(jī)器。他們?cè)趫?chǎng)里放上幾年羊之后,個(gè)個(gè)就都成了附近的羊大戶。后來(lái)場(chǎng)里發(fā)現(xiàn)了,讓公安上的人來(lái)查,最后也沒(méi)有查出什么眉眼,不了了之了。關(guān)鍵是后面沒(méi)有人來(lái)?yè)窝瑖?guó)家的腰軟了,財(cái)產(chǎn)就這樣流失了,場(chǎng)里只把以前的幾個(gè)養(yǎng)把式辭退了。”人們?yōu)榱隋X(qián),用羊絨爪子狠命地抓羊絨,可以把白山羊變成血淋淋的紅山羊。山羊在這里就成為一個(gè)顯豁的隱喻,對(duì)人們喪心病狂的欲望進(jìn)行了揭示。“我”的立場(chǎng)和態(tài)度在父親的堅(jiān)守與老馬、老賽的唯利是圖之間的曖昧,小說(shuō)的高妙之處在于沒(méi)有將這種人性道德上的潰敗,僅僅歸結(jié)為個(gè)人的道德品質(zhì),而是將其與國(guó)家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大轉(zhuǎn)型結(jié)合起來(lái),從而顯示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廣度。《頌?zāi)颂帷穭t是另一篇直接討論宗教儀軌的小說(shuō),所謂頌?zāi)颂峋褪墙o包皮過(guò)長(zhǎng)的娃娃做手術(shù),有些地方則稱(chēng)作海太乃,叫法不同,翻譯過(guò)來(lái)叫做割禮,意思是干了一件善事,做了一件好事。小說(shuō)通過(guò)少年伊斯哈格給自己做割禮前后的心理活動(dòng),形象地展示了一個(gè)通過(guò)儀式。有意思的是這個(gè)小說(shuō)所體現(xiàn)的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殘酷青春,沒(méi)有成年人的支持和在場(chǎng),完全靠主人公自己個(gè)人的內(nèi)在力量,去追求一種清潔的精神,作者在這里實(shí)際上對(duì)宗教本身是毫無(wú)保留的接受的,因而缺乏一種自我反省。這些作品豐富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形式,卻普遍采取了平面化視角,除了為數(shù)不多涉及到深層次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性變遷的,大多數(shù)是如其本然地觀察與回望,從這個(gè)意義來(lái)說(shuō)反倒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主義內(nèi)涵的縮減。
二、自動(dòng)寫(xiě)作或經(jīng)驗(yàn)寫(xiě)作
自動(dòng)寫(xiě)作原先是20世紀(jì)20年代法國(guó)興起的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一種寫(xiě)作方式。在其倡導(dǎo)者布勒東(André Breton,1896-1966)看來(lái),“經(jīng)驗(yàn)本身也有其局限性……經(jīng)驗(yàn)就像關(guān)在籠子里的困獸,要把它從籠子里放出來(lái)是越來(lái)越難了。經(jīng)驗(yàn)也要依賴(lài)即時(shí)效用,而且還要靠理性去保持。人們打著進(jìn)步的借口,以文明為幌子,最終從那些被輕率地當(dāng)作迷信及幻覺(jué)的東西里將思想清除掉,摒棄所有追求真理的方式”[11]P16,因而他強(qiáng)調(diào)弗洛伊德的無(wú)意識(shí)理論,提倡不受任何理性控制的“自動(dòng)寫(xiě)作”,使意象與意象的連綴超出常規(guī)。這種詩(shī)歌宣言也影響到其他藝術(shù)門(mén)類(lèi),而在當(dāng)代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當(dāng)中也有著有意無(wú)意的暗合,它們或者體現(xiàn)為盡量擺脫邏輯束縛,而跟隨意識(shí)流動(dòng)的自動(dòng)寫(xiě)作,或者表現(xiàn)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不加剪裁的自然主義式映照。雖然最初自然主義是被現(xiàn)實(shí)主義所摒棄的,而自動(dòng)寫(xiě)作又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叛逆,但如果從“無(wú)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角度來(lái)看,它們都是現(xiàn)實(shí)寫(xiě)作的一種。
楊仕芳(侗族)《白天黑夜》就可以視為一種本土自動(dòng)式寫(xiě)作,這是個(gè)用6個(gè)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中篇小說(shuō)連綴而成的一部散文式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每個(gè)故事都來(lái)自故鄉(xiāng)”,分別講述了以某個(gè)故事為核心的村莊人物志。“我”作為遺棄兒的身世和民辦教師姐夫的經(jīng)歷,顯示了底層民眾的艱難生活,這種生活本身的素樸、雜亂、齟齬沒(méi)有慣常小說(shuō)中所見(jiàn)的戲劇性,而只有為生活所迫的困窘、變通和適應(yīng)。楊樹(shù)枝在山路上惡作劇挖坑陷人,無(wú)意中使得劉婄鳳墜落山坡,她的家庭因而陷入困境,兒子楊果被送入縣城,卻又難以適應(yīng),逃回家中,在給臥床的母親撈魚(yú)時(shí)被河水淹死。偶然性造成的傷害成為楊樹(shù)枝和目睹者“我”長(zhǎng)久的心理負(fù)擔(dān),換個(gè)角度看,偶然性其實(shí)也是必然性。吳玉柴的父親有精神病,他從云南帶回的女人與電影放映員私通,卻又因?yàn)殡y產(chǎn)而死去。在吳玉柴與放映員的和解中,可以看到在無(wú)可奈何中的悲憫,這是鄉(xiāng)村情與欲在沉重現(xiàn)實(shí)里的棄絕。患了絕癥的“我”的生母與失憶的生父再次出現(xiàn)在村頭,但他們背后的故事被歲月的風(fēng)塵湮沒(méi),在“我”的猜測(cè)中若隱若現(xiàn)而難以連貫清晰,他們與遠(yuǎn)方的城市一樣構(gòu)成了鄉(xiāng)村缺席的在場(chǎng)。楊樹(shù)根與王菊花有著質(zhì)樸的鄉(xiāng)村之戀,卻因?yàn)闂顦?shù)根救回跳水的母女而產(chǎn)生誤會(huì)出走,進(jìn)而造成兩個(gè)人十幾年的分離。小說(shuō)情節(jié)有種非理性的轉(zhuǎn)折,卻在不合情理中凸顯了愛(ài)的執(zhí)著和決絕。復(fù)員歸來(lái)的楊桃與縣城里的白潔真誠(chéng)相愛(ài)回到鄉(xiāng)村生活,白潔卻又因?yàn)樗L(zhǎng)期在外而與教師李強(qiáng)發(fā)生婚外戀。在村莊的巨大寬容中,白潔最終得到了原宥和諒解,再次坦然地與楊桃和好如初。這些情節(jié)如同山野間瘋長(zhǎng)的野草,枝蔓雜生,旁枝逸出,缺乏典型性的性格與敘事的主線,時(shí)常出現(xiàn)大段的議論和無(wú)關(guān)緊要的插曲,那些插曲的出現(xiàn)與隱沒(méi)毫無(wú)征兆,也沒(méi)有必要的解釋和歸束,敘事者就像一個(gè)充滿悲憫情懷的旁觀者,沉溺于自我反思和傷感抒情之中。“生活遠(yuǎn)比我想象的深厚和寬廣”,“在生活面前,手中的筆是無(wú)力的,現(xiàn)實(shí)的堅(jiān)硬讓人絕望”。[12]P226這種敘事上的粗糙和不加節(jié)制,可以看到某種類(lèi)青春期寫(xiě)作的色彩——敏感的作者從鄉(xiāng)土中來(lái),難以割舍對(duì)于故鄉(xiāng)的那份深情,進(jìn)而試圖在自己筆下展現(xiàn)風(fēng)俗畫(huà)式的全景,因而無(wú)力、更多是不愿意舍棄那些雜草叢生般的人事與感觸。這一方面固然是生活本身的豐富與復(fù)雜大于小說(shuō)造成,另一方面卻也表現(xiàn)出作者在敘事上仍然需要打磨和提煉,樹(shù)立起一個(gè)敘事者應(yīng)該有的價(jià)值觀,而不是被敘事對(duì)象所覆蓋,畢竟經(jīng)驗(yàn)如果要轉(zhuǎn)化為表述,需要提煉。《白天黑夜》與作者之前的《故鄉(xiāng)在別處》構(gòu)成了“故鄉(xiāng)三部曲”的前兩部,還帶有學(xué)步期的探索色彩。如何抵達(dá)日益變化的鄉(xiāng)村的核心,龐雜的經(jīng)驗(yàn)與細(xì)膩的感受固然必不可少,可能也需要在既有鄉(xiāng)村書(shū)寫(xiě)的模式中跳脫出來(lái),在普遍性的底層危機(jī)和生活洪流中尋找到獨(dú)特性的書(shū)寫(xiě)者的路向,這未必是要確立某種導(dǎo)向,而是從生活的雜質(zhì)中凝練出某種新鮮的經(jīng)驗(yàn)和價(jià)值。
涂克冬·慶勝(鄂溫克族)的小說(shuō)則普遍有種準(zhǔn)自然主義的傾向,一方面在內(nèi)容和題材上并沒(méi)有刻意提煉某個(gè)核心情節(jié)或者線索,而是讓事件自行流淌,或者截取某個(gè)人生斷片,在這個(gè)斷片中,意外的人物和事情隱現(xiàn)無(wú)常;另一方面在語(yǔ)言和技法上也采取的是“順其自然”的原生語(yǔ)言,有時(shí)候不加節(jié)制,使得他的人物對(duì)話更像是某個(gè)現(xiàn)實(shí)語(yǔ)境中的交談,風(fēng)格也顯得粗暴,卻也正因?yàn)榇直┒兊糜辛Α_@一切給慶勝的小說(shuō)帶來(lái)了一種“似真性”,他似乎就是把日常生活、社會(huì)經(jīng)歷中的某個(gè)真實(shí)部分原封不動(dòng)地截取下來(lái),用文字還原給讀者。初讀慶勝的小說(shuō),往往給人一種晚清黑幕小說(shuō)式的閱讀體驗(yàn),像那些在新興報(bào)刊上連載社會(huì)百態(tài)的精于世故的作家一樣,慶勝有著極其豐富的社會(huì)經(jīng)歷,因而從寫(xiě)作一開(kāi)始實(shí)際上就已經(jīng)確立了自己的風(fēng)格和方式。他的處女作《第五類(lèi)人》就是個(gè)以平視視角緊貼著生活來(lái)寫(xiě)的作品:一群少年經(jīng)歷過(guò)“文化大革命”,中年投入改革開(kāi)放和商品經(jīng)濟(jì)大潮中的大院子弟,去西藏自駕游的“在路上”。這個(gè)小說(shuō)元?dú)饬芾欤兄鷻C(jī)勃勃的活力,任憑敘事自動(dòng)展開(kāi),性格面貌各自呈現(xiàn)。這個(gè)敘事中,作者并不以塑造某種典型人物為旨?xì)w,也不在意某種超越性思想的反思,而是“展示”日常本身粗糙、鄙陋、心血來(lái)潮和偶爾讓人心領(lǐng)神會(huì)的感動(dòng)瞬間。作者主體是淹沒(méi)在情節(jié)之中的,雖然文本中隨處可見(jiàn)敘事者的主觀心理活動(dòng)、回憶等等,但他并沒(méi)有表明某種明確的道德態(tài)度和價(jià)值立場(chǎng)。我將這樣的小說(shuō)稱(chēng)為經(jīng)驗(yàn)型小說(shuō)。與體驗(yàn)型小說(shuō)的不同之處在于,經(jīng)驗(yàn)型小說(shuō)很少借助于抽象的哲思、超脫的想象、理性的反省,它與作者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密不可分,繁復(fù)豐富的經(jīng)歷會(huì)壓倒塑造人物、刻畫(huà)典型的欲望,呈現(xiàn)出籠統(tǒng)的、含混的、鋪天蓋地的瑣碎而龐雜的經(jīng)驗(yàn)。因而,經(jīng)驗(yàn)型小說(shuō)總帶有自敘傳的色彩,但這種自敘傳又不是像日本“私小說(shuō)”那樣是內(nèi)傾型的心理、情感與欲望,而是外在現(xiàn)象的觀察、看法與意見(jiàn)。
《跨越世界末日》雖然主人公是王倩妮,但她只不過(guò)是個(gè)線串式人物,通過(guò)她貫穿起律師業(yè)所涉及到的政府官員、法官、商人、軍人、黑社會(huì)、罪犯等方方面面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因而敘事的主體其實(shí)是社會(huì)關(guān)系,小說(shuō)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所營(yíng)造的是一種社會(huì)氛圍:一個(gè)人人都利益至上的社會(huì)氛圍。小說(shuō)的風(fēng)格同樣是平實(shí)白描,緊貼著生活來(lái)寫(xiě),袒露出真實(shí)的心理、卑瑣的人性、丑惡的社會(huì)。作者在鋪陳各種人物的行為舉止、語(yǔ)言和觀念時(shí),摒除了道德判斷,讓人與事粗礪的真實(shí)感自己呈現(xiàn)。王倩妮是個(gè)自我中心的當(dāng)代女性,從小縣城飛出來(lái)的鳳凰女,一心希望通過(guò)自己的能力實(shí)現(xiàn)在大城市立足的愿望。她在行事的時(shí)候?yàn)榱诉_(dá)到目的,似乎沒(méi)有道德掙扎和猶疑,這種價(jià)值觀上的淡然甚至冷漠是一種“時(shí)代病”,而不是一般我們所謂的“城市病”。這種“時(shí)代病”的基本特征體現(xiàn)在對(duì)權(quán)勢(shì)、金錢(qián)、欲望的艷羨和追求,而將其他的各種諸如倫理、理想、公義、感情都置之于無(wú)視和擱淺的境地。在這樣的經(jīng)驗(yàn)型小說(shuō)中,可以看到當(dāng)下社會(huì)的第一手材料,可以看到那些經(jīng)過(guò)語(yǔ)言和技巧修飾了的現(xiàn)實(shí)表述中所沒(méi)有的讓人觸目驚心的人性黑洞與道德絞肉機(jī)。個(gè)體與社會(huì)、小民族與大時(shí)代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一直體現(xiàn)在慶勝的寫(xiě)作主題中。他似乎無(wú)意識(shí)地表達(dá)了這樣一個(gè)理念,即任何一個(gè)哪怕是極其邊遠(yuǎn)地帶的、似乎很邊緣的人群,也始終與整體性的社會(huì)變局聯(lián)系在一起。寫(xiě)鄂溫克民眾自發(fā)抗日的歷史題材小說(shuō)《薩滿的太陽(yáng)》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情節(jié),青年滿嘎試圖聯(lián)絡(luò)同胞抗日,在征詢族內(nèi)老人們的意見(jiàn)時(shí),木哈力大叔強(qiáng)調(diào)保全族群存活比榮譽(yù)重要,而鄂溫克人原先是大清國(guó)的戍邊士兵,如今被滿洲國(guó)和中華民國(guó)都拋棄了。這顯然是魯迅所批判過(guò)的只知有家,不知有國(guó)的“沙聚之邦”的看法,最終滿嘎還是走向了抗日的道路,也正是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進(jìn)程中凝聚形成的復(fù)雜與曲折。這些作品放在整個(gè)中國(guó)文學(xué)的大背景中看,有個(gè)很重要的啟示,即邊地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除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之外,也有著與東南沿海、中心城市共通的命運(yùn);一個(gè)小民族的作家在言說(shuō)我們時(shí)代最深刻的政治經(jīng)濟(jì)與精神轉(zhuǎn)型時(shí),其可以抵達(dá)的經(jīng)驗(yàn)深度較之于發(fā)達(dá)地區(qū)的作家一點(diǎn)也不遑多讓。*上述提到的涂克冬·慶勝作品包括:長(zhǎng)篇小說(shuō)《第五類(lèi)人》,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長(zhǎng)篇小說(shuō)《跨越世界末日》,呼和浩特:遠(yuǎn)方出版社,2007年。長(zhǎng)篇小說(shuō)《薩滿的太陽(yáng)》,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短篇小說(shuō)集《陷阱》,呼和浩特:遠(yuǎn)方出版社,2011年。
夏魯平(滿族)的小說(shuō)則較少涉及具體民族,他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作品是寫(xiě)中低層公務(wù)員和公司職員的日常處境、行為模式與處世心態(tài)。這些作品包括《監(jiān)控盲區(qū)》、《單位》、《找魂兒》、《放松》、《風(fēng)在吹》、《競(jìng)爭(zhēng)》、《緊張》、《一罐茶》、《回家》、《升遷》,主要的人物有侯處長(zhǎng)、馬大壯、徐文達(dá)、李純剛、李奇、李老蔫兒等。在這些小說(shuō)的寫(xiě)作中,夏魯平很少進(jìn)行描寫(xiě)和刻畫(huà),而更多是一種講故事的口吻來(lái)展現(xiàn)一種當(dāng)代官場(chǎng)眾生相。這些人物大多是科級(jí)到處級(jí)干部,他們的面目很相似,有的甚至直接以職位代替名字,是一種群像式的展示而不是性格的塑造。小說(shuō)從外在的角度進(jìn)行生態(tài)描摹,無(wú)論是一心向上爬的小職員,退休賦閑在家的老干部,還是正處于權(quán)力斗爭(zhēng)漩渦的實(shí)權(quán)派,這些人都不是某種道德高尚的人,但也不是惡貫滿盈道德敗壞之人,而是在一地雞毛、無(wú)可奈何的處境中掙扎的普通人。普通人的性格特點(diǎn)不是那么鮮明,他們之間的性格特征趨同,完全可以互換,因而在這些短篇之間互文式情節(jié)的相互補(bǔ)充之中,形成了一種類(lèi)型化色彩。在這種類(lèi)型當(dāng)中,我們可以看到官場(chǎng)人物關(guān)系之間的微妙,人物心理內(nèi)部變化的幽微曲折,人際交往中的謹(jǐn)小慎微、斤斤計(jì)較。在這里可以看到社會(huì)的普通常態(tài),夏魯平是用一種自然主義式的純寫(xiě)實(shí)手法講述當(dāng)代中國(guó)生活的一個(gè)社會(huì)空間普遍狀態(tài)。
在這個(gè)過(guò)程當(dāng)中作者沒(méi)有設(shè)立一個(gè)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或者道德評(píng)判的尺度,有一種溫柔敦厚的悲憫在里邊,因?yàn)檫@些人都是在時(shí)代的大潮和復(fù)雜社會(huì)當(dāng)中的螻蟻,放逐了任何諸如為人民服務(wù)這樣的崇高目的,而僅僅是謀生糊口、爭(zhēng)權(quán)奪利。這就使得人物的命運(yùn)具有偶然性的荒誕感,有時(shí)候他們用盡心機(jī)拼盡全力,只是得了一個(gè)荒謬的結(jié)局,比如《監(jiān)控盲區(qū)》和《緊張》是少有的在心理描寫(xiě)上下了比較大工夫的作品,小說(shuō)通過(guò)淋漓盡致鋪張揚(yáng)厲的細(xì)膩刻畫(huà),主人公的焦慮、恐懼與后來(lái)的結(jié)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得到了一種反諷的效果。這些小說(shuō)有意義的地方在于它無(wú)形中顯示了我們社會(huì)在共識(shí)與情感上的分裂。《一罐茶》以一罐從臺(tái)灣帶回來(lái)的茶輾轉(zhuǎn)于不同人物之手,平實(shí)地展現(xiàn)了權(quán)力之間的爾虞我詐以及在底層人那里關(guān)聯(lián)起恒久情感的意義,小說(shuō)最后還形成了一個(gè)反諷:即那罐在公司老總李純剛那里很普通的茶,卻被保潔工李春梅的奶奶當(dāng)作了精神寄托。“李春梅在講述中已哭成了淚人。許多天里,李純剛望著頭頂那個(gè)小小的窗口,都無(wú)法理解李春梅為什么把自己哭成那樣。”[13]P131這里面有著兩個(gè)階層間的互不理解和隔閡。李純剛只有突破“頭頂那個(gè)小小的窗口”,才有可能與他人達(dá)成情感上的共通。《回家》和《升遷》中許文達(dá)被紀(jì)檢部門(mén)調(diào)查的時(shí)候一度落勢(shì)返鄉(xiāng),而家鄉(xiāng)的親戚鄰居并沒(méi)有帶來(lái)想象中的慰藉,而只是充滿了投機(jī)與利用心理,一旦發(fā)現(xiàn)真相后便暴露出勢(shì)利的態(tài)度。但許文達(dá)再度升遷后,鄰居農(nóng)民孫亞芝依然不依不饒地胡攪蠻纏。親情作為最后的港灣,也無(wú)法消除人際之間的刻薄與冷漠。《世事難料》中城市白領(lǐng)之間無(wú)視道德倫理的婚外情更是讓愛(ài)情也染上了玩世不恭與及時(shí)行樂(lè)的色彩。這樣的觀察因?yàn)槠淇坦堑恼鎸?shí)感,而讓人肌膚生涼。但作者卻無(wú)法給出一種想象中的解決方案。因?yàn)槿绻麤](méi)有某種內(nèi)在自我設(shè)立的目標(biāo),人物只能在做無(wú)規(guī)則的布朗運(yùn)動(dòng),這里顯示出當(dāng)代小說(shuō)具有普遍性的一個(gè)問(wèn)題,即價(jià)值觀的缺失。《找魂兒》形象地體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退休以后的侯處長(zhǎng)百無(wú)聊賴(lài),希望在傳統(tǒng)的薩滿教中找到精神家園,而事實(shí)證明那不過(guò)是南柯一夢(mèng)式的發(fā)癲,“外孫女才是他全部的魂”。這種“魂”的失落和最終落腳于日常親情之中,其實(shí)無(wú)法給他帶來(lái)靈魂的安頓。這一系列某種意義上可以稱(chēng)之為“官場(chǎng)小說(shuō)”的短篇作品可以視作分散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章節(jié),如果將他們統(tǒng)攝在一起可能會(huì)起到一個(gè)集束式的效應(yīng),但根本問(wèn)題是需要構(gòu)建一種批判視角,想象一種可能性生活,而不僅僅停留于生活表面雞零狗碎式的世情描摹。
另外一部分作品是帶有所謂的“正能量”意味的作品,比如《去王家村》、《土鱉》、《參園》和《北京鄰居》。多以底層民眾的苦難為主,敘事人的情感往往是零度介入的。在這些小說(shuō)當(dāng)中,夏魯平竭力追求一種類(lèi)似于歐·亨利式的結(jié)局,欲揚(yáng)先抑或者是在層層鋪墊之后突然逆轉(zhuǎn),給故事一個(gè)光明或溫馨的結(jié)尾,這可能跟發(fā)表的刊物或者報(bào)紙要求有關(guān)系,往往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jué)。《土鱉》對(duì)于親情在金錢(qián)社會(huì)中的淪喪有著清醒冷靜的揭示,《參園》里沉淪于生存苦海中的農(nóng)民之間的冷酷關(guān)系的展示,都是表面平靜實(shí)則驚心動(dòng)魄。但作者無(wú)意挖掘其背后整體性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因素,因而使得小說(shuō)透視生活的力度打了一定的折扣,因?yàn)榈讓用癖娭g相互的溫情體恤來(lái)化解之前累積的矛盾,固然有著人性上的可能性,卻并沒(méi)有解決問(wèn)題,而只是暫時(shí)的和解。短篇小說(shuō)因?yàn)槠木壒释鶡o(wú)法進(jìn)行廣闊層面的鋪寫(xiě)和深度的精神剖析,它要求在精致結(jié)實(shí)的情節(jié)構(gòu)造和凝練的語(yǔ)句中蘊(yùn)藉一種力道,以小見(jiàn)大、見(jiàn)微知著,通過(guò)核心性的意象或人物袒露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復(fù)雜與豐富。這是小說(shuō)區(qū)別于故事的地方,即文學(xué)在拆除和顛覆既有的現(xiàn)實(shí)時(shí),一定要確立某種整體性和超越性的視角,從而給讀者在帶來(lái)閱讀的娛樂(lè)的同時(shí),也有思想上的啟迪與引發(fā)進(jìn)一步思考的韻味。這可能不僅僅是夏魯平,而且也是很大一部分作家在將來(lái)的創(chuàng)作中有更多發(fā)揮空間的地方。
三、先鋒與日常
1986年前后興起的“先鋒小說(shuō)”經(jīng)過(guò)三十年的起伏,如今已經(jīng)沉淀為文學(xué)史的一部分。盡管早期充滿形式探索、語(yǔ)言變革和反叛意識(shí)的先鋒小說(shuō)進(jìn)入新世紀(jì)以來(lái)逐漸趨于弱化,早年的先鋒作家如格非、余華、蘇童也發(fā)生了創(chuàng)作轉(zhuǎn)型,新生的70后、80后作家也很少再刻意踏上先鋒小說(shuō)的路徑。但這并不意味著先鋒小說(shuō)已經(jīng)在歷史中耗盡了它的能量,恰恰相反,先鋒小說(shuō)的遺產(chǎn)已經(jīng)成為一種正典化了的遺產(chǎn),浸潤(rùn)在當(dāng)下寫(xiě)作的日常之中。特定時(shí)期產(chǎn)生的先鋒小說(shuō)無(wú)疑有著隱秘的意識(shí)形態(tài)意義,無(wú)論就其形式還是就其表達(dá)的觀念與思想,都有對(duì)抗、顛覆、變革之前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或抒情式寫(xiě)作的自覺(jué)意愿,而這種功能在經(jīng)過(guò)了世紀(jì)之交巨大變遷的新語(yǔ)境中已經(jīng)不再成為問(wèn)題,或者說(shuō)文學(xué)再次要面對(duì)的革新對(duì)象已經(jīng)變了,曾經(jīng)的方式不再適用,作家們必須要尋找自己的方法。
次仁羅布(藏族)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祭語(yǔ)風(fēng)中》和中短篇小說(shuō)集《放生羊》無(wú)疑體現(xiàn)了先鋒小說(shuō)的當(dāng)代面貌。如果回眸藏族文學(xué)的當(dāng)代脈絡(luò),可以清晰地看到從最初的革命英雄傳奇到八十年代興起的西藏“新小說(shuō)”與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轉(zhuǎn)變路徑,而到了次仁羅布這里,魔幻現(xiàn)實(shí)已經(jīng)內(nèi)化為一種自然,它不再刻意尋求敘事上的標(biāo)新立異,或者追求某種玄幻的終極意蘊(yùn),而是將魔幻化為日常,通過(guò)重寫(xiě)歷史進(jìn)而復(fù)歸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本源。《祭語(yǔ)風(fēng)中》將西藏和平解放至當(dāng)下的發(fā)展歷程與11至12世紀(jì)藏密大師米拉日巴的一生雙線交織起來(lái),通過(guò)細(xì)微的人物命運(yùn)關(guān)聯(lián)宏大的民族國(guó)家歷史,這里也可以看到先鋒小說(shuō)乃至新歷史小說(shuō)的潛在影響。小說(shuō)起于帕崩崗天葬臺(tái),這是舊時(shí)代的死亡,同時(shí)也是新時(shí)代的誕生;終于帕崩崗天葬臺(tái),則是歷史中的個(gè)人體悟到命運(yùn)的輪回與救贖的可能:“漫天的星光閃閃爍爍,習(xí)風(fēng)微微吹蕩,我的心卻靜如一面湖水。我們經(jīng)歷的一切會(huì)隨風(fēng)吹散,不會(huì)留一絲絲的痕跡!”[14]P442也許這樣的歷史觀并沒(méi)有脫離宗教的窠臼,但藝術(shù)的特權(quán)在于它無(wú)需像哲學(xué)一樣周延完整,它正是通過(guò)這種偏狹顯示了一種現(xiàn)實(shí)的存在。
來(lái)自于湘西的作家于懷岸(回族)的《巫師簡(jiǎn)史》也是一部富于野心的作品,它的氣質(zhì)就如同馬爾克斯《百年孤獨(dú)》與陳忠實(shí)《白鹿原》的雜糅結(jié)果,某些情節(jié)和片斷富于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般的神秘色彩,總體上卻又具有極強(qiáng)的“在地性”,浸染著濃郁的湘西地方信仰、宗教、風(fēng)俗、血性和情感。小說(shuō)橫貫從清末到新中國(guó)成立后的肅反與鎮(zhèn)壓反革命的半個(gè)世紀(jì)歷史進(jìn)程,焦點(diǎn)集中于貓莊這一偏僻湘西山鄉(xiāng)的村落,線索人物是貓莊的巫師與族長(zhǎng)趙天國(guó)。巫師簡(jiǎn)史即是貓莊的近代史(它本身就是由《貓莊史》擴(kuò)展改寫(xiě)而來(lái)),也是湘西地方文化現(xiàn)代蛻變與陣痛、疏離與融入、掙扎與奮斗的軌跡。國(guó)與家、公與私、政治與宗族之間的糾纏與沖突是盤(pán)旋在整個(gè)小說(shuō)中縈繞不去的情結(jié)。作為族長(zhǎng),趙天國(guó)從繼承家族使命開(kāi)始,無(wú)論是領(lǐng)導(dǎo)貓莊與白水寨土匪的對(duì)抗,還是當(dāng)保長(zhǎng)周旋于軍閥勢(shì)力和自治地方官員收租與征兵的盤(pán)剝之中,還是對(duì)國(guó)民黨和共產(chǎn)黨的雙重疏離,自始至終都是為了保全貓莊及其子弟的存續(xù)和綿延。他是宗法制度和鄉(xiāng)野倫理結(jié)出的最后果實(shí),心中念茲在茲的是家園的守衛(wèi)。這種意識(shí)是如此強(qiáng)烈,以至于成為一種執(zhí)念,而拒絕了個(gè)人與國(guó)家,糾結(jié)于橫亙?cè)诙咧虚g的“家族”的存亡絕續(xù),因而注定要在個(gè)性自主日益自覺(jué)、國(guó)家主權(quán)逐漸確立的情境下趨于失敗。這是現(xiàn)代以來(lái)中國(guó)社會(huì)堪稱(chēng)天翻地覆的結(jié)構(gòu)性變遷,鄉(xiāng)土社會(huì)中的鄉(xiāng)紳、族長(zhǎng)、頭人這一聯(lián)系底層細(xì)民與國(guó)家政權(quán)的階層,在洶涌而至的外部威脅(包括經(jīng)濟(jì)、軍事、政治和文化)之中,或者走向墮落蛻化成為土豪劣紳,或者成為極少數(shù)堅(jiān)持傳統(tǒng)倫理道德、道義觀念的悲劇性英雄。趙天國(guó)無(wú)疑是后一種,他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地守護(hù)的家族觀念固然有其合法性,卻是過(guò)時(shí)與注定落敗的,乃至自外于大環(huán)境之外,這使得他的無(wú)望的守護(hù)有種宿命與反抗宿命的悲涼,就像他在十四歲從父親受眾解雇巫師法器的時(shí)候已經(jīng)觀看到一生最終的結(jié)局,卻依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巫術(shù)與科技、神秘與解魅、情感與理性則是與主線同時(shí)并行的隱線。作為巫師,趙天國(guó)有著占卜預(yù)測(cè)的神秘能力,然而從一開(kāi)始,他就已經(jīng)悲哀地感到“世道越來(lái)越亂,巫師的法力卻越來(lái)越小。”[15]P5小說(shuō)結(jié)尾部分借制作棺材的小師傅之口又呼應(yīng)道:“神都走了,通神的人還能靈嗎?”貓莊在亂世中茍延殘喘的半個(gè)世紀(jì),同時(shí)是巫師的神性逐漸淪喪的過(guò)程。彭武平一槍擊碎了法器羊脛骨,就是現(xiàn)代科技擊潰古老秘技與信仰的象征。盡管山野村莊中依然殘存著飄魂、夢(mèng)兆這樣的靈異現(xiàn)象,現(xiàn)實(shí)已然發(fā)生改變,這是金與鐵、利與權(quán)交織的世界,正在逐步蠶食古老村莊悠久的傳承與美德。最后一個(gè)趕尸人雷老二在戰(zhàn)場(chǎng)的死去,預(yù)示著一切都在祛魅,抗日戰(zhàn)爭(zhēng)、解放戰(zhàn)爭(zhēng)、土地革命正在使得世界日趨透明化,而籠罩在寒冷、陰郁煙云中的村莊也日益被納入到體制化、規(guī)范化、標(biāo)準(zhǔn)化的現(xiàn)代性建構(gòu)之中。土匪龍大榜、國(guó)民黨軍彭學(xué)清、紅軍彭武平……這些從貓莊及周邊走出的人,他們的身份都在不停地隨著時(shí)代和局勢(shì)的變化移形換位;苗人、畢茲卡人、漢人和“貓莊人”的認(rèn)同,既在情義恩仇中固守,又在時(shí)代裂變中瓦解與重組。在變與不變之間,鄉(xiāng)土中國(guó)的根脈和血性經(jīng)受著一輪又一輪的洗禮,得到的終將得到,失去的已經(jīng)失去,《巫師簡(jiǎn)史》留下的是中國(guó)大地上一段既普通又獨(dú)特的記憶,就像小說(shuō)本身寫(xiě)法上時(shí)而空靈詭異、時(shí)而冷峻寫(xiě)實(shí)一樣,這是一部充滿了先鋒精神與日常經(jīng)驗(yàn)的作品,雖然沒(méi)有提供新的寫(xiě)作范型,卻在已有的文學(xué)典范中增添了湘西敘事的別樣視角,并通過(guò)這種地方經(jīng)驗(yàn)達(dá)致了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中國(guó)現(xiàn)代史體驗(yàn)。
云南納西族作家和曉梅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審美風(fēng)格,與她那些充滿神秘邊地、怪異異域的題材相得益彰的是空靈、飄忽卻又銳利而有力的文體,這兩方面形成了一種別具特色的風(fēng)格化小說(shuō)。這種風(fēng)格糅合了福克納的雜亂與明媚和蘇童的陰郁與唯美,加上阿來(lái)的《塵埃落定》式的縹緲與羅曼蒂克色彩,突出地體現(xiàn)在她的《賓瑪拉焚燒的心》里。這個(gè)小說(shuō)以獨(dú)白和私語(yǔ)的方式,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并由自身的經(jīng)歷折射出周邊地域的變遷。獨(dú)白與私語(yǔ)的方式是女性文學(xué)的常見(jiàn)表述方式,最典型如林白、陳染,有種排他性,即以第一人稱(chēng)的主觀直接呈現(xiàn)對(duì)于自我與世界的認(rèn)知。它可能會(huì)忽略廣闊社會(huì)背景的縱橫捭闔與開(kāi)闊視野,好處卻是能夠更加貼切地顯示內(nèi)心的真實(shí)和情感的深度。而這種表述方式與小說(shuō)要講述的內(nèi)容恰是非常吻合的,因?yàn)闊o(wú)論是上部“獵與物”還是下部“時(shí)與光”,故事都是發(fā)生在一個(gè)另類(lèi)空間。僅從文本來(lái)看,這個(gè)空間是無(wú)所有的,盡管讀者可以從作家本人的身份和所在地域做出一些推斷,比如她寫(xiě)的可能是滇西南某處,但這并不重要,和曉梅寫(xiě)的其實(shí)是個(gè)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空間。這個(gè)空間容納了那些在現(xiàn)代制度性規(guī)劃之外的神秘、蒼茫、悠遠(yuǎn)、偏僻的叢莽與山谷、河流與垣陵。只有在這樣富含隱喻并且難以索解的空間中,那些有關(guān)人性與時(shí)代的最根本的主題才會(huì)如你所見(jiàn)、如是我聞般地顯露出它們最初的質(zhì)地。
《賓瑪拉焚燒的心》有著明顯的女性敘事的特色,似乎延續(xù)了和曉梅之前作品的主題,比如《女人是“蜜”》里幾代女人的生活與命運(yùn)。小說(shuō)的主要角色都是女人,男人雖然看似強(qiáng)勢(shì)、甚至能夠主宰女人的命運(yùn),但他們左右不了女人獨(dú)立的自我、幽微的內(nèi)心。賓瑪拉墨是在傈僳女人的共同體中長(zhǎng)大的,雖然女人們之間也有著各種小心眼,卻從來(lái)不是根本性的沖突。她和格木人獵人烏卡是自由的結(jié)合,但保持了個(gè)體的獨(dú)立,是一個(gè)背著弩弓的女獵人。賓瑪拉金夫人似乎依附于土司家的哲格汝總管,但一直有著自己無(wú)法被總管理解的超脫的精神世界。幾代女人面目模糊,她們之間的區(qū)別并不明顯,因而可以看作是女人整體的歷史性展開(kāi)。在這個(gè)女性共同體中,她們共同體驗(yàn)到愛(ài)情、嫉妒、生育、等待、憤怒、仇恨、痛苦和期盼,以及與男人之間百多年來(lái)愛(ài)恨交織、糾葛纏綿的歷史。這是個(gè)情感的共同體,共守著女性所特有的對(duì)于世界原初的認(rèn)知,也共享著對(duì)于永恒事物的基本信念和對(duì)外來(lái)神奇的預(yù)測(cè)與判斷。這是個(gè)有別于男性思維方式和世界觀的觀察視角,在政治斗爭(zhēng)、金錢(qián)謀利、爾虞我詐之外,關(guān)心最細(xì)微的心靈痛楚、大自然的和諧生態(tài)、非理性的認(rèn)識(shí)方式。賓瑪拉墨少時(shí)見(jiàn)到的那幾個(gè)偷牛賊殺死了牛,但最終都因?yàn)樵{咒而受到了懲罰。而這個(gè)詛咒正是來(lái)自于女巫師賓瑪拉金。這也可以視為性別之爭(zhēng),男性似乎以功利的態(tài)度主宰著世界、捕獲著獵物,而女性卻在這個(gè)邏輯之外,用巫師式的態(tài)度與做法委婉而又堅(jiān)韌地予以反擊。獵物自身會(huì)復(fù)仇,就讓“獵”與“物”之間的主客關(guān)系被顛倒了。但性別議題只是小說(shuō)的一個(gè)方面,下部“時(shí)與光”則是以性別角度觀察到的時(shí)間主題,換句話來(lái)說(shuō)是個(gè)變遷主題。賓瑪拉金希望用光線的變化試驗(yàn)來(lái)改變時(shí)間,這是一種“賓瑪拉式”的思維,也即尚未同神性斷裂的巫術(shù)思維。這種思維看似野蠻,里面卻有種人類(lèi)的初心和童真,就像小說(shuō)開(kāi)篇題詞中祖母女祭司賓瑪拉赫的話:“盡管我深知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gè)怎樣蒙昧的世界,但我依然愿意,為無(wú)知保持必要的好奇,為野蠻保留必要的童貞,畢竟我們的任何一次選擇,都來(lái)自我們純凈的內(nèi)心。”[16]P1但是光線卻并不能擾亂時(shí)間,因?yàn)樾≌f(shuō)中隨處可以看到變化的來(lái)臨,即便在深山密林之中,商人還是將貿(mào)易的觀念以及欺騙帶了進(jìn)去。賓瑪拉墨的兩個(gè)舅舅知道用金錢(qián)作為統(tǒng)治奴役他人的技巧。這一切與“賓瑪拉式”的生活都是相悖的。變化和失敗已然到來(lái),賓瑪拉赫的心在燃燒,賓瑪拉女人們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方式進(jìn)行保全的努力,保存那些人類(lèi)最后的天真與淳樸、柔情與愛(ài)、非功利的生活方式。
和曉梅的敘事就在情感與時(shí)間的交錯(cuò)中,走向了一種個(gè)體的生存論式的敘說(shuō)。賓瑪拉女巫家族身處的變革時(shí)代,正是一個(gè)現(xiàn)代性逐漸入侵與消解神性的時(shí)代。用克爾愷郭爾(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的話來(lái)說(shuō),這是一個(gè)“溶解的時(shí)代”[17]。圓融自足的自然個(gè)體,被消融在缺乏激情、平庸功利的時(shí)代汪洋之中,難以抵抗。賓瑪拉那顆焚燒的心,就是一個(gè)被焚燒的神性主體。這造成了自然式個(gè)人的毀滅,女巫再也無(wú)法預(yù)測(cè)一個(gè)確定性的未來(lái),或者通過(guò)詛咒與光線的試驗(yàn)來(lái)左右命運(yùn)與時(shí)間。賓瑪拉這樣超越性的、充滿神秘魅力的家族將要走向終結(jié),雖然在毀滅的過(guò)程中會(huì)留下亙久不滅的馨香,但也不可避免地散發(fā)出悲愴的氣息。這也是文學(xué)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意義所在,當(dāng)一切都已經(jīng)按照發(fā)展模式?jīng)皼跋蚯埃ぞ呃硇圆豢杀苊獾厍治g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種情形下,唯有文學(xué)還可以給我們的心靈以慰藉,給我們的精神以超脫之境,給我們的靈魂以棲居之所。
四、素樸與感傷的詩(shī)
詩(shī)歌一直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當(dāng)中最為出眾的文類(lèi),因?yàn)檎Z(yǔ)言和文化的差異性很容易帶來(lái)陌生化的美學(xué)效果,以及在運(yùn)思方式和精神觀念上的特異性。另外,由于許多民族有著自身悠久厚重的母語(yǔ)詩(shī)歌傳統(tǒng),在進(jìn)行現(xiàn)代轉(zhuǎn)化過(guò)程中,當(dāng)代少數(shù)民族漢語(yǔ)詩(shī)歌很自然地將許多迥異于刻板話語(yǔ)的形式與內(nèi)容帶入進(jìn)來(lái)。詩(shī)歌語(yǔ)言本身的高度本質(zhì)直觀性,又使得溝通更為便捷。除了漢語(yǔ)寫(xiě)作的詩(shī)歌之外,雙語(yǔ)詩(shī)歌則是少數(shù)民族詩(shī)歌獨(dú)有的現(xiàn)象。阿庫(kù)烏霧(彝族)多年來(lái)一直致力于母語(yǔ)詩(shī)歌及其理論的創(chuàng)作與實(shí)踐。由他與文培紅、馬克·本德?tīng)柡献鞯臐h英雙語(yǔ)詩(shī)歌集《凱歐蒂神跡》可以說(shuō)是數(shù)年來(lái)成績(jī)一個(gè)集中性的展示。這些詩(shī)歌是他“在數(shù)次旅美之行期間創(chuàng)作的。這些詩(shī)歌中很大一部分表達(dá)了詩(shī)人對(duì)美國(guó)印第安文明的獨(dú)特看法。首先是印第安人信仰的神靈世界,與阿庫(kù)自己文化中的傳統(tǒng)信仰形成共鳴,詩(shī)人還對(duì)印第安文明史中負(fù)面的部分內(nèi)容做了評(píng)述。在族群關(guān)系方面,詩(shī)人倡導(dǎo)一種‘差異的平等’。整部詩(shī)集中體現(xiàn)了詩(shī)人的人文關(guān)懷和世界多樣性的理想。”[18]P364這是一種“雙重寫(xiě)作”,我之前曾經(jīng)在一篇論文中指出雙重寫(xiě)作是一種內(nèi)在包含了比較的跨文化寫(xiě)作。它與一般所說(shuō)的“翻譯寫(xiě)作”不太一樣,而是一種同時(shí)在不同地方用不同語(yǔ)言發(fā)表的作品,意圖在文本旅行中獲得疊加傳播的效應(yīng)。遷移與旅行賦予了回憶行為以“召喚”與“追憶”的移動(dòng)和彈性,讓不同的歷史連接起來(lái),同時(shí)呈現(xiàn)出“民族”文學(xué)所很少看到的對(duì)不同種類(lèi)文化的雙重批判。[19]P45-63這種詩(shī)歌門(mén)徑是外在于主流詩(shī)歌關(guān)于語(yǔ)言討論的邏輯之外的,而將詩(shī)與思對(duì)接于全球性的跨文化語(yǔ)境,從而彰顯了某種弱勢(shì)文化的獨(dú)特意義,豐富了被主導(dǎo)性文學(xué)權(quán)力宰制的文學(xué)生態(tài)。
不過(guò),此類(lèi)嘗試并不是很多,絕大部分少數(shù)民族詩(shī)歌依然屬于古典詩(shī)歌式的自然抒情狀態(tài),更多注目于本族群文化的變遷和鄉(xiāng)土風(fēng)物的謳歌,較少致力于語(yǔ)言試驗(yàn)與哲思提煉。龍道熾(侗族)《清水江歌行》以“清江水月”、“森林部落”、“村莊行走”、“時(shí)光鏡像”四輯集中抒寫(xiě)了黔東南境內(nèi)沅江的上游清水江的青山綠水、丹楓白鷺,鄉(xiāng)風(fēng)俚俗、如潮世聲。那是“盛產(chǎn)民歌和銀飾的水鄉(xiāng)/天生帶著雨種/繁衍了中國(guó)林業(yè)的戀史……我的先祖 先祖的先祖/就在這方盛產(chǎn)水稻和杉木/盛產(chǎn)民歌和銀飾的江邊/耕作 栽培 編織 撒網(wǎng)/ 在山川 壩子 田間/ 收割 歌唱 祭祀 祈求豐年/用琵琶和蘆笙敲擊歲月/ 他們滾出玉米粒/吐出桐油的體氣 糯米粑粑的香味/在節(jié)日里燒幾顆辣子/擺一壇腌魚(yú)和家酒/便可以游方 斗牛 賽龍舟”[20]P2-3。通觀這些詩(shī)篇,清淺直白,卻是出自質(zhì)樸心聲。也有舊體詩(shī)詞的創(chuàng)作,如吳隆文(侗族)《嘯詠遏行云》是以七絕、七律、五絕、五律等舊體詩(shī)寫(xiě)作的合集,頗有風(fēng)雅余韻。這些詩(shī)歌如果不是放入“少數(shù)民族詩(shī)歌”的視野里,很難進(jìn)入到批評(píng)家的視野之內(nèi),但是它們構(gòu)成了少數(shù)民族詩(shī)歌的一般狀態(tài),與泥沙俱下的形形色色詩(shī)歌圈子里自我抒懷與自我撫摸的詩(shī)歌相似,它們也構(gòu)成了一種自?shī)首詷?lè)的文學(xué)樣態(tài),在客觀上對(duì)于地方風(fēng)物與民族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塑像與宣傳作用。
彝族詩(shī)人群近年來(lái)引起廣泛關(guān)注,不僅因?yàn)橛屑荫R加這樣具有國(guó)際性影響的詩(shī)人,而且由于詩(shī)歌屬于他們文學(xué)生活的一種形式。略舉并不出眾的沙馬阿古(彝族)為例,他的詩(shī)集《彝人夢(mèng)》是在撕裂性的現(xiàn)實(shí)中書(shū)寫(xiě)陣痛,在針砭和諷刺種種扭曲與齷齪之后,表達(dá)無(wú)奈的感傷和期冀:“我多么希望/讓神扇繼續(xù)攥在畢摩的手中搖曳下去/誦經(jīng)祈福 幸福安康/讓神鼓依然握在蘇尼的手中繼續(xù)扭轉(zhuǎn)乾坤/讓德古又重新周旋在不共戴天的仇敵之間/化干戈為玉帛/讓工匠再次歸位/操起他的家當(dāng)/施展超凡的技藝/讓駿馬再回到奔馳的賽場(chǎng)上/馳騁在眾目睽睽之中/我的夢(mèng)/彝人的夢(mèng)/讓我們的后裔酷愛(ài)自己的文字/用母語(yǔ)大聲說(shuō)話/用母語(yǔ)對(duì)話/與世界對(duì)話/讓大人們永無(wú)止境地說(shuō)唱爾比爾吉下去/讓老人們陶醉在克哲的雄辯中安然離去”[21]P2-3。無(wú)疑,這種“夢(mèng)”是一種逃遁與回避,而詩(shī)人所操持的意象也基本上都是彝族文化中的刻板化了的符號(hào),因而這種感傷的詩(shī)某種意義上是脫離個(gè)性化感受的,而成為一種抽象的抒情。此類(lèi)詩(shī)歌大量生產(chǎn),既可以見(jiàn)出其繁榮的一面,同時(shí)也顯示了豐盛下的匱乏,即其表意方式較為單一,而表達(dá)的觀念也缺乏創(chuàng)新。倒是詩(shī)歌與流行音樂(lè)的結(jié)合,有著令人驚喜的一面,瓦其依合、莫西子詩(shī)、阿魯阿卓、吉克雋逸這些彝族歌手,通過(guò)在大眾傳媒中的創(chuàng)作與表演,反倒起到了書(shū)面詩(shī)歌所很難達(dá)到的宣傳效果和廣泛影響力。在新媒體日益盛行的當(dāng)下,詩(shī)歌的發(fā)展形態(tài)可能會(huì)越來(lái)越趨向于與新技術(shù)的結(jié)合,擺脫精英化,重新進(jìn)入到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來(lái)。
五、非虛構(gòu)趨勢(shì)
“非虛構(gòu)”在2010年以來(lái)成為當(dāng)代寫(xiě)作的一個(gè)熱門(mén)話題,它與此前“紀(jì)實(shí)文學(xué)”、新聞特寫(xiě)、報(bào)告文學(xué)的不同之處在于突出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擔(dān)當(dāng)、個(gè)人介入和參與式體驗(yàn)。波及到虛構(gòu)性作品之外的一切寫(xiě)作都沾染了“非虛構(gòu)”色彩,也因此它成了一個(gè)無(wú)所不包的大筐,但其中還是以散文為主。事實(shí)上張承志、烏熱爾圖、阿來(lái)等作家早在上個(gè)世紀(jì)九十年代已經(jīng)開(kāi)始了這樣的轉(zhuǎn)型。“非虛構(gòu)”的核心問(wèn)題在于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再認(rèn)知,它力圖從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的定型中走出,重建關(guān)于真實(shí)的表述。
如果要在少數(shù)民族寫(xiě)作中選出一部最為切合“非虛構(gòu)”界定的作品,顯然非夏曼·藍(lán)波安(達(dá)悟人)的《冷海情深》莫屬。夏曼·藍(lán)波安原先在臺(tái)灣淡江大學(xué)讀法文,后在臺(tái)灣清華大學(xué)人類(lèi)學(xué)研究所獲得碩士學(xué)位。一度曾經(jīng)參與“臺(tái)灣原住民運(yùn)動(dòng)”,1989年回到故鄉(xiāng)蘭嶼島上開(kāi)始回歸祖輩潛水射魚(yú)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并且積極參與了反抗核廢料存儲(chǔ)蘭嶼的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冷海情深》中收羅的作品都在他臺(tái)北求學(xué)與謀生十六年之后,回鄉(xiāng)重新經(jīng)歷文化沖擊和再次接受祖輩傳統(tǒng)文化教育與踐行的記錄。這些作品每一篇都充斥著一個(gè)具有反思精神的“我”,他在不斷的再學(xué)習(xí)和融入到祖輩生活共同體中之時(shí),經(jīng)歷了情感心理與現(xiàn)實(shí)困窘的種種沖突,這個(gè)過(guò)程中逐漸樹(shù)立了堅(jiān)強(qiáng)的認(rèn)同感:“當(dāng)你越是了解老人們的固執(zhí)時(shí),你就越是敬畏大自然的一切神靈,你就有義務(wù)為山林的樹(shù)木祈福。你念的書(shū)是漢人寫(xiě)給你們的,你寫(xiě)的書(shū)是島上的一切贈(zèng)予你的,你也提供了祖先的生活智慧給后代的雅美人。所有的勞動(dòng)的價(jià)值是為自己求生存而勞動(dòng)的人,方是你要尊敬的人,更是你創(chuàng)作的泉源。月懸掛在族人幻想的宇宙間,我的父親們不曾企圖用文字記載族人的歷史,他們只有在腦海里雕刻所見(jiàn)所聞的事物。他們都是七旬以上的老人,但他們的思路清晰得令我心服口服。我唯一的途徑就是努力地創(chuàng)作,才能記錄有海洋氣味的作品,我如是勉勵(lì)自己。”[22]P78-79他在父輩那里學(xué)習(xí)月亮與潮汐的關(guān)系、洋流與魚(yú)群的線索、山林與惡靈的禁忌,這些地方性知識(shí)成為在蘭嶼小島安身立命的實(shí)用技巧和精神依托,夏曼·藍(lán)波安因此也就不僅僅是一個(gè)觀察者與記錄者,更是一個(gè)身體力行者,并且通過(guò)自己的實(shí)際行動(dòng)召喚了一種岌岌可危的海洋民族文化的自我救贖。
“非虛構(gòu)”浪潮滲透到少數(shù)民族散文創(chuàng)作之中,特點(diǎn)是絕少現(xiàn)代主義式的虛擬玄思和尋章摘句的修辭雕琢,而更多本鄉(xiāng)本土實(shí)際經(jīng)驗(yàn)的平白書(shū)寫(xiě)。王小忠(藏族)《靜靜守望太陽(yáng)神》主要集中于他所熟悉的甘南自然與人情的心像留影。他傾心于甘南草原上的草地、寺廟、院落、節(jié)日和風(fēng)物,樸實(shí)文句中透露出親身體驗(yàn)的真切感受。這個(gè)小鎮(zhèn)青年曾經(jīng)是游蕩的行吟詩(shī)人、恬淡的鄉(xiāng)村教師,如今在城里生活卻依然按捺不住對(duì)于草原的懷念,在邊走邊想的旅行中展現(xiàn)記憶與現(xiàn)實(shí)的疊合與落差。因?yàn)閷?duì)生活本身的熟悉,那些帶有偏僻地域風(fēng)情意味的曬佛節(jié)、亮寶節(jié)、香浪節(jié)、采花節(jié)、插箭節(jié)、賽馬節(jié)就脫去了遙遠(yuǎn)與疏離的感覺(jué),而呈現(xiàn)為個(gè)人的經(jīng)驗(yàn)。作者在向一個(gè)不熟悉的外鄉(xiāng)人講述的同時(shí),也浸潤(rùn)了人們共同的感受。故鄉(xiāng)草原曾經(jīng)孕育了一顆敏感而富于反思精神的靈魂,而這顆靈魂回饋的則是在文字中對(duì)它如其本然的自然呈現(xiàn)。“我見(jiàn)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jiàn)我亦多情”,這是一種日常化的情景交融。相較于脫去時(shí)間感的民俗,那些在行走中的沉吟和思索則是最打動(dòng)人的部分。從郎木寺到扎尕那,從桑科草原到冶力關(guān),王小忠對(duì)甘南這塊土地陌生又熟稔,總是能夠發(fā)現(xiàn)那些可能很容易被無(wú)所用心的觀光客所忽略的細(xì)節(jié)。他在首曲黃河的南岸看到兩艘年久失修的破船:“我的身后是無(wú)窮無(wú)盡的草原,我的身前是一覽無(wú)遺的黃河。水的漫漶使岸邊五米之外的草地全積滿了酥軟的泥沙。當(dāng)回望那停泊在岸邊突兀的棄船時(shí),悵然所思:黃河緩緩而去,緩緩而去的河面之上滿是飄動(dòng)著的歲月碎屑。那些載歌載酒,曾經(jīng)泅渡的艱難歲月越來(lái)越蒼茫,生命的堅(jiān)韌和張揚(yáng)也似乎在不斷地萎縮,只剩下苦苦的記憶。”[23]P8時(shí)代與外部世界帶來(lái)了變遷,這是無(wú)法抗拒的時(shí)代潮流,就像他寫(xiě)道的:“落日使人情不自禁地憂傷起來(lái),但我不能拒絕它的到來(lái)。”但是草原無(wú)聲卻又具有柔韌的堅(jiān)守,尕海湖邊“三兩只紫蝴蝶和藍(lán)蜻蜓閃閃爍爍,追逐嬉鬧。黑天鵝似夢(mèng)里飄來(lái)的仙子,輕盈、柔緩,神秘而孤獨(dú)。極目遠(yuǎn)望,水域、蒿草、紫穗,這些隨風(fēng)而動(dòng)的事物仿佛凝固在云朵中。此刻,花前月下、十指相扣的伊人就會(huì)從遙遠(yuǎn)的記憶中蹣跚而來(lái),帶著露水,帶著花香,帶著小紅馬清脆的響鈴,在一片蔚藍(lán)里蹁躚起舞。誰(shuí)能守住如此美妙的瞬間,誰(shuí)就守住了高原盛大的溫暖。”可以看到,盡管在作者心中天堂般的草原已經(jīng)日益為旅游業(yè)和商業(yè)邏輯所侵蝕,但那的底質(zhì)和氣韻仍在,而那些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底層文人的所看所感所思所想,這些文字就是見(jiàn)證之一。
山東的回族作家王樹(shù)理《大道通天》是關(guān)于回族與移民主題的系列散文,立意在“既有記錄整個(gè)族群通過(guò)正信正行的修為弘揚(yáng)圣潔信仰的一面,更注重用鮮活的事實(shí)再現(xiàn)回族兒女與祖國(guó)同呼吸共命運(yùn)、與時(shí)代同振幅的含義”[24]P256。當(dāng)然,文集關(guān)涉到穆斯林諸多兄弟民族,他們的歷史、文化、古跡、風(fēng)俗和當(dāng)代生活,作者以質(zhì)樸的文字表達(dá)真實(shí)的情感與憂思,可謂相得益彰。與王樹(shù)理綜攬古今與中外的題材不同,譚功才(土家族)的非虛構(gòu)散文集《鮑坪》則通過(guò)地理、人物、風(fēng)俗、風(fēng)物不同的篇章,集中筆墨細(xì)描鄂西鄉(xiāng)下一個(gè)小村莊的時(shí)間地理與日常人文。他在開(kāi)篇《在異鄉(xiāng)》的詩(shī)中寫(xiě)道:“在祖國(guó)的河流上/在大風(fēng)吹過(guò)的早晨,在緩緩駛過(guò)的輪船上/雨水讓我想起湖北,洪峰拐彎之處/在粵語(yǔ)南國(guó),在番石榴飄香的中山/在棲居之斗室,在寬大的書(shū)桌前:嘆息。/故鄉(xiāng)是一個(gè)名詞,活在祖先的墓地,活在/女兒出生證籍貫之一欄,活在地圖標(biāo)注之一點(diǎn)/活在我未能完全遮蓋的口音里,活在云橫之嶺南/在嶺南,我一路搬遷的肉體不再遷移/一只蝸牛,背上潮濕而脆弱的家園”[25]P1。與王小忠在本土行走不同,這是一個(gè)生活在廣東中山的 “離散”恩施作家回望故鄉(xiāng)的深情吟唱。但是,“作者沒(méi)有呼天搶地,沒(méi)有申告呼吁,沒(méi)有嘆息哀婉,沒(méi)有涕淚漣漣,甚至很多時(shí)候是充滿幽默和喜感的。他只是默默地、忠實(shí)地再現(xiàn)記憶,盡可能地試圖呈現(xiàn)真實(shí),卻自有一種直指人心的力量如暗潮涌動(dòng),這是節(jié)制的藝術(shù)”[26]P6。在這種節(jié)制中,可以看到皇天后土、鄉(xiāng)土中國(guó)的溫厚穩(wěn)固的根性,也正是這樣的根性使得在面臨當(dāng)代社會(huì)的諸種堪稱(chēng)天翻地覆的變革中的,那種雖然很難清晰定義,卻依然可以感受到的、我們稱(chēng)之為“民族性”的東西,不至于蕩然無(wú)存,反而成為在庸常瑣碎、奔波勞碌的生活中帶來(lái)慰藉的源泉。
結(jié)語(yǔ)
通過(guò)以上的觀察,可以看到現(xiàn)實(shí)在當(dāng)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書(shū)寫(xiě)當(dāng)中,呈現(xiàn)出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不同變體。它們或者竭力平視等同于現(xiàn)實(shí),這是對(duì)來(lái)源于現(xiàn)實(shí)又高于現(xiàn)實(sh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經(jīng)典律令的轉(zhuǎn)移,卻有可能在技術(shù)性的精確中放逐了目的和倫理旨?xì)w,從而使得價(jià)值判斷遠(yuǎn)離,而讓文學(xué)成為一種平面的反映之鏡;或者低于現(xiàn)實(shí),而刻意謀求某種巨細(xì)無(wú)遺的“真實(shí)性”,但是在追影摹蹤上,書(shū)寫(xiě)永遠(yuǎn)跟不上外在世界的紛繁復(fù)雜,尤其是當(dāng)攝影、電視、網(wǎng)絡(luò)已經(jīng)全面侵占到原先許多屬于文學(xué)的領(lǐng)地的時(shí)候,文字的技術(shù)無(wú)法匹敵聲光影像的立體式呈現(xiàn)。如此種種,會(huì)帶來(lái)片段化的現(xiàn)實(shí)書(shū)寫(xiě)。誠(chéng)然文學(xué)中的現(xiàn)實(shí)從來(lái)都是片面的,但在它的片面之中一定要有種現(xiàn)實(shí)感,這種現(xiàn)實(shí)感使得一面鏡子可以照見(jiàn)大千,一滴水可以折射陽(yáng)光。當(dāng)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一種顯著趨勢(shì)就是對(duì)傳統(tǒng)的迷戀,這個(gè)傳統(tǒng)內(nèi)在地包含了族群、地域、宗教、時(shí)代的因素,它往往由于情感認(rèn)同的作用而被賦予了壓倒一切甚至發(fā)展權(quán)的價(jià)值。極端的傳統(tǒng)主義者意味著對(duì)外在不同于自身的一切抱有本能的懷疑、對(duì)理智的自覺(jué)選擇有著非理性的拒斥,那些高聲大嗓、自我標(biāo)榜的浪漫主義者的后裔們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變化視而不見(jiàn),聽(tīng)而不聞,有意背過(guò)臉去,只對(duì)自己一廂情愿的狹隘內(nèi)心說(shuō)話。這只會(huì)使得原本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狹隘化和封閉化。
所有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及其變體其根本的關(guān)切在于“現(xiàn)實(shí)”,這種現(xiàn)實(shí)既包含了信息社會(huì)的媒體呈現(xiàn)的編輯與整合過(guò)的新聞現(xiàn)實(shí),也包括社會(huì)中人所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在經(jīng)歷與體驗(yàn)著的心理與情感現(xiàn)實(shí),更主要的是隱藏在紛繁復(fù)雜的社會(huì)與人物事象背后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性現(xiàn)實(shí)。真正的現(xiàn)實(shí)感要求有一種盧卡契(Georg Luacs,1885-1971)意義上的整體對(duì)各個(gè)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tǒng)治地位,“假若一個(gè)作家致力于如實(shí)地把握和描寫(xiě)真實(shí)的現(xiàn)實(shí),就是說(shuō),假若他確實(shí)是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那么現(xiàn)實(shí)的客觀整體性問(wèn)題就起決定性的作用。”[27]P156即社會(huì)生活中的孤立事實(shí)不能通過(guò)自身得到說(shuō)明,而必須把它作為歷史發(fā)展的環(huán)節(jié),并把它歸結(jié)為一個(gè)總體的情況即與總體相聯(lián)系才可以得到揭示,這樣的話,對(duì)于事實(shí)的認(rèn)識(shí)才能成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認(rèn)識(shí),這才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內(nèi)容本質(zhì)所在。而另一方面,如同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所說(shuō),藝術(shù)之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者,也是一個(gè)藝術(shù)之外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者。現(xiàn)實(shí)主義寫(xiě)作方法不應(yīng)該拘泥于19世紀(jì)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陳規(guī),而要更加現(xiàn)實(shí)的變化發(fā)展出自己的廣闊性與多樣性:“關(guān)于文學(xué)形式,必須去問(wèn)現(xiàn)實(shí),而不是去問(wèn)美學(xué),也不是去問(wèn)現(xiàn)實(shí)主義美學(xué)。人們能夠采用多種方式埋沒(méi)真理,也能夠采用多種方式說(shuō)出真理。我們根據(jù)斗爭(zhēng)的需要,來(lái)制訂我們的美學(xué),像制定道德觀念一樣。”[28]P324盧卡契與布萊希特的結(jié)合,也是我對(duì)近年來(lái)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現(xiàn)實(shí)主義復(fù)歸所抱有的期望,即一方面期待它擺脫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本質(zhì)主義式的執(zhí)念,另一方面希望它不偏執(zhí)于建構(gòu)主義式的幻想,而將現(xiàn)實(shí)感落實(shí)到對(duì)于某個(gè)民族歷史進(jìn)程的體認(rèn)、現(xiàn)實(shí)語(yǔ)境中橫向交往的理解,進(jìn)而全面、立體、完整地進(jìn)行呈現(xiàn)、再現(xiàn)與表現(xiàn)。
[1]羅杰·加洛蒂.論無(wú)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M].吳岳添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2]葉廣芩.采桑子[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
[3]石玉賜.逃漢[M].貴陽(yáng):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
[4]石舒清.遷徙[M].見(jiàn)《灰袍子》.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
[5]馬金蓮.念書(shū)[M].長(zhǎng)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后文涉及馬金蓮作品引文均來(lái)自小說(shuō)集《長(zhǎng)河》,不再一一標(biāo)注.
[6]木妮.雙魚(yú)星座[M].彼岸燈火.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后文涉及木妮作品引文均來(lái)自小說(shuō)集《彼岸燈火》,不再一一標(biāo)注。
[7]曹海英.半杯水[M].見(jiàn)《私生活》.銀川:陽(yáng)光出版社,2013.
[8]馬麗華.風(fēng)之浴[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9]了一容.紅山羊[M].紅山羊:了一容小說(shuō)經(jīng)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5.后文涉及了一容作品引文均來(lái)自小說(shuō)集《紅山羊:了一容小說(shuō)經(jīng)典》,不再一一標(biāo)注.
[10]馬克思.黑格爾法律哲學(xué)批判導(dǎo)言[M].費(fèi)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11]布勒東.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宣楊[M].袁俊生譯.重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0.
[12]楊仕芳.白天黑夜[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
[13]夏魯平.一罐茶[M].風(fēng)在吹.長(zhǎng)春:時(shí)代文藝出版社,2015.后文涉及夏魯平作品引文均來(lái)自小說(shuō)集《風(fēng)在吹》,不再一一標(biāo)注.
[14]次仁羅布.祭語(yǔ)風(fēng)中[M].北京:中譯出版社,2015.
[15]于懷岸.巫師簡(jiǎn)史[M].北京:中國(guó)青年出版社,2015.本文涉及該作引文均來(lái)自此一版本,不再一一標(biāo)注.
[16]和曉梅.賓瑪拉焚燒的心[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15.
[17]轉(zhuǎn)引自k·洛維特.克爾凱郭爾與尼采[J].李理譯.哲學(xué)譯叢,2001,(1).同時(shí)參見(jiàn)洛維特《基爾克果與尼采——對(duì)虛無(wú)主義的哲學(xué)和神學(xué)克服》,收入洛維特、沃格林等著《墻上的書(shū)寫(xiě):尼采與基督教》,田立年、吳增定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91頁(yè)。兩文譯法不同,后者譯為“崩解的時(shí)代”,本文從李理譯。
[18]文培紅.譯后記[A].見(jiàn)阿庫(kù)烏霧.凱歐蒂神跡:阿庫(kù)烏霧旅美詩(shī)歌選[C].文培紅,馬克·本德?tīng)栕g.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19]Wen Jin, Liu Daxian,“Double Writing: Aku Wuwu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Writing in the Americas”,Amerasia Journal, Issue 38:2; Summer/Fall, 2012.
[20]龍道熾.清水江歌行[M].貴陽(yáng):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
[21]沙馬阿古.彝人夢(mèng)[M].沈陽(yáng):白山出版社,2015.
[22]夏曼·藍(lán)波安.敬畏還的神靈[A].冷海情深:達(dá)悟男人與海的故事[C].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2015.
[23]王小忠.時(shí)光里的尕海湖[A].靜靜守望太陽(yáng)神:行走甘南[C].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本文涉及王小忠引文均來(lái)自此散文集,不再一一標(biāo)注.
[24]王樹(shù)理.大道通天[M].北京:線裝書(shū)局,2015.
[25]譚功才.鮑坪[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26]劉川鄂.那一抹揮不去的“鄉(xiāng)愁”——序譚功才鄉(xiāng)土散文集〈鮑坪〉[A].鮑坪[C].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27]格奧爾格·盧卡契.問(wèn)題在于現(xiàn)實(shí)主義[A].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所、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資料叢書(shū)編輯委員會(huì)編、張黎編選.表現(xiàn)主義論爭(zhēng)[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2.
[28]貝托特·布萊希特.論現(xiàn)實(shí)主義寫(xiě)作方法[A].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所、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資料叢書(shū)編輯委員會(huì)編、張黎編選.表現(xiàn)主義論爭(zhēng)[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2.
責(zé)任編輯:杜國(guó)景
TheFlowingRealism:ScanofMinorityLiteraryCreationinRecentYears
LIU Daxian
The return of realism is an outstanding feature of minority literary creation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a scan of contemporary minority novels, poems and essays, we find that the return of realism includes the classical realist techniques of the 19thcentury, an adoption of naturalism, an intake of vanguard literature’s nutrition, and the non-fictional writing based on “reality”. Hence, the realism is a “flowing realism” that takes on a different look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It is argued that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erms of varieties of realism in contemporary minority literature, yet there are risks of flatness, insularity and narrowness; hence, the overall features of Georg Luacs and the realistic features of Bertolt Brecht should be combined so as to advocate an overall, cubic and entire creation self-awareness of 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expression.
borderless realism; flatness; automatic writing; plain poem; non-fictional
I2
A
1003-6644(2016)02-0076-21
* 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重大招標(biāo)項(xiàng)目“《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文庫(kù)》編纂與研究”子項(xiàng)目“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文庫(kù)·研究卷”[項(xiàng)目編號(hào):11&ZD12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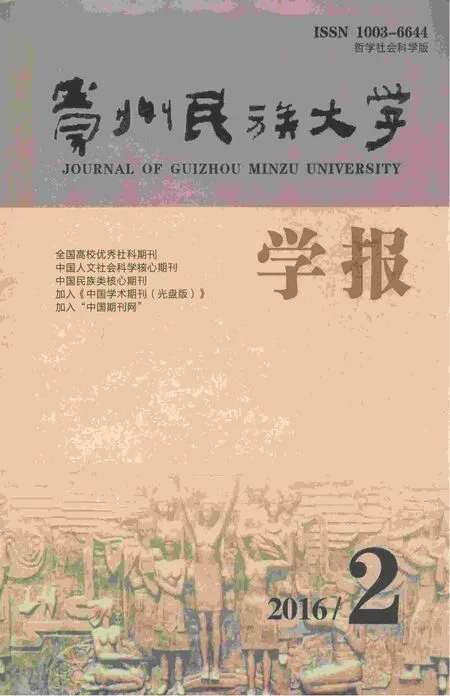 貴州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2期
貴州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年2期
- 貴州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刑事案件陪審員制度實(shí)證研究———基于J 省、C 市部分基層法院的考察和分析
- 司法體制改革的憲法學(xué)評(píng)估
- 貴州民族村寨旅游開(kāi)發(fā)模式利益主體訴求及其效度分析
- 不甘隕落的歌者 ——肅南裕固族民間口頭傳統(tǒng)傳承人調(diào)查
- 略論故事形態(tài)學(xué)理論研究的新進(jìn)展
- Langacker的事件認(rèn)知模型與語(yǔ)言編碼中的工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