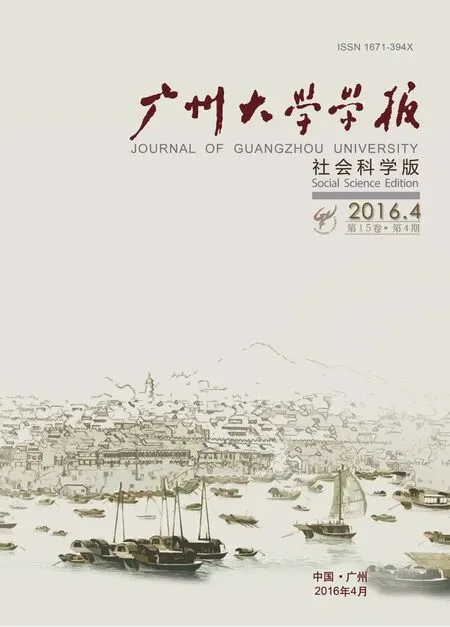現代化進程中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正義原則
鐘明華,鄧欣欣,2
(1.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廣州 510275;2.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廣東廣州 510320)
?
現代化進程中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正義原則
鐘明華1,鄧欣欣1,2
(1.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廣州 510275;2.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廣東廣州 510320)
摘 要:伴隨現代化的飛速發展,城市空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學習和發展的重要地理標識。對經濟發展速度的盲目追求和對城市、城市空間認知的缺位,正在使城市空間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經濟、文化矛盾與沖突最集中的地方。空間與人的發展的失衡,空間的過度同質化,空間的“權力”特征和對自然空間的掠奪,日益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城市空間研究的突出問題。回歸人的需要,尊重城市的本質,包容異質文化的多樣性,回歸城市與自然的生態平衡,將成為我國城市空間正義追問中人們對空間發展的期待。
關鍵詞:現代化進程;城市空間;空間危機;空間正義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經濟建設開啟,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基本實現了經濟現代化,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城市化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當前,城市正在成為社會發展中各種矛盾集中的地方,對于城市空間正義的追問日漸成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和理論視角,空間正義如何實現成為人們期待解讀當前社會關系的思考路徑。
一、現代化進程中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危機
(一)空間與人的發展的失衡
我國空間發展和人的發展出現失衡,主要因為城市空間的稀缺性和城市人口數量迅速增長的矛盾,這一矛盾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城市空間的稀缺性。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農業占地面積較廣,城市發展受到土地資源的限制。當前我國城市空間的發展常常是以犧牲農業用地和農村空間為代價,空間的總量有限,城市空間更加有限。在大城市寸土寸金,土地的稀缺性增加了土地尋租的機會,成為貧富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城鄉關系的緊張也在某種程度上來自空間的稀缺性。
第二,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長。人口數量是衡量一個城市大小的重要因素,很多地理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把人口作為考察城市發展和城市化的重要標志。我國截止2013年有大約13.6億人口,其中城市人口約占總人口的50%,而生活、工作在城市的農民工和農村戶口人員大約有20%。
第三,城市人口素質亟待提高。在大量人口涌向城市的過程中,人口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人的城市化”主要是指進入到城市生活的人們和城市里大多數人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能保持一致或者能跟上城市文明發展的步伐,可以適應城市生活的節奏和文明程度。由于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質和思想素質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個體素質差異較大,并不是所有城市人口都能“城市化”,跟上城市文明發展的步伐。
(二)空間的過度同質化
城市的生命在于城市的個性,在中國的很多城市里,連鎖商業模式和品牌連鎖機構已經成為城市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的意義被過度同質化,不僅如此,很多極富特色的傳統文化、文化遺產、風俗習慣也在被逐漸弱化,忽視了不同城市空間發展的個性和特色。根據列斐伏爾對資本主義社會空間擴張的理論分析,這是資本主義通過空間的擴張,占據空間、生產空間以減輕社會的內在矛盾,人為創造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條件的一個重要途徑。
可以說,中國城市空間發展的同質化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原因有二:其一,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對經濟增長速度要求較高;其二,我國的城市發展之路屬于摸著石頭過河,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我國長期處于農村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狀態,進入城市化的時間較晚,對于社會主義城市的建設缺乏經驗,進入城市化進程后,經濟建設盲目地追究速度,忽視了城市的差異性建設,特別是城市精神面貌和城市文化特色等無形城市空間形態建設。
(三)空間的“權力”特征明顯
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是政治性的。空間不是一個被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學的對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戰略性的……是一種完全充斥著意識形態的表現。”[1]我國城市空間作為一個整體系統的存在,其發展離不開政府的總體規劃和制度設計,具有較強的政治性。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計劃經濟體制,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的生產、資源的分配和產品的消費等社會行為幾乎都來自指令性計劃。這種傳統的經濟模式在建國初期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隨著我們經濟的迅速發展呈現出計劃與實際脫節,產需分開,效率低下,動力不足等弊端,逐漸被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但是計劃體制的思想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著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進而影響城市空間的“設計”。我國的政治制度長期呈現出“行政化”“集權化”的“權力”特點,城市空間的權力過度化使空間變成某些人的“空間”,留下深刻的“政治”烙印過度的“權力”印記,會使城市空間失去城市的本來意義。
(四)對自然空間的掠奪
城市空間的不斷擴張中,人們似乎低估了自然的力量。山林、平原、湖泊、耕地、城市用地這些空間的自然形態被城市化膨脹的人口,硬化的土地和到處蔓延的大工業工廠慢慢吞噬,生態危機的解決已經刻不容緩。在城市化的發展中,人口不斷暴漲,增加了有限資源的負擔,城市的擴張不斷地侵蝕著土地資源,“據估計,2000年全國已有5 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在2001~2005年4年間,全國又凈減少2 691萬畝耕地,按勞均4畝耕地計算,相當于增加了670萬農業剩余勞動力。如果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到2020年又將有6 000萬農民失業和失去土地。[2]城市空間不斷對農村空間進行侵占,城市空間本身的擁擠狀況也沒有得到改善。住房緊張,道路擁擠,就業困難,環境污染,這些問題都困擾著城市空間的發展。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認為:“市場社會是不可能持續的,因為它會對人類賴以生活的自然與人文環境造成致命的破壞。”[3]城市空間的發展如果是以生態環境的犧牲為代價,就必定要面對大自然無情的報復。
二、現代化進程中我國城市空間正義的詰問
面對城市空間的危機,我們也不得不思考,我們需要怎樣的城市空間?在借鑒和參考西方空間危機及其發展的基礎上,我們試圖回到城市空間,開啟對城市空間正義的詰問。
(一)城市空間是誰的空間:人還是“物”化的人
馬克思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人的生存狀態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4]。“物化”的意義在于知識形態轉化為物質形態成為現實的生產力。但是,“物化”也可能會使人異化,使人與人的關系變成赤裸裸的物的關系。馬克思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對象化活動,人的類本質發生異化是資本不斷增值的結果,資本的增值使人逐漸喪失了“主體性”,成為資本和商品的奴隸,商品交換本來應該是人與人的關系,但是在資本和利益的驅動下,卻顛倒成為物和物之間的關系,物對人的依賴性變成了人對物的依賴性。
城市空間是“屬人”的空間,人作為手段和目的統一于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出現的初衷是為了人們能更好的生活,對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發展的目的性追求應是城市空間存續的價值內涵。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人們的物質財富不斷增長,在城市空間的發展過程中,人的主體性隨著對“物”的依賴,開始弱化或喪失。城市空間為人們提供了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發展機會,同時成為資本積累的物質基礎。馬克思說,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人的目的性的實現離不開作為手段的人的對象性活動,手段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當手段是“物”時,它的價值在于對于人的需要的滿足,即是對人的有用性,一旦“物”成為人的目的性,城市空間就會變成對“物”的追求,人與人的關系就會變成赤裸裸的交易關系,人的手段價值會被擴大,甚至濫用,投射到城市空間上,就會倒置城市空間和人的發展的關系。
(二)城市空間的張力:同質還是多樣
城市空間作為城市中政治、經濟、文化和人的整體反映,既有同質性又呈現出多樣性。多樣性主要表現為:城市空間由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層級組成,不同利益的差別使社會群體在城市空間中呈現出不同社會需求,表現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價值理念和組織方式;不同社會意識形態的國家城市空間有不同的城市個性,有不同的文化樣態和價值理念;相同社會的意識形態中,城市空間也因歷史、地域、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
我國城市空間的現狀正如我國當下的社會現實和社會狀況,因為不同物質利益群體的存在產生差異。馬克思說:“人類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5]我國當前差異性社會的現狀是:“人民內部根本利益一致或趨于一致、而局部利益和當前利益則存在著各種差別、人民仍然分成各個階級和階層的社會。”[6]因為統一性和差異性的共同存在,在城市空間的發展上應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求同是因為我們的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社會,人們的共同目標一致,同樣生活在城市空間中的人應該機會均等,受到公平對待。承認差異,是因為我國目前的現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且長期會處于這個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我們的生產力水平還不高,社會發展的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的產業結構之間還存在很多差異。應該對不同地區、不同的行業、不同的領域、不同的產業給予不同的差異政策。城市空間作為一個整體,需要包容差異、和諧共進,又要在統一的目標下完成空間整體的發展和進步。
(三)誰在影響城市空間:資本還是權力
城市空間中誰在影響或者主導著城市空間發展的進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發展史告訴我們,在很長時間追求“價值”和“利潤”的機器大工業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化進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到20世紀60年代基本完成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特征的第一次現代化,在開始向第二次現代化過渡的過程中,城市空間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機器工業大生產和對資本的無限追求。國家權力規定了法律、私有財產、契約和貨幣安全并且擁有暴力機構的制度框架,保證進行資本主義活動時,有穩定的契約法則和法律保證,在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時,監管框架能夠處理階級沖突和調節不同資本集團的利益訴求。國家對于制度的制定和對暴力機構的擁有是權力的體現,從一開始,資本和權力就在城市空間政治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我國建國初期直到20世紀70年代,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下,“權力”深刻地影響著城市空間的發展。比如我國的戶籍制度,分割了城市和鄉村的人口,區分了“非農業”和“農業”兩類不同的戶口之間在就業、教育、社會保障和生活福利等社會資源的不均衡分配。可以發現,當時戶籍制度已經成為一種制度和權力在城市空間分配中的象征,這種制度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市空間的發展。現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們對“資本”的盲目崇拜,資本“這東西,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7]。物欲的膨脹和精神的匱乏使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開始不協調,人與人的關系開始物化,資本和權力成為影響城市空間發展的重要因素。
(四)城市空間的生態博弈:人與自然孰輕孰重
20世紀60年代之后,曾經一度,人們感受到城市空間的萎縮和倒退。隨著城市經濟的衰退、企業的破產、工人的失業、貧富差距的加大,人們開始對城市失去信心。例如戰后的美國人口緊急下降,城市的郊區化發展,汽車工業的衰退,城市病的頻出,貧富分化的加劇等。中國在近幾年也出現了嚴重了城市問題:貧富分化,城市貧困,城市犯罪,城市發展的瓶頸制約等。最重要的是,城市的擴張是以工業化對城市生態和生態系統的侵蝕為代價的,而這種不計后果的發展帶來的是更為可怕的生態危機。“城市性”不能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被提到重要的位置,這就是“城市的生態性”。
人與自然的生態競爭歸根到底源于資本化利益驅動,而這種以敵對開始的不良關系,讓雙方的利益受損,生態資源日趨緊張,生態赤字日益嚴重,空間的分配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產生不公平、不正義的“空間分配結構”。城市空間中,資源是有限的,對有限資源的不平等占有和分配是造成環境和社會敵對的主要原因,究其根源還在于政治經濟的原因。人們創造了城市,但是肆意地濫用城市資源,破壞城市自然環境,忽視對城市自然生態的關注,會使人類自身的利益受損。自然和生態也已經成為城市空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隨著城市空間的演化,自然生態正在和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方向與步伐保持一致。哈維就此提出了環境正義的概念,他指出要和環境合作,這樣“才能獲得先發制人的環境主動性,所以,環境正義問題就不得不與長期的可持續性探索結合在一起,這在某種程度上實際地適應了當代主要生態問題的國際性需要”[8]。人們對生態欠下的債務要償還,但是這種償還是以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為前提的。
三、城市空間正義實現的原則
城市空間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空間,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關系在空間上的整體突現。哈維指出,解決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危機應當結合社會空間和社會關系,從地理、空間的維度尋找解決的途徑。不僅關注分配的結果,還強調公正的分配過程。在當下我國討論空間正義的語境中,空間正義“更多是意味、指向或者說希望一種社會正義,希望在社會關系層面,在不同的主體之間具有相對平等、公平的空間”[9]。我國城市空間正義的實現應把握以下原則。
(一)城市空間正義應體現“以人為本”
城市空間是人的空間,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城市空間建設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會使空間的人性張力得到豐富和充實。近代工業化以來,由于對經濟利益的過度追求,城市空間中出現了很多違背人本的現象,如:城市規劃的失衡、城市空間結構設計的錯位、城市功能定位不準確等,并引發土地資源的過度開發、社會治安混亂、生活壓力增大、人際交往的異化、理想信念的缺失、人們幸福指數偏低。這些問題的存在,與城市發展的本質相背離,不能滿足人的發展的需要。
馬克思認為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怎樣的社會關系決定著怎樣的人。在以商品經濟和經濟利益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社會關系主要表現為“金錢關系”,而人也變成了“物”。在我國當代城市空間的發展中,受西方“物欲”經濟的影響,“消費主義”和“金錢關系”成為一種非主流的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年輕人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品質。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的需要體現了人們的本性,而本性又是人本質的表現。人對自己的需要是從“自己出發”去發現的,人的需要從最基本的物質需要開始,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的不斷發展,在社會關系中得到社會交往的滿足和對自己的精神需求,是人的需求的更高需要。人對城市空間的建造、占有和發展,會因為各種不正義的狀況發生而突顯對正義的渴望。城市作為各種文明要素的系統構成,城市應該滿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讓更多的人享受到公正和平等,它的精神內在在于“以人為本”,體現人的需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是空間的更大正義。
(二)城市空間正義的價值在于城市意義的回歸
城市作為一個特定的空間有機體,它的公平正義是維持其繼續繁榮、穩定發展的前提,城市性是“城市在歷史發展中所生成與顯現的城市的本質;在理念與實在的統一中,城市是人的社會性、創造性的現實化、經驗化、空間化,城市是人的社會性、創造性在空間中的可經驗性、可感受地具體生成、聚集與轉換,也就是各類文明要素的空間聚集于系統轉換”[10]。城市性和城市的發展相契合,空間正義的探討是為了解決空間中的危機,重建空間正義的倫理價值。
列斐伏爾指出,城市化的過程也是為城市權而斗爭的過程,社會的城市化使社會的基本存在和運行方式都不能離開城市存在,過去在“工廠一個場所進行的工人和資本家的斗爭,已經轉移到交通建設決策部門和那些受到這些決策影響的工薪窮人之間的斗爭,轉移到城市化過程中那些被動城市化的居民和那些主持城市化、甚至那些通過城市化大發不義之財的開發商之間的斗爭”[11]。列斐伏爾認為控制了城市權就掌握了城市發展進程的權利,為資本家制造更多的“空間生產”的機會。城市化作為資本主義所有方面的對立統一體,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貪婪性中呈現出城市的異化。
哈維進一步指出,城市社會空間生產的民主管理權是城市權的重心,城市是政治、制度、文化在規劃上的總體體現,城市空間問題的解決應該從內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進行調整,同時通過城市空間的設計從形式上消解城市空間內容的矛盾。也就是說,城市雖然是人工建成,但是城市具有其本來的意義,對城市空間正義的追求,應該充分體現城市的現代價值和文明理性,城市空間應該回歸本來的規劃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成為社會空間和人的關系的空間。
(三)城市空間正義應尊重異質文化的多樣性
隨著全球化的蔓延,在空間橫向延伸和空間結構重組不斷引發意識形態的困擾和價值觀多元化的沖突時,人們不禁會進行城市空間正義的文化追問。
20世紀80年代,世界的冷戰體系成為歷史,塞繆爾·亨廷頓指出:“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人們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于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的層面上認同于文明”。[12]文化的流變和斷裂,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時有發生,全球空間的開放已經打亂了人們認同的固有模式和固有格局。
在當代的城市空間中,現代性和后現代的對話不斷引發意識形態領域的空間反思,全球化帶來的空間擴張開始產生均質化的趨勢,但是異質文化并沒有因為它的多樣性而更快地被傳統認可,反而激發了城市空間多元價值的碰撞和沖突。可以發現每一次社會轉型都會伴隨社會文化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激烈碰撞,每一種文化和意識形態思潮所代表的社會利益都希望占領到政治的制高點,而城市空間就成為激烈碰撞的空間載體。
在城市空間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國哥特式建筑高聳入云的尖頂,美國新古典主義自由又不失傳統的田園別墅,巴洛克建筑的自由動感和離經叛道,拜占庭式鮮明宗教色彩的高大穹頂,洛可可超越真實的夢幻空間結構等。這些外在的面貌都顯示出不同社會利益集團在社會空間中曾經的利益權衡和權力彰顯,以及他們對于生活的理解和文化藝術的呈現。
列斐伏爾用“文化革命”一詞來描述城市空間的文化體驗,他認為社會的發展在城市空間并通過都市社會的實現得以感受,對文化的詮釋將成為城市空間日常生活的根源追問。城市空間因不同的文化觀念、文化行為、文化審美、文化信仰和文化傳統帶來空間價值的不同判斷標準,城市空間正義的實現,應回歸城市空間的日常生活,在堅持傳統的基礎上,尊重異質文化的多樣性。
(四)城市空間正義的實現應回歸其生態性反思
過速的城市擴張常常以工業化對城市生態和生態系統的侵蝕為代價,城市病的頻出使“城市的生態性”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近年來為國人所熟知的“霧霾”已經成為城市空間環境惡化的代名詞,霧霾的產生源自使每天84個自然村消失的城市化和獲利遠遠小于危害的各種大工業的擴張、工業產品的產生和對GDP的盲目追求。一旦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失去本身應有的積極意義,變成“政績的化妝品”,就會有“形象工程”“城市包裝”和腐敗滋生的溫床。城市空間正義應該建立在城市的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的基礎之上,一味地追求經濟的過速增長已經成為“單向度”的發展模式。
城市空間中對有限資源的不平等占有和分配是造成環境和社會敵對的主要原因,人與自然的生態競爭歸根到底源于資本化利益驅動。城市空間正義危機之一,就是城市空間的發展是以對自然生態的無情掠奪為代價的,生態資源日趨緊張,生態赤字日益嚴重。工業化雖然極大地促進了城市空間的繁榮,但是城市化不代表工業化,城市空間的發展也并不是工業化或者資本化。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城市空間的發展正在回歸生態理性,正義的環境不僅是環境問題,而是城市空間生態現代化的追求。環境的管理將成為城市空間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空間的分配不僅體現在人與人之間,還包括在人與自然之間,城市空間正義回歸生態理性,是空間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和正義的重要保證。
【參考文獻】
[1] 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M].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6.
[2] 陸大道,等.2006年中國區域發展報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5.
[3] 段進軍,倪方鈺.關于中國城市社會空間轉型的思考——基于“社會—空間”辯證法的視角[J].蘇州大學學報,2013(1):49-53.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6] 任平.論差異性社會的正義邏輯[J].江海學刊,2011 (2):24-31.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60.
[8] 戴維·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M].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33-435.
[9] 陳忠.愛德華·索亞.空間與城市正義:理論張力和現實可能[J].蘇州大學學報,2012(1):1-6.
[10]陳忠.城市意義與當代中國城市秩序的倫理建構[J].學習與探索,2011(2):1-6.
[11]吳細玲.城市社會空間與人的解放[J].哲學動態,2012(4):26-33.
[12]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劉緋,張立平,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5.
[責任編輯 林雪漫]
The Principle of Spatial Justice in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ZHONG Minghua1,DENG Xinxin1,2
(1.Marxist School,Sun Ye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China;2.Finance&Economics Law School,Guangdong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320,China)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ce is accompanied by China's modernization.Urban space be-comes an importan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which indicates People's daily life,learning and development.The blind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lack of awareness about urban,make the urban space an area with most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of politics,economy and cultur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The imbalance of space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excessive homogeneity of space,"power"feature of the space and plunder of natural space become prominent issues of urban space research.Return to people's needs,respect for the essence of city,tolerance of diversity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and ecological balance between city and nature will be people's expec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ace in the inquiry of urban spatial justice.
Key words:modernization process;urban space;space crisis;spatial justice
作者簡介:鐘明華,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倫理學研究;鄧欣欣,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廣東財經大學副研究員,從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人的發展與現代化、高等教育研究。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GD14CMK01)
收稿日期:2016-03-02
中圖分類號:B82;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394X(2016)04-00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