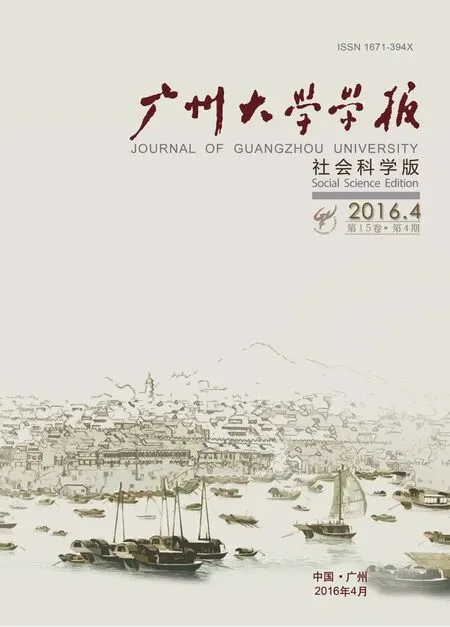“負面解讀”治理與公信力重塑問題探析
李 宏
(中共大連市委黨校應急管理教研部,遼寧大連 116013)
?
“負面解讀”治理與公信力重塑問題探析
李 宏
(中共大連市委黨校應急管理教研部,遼寧大連 116013)
摘 要:當前在各種情緒相互沖撞且日趨復雜化的輿論場中,日漸盛行的“負面解讀”現象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從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層面考量,“負面解讀”盛行所折射的,最終仍然是“社會化媒體環境”下相關主體頻繁互動的過程中,“不信任感”日益上升的問題,各種負面情緒及其背后的不良心態在根本上主要來源于“公信力”的普遍缺失。為此,有效治理“負面輿情”與重塑公信力的對策主要在于:充分發揮“法治”的引領效果和規范作用;增進政府、媒體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全面、系統地開展媒介素養教育與培訓;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構筑共同的精神家園。
關鍵詞:公眾輿論;負面解讀;輿情生態治理;公信力;對策
中國正在由網絡大國向網絡強國邁進,但社會化媒體環境的形成與發展,不僅給信息的傳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時也由于前所未有的“即時互動”和由此強化的“混沌效應”,而給當前的“輿情生態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結合對正在經歷話語體系被解構和重塑,且日趨復雜化的國內輿論場的觀察與思考,透過以各類“段子”為代表的各種負面情緒的宣泄與表達現象,我們特別注意到并總結出了“負面解讀”的有關問題。
一、“負面解讀”及其基本特征
眾所周知,“負面”與“正面”是相對而言的,就公眾輿論而言,大多數時候都是可以用“消極”和“積極”予以分別替代的,主要用來反映公眾對待特定公共事務和熱議話題的一般態度。著名學者林語堂曾提出,從整個新聞傳播與輿論發展的歷史來看,“中國新聞史就是民間輿論和中國當權者之間的斗爭史”,“公眾批判”不僅由來已久,而且使得“中國人民對于統治階層來講是偉大的諷刺家”。[1]不過,本文所關注的“負面解讀”,主要是指公眾針對通常所關注和熱議的公共事務與話題(典型的如涉及民生的問題,官員貪污腐敗現象,以及企業的制假售假行為等),基于個人的偏好與判斷而形成的,傾向于從消極的方面來予以闡釋的各種觀點和言論的表達行為和現象。這其實也就是說,我們更為關注的事實上是很早就由法國社會學家勒龐(LeBon)所提出來的,諸如“沖動、興奮”“暗示、輕信”“夸張、單純”“偏狹、保守”和“道德色彩”等情感因素[2],對公眾輿論形成的顯著作用。例如,一種比較典型的情況是,當有關某地或某部門貪腐案件進展的新聞報道出現時,多數社會公眾一般會對當前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和常態化表示認同和贊賞,但同樣也會有一部分公眾會認為它只是“九牛一毛”或“冰山一角”,并可能對特定的案件中是否“另有隱情”表示懷疑。這其中,部分公眾所持有的“懷疑”態度,往往并不是以掌握充分的證據為前提。而如果始終對特定事務抱有“相反”的看法,并總是傾向于在各種場合發表類似的意見,就形成了本文主要關注的“負面解讀”現象。
事實上,2010年時美國的“尼爾森調查公司(The Nielsen Company)”就發表過與此相關的調查結果,并在國內引起過短暫的熱議與討論,其結論之一就是亞太地區的各國網民之中,唯有中國網民發表負面評論的意愿大大超過了正面評論,具體比例為62%,而全球網民的這一比例為41%,這被一些國內學者總結為“壞消息綜合征”[3]。不過,僅僅注意到這種現象顯然是不夠的,而且這類現象的蔓延也絕不僅是導致“真相迷失”。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當前國內熱點輿情中的情感傾向,一直在沿著“兩極分化”的方向發展。如新華網輿情監測系統對2015年前三季度熱點輿情事件的最新統計與分析結果表明(見圖1),第三季度“含有惡性犯罪、非正常死亡、貪腐、社會失德等負面情感傾向的新聞占比為27%”,屬于“社會問題治理、重大案件偵破、社會先進事跡表彰等正面新聞占比為29%”。[4]

圖1 2015年前三季度熱點輿情的情感傾向① 作者依據新華網輿情監測分析中心發布的2015年第一、二、三季度“熱點輿情報告”的統計結果整理得到。
從被譽為“公關之父”的愛德華·伯內斯(Ber-nays)的觀點出發,作為公眾輿論組成部分的“負面解讀”,顯然兼具“冥頑不化”和“可被塑造”的兩種相反特性,而即使人們對于某個問題一無所知卻也“總是會對該問題形成確定和主動的判斷”,在今天也仍然是“協調社會關系、形塑社會認同”所要面對的一個基本事實[5]92。這一點,至關重要。為此,筆者以為,從基本的屬性、來源、形式及結果等方面看,“負面解讀”有如下四個基本特征。
第一,“負面解讀”行為和現象本身首先依然是“中性”的,因其本質上仍是屬于公眾輿論的組成部分,即“意見主體對客體作出的反應而非對客體本相的認知”[6]。當然,如果有涉及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的行為,如制作和傳播虛假信息和謠言以及惡意中傷誹謗他人等,就不能將其簡單歸屬于該范疇。
第二,“負面解讀”是公眾針對特定公共事務與話題思考的結果,反映了一部分社會成員對經濟社會發展形勢與問題的關注,盡管包含了大量“并非建立在調查研究和邏輯推斷基礎之上”的“教條化表述”[5]96,但其所承載的負面情緒的確表達了部分社會成員的不滿,而其得以傳播和流行則反映了某些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第三,“負面解讀”的形式是多種多樣且動態變化的,它同樣符合麥克盧漢(McLuhan)所提出的“媒介即訊息”特性[7],并有待我們展開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其具體形式的變化主要與大眾傳播技術與平臺的快速發展有關,如從較早的短信息(純文本)發展到后來以“微博”與“微信”(圖文并茂乃至可以包括視頻等)為主渠道,而帶有強烈感情色彩(如夸張)與敘事結構的各類“流行語”與“段子”,則成為最為常見和流行的表達形式。
第四,“負面解讀”并非一定就是“負面新聞”,也并非必然地只會傳遞“負能量”,而是同樣可以具備“正能量”與“正功能”。眾所周知,有關“負面新聞”的辨析與討論,其實可以說由來已久,而多數專家學者也都認為它在很多時候都導致了“含混”,并且失之偏頗。同時,如果公眾就某些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產生質疑、提出不同見解,有時候也能夠起到推動變革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積極效果。
二、“負面解讀”盛行根源于公信力的普遍缺失與諸多不足
“負面解讀”的盛行可謂是有目共睹,但其影響與關鍵卻并非是導致“真相迷失”那么簡單,因為無論是公眾對熱點事件的關注、意見表達與情感宣泄,還是帶來了日漸復雜化的輿論場格局,以及導致不安定因素增多甚或強化負面情緒等等,都只是對現象本身的概括或者僅僅是表面上的結果而已。從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層面來考量,“負面解讀”盛行所折射的,最終仍然是社會化媒體環境下相關主體頻繁互動的過程中,“不信任感”日益上升與“簡化復雜性難題”的累積問題[8],而各種負面情緒及其背后的不良心態在根本上主要來源于“公信力”的普遍缺失。
(一)社會矛盾沖突的集聚、交織與凸顯導致了不信任感的增加
眾所周知,我國當前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重要的基本國情,也是我們探究各種社會現象與相關問題的出發點和必然基礎。這意味著“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相對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始終是普遍存在的,諸如就業、教育、醫療和養老等社會問題必然也會長期存在。尤其是作為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人口大國而言,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上述涉及民生領域的各種社會問題不僅持續存在,而且迫切需要找尋具體的出路與解決辦法。例如,隨著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體系的建立健全,當前我們也正面臨著巨額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這個問題不僅早已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與熱議,甚至還有少數人開始質疑現行的社保體系。由于政府不再如傳統計劃經濟時期般實施“包攬”政策,而是需要與企業和個人實現“三方共擔”,就有人開始將其總結為“甩包袱”或“與民爭利”,并用各種形式進行歪曲性的解讀。筆者就近年常見的一篇名為《社保真相》的帖子在“凱迪”和“天涯”兩大論壇進行了查詢,發現該文最早出現于2011年12月,其運用似是而非的“計算”得到了現行社保制度“劫貧濟富”實為“謊言”的結論。2015年初,由于“延遲退休”成為熱議話題,于是該文又被網友原封不動地貼出,并得到了萬次以上的點擊量。[9]
從現階段我國最容易引起公眾關注的問題來看,較為常見的一些問題往往都有著典型的階段性特征,這些問題所隱含的矛盾沖突相互交織,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因制度不健全或需長期治理而得到凸顯。例如,一項基于2012~2015年間我國社會化媒體與輿情發展的研究表明,“食品安全”“環境保護”和“反腐倡廉”是當前社會普遍關注的三大議題[10]。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引起普遍關注和廣泛討論的議題均帶有較強的階段性特征,它們在與普通公眾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同時,也都是與現階段相關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并且需要系統地加以治理等緊密相聯。由于類似的矛盾沖突既牽涉各個相關主體的利益,同時也難以立即得到有效根治,于是自然就產生了“不滿”和“不信任感”上升的問題。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源于此而產生的各類“負面解讀”現象,可以說是改革與發展過程中的“陣痛”之一。
(二)公眾的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意愿借助信息技術發展實現驟升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在物質生活條件和健康水平等方面得到快速提升的同時,也逐步提高了對所應具備的政治法律地位與所應承擔的權利義務關系的自我認識,并開始嘗試基于活動主體和公共關系來構建心理認同與理性自覺。因此,隨著公民意識的不斷覺醒,公眾對于涉及公共事務的相關議題逐步展示出了更為強烈的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等意愿。在這個過程中,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適逢其時,并極大地刺激和強化了公眾的上述意愿。實際上,“互動式社會”的形成不僅意味著“真實虛擬的文化”及可能的“受眾的終結”,[11]4同時也意味著由于信息技術革命對所有人類活動領域的全面滲透,而導致分析當代正在成型的新經濟、社會與文化之復雜狀態,除了信息技術本身再無其他任何適合的“切入點”[11]308。
在信息化時代全面到來之后,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加快了公眾對公共事務和公共議題展開討論并參與決策的進程,而網絡渠道的相對通暢,甚至使得中國的網絡輿論立即呈現出了“井噴”之勢。可以看到,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每一次的互聯網技術發展與進步都在降低普及成本的同時,極大地促進了網絡輿論的“空前發達”。例如,有人認為2003年因“孫志剛收容遣送致死案”的網民參與討論,應被視作中國的“網絡媒體元年”[12],當時也正好是“寬帶”開始普及的時期;而2008年被稱為“網絡問政元年”,其時也正好是“光纖”得到發展,中國的網民人數首次超越美國而躍居世界第一位。后來,“微博平臺”的出現,則使得一系列重大突發事件的相關信息,都開始通過“自媒體”渠道得以首先發布,恰如2011年的“7·23動車追尾事故”和2015年的“天津8·12爆炸事故”等所展現的那樣。
截止2015年6月,我國的網民人數已經達到了6.68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8.8%(見圖2),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更是造就了信息獲取類應用朝著“個性化”和“精準化”方向快速發展的趨勢。與此同時,結合現階段我國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和基層民主的不斷擴大,公眾參與公共事務討論與決策的渠道日益多樣化,而信息化與網術的發展則顯然是大大地便利和推動了這一發展進程。為此,包括“負面解讀”在內的各種參與行為和意見表達,也是互聯網發展和“大眾麥克風時代”來臨之后的必然產物。

圖2 中國網民規模與互聯網普及率(2008~2015)① 作者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4-3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整理得到。
(三)政府機構、媒體與公眾之間的溝通不暢導致了“塔西佗陷阱”
政府的合法性源自人們對權威的認同,并表現為公眾的信任與服從[13],而無論是基于“政治倫理”“經濟效率”,還是“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何種考量,有效的溝通始終都是建立“信任”的基石。在矛盾沖突聚集和互聯網快速發展背景下,政府機構、媒體與公眾之間的溝通不暢,則是導致公信力缺失乃至“塔西佗陷阱”狀態的重要原因。這也就是說,大量“負面解讀”行為和現象的產生,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而及時有效的溝通卻因為體制不健全、形勢急劇變化及應對經驗匱乏等而開始變得愈加困難。當溝通失敗或者處于低效率的狀態時,部分公眾就會傾向于質疑政府部門的相關態度與行為,或者夸大自身由于各種原因而面臨的風險水平,而某些媒體的不恰當加入與推波助瀾則很可能會導致政府部門徹底陷入公信力危機。
例如,近年來反復出現并始終困擾多地的“PX項目恐懼綜合征”,就是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信任危機的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自2006年以來,廈門、大連、寧波、昆明和廣東茂名等地,均陸續出現了總體上處于“安全可控”范圍的PX項目難以落地,甚至遭遇不了解真相的民眾經“網絡號召”后大量聚集予以反對和抗議的情形。事實上,與之類似的“核電”“垃圾焚燒”和“磁懸浮”等項目,都較為普遍地存在著“上馬——抗議——停止”的劇情,而“一鬧就停”似乎成為了一些地方應對民眾抗議的必然選擇[14]。于是,有關“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NIMB)”的傳染性,以及整個過程中某些媒體的催化和影響[15],已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思考和研究,而這其中的根本問題其實也就是一個如何加強有效溝通和解決相關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之所以未能有效破除“一鬧就停”的尷尬局面,既有礙于體制因素而導致的溝通不充分的原因,如涉及多個相關部門和主體的協調,也有形勢變化太快和應對經驗不足而導致的溝通不及時和低效率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部分媒體的“推波助瀾”也是應當引起充分關注的重要方面,因為媒體的傾向和態度會對溝通過程與結果產生巨大的影響。例如,回過頭來看,作為一場并不十分嚴謹的科學邏輯的“演說”,2015年2月某知名媒體人士有關霧霾治理問題的意見、看法和觀點,在促進民眾環保意識覺醒的同時,由于傳播了一些實際上仍然模糊的理念與邏輯,也誤導了一批為數不少的社會公眾。[16]顯而易見的是,暫且拋開“議程設置”不談,結合“負面解讀”盛行所反映的潛在問題,究竟是否有效地化解了信息不對稱局面,應當成為判斷溝通有效性的一個最為核心的標準。簡而言之,只要這種局面沒有得以真正破除,“負面解讀”現象就必然會持續,而公信力危機也就不會真正消失。
(四)經濟、政治與道德領域的某些失范行為直接損害了公信力
誠如美國社會學家默頓(Merton)所言:“失范”的本質就是“規范的缺席”,當社會把成功的標志看作是財富的積累的時候,反社會行為就是一種正常的反應[17]。當前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轉型時期的中國,由于在經濟、政治與道德等領域存在著某些失范行為,不僅直接損害了整個社會的公信力,而且也給“負面解讀”呈上了一些最為直接同時也異常豐富的“基本素材”。無論是一些普通公眾出于表達不滿情緒的目的,還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出于“唱衰”和“抹黑”的動機,都會將目光聚焦于上述各領域中的一系列“失范”行為,并據此炮制和傳播一些“段子”,以便達到直至超越“取悅公眾”的效果。
例如,在經濟領域,假冒偽劣產品的橫行,直接侵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而且在導致企業信譽度降低的同時也損害了產品質量監督機構的公信力。于是,一旦有媒體進行針對性的“曝光”,立即就會導致公眾輿論的一致譴責,而“在情感區(Sentiment Area)內,公共事務是不容爭辯的”[18]57。在2012年央視某主持人微博爆料“老酸奶”事件中,該主持人甚至以“不細說”的表述,給公眾一種“諱莫如深”或“欲擒故縱”的印象。[19]在這種背景下,“2012,皮鞋很忙”的惡搞段子迅速出爐并受到網民的極力追捧,“中青在線”對相關輿情的監測結果表明,在曝光后的15天里就有1.84萬篇新聞、1.91萬篇論壇帖文和1.25萬篇博文與之相關,閱讀量超過1 300萬人次,回復量也達到了26.5萬次;[20]在政治領域,少數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和一些司法不公正現象,無疑是導致“公信力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部分網民和媒體會就此抓住其中的一些細節來提煉出所謂的“特征”,典型的如“房叔”“表哥”“家中現金過億”,以及后來的“雅賄”等等。“負面解讀”的關鍵問題則在于依據這些特征來進行“臉譜化”和“污名化”,最終演變成只要是官員符合戴名表、有多處房產或其他表明身家豐厚的特征,就一定是“貪官”;在道德領域,失范行為與負面解讀之間,似乎已經形成了相互促進的發展趨勢,如近年來一直都流傳著有關“扶摔倒的老人是炫富行為”的各種段子,它們在表達公眾有關“道德底線”的看法的同時,似乎也起到了某種“警示”的效果。[21]
三、有效治理“負面解讀”并重塑公信力的對策
至此,我們不難明確的是,“負面解讀”的盛行,并不能簡單地被歸結為“負面輿情”,更不能籠統地將它概括為源于非理性而形成的“戾氣”[22],因為這其中實際上包含了技術發展、時代進步、社會轉型,以及不同主體間互動與溝通等多方面的復雜因素,所以需要在專門地予以充分關注的基礎上,結合公信力缺失這個根本問題來展開有效的治理。
(一)制度規范:充分發揮“法治”的引領效果和規范作用
目前,從整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大局來看,我國正面臨著“國內外形勢的深刻復雜變化”與“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依法治國”不僅是當前發展戰略布局的重要核心與基礎,同時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負面解讀”盛行的背后所折射的“信任危機”,從根本上來說,只能通過持續深入地推進“依法治國”戰略來予以徹底化解。因為,只有讓一切都真正走在法律規范所允許的軌道上來,才能夠真正從源頭上切斷“基本素材”的輸送,才能夠減少和化解社會轉型過程中累積起來的各種矛盾與風險,才能夠徹底扭轉公信力普遍缺失的危局,從而才能夠讓當下的種種“負面解讀”行為和現象真正由“盛行”走向“衰弱”。具體而言,我們可以通過“立法”“執法”和“守法”三個方面來予以把握。
在立法方面,針對“負面解讀”所重點關注和明確指向的問題,如食品、貪腐和環保等,應當加快健全相關的法律與法規體系,同時還應當根據具體的典型案例和不斷的經驗總結,來逐步提高相關法律法規的針對性與可操作性。
在執法方面,對于普遍反映較為突出的“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和“不文明”現象,必須及時嚴格地予以查處和糾正,并持續加大對司法不公正與腐敗問題的治理力度。
在守法方面,既要通過嚴格紀律和加大懲處力度等方式,來杜絕國家工作人員的“知法犯法”和“徇私枉法”等行為和現象,同時也應當積極引導社會成員“尊法信法”,并能夠經由合法的渠道來維護法律所賦予的權益。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發起和傳播“負面解讀”的個體,盡管還沒有觸及“制作、傳播謠言”和“網絡暴力”的底線,但以負面解讀方式來發泄負面情緒和表達不同意見,事實上往往也都可以認為是在以不夠合理的手段與方式,來爭取和實現個人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為此,“負面解讀”本身也存在著需要規范的問題,近年來有關網絡暴力的司法解釋和用戶名規范等的出臺,顯然對于規范此類行為從而引導公眾實現有序的參與和表達,都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信息溝通:增進政府、媒體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
“溝通是意義的傳遞與理解”[23],所以溝通是否有效,關鍵就在于能否保證溝通的內容——信息,是否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傳遞”,以及是否能夠為溝通對象所真正“理解”。如前所述,當前公信力缺失與“負面解讀”盛行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政府、媒體與公眾之間信息的不對稱且溝通存在缺陷,因此要跳出公信力缺失與“負面解讀”盛行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就只有增進有效溝通這一個途徑與方法。與此同時,筆者認為,正確的“理解”毫無疑問要以充分的“傳遞”為基礎,當前增進有效溝通的關鍵首先還是在于解決加強“傳遞”的問題,而這具體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常規溝通機制的建立與健全;二是專門針對熱點問題與突發公共事件進行充分的溝通,或曰危機狀態下的溝通。
對于常態化溝通機制的建立與健全,主要就是需要解決好當前最為突出的、溝通主體的認知與溝通渠道兩個方面的障礙。
在溝通的認知方面,政府機構的觀念轉變至關重要,尤其是單向的“官本位”式的傳播理念迫切需要轉變。例如,盡管《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于2007年頒布實施,并且對于公開的范圍、方式、程序和監督等都作了較為明確的界定,但在實際實施的過程中依然大量存在“敷衍應付”“關鍵信息公開不足”與“形象展示多于知情權保障”等比較突出的問題[24]。
在溝通的渠道方面,傳統的單向垂直傳播模式需要盡快得到改變,等級森嚴的科層制配置,不僅使信息傳播的中間環節繁多,同時也驅使官員為個人或部門利益而“報喜不報憂”,信息溝通通道嚴重不暢。
對于危機狀態下的溝通,關鍵就在于真正地認識到,有效的溝通不僅是基于決策者(溝通者)對公共危機發生與發展過程中一系列狀態的判斷,同時也影響和決定著危機之后政府部門形象的重塑,與媒體和公眾之間關系的修復,以及廣大公眾對于克服困難和渡過危機的信心的重建[25]。
事實上,從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到2011年的“7·23動車追尾事故”,再到2015年的“天津8·12爆炸事故”,相關應對實踐已經一再地向我們證明,有效溝通從來都是解決公共危機的關鍵所在。結合“負面解讀”盛行現象來看,恰如李克強總理視察天津火災爆炸事故現場時指出的:“權威發布跟不上,謠言就會滿天飛。”[26]
(三)媒介素養:全面、系統地開展媒介素養教育與培訓
目前,“媒介素養”正在國內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西方國家則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提出,要針對人們判斷、評價、制作和傳播媒介信息的能力,開展全面而系統的教育與培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快速發展,以及各國人民物質生活條件的迅速改善,發達國家普遍開始重視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互動,并通過媒介素養教育與培訓來引導公眾,學會“辨識”和“批判”媒介及其所承載的信息。20世紀80年代,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將媒介素養教育納入到了正式的教育體系之中[27]。與此同時,我國則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才在新聞與傳播專業領域中引入相關概念,而面向青少年、公務員和普通公眾的教育與培訓,總體上只是剛剛起步而尚未全面展開。當前,我們應當進一步明確地認識到,媒介素養的逐步提升必然有助于各個主體的自我完善,以及對公共事務的有序參與,因此對于增進全社會的團結與互信,進而破除“負面解讀”盛行的局面,就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現階段媒介素養教育與培訓的開展,同樣可以從三個不同主體的角度來加以認識,即公務員、公眾與媒體人士。
公務員作為政府機構的代表,顯然應當具備符合“行使權力和執行公務”需要的媒介素養,即認知、解讀、評判、駕馭和引導媒介與輿論的基本素質和能力。事實上,僅從公務員所應當具備的“九大通用能力”的角度看,關注媒介的發展、所承載的信息以及所反映的態度和觀點等,也始終都是公務員能力培養的“應有之義”。自2009年以來,國內不斷涌現的諸如“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等各種“雷人官腔”,說到底都可以歸結為媒介素養方面的問題。
從公眾媒介素養的角度來看,目前我們還主要停留在“不信謠、不傳謠”的低級層面,真正對應社會化媒體環境所要求的“選擇”“質疑”“理解”和“評估”能力,顯然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媒體人士的媒介素養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因為他們有著專業背景并身處專業領域,但類似2015年初的“偷拍遺體”風波,及4月央視某著名主持人的“不雅視頻”事件等,[28]都再次地提醒了人們,當前國內媒體人士的媒介素養提升似乎更加刻不容緩。
(四)文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構筑共同的精神家園
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實現生存與發展目標的靈魂之所在,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關鍵就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健康發展,沒有“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和強大精神支柱的支撐,就無法真正構筑起全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透過“負面解讀”盛行現象,我們不難看到“粗口”“惡搞”和“拜金”等“低俗文化”的泛濫,同樣也很容易辨識出,隱藏在各類流行語與段子中的“自嘲”與“憤怒”背后的,往往是深深的“不自信”與“偏執”。所以,“負面解讀”的盛行,往往起于“公信力缺失”,同時也漲于“主流價值觀的迷失”。而這一切,歸根結底仍然是需要通過加強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建設,通過消解低俗文化和重構道德體系來凝聚全新的“社會共識”。結合公眾輿論傳播來看,這也正與哈羅德·拉斯韋爾所提出的“對應程度的啟蒙原理”[18]60相契合,即在全社會的范圍內通過“高度等效的啟蒙”,來達到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或曰形塑社會認同的效果。
根據當前思想文化建設所處的新階段,以及治理“負面解讀”與重塑公信力的需要,筆者以為主要仍需牢牢把握好以下三點。
一是應以實際行動去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包含了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的價值目標與價值準則,同時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自信的重要支撐[29]。
二是應善于研究和發現更為豐富的“激活和傳遞正能量”與“增強思想文化的吸引力與感染力”的方法與途徑,除了繼續“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之外,還應在深入分析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主要矛盾與情緒的基礎上,去領會和把握日趨復雜化的輿論場與各種大眾傳播現象,既不能思維僵化草木皆兵,也不應被互聯網的“放大鏡效應”輕易迷惑。
三是應進一步凈化網絡環境和拒絕低俗化表達的傾向,通過打造安全、清朗的網絡空間,最終實現由“網絡大國”邁向“網絡強國”。“整治低俗語言”在于“治標”,普及網絡基礎設施、保障網絡安全、發展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并讓網絡真正惠及所有人,是為“治本”。總之,當我們真正掌握了思想文化與價值觀念領域的主導權與話語權的時候,“負面解讀”必然“式微”而“公信力缺失”也自然可得以破解。
【參考文獻】
[1] 林語堂.中國新聞輿論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18.
[2]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13-31.
[3] 丁建庭.謹防“壞消息綜合征”導致真相迷失[N].南方日報,2013-07-11.
[4] 新華網輿情監測分析中心.2015年第三季度熱點輿情報告[R].2015-10-14.
[5] 愛德華·L·伯內斯.輿論的結晶[M].胡百精,董晨宇,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
[6] 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M].閆克文,江紅,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集團,2014:21.
[7]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8.
[8] 尼古拉斯·盧曼.信任:一個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3.
[9] 中國社保的真相[EB/OL].[2015-12-15].http://bbs.tianya.cn/m/post-university-300573-1.shtml.
[10]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當前中國主要社會矛盾與問題研究[R].人民網,2015-01-23.
[11]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2]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如何應對網絡輿情?[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2.
[13]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M].趙旭東,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2.
[14]范正偉.靠什么破解“一鬧就停”難題[N].人民日報,2014-04-15.
[15]華杰.全媒體背景下鄰避效應的揚正控負策略[N].光明日報,2015-07-25.
[16]柴靜穹頂之下問真相,霧霾調查引爆兩會話題[EB/OL].(2015-03-01).http://www.chinanews.com/sh/2015/03-01/7089712.shtml.
[17]ROBERT K MERTON.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38,3(5):672-682.
[18]哈羅德·拉斯韋爾.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
[19]肖丹,岳亦雷.趙普“老酸奶說”激起千層浪[EB/OL].(2012-04-10).http://news.china.com.cn/txt/2012 -04/10/content_25102651.htm.
[20]蔣琰.果凍酸奶皮鞋造事件報告[EB/OL].(2012-04 -27).http://article.cyol.com/yuqing/content/2012-04/27/content_6142009.htm.
[21]李文富.扶起摔倒老人是社會文明在呼喚[EB/OL].(2013-12-3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0/c_125933091.htm.
[22]王漢超.用理性化解網絡戾氣[N].人民日報,2014-05-29.
[23]賴英騰.公共危機中的信息溝通及其治理機制[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8(5):177-179.
[24]楊亞佳.政府信息公開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J].人民論壇,2013(8):26-27.
[25]陳虹,沈申奕.新媒體環境下的危機信息溝通機制研究[J].現代傳播,2011(3):121-125.
[26]李克強·權威發布跟不上,謠言就會滿天飛[EB/OL](2015-08-16).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8/16/c_1116268775.htm.
[27]陸曄,等.媒介素養:理念、認知、參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33.
[28]林振芬.央視:畢福劍言論造成嚴重社會影響,將嚴肅處理[EB/OL].(2015-04-09).http://www.sh.xin-huanet.com/2015-04/09/c_134135694.htm.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課題組.振奮起全民族的“精氣神”——十八大以來中央關于思想文化建設的新思想[J].黨的文獻,2015(4):18-24.
[責任編輯 肖 湘]
On the Governance of"Negative Interpretation"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Trust
LI H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Party School of Dalian Committee of C.P.C.,Dalian,Liaoning 116013,China)
Abstract:In the current public opinion field of our country,all kinds of emotions collide with each other,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The phenomenon of"negative interpretation",which is increasingly popular,should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refraction of the"nega-tive interpretation",is still the growing"distrust"under the"social media environment".All kinds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negative mentality behind them come mainly from the general lack of"credibility",especially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media.Therefore,the countermeasures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to"negative public o-pinion"and credibility rebuilding mainly lie in:giving full play to the"rule of law"leading effect and normative role;promoting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media and the public;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carrying out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training;strengthening socialist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Key words:public opinion;negative interpretation;ecological governance of public opinion;public trust;countermeasure
作者簡介:李宏,中共大連市委黨校副教授,博士,從事國民經濟管理、應急管理研究。
基金項目:遼寧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L14AGL009);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3CGL134)
收稿日期:2016-01-10
中圖分類號:D035.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394X(2016)04-00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