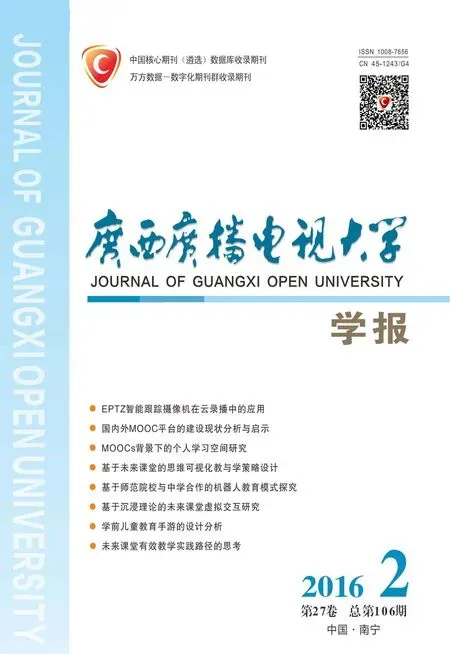具身認知視角下的教學設計原則
扎麗瑪
(內蒙古師范大學 網絡信息中心,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具身認知視角下的教學設計原則
扎麗瑪
(內蒙古師范大學網絡信息中心,內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文章針對當下教學設計疏遠學習者身體活動的問題引入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的相關理論,客觀解析具身學習的相關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種具身學習的教學設計原則:(1)學習環境應當能夠促進深度學習,在這種學習環境中學生可以從身體活動中獲得隱喻的意義感,即便是回憶這些活動時,仍然能夠獲得這些意義感;(2)創建和促進物理交互以生成與所期望的學習結果相匹配的概念推理和思維模式;(3)使學習者與各種物質的、認知的工具或技術以最優的方式結合而促進學習。
具身認知;具身學習;具身設計
引言
具身認知也稱為“具體化”,是當代心理學與認知科學領域中的新興論題。經典認知科學主張“非具身”,認為認知是一種信息的表征與加工,從本質上講與承載它的身體無關。“弱具身”強調了認知對身體的依賴性,但是卻保留了認知的計算和表征功能。“強具身”則極力主張認知是被身體作用于世界的活動塑造出來的,身體的特殊細節造就了認知的特殊性。“強具身”理論對于身體的重視創新了學習的文化,拓展了學習科學的研究領域,同時也為教學設計提供了新的關系視角。以往的教學設計都是基于“非具身”或是“弱具身”理念。文章針對當下教學設計疏遠學習者身體活動的問題引入心理學與認知科學領域的相關理論,客觀解析具身學習的相關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種具身學習的教學設計原則。
一、具身認知理論
具身認知理論是通過強調知覺對于概念學習的重要性來審視人類認知的一種新的方法。在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中,知覺和概念彼此之間是徹底分離的。基于此二元論,知覺一直被認為是物理性質的而概念則被視為純粹精神的,因而概念獨立于我們感知物理事物的能力。依據這一哲學假設,傳統認知理論認為知識是一種抽象命題網絡,它是以一種分離于我們知覺、身體活動和心理狀態的語義記憶系統的形式存儲于我們的長時記憶。然而,Wilson(2002)曾聲明,“具身認知”意味著思維和知識是從身體與物理世界的動態交互中生成的。Barsalou(2008)用“扎根認知”代替“具身認知”以強調認知不僅僅取決于物理狀態而實際上來自于多重本源,如知覺刺激,情景行為,社會交互,情感狀態和環境。
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對于認知的具身本質有著不同的觀點和視角。比如認知語言學家(Gibbs,2003;Lakoff&Nunez,2000;Lakoff&Johnson,1980)強調身體本身對于理解抽象概念的重要性。他們視身體為知覺經驗的接收器并將這些經驗所生成的思維表征視為意向圖式。與認知語言學家不同,認知心理學家將單一的感覺模態定義為知覺經驗的源泉,而將多模態的表征視為由這些經驗所生成的思維表征。因此,認知語言學家和認知心理學家對于具身認知結構的認識是相似的。他們都認為思維表征(意象圖式和多模態表征)是由物理交互所生成,這些物理交互是理解抽象概念的認知基礎。但是,他們對于思維表征的建構機制的解釋存在異議。
加州大學副教授馬格雷特·威爾遜(Magaret Wilson)曾在《Psychonomic Bulletin&Review》中發表文章,總結出具身認知的六個基本觀點:1)認知是在情景中的。認知活動在真實世界的文脈中展開,固有地包含感知和行為;2)具身認知含有時間壓力。認知需要在真實的環境時間中考慮;3)人利用環境幫助自己認知。人的時間處理能力限制導致人使用環境為自己存儲、甚至處理信息;4)環境是認知系統的一部分。思想和世界的信息交互是持續的;5)認知以行動為目的。思想的功能在于引導行為,感知和記憶等思維活動需要從它們對適宜行為的作用的角度理解;6)脫離環境的認知以身體為基礎。離開環境之后的思維活動基于身體與環境交互的機制——感覺處理機制和行為控制機制。
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約翰遜將語言學與具身認知理論結合,提出了“具身圖式”也稱為“意象圖式”(image schema)或“動覺意象圖式”,意指一種重復出現在人類秩序性活動中的模式、形狀和規律。它們是具有意義的結構,作用于人類在空間中的身體移動、對物體的操作和知覺的交互中。萊考夫和約翰遜對具身圖式的探討包含兩個步驟:首先是通過現象學的視角以描述的形式找出先于概念的經驗結構,而后將經驗結構的圖像延伸進入抽象的理解和推理中,由此身體體驗中的意義通過具身圖式轉移到抽象概念中。
二、具身學習的基本概念
(一)認知系統
當我們沉浸于感知覺和動覺活動時,我們動用了復雜的認知和運動系統,期間我們卻很少需要思考。但是,當我們開始討論知覺和行動時,我們動用了另一種不同的認知系統,這種認知系統的活動不同于身體經驗所指涉的認知活動。這兩種認知模式的區別在于一個是直接的“做”,另一個是間接的“想”。理解這兩種認知模式之間的區別對于具身學習的理論與實踐非常重要。
通過結構化的映像,被吸收的經驗流能夠被更好的理解。正如杜維所說,“事件被轉換為有意義的對象、事物……它們可以通過想象無限地組織和重排……因而極其更易于操控、更加持久、更加靈活”(杜威,1958)。當我們明確地表達我們的潛意識和隱性知識,這就仿佛在我們自身與經驗之間投射了一個概念屏幕(波蘭尼,1958)。這一二元系統論被并行引入到了學習科學的基礎文獻。比如,認知發展心理學家皮亞杰很好的區分了感性和理性知識,文化歷史心理學家維果斯基提出了自然和科學概念。
卡內曼(2003)區分了毫不費力的知覺和深思熟慮的推理,前者是迅速的、啟發式的、相對不易于改變的,后者較為緩慢但更為精確且易于改變。
在許多日常活動中,意義是隱喻的、情景化的、計劃性地趨向于特定環境下所要獲得的目標,是一種直覺的模式。然而,STEM學科的學習需要具化、理解、分析、量化這些自然的交互,是一種分析的模式。要理解STEM的內容,學習者必需在直接的知覺活動與間接的學科實踐中的結構之間不斷協調。
(二)動作與行為
許多人相信思維在本質上是分離與感覺輸入或行為輸出的心理活動。與此相反許多認知科學研究發現:抽象概念是感性的,它是基于外部與內在事件的暫時的擴展模擬。如果是這樣,思維就是對物理世界感知的喚醒和動態操縱。Melser (2004)提出思維是一種隱蔽的縮短的活動形式,“縮短”是因為關于計劃和執行物理活動的神經官能參與了進來而肌肉卻沒有。神經成像的實驗證據支持了這一觀點,發現了理性思維直接使用了感覺-動覺身體機制,它是對我們身體常規操作的利用。比如,當我們想象時,會激活與我們實際觀看時所使用的大體上一致的大腦區域。當我們聽到“舔、摘、踢”等動詞時我們分別秘密地激活了控制嘴、手和腿的運動系統。這些發現使一些學者到此為止廢棄了心理表征的傳統概念并且重新依據主體-環境動力學重新闡述認知。
發展心理學家廣泛地認同身體活動在概念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維果斯基曾提出:“言語不是開始,行動才是第一”(Vygotsky,1962)。皮亞杰認為在處理具體情景時行動導向的心理過程在人們學習數學或科學概念時同樣起著一定的作用,如“平方”或“重力”的概念。他宣稱:“邏輯思維的根源不僅能夠在語言中發現......但是……更普遍的是在動作的協調中,它是抽象思維的基礎”(Piaget,1968)。
像皮亞杰一樣,許多當代認知科學家提出模型來解釋抽象概念怎樣來源于具體的感覺運動經驗。認知語義學中的概念隱喻理論假設所有人類的推理是基于意象圖式,“我們身體的定位、運動、交互模式......它們以想象的方式發展而后建構了我們的抽象推理”(Lakoff&Johnson,1980)。比如說,我們能夠理解“集合”這一數學概念,只因為我們知道物理對象是如何被聚集在容器里的。
幾位心理學家研究了人們在說話和解決問題時會有什么樣的姿勢,這些研究為思維的具身性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證據。比如,觀察人們在談及剛剛學會操縱的工具時,他們怎樣移動自己的手,幫助我們理解實際的交互怎樣發展為模擬行為,這些模擬行為將對以后的身體的和認知的表現產生影響。一些科學家研究了算盤專家的心理算術之后總結道:算盤操作會在一個過渡階段內化為心理操作,在這一階段中心理操作并不完全獨立于運動系統,算盤模擬時的手指運動為這一觀點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三)技術與工具
人類認知和技術工具的關系長期以來吸引著學者們。這兩種實體,一個是精神的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有生命的一個是無生命的,是以怎樣的方式合成在人類的神經系統中?通過操縱外在于大腦的工具經歷概念轉變意味著什么?當我們參與這樣的活動,我們是否可以獲得一些有用的知識,即使在沒有工具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應用這些知識?
有證據證明學習者確實可以從這樣的活動中獲得知識。比如,當一個盲人第一次使用木棍與實體空間交涉時,他會有一些簡單的感覺——依靠手指和掌心獲得質感和觸感。但是當這個人開始學會使用木棍去感覺他腳下的道路,那些簡單的感覺被轉換了,他會感覺到木棍觸碰物體的那個點。這個例子說明工具會影響我們的認知,這種影響是通過我們發展操作工具技能時不斷增強的適應性體驗而起作用。也就是說,當我們想出怎樣根據自己的需要使用工具時,我們通過工具發展了我們控制和解釋世界的能力。無論何時,當工具缺失時,它潛在的結構和隱含的功能會變得透明,也就是說,它們所塑造的思想和行為仍然存在。
我們使用技術拓展自己的知覺運動和認知能力。通過技術的中介結構,我們內化了與世界交互的身體和思維習慣。當這些技術不能起到預期作用時,我們有意識的反思,重新校準或者改變我們參與世界的方式。那就是,我們所學會的。
三、具身學習設計原則
當我們應用具身認知理論去創造學習環境時,我們在從事具身設計。具身設計這個短語是由Thomas Van Rompay首先杜撰,然后由認知心理學家轉化為工業設計,他用概念隱喻理論去協調由公共結構體所誘發的情感經歷。Abrahamson(2009)將這一短語引入到學習科學,去描述一種教學設計方法,這種方法將教學設計的工具與活動調節到與人類自然感知世界的方式相匹配,并且有助于學科的重新分析和表征。在一個基于具身設計原則的環境中,學習者可以利用他們身體的自然本能和運動去研究一個化學的,生物的,物理的或數學的問題。
在許多日常活動中,意義是隱喻的、情景化的、計劃性地趨向于特定環境下所要獲得的目標,是一種直覺的模式。然而,STEM學科的學習需要具化、理解、分析、量化這些自然的交互,是一種分析的模式。要理解STEM的內容,學習者必需在直接的知覺活動與間接的學科實踐中的結構之間不斷協調。學習環境是否可以促進深度學習,在這種空間中學生可以從身體活動中獲得隱喻的意義感,即便是從形式上回憶這些活動,仍然能夠獲得這些意義感。概念推理起源于物理交互并且內化為模擬行為,我們積極地選擇、創建和促進物理交互以生成與所期望的學習結果相匹配的概念推理和思維模式。三是我們使用技術拓展我們的知覺運動和認知能力。通過技術的中介結構,我們內化了與世界交互的身體和思維習慣。當這些技術不能起到預期作用時,我們有意識的反思,重新校準或者改變我們參與世界的方式。那就是,我們所學會的。我們需要使學習者通過最有效的方式利用這些技術而完成學習。
四、結語
具身學習設計原則的總結是:對學習最有效的活動是利用學生的先天能力在真實或虛擬的三維空間中去定位和調適。活動要求學生使用他們的知覺判斷力和動覺協調力去判斷刺激的屬性并執行新的動作。學習活動應該位于一個合成的環境中,其中包括技術工具和教師。學生應該有機會在這些環境中找到合適的目標,就像他們在無中介的世界中操縱復雜的材料結構時一樣。最佳促進概念發展的運動和身體參與模式并不總是自然發生,學生常常需要腳手架來采取行動和移動他們的身體——為目標知識領域制定功能隱喻。
[1]Abrahamson,D.(2009).Embodied design:Constructingmeans for constructingmeaning.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70(1),27-47.
[2]Barsalou,L.W.(1999).Perceptual symbolsystems.BehavioralandBrainSciences,22,577-660.
[3]Barsalou,L.W.(2008).Grounded cognition.Annual Review ofPsychology,59,1-21.
[4]Barsalou,L.W.,Niedenthal,P.M.,Barbey,A.K.,&Ruppert,J.A.(2003).Social embodiment.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43,43-92.
[5] Black, J.B.(2010).An embodied/ grounded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In M. S.Khine, &I.M.Saleh(Eds.), New science of learning:Cognition, computers and collaboration in education.New York.NY:Springer.
[6]Lakoff,G.,&Johnson,M.L.(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Melser,D.(2004).The act of thinking. Cambridge,MA:MITPress.
[8]Piaget,J.(1968).Genetic epistemology (E.Duchworth,Tra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Vygotsky,L.S.(1962).Thoughtand language.Cambridge,MA:MITPress.
[10]葉浩生.具身認知:認知心理學的新取向[J].心理科學進展,2010(5).
[11]葉浩生.心智具身性:來自不同學科的證據[J].社會科學,2013(5).
[12]葉浩生.身心二元論的困境與具身認知研究的興起[J].心理科學,2011(4).
[13]楊南昌,劉曉艷.具身學習設計:教學設計研究新取向[J].電化教育研究,2014(7).
[責任編輯張宜]
G434
A
1008-7656(2016)02-0046-04
2016-05-26
扎麗瑪,內蒙古師范大學網絡信息中心實驗師,在讀博士,研究方向:學習科學與技術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