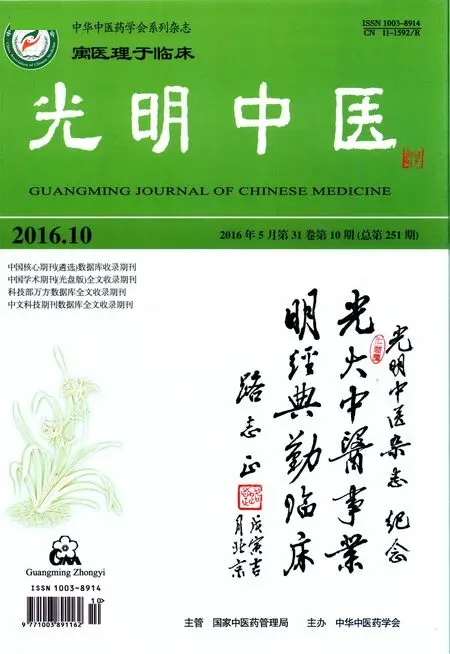淺談郁證的診治
馮秀君 林雪娟
?
淺談郁證的診治
馮秀君1林雪娟2
1.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碩士研究生2014級(福州 350122);2.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證研究基地(福州 350122)
摘要:目的探討郁證的不同辨證角度。方法郁證作為以郁為特征的一類病證,其發病原因多樣。郁之初并沒有典型臨床表現,發病以后甚至還是無證可辨,即使有表現也是百般復雜。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大量文獻的查閱來總結出各種不同的辨證角度,并且分析各種角度的利弊,最后找出更加準確實用的辨證思路。結果郁證的診療應當多角度辨證并且靈活結合運用。結論通過辨臟腑、辨六郁、辨虛實、六經辨證等角度層層遞進或者結合運用到郁證的辨證治療中,從而形成縝密的辨證思路,才可以取得更準確的辨證及治療。
關鍵詞:郁證;臟腑;六郁;虛實;六經辨證
郁證是由于情志不舒、氣機郁滯,以心情抑郁、情緒不寧、胸部滿悶、脅肋脹痛,或易怒易哭,或者咽中有異物梗塞等癥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類病證[1]。而《類證治裁》云:“七情內起之郁,始而傷氣,繼降及血,終乃成勞,主治宜苦辛涼潤宣通。”[2]這足以說明郁證的起病及后期的發展進程,其發病之緩慢不容易被重視,然到傷氣、傷血、成勞之境地才足以顯示出它的危害之大。西醫則表現在精神疾患上,比如西醫的心臟神經官能癥、抑郁癥、神經衰弱、焦慮癥等疾病都屬于中醫郁證的范疇,這樣相對就縮小了中醫的郁證范圍。在實際臨床當中很多時候當患者出現以心悸、氣短為主癥時,醫生則受到西醫思維的影響,首先考慮為心血管疾病,往往造成郁證的漏診,延誤了病情。還有相關研究發現,中醫中藥配合治療郁證比單純使用西藥療效明顯。因此,中醫作為以辨證論治為主體思想的醫學模式,無論是郁證的診斷還是治療較西醫都更為有優勢。從古代到現代,歷代醫家關于郁證的認識也逐漸深入,目前辨臟腑、辨六郁、辨虛實、六經辨證都成為了診斷和治療郁證的主要臨床思路。
1 辨臟腑到辨六郁
追溯郁證的發展,最早可以見于《黃帝內經》:“天地有五運之郁……而郁證作矣。”“郁之甚者,治之奈何”,“人或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即傷肝也”,還有《素問·舉痛論》曰:“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3]另外張景岳在《景岳全書》中也指出郁與心的關系。可見郁證的發病與心有著密切關系。從心的功能來看,主神志和主血脈,這也不難看出人的情志活動主要是心之功能的體現,而唯有氣血正常循環往復于全身才可以保證心功能的正常,才可以有良好的情志活動。故而,郁證與心有著密切聯系。
《類證治裁》:“凡上升之氣,自肝而出。”[2]肝主疏泄,既能夠疏泄無形之氣,又能夠疏泄有形之氣血,通過疏導身體的氣、血、津、液,來達到機體的一種平衡狀態,通而不滯,散而不郁。況且,肝性喜調達而惡抑郁,長期的精神壓力甚者憤怒得不到發泄會導致肝氣郁結,肝氣郁結又會影響氣血津液的運行,從而產生病理產物,比如痰、瘀血等等。
清代的李冠仙認為肝氣一動,即乘脾土或者上犯胃土,可見肝氣不暢橫逆客犯脾土,這就是所謂的木旺克土,而脾土健運失常又會反過來影響肝木的疏泄功能,即所謂的土虛木郁。肝與脾相互影響,關鍵在于搞清楚先發病之臟腑,并且辨別清楚孰輕孰重,才可以很好的遣方用藥。
基于這些對于臟腑的認識,以臟腑為切入點來考慮郁證的診療,便成為現代醫家的思路,而且辨證更容易被理解。然而,郁證作為一類多因素作用的疾病具有自身的復雜性,這就決定了郁證不可能是單一臟腑受病,而是多臟腑波及,相應的臟腑論治就形成了,這樣一來,如果僅僅考慮臟腑的受病而忽略對于病理產物的消散,調節臟腑就顯得過于機械。因此,朱丹溪以氣血為基礎考慮,提出的六郁論治就是對于臟腑論治很好的補充,并且創立了著名的越鞠丸、六郁湯,對于后世郁證的診療都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從《黃帝內經》基礎上發展的五臟郁是以臟腑生理功能為基礎,到朱丹溪的六郁以臟腑生理功能失調產生的病理產物出發考慮,二者的目標都是為了恢復臟腑功能,只是出發點略有不同,在當前日漸復雜的臨床上如若能夠結合兩種思路考慮郁證,相信一定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辨虛實
《黃帝內經》之“五行之郁”及朱丹溪的“六郁”多為郁證診療的理論源泉,可能是醫家沒有領悟其中的真正內涵或者疾病還沒有發展至復雜的緣故,醫家們多從實邪出發進行論治,而直到明代的張景岳,明確指出了郁證應該有虛實之分,并且將自己的溫補思想貫穿于郁證的治療當中。正是由于張景岳的溫補思想極其具有實用性及前瞻性,因此現代對于溫補思想的進一步研究仍然大量存在。比如霍云華等[4]通過對李炳文教授的學術思想研究發現,李炳文把郁證范疇的抑郁癥歸結到了中醫的虛勞中,認為抑郁癥應該就是虛勞加郁證,治療上形神兼顧,治養結合,使得臟腑陰陽和調,氣血暢通。然而,現代由于西醫西藥的運用,以至于某些臨床癥狀被掩蓋,因此不能很好的辨別虛實,尤其在辨證不清楚之時又簡單的以虛實夾雜作為診斷,最后往往收不到明顯的治療效果。
3 六經辨證
中醫人所推崇的張仲景在郁證的診療方面有沒有其特殊貢獻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了,其中現在大家基本認為《金匱要略》中所記載的婦人臟躁和梅核氣均屬于郁證范疇。謝勝,韋金秀等[5]通過臨床的不斷摸索總結,初步總結出了桂枝類、梔子湯、柴胡湯類、四逆輩均可以被運用在治療郁證當中,療效顯著,具體如何運用六經辨證未作詳細說明。可見,張仲景所推崇的六經辨證形成的經方在郁證的辨證治療方面是有很大優勢的。但是在運用仲景的經方之前必須體會其六經辨證的真正內涵,切不可生搬硬套經方,以至于貽誤治療,造成誤診誤治。
4 小結
郁證是以郁為特征的一類病,這里的“郁”既可能是有形之郁,也有可能是無形之郁,個體不同,疾病所處階段不同,因而臨床表現千差萬別,這就為疾病的診療帶來極大困難。因此,對于郁證的診治應當放寬自己的視野,不能僅僅局限在精神疾患方面,而是要牢牢地把握病機,通過辨臟腑、辨六郁、分虛實層層遞進或者靈活結合運用,以求得更清楚的認識郁證。甚至,在某些必要的時候融合仲景的經方思路于郁證的診療當中,以求得辨證思維上的突破。另外,臨床診療中不可過度依賴問診,而應當四診合參,甄別出有用信息,取得更加準確的辨證論治,以更好地解郁、發郁。
參考文獻
[1]周仲瑛.中醫內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373.
[2]類證治裁[M].林珮琴編注.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196;188.
[3]素問[M].穆俊霞,王平校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63.
[4]霍云華,韓笑冰,曹守忠,等.李炳文治療抑郁癥經驗[J].世界中西醫結合雜志,2012,7(2):104-106.
[5]謝勝,韋金秀,侯秋科,等.仲景經方治療郁病初探[J].遼寧中醫雜志,2014,41(9):1984-1986.
doi:10.3969/j.issn.1003-8914.2016.10.021
文章編號:1003-8914(2016)-10-1394-02
收稿日期:(本文校對:劉言言2015-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