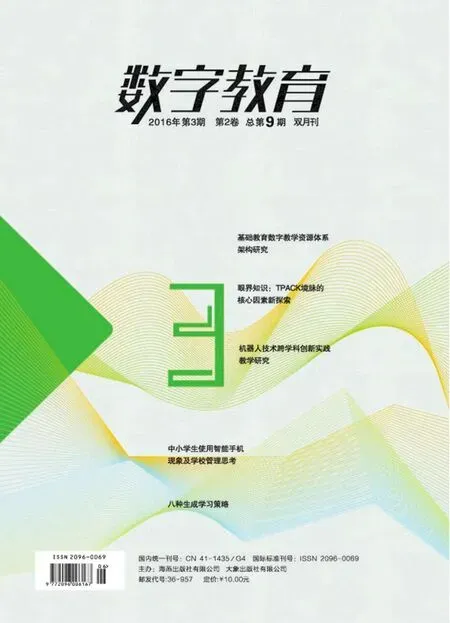眼界知識:TPACK境脈的核心因素新探索
章洋張海王以寧
(1.黑龍江大學 應用外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2.東北師范大學 傳媒科學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眼界知識:TPACK境脈的核心因素新探索
章洋1張海2王以寧2
(1.黑龍江大學 應用外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2.東北師范大學 傳媒科學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眼界知識作為鮑爾等人提出的數學知識框架中的一個要素,近年受到研究者廣泛關注,但是相關研究成果尚未達成明確共識。文章對眼界知識的起源和定義進行介紹,分析了眼界知識與用于教學的數學知識框架各要素的關聯,并探討了今后眼界知識相關研究的開展方向,以期為后續研究提供思路。
數學教學;用于教學的數學知識框架;眼界知識
眼界知識(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HCK)是TPACK境脈研究中一個比較新且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是從小學數學教學實踐中提煉出來的一種教師應具備的知識。掌握HCK有助于教師建立學科教學全局觀,更有效地開展教學,提高教學效率。雖然HCK概念的定義、分類等尚存爭議,但并不妨礙其被廣大學者接受。自2008年在用于教學的數學知識框架(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Framework,MKT) 中 正式提出以來,HCK研究的關注度逐年遞增,并呈現從理論研究向理論、實證研究并進的發展趨勢。
一、HCK的概念界定
(一)HCK的提出
HCK概念的出現比MKT框架的提出早了20年,這與鮑爾(Ball)及其團隊的研究方法不無關系。在過去的30多年里他們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研究“基于實踐的理論”。核心假設是“了解學生數學學習需求、梳理數學教學中必要的學習資源的有效方法,是從數學教學活動入手進行直接分析”。[1]因此他們的研究大致分成三個階段:確認小學數學教學中的重復性任務——分析其中包含的必要數學知識(從中提取出諸如HCK等知識)——形成用于教學的數學知識理論框架(MKT)。
HCK概念被提出后,命名幾經變更,如數學眼界(mathematical horizon,1993)、眼界知識(horizon knowledge,1993)、學科眼界知識(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2008)、數學眼界知識(knowledge at the mathematical horizon,2009)等,最為研究者們接受的還是HCK。臺灣地區根據2009年的名稱將HCK譯為“眼界數學知識”,而MKT被譯作“教數學所需的知識”[2]。
筆者認為,Ball等人研究的是小學數學教學,因此2009年的名稱最為具體。但是國外論文一直沿用“HCK”的說法,而在中譯時應考慮詞性構成,譯為“眼界知識”更易接受。
(二)HCK的定義
HCK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解釋尚存爭議。鮑爾和貝斯(Ball & Bass,2009)認為HCK“是一種以現有經驗和教學可以看到的廣闊數學風景的意識”,教師掌握的HCK知識既非通過學習獲得,更不必解釋給學生。在Ball等人的MKT框架中,HCK是“一種周圍眼界(peripheral vision),一種深層的了解,將各個數學概念串聯起來,并且察覺數學概念于未來學習的助益”(林勇吉、金鈐,2014)。與Ball等人自下而上從基礎數學的角度看待更高級數學的視角相反(2008,2009),扎基斯和馬莫洛(Zazkis & Mamolo,2011)自上而下主張應用高等數學于小學數學教學中[3]。后者的看法受到眾多質疑:菲格拉斯(Figueiras)等人(2011)認為這會將學生引入歧途,誤以為方法不重要、解決數學問題就必須懂得多[4];雅各布森(Jakobsen)等人(2012)認為高級知識不能保證教師了解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想法[5]。
即便觀點不統一,不少研究者還是肯定了HCK的積極作用:通過HCK,教師能夠判斷哪些是教學中必不可少的數學知識和內容,了解學生想法背后的重要數學概念,知道當前的數學內容如何與過去舊知、未來新識聯系與發展、承前啟后(Jakobsen等,2012)。具有HCK知識的數學教師能夠有更好的教學決策能力,并且能更有效地幫助學生學習(Zazkis & Mamolo,2011)。
二、MKT框架簡介
(一)與舒爾曼“教師專業知識基本框架/結構模型”的淵源
數學教師的知識構成研究一直是一個比較活躍的領域,其中舒爾曼的理論最有影響力(Mosvold & Fauskanger,2014)。舒爾曼(1986)指出當時的研究忽略了三個范式: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又叫Subject Matter Content Knowledge)、學科教學法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和課程知識(Curricular Knowledge)[6],因此將這三類知識歸入他1987年提出的“教師專業知識基本框架/結構模型”中。
在舒爾曼看來,“學科知識”是指教師頭腦中儲備的學科知識及其組織結構。“學科教學法知識”是指最有用的教學內容呈現形式,最給力的類比、說明、舉例、解釋和實證——簡言之,是易于理解的最有用的陳述和表達……還包括了解教學內容的難易點,是“學科內容知識與教學法知識的整合”[7]。“課程知識”是指某個學科、某些內容在某個水平上教學的全過程,豐富的相關教學材料,在一定條件下作為正、反指示如何使用某課程或教學材料的特點的集合。它分為橫向和縱向兩類:“橫向課程知識”指與學生正在學習的其他課程內容的聯動;“縱向課程知識”指在現階段以及未來幾年在校期間,本學科內已學知識和未來要學的知識之間的聯系以及相關材料。
舒爾曼的提議為其他人的研究提供了思路。由于對教師所掌握的知識類型的理解尚不全面,分類及命名也沒有固定,后人對舒爾曼的框架進行了各種修訂嘗試。Ball等人提出的MKT框架就是其中之一(如圖1)。該框架改造了舒爾曼(1986)的學科知識,提出數學普通知識、數學眼界知識與數學專門知識三個構成元素;保留了學科教學法知識,其組成要素數學學習規律的知識和數學教學規律的知識也與舒爾曼看法一致,并參考舒爾曼團隊后續研究結果將課程知識并入學科教學法知識。[8]

圖1 MKT框架(Ball & Bass, 2009)
(二)HCK與MKT框架其他要素的關系
Ball和Bass(2009)對MKT框架各要素的內容做了詳細總結。框架右側的學科教學法知識是內容知識和教學知識的結合,包含:1.數學學習規律的知識(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Students, KCS),掌握這類知識的數學教師能夠了解學生們學習某個數學內容時的普遍認識和誤解;2.數學教學規律的知識(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Teaching, KCT),指和教學設計有關的教學活動,如教學流程設計、教學效果評價、教學方法選擇等;3.內容和課程的知識(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Curriculum,KCC),如一個教學主題所涉及的教育目標、標準、測試、年級水平等。
框架左側的學科內容知識(Subject Matter Knowledge),指純數學知識,與教學或學生無關(Ball等)。包括:1.數學普通知識(Common Content Knowledge, CCK),指不僅在數學教學活動中,還在其他情境下,都會涉及的數學知識和技能。換句話說,CCK指不僅數學教師,其他人也具備的一般性數學知識和技能。2.數學專門知識(Specialized Content Knowledge, SCK)指數學教師獨有的數學知識和技能。這些知識和技能被用于但又不局限于教學情境下的各種工作,如調適學習任務難度、提出有成效的問題、評價學生發言、解答學生疑難、評估教材內容的優劣并做出調整、向家長闡述教學目標等。3.數學眼界知識(Knowledge at the Mathematical Horizon), 即HCK。HCK繼而又被分為四類:(1)對當前情況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及周圍數學環境有清醒的認識;(2)主要的學科概念和結構;(3)關鍵的數學實踐;(4)核心的數學價值觀和數學情感。作為純數學知識,HCK知識不存在于教學活動中,也不能通過學習獲取。具備該知識的數學教師表現為能用意識、情感、意愿等去影響、激發、支架教學實踐活動。
正如舒爾曼的框架被其他人不斷修訂一樣,Ball等人認為自己的提法也需不斷改良和修正。首先,課程知識被并入學科教學法知識是“暫時的”, 因為課程知識與KCT的關系、是否與MKT中多個子類型有交集、抑或成為一個獨立元素,都尚無定論;其次,HCK被安置在學科內容知識中也是“暫時的”,因為HCK是應該被歸入學科內容知識還是與MKT中多個子類型有交集也沒有結論。總之,Ball及其團隊認為現有MKT框架存在三個主要問題:一是這些要素令教與學的構成變得復雜和混亂;二是靜止的框架及要素反映不出動態的知識調用過程;三是要素之間的界線還不夠明確。希望這些待解決問題將來在教師教育或職業發展課程材料開發等方面,通過理論研究、課堂觀察、實踐分析等方法繼續深入探究。MKT對HCK的闡述還不夠全面,其他研究者是在認可HCK存在的假設下從事HCK理論與實證研究。
三、HCK研究的進展
(一)對HCK的理解繼續深化
隨著研究的深入,不斷有人對HCK加以解讀。Jakobsen等人(2012)定義HCK,是指高級知識的教學取向和對高級知識的熟悉度,以利于中小學學科教學的進行,使教師明了正在講授的內容如何為本學科更廣泛的內容鋪設情境并取得聯系。它包括便于了解專業的方法和工具方面的知識、知識的類型和依據、想法的來源及有效性如何建立,還包括對專業核心取向和價值、專業主要結構的認知。HCK能夠幫助教師傾聽學生的看法,判斷具體看法和提問的重要性,促進學科內容的融合,所有資源都是為了實現一個基本任務,即將學生引向更廣闊、更先進的領域。
福斯特(Foster)(2011)提出 HCK 架構中存在一種“周邊數學知識”(Peripheral Mathematical Knowledge),用于緩沖與支持學生的學習軌道向上提升。具體而言,是教師內化經常使用的數學知識,并用于引導學生學習的知識。[10]例如教師不需要計算,就知道210=1024。因此當學生一說出答案,教師就能夠不假思索地判斷對錯,進一步決定要如何引導學生(林勇吉、金鈐,2014)。
(二)更加關注實證研究
HCK理論探索有待更多實證研究的佐證。2008年Ball等人曾在論文中指出未來HCK研究的五個方向:1.是否對教學有效;2.HCK在教學方面延伸的程度與方向;3.HCK的有用程度;4.HCK如何習得與發展;5.如何測量HCK。
在HCK與教學的關系方面,莫斯沃爾德和福斯康爾(Mosvold & Fauskanger,2014)調查顯示,相較于對學科知識的關注,挪威教師們對HCK比較忽略。[11]現實雖然尷尬,但另一項在挪威進行的研究成果又強調HCK是MKT框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相關教學方法能夠對未來的數學學習起到幫助。[12]
臺灣的林勇吉和金鈐(2014)根據Ball等人的研究提出一個整合的HCK模型,并就此模型中的“基礎數學知識”設計“HCK取向”與“解題取向”兩種教學方式的對比實驗,結果證明HCK取向能夠幫助多數學生學習如何解題,特別是對低成就的學習者更為有效。
在HCK測量方面,已有研究證明小學數學教師所掌握的知識是由學科知識、數學學習規律的知識等多個元素構成的[13]。古貝爾曼和戈列夫(Guberman & Gorev,2015)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結合的方法對118名小學數學教師進行研究,發現被試教師的HCK知識具有“數學洞察力”(Mathematical Insight)、數學關聯(Mathematical Connections)和元數學知識理解力(Understanding of meta-mathematics)三個組成要素。[14]
總之,數學教師的知識構成研究一直是一個比較活躍的領域。HCK研究起源于數學教學,并在數學學科獲得進一步發展,HCK對教學的積極意義已經獲得很多研究證實。但是相關研究遠沒有達到完全清楚和取得共識的程度:其他學科教學中是否也存在這樣一種知識類型?HCK知識如何習得,如何用于指導教師培訓?上述疑問還需要更多研究來回答。
[1]Ball,D. L. & Bass,H.(2009).With an eye on the mathematical horizon:Knowing mathematics for teaching to learners’mathematical futur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2009 Curtis Center Mathematics and Teaching Conference.
[2]林勇吉,金鈐.探討學生對HCK取向與解題取向教學的知覺[J].科學教育月刊,2014,(6):2-16.
[3]Zazkis,R.& Mamolo,A.(2011) Reconceptualizing knowledge at the mathematical horizon.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31(2),8-13.
[4]Figueiras,L.,Ribeiro,M.,Carrillo,J.,Fern ndez,S.&Deulofeu,J.(2011) Teachers’ advanc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solv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challenges:a response to Zazkis and Mamolo.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31(3),26-28.
[5]Jakobsen,A.,Thames,M.H.,Ribeiro,C.M.& Delaney,S. (2012) Using practice to define and distinguish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Pre-proceedings of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pp.4635-4644.Seoul,South Korea: ICMI.
[6]Shulman,L.S.(1986).Those Who Understand:Knowledge Growth in Teaching.Educational Researcher,15(2),4-14.
[7]徐鵬,張海,王以寧,劉艷華. TPACK國外研究現狀及啟示[J].中國電化教育,2013,(9):112-116.
[8]Ball,D.L.,Thames,M.H.& Phelps,G.(2008) Content knowledge for teaching: what makes it special?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59(5),389-407.
[9]Fern ndez,S.& Figueiras,L.(2014)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 Shaping MKT for a Continuous Mathematical Education. REDIMAT,Vol 3(1),7-29.DOI:10.4471/redimat.2014.38.
[10]Foster,C.(2011) Peripheral Mathematical Knowledge.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31(3),24-26.
[11]Mosvold,R.& Fauskanger,J.(2014) Teachers’Beliefs about Mathematical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 Learning,2014(9):1-16.
[12]Jakobsen,A.(2014)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Experiences from a Practice-based Approach in Norway.http://www.directorymathsed.net/ montenegro/Jakobsen.pdf.
[13]Hill,H.C.,Schilling,S.G.& Ball,D.L.(2004) Developing Measures of Teachers’ Mathematics Knowledge for Teachi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Vol 105(1):11-30.
[14]Guberman,R.& Gorev,D.(2015)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mathematical horizon:a close view. Math Education Research, (2015),27:165-182.DOI:10.1007/s13394-014-0136-5.
(責任編輯 杜丹丹)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A New Exploration of Core Factors in TPACK Context
ZHANG Yang1,ZHANG Hai2,WANG Yining2
(1.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China 150080; 2.Media Science School,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China 130117)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one component of Ball et al.’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framework (MKT),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these years;yet relative researches have not reached a clear consensus.This article introduces HCK’s origin and definition,analyzes HCK and its relevance to other components in MKT,probes into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related to HCK,expecting to offer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mathematics teaching;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Framework (MKT);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 (HCK)
G434
A
2096-0069(2016)03-0008-05
2016-03-31
本論文獲得東北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基金重點項目“卓越教師素質結構實證研究”(課題號131005003)、東北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基金一般項目“卓越教師培訓能力遷移影響因素實證研究”(課題號131005012)、 東北師范大學教師教學發展基金項目“面向高水平復合型傳媒人才UGMR創新培養模式的實踐型教師共同體建設”(課題號15T1JGJ004)資助。
章洋(1981— ),北京人,黑龍江大學講師,研究方向為技術支持的英語教育;張海(1977— ),男,遼寧海城人,東北師范大學傳媒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東亞媒體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教師教育技術;王以寧(1957— ),男,吉林省長春人,東北師范大學傳媒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新媒體教育應用和教師教育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