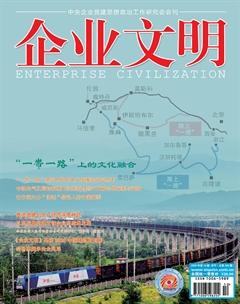應(yīng)用微信創(chuàng)意 提升文化宣傳“氣質(zhì)”“顏值”
費保升
文化宣傳工作是企業(yè)內(nèi)聚人心、外樹形象的重要手段,對于展示企業(yè)軟實力、提升企業(yè)核心競爭力、確保企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尤其是在網(wǎng)絡(luò)時代,新媒體的發(fā)展為企業(yè)文化宣傳提供了新渠道,其中,微信公眾號因其及時性、互動性等傳播優(yōu)勢而成為不少企業(yè)文化宣傳工作的“標(biāo)配”。
“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是中國中鐵十局集團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鐵十局五公司”)的官方微信公眾平臺。“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自2018年12月26日全新改版以來,在全面報道企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改革發(fā)展成果的同時,結(jié)合企業(yè)文化特色、應(yīng)用相關(guān)創(chuàng)意,推出了一系列反映廣大職工精神風(fēng)貌的原創(chuàng)作品,實現(xiàn)了企業(yè)文化“氣質(zhì)”與“顏值”并舉的宣傳效果。
文化推送的內(nèi)容上講“氣質(zhì)”
清晰定位,無形滲透企業(yè)文化。文化的競爭優(yōu)勢是獨特的、不可模仿的。企業(yè)文化宣傳需通過一定力度和技巧的反復(fù)強調(diào)積聚文化印象,從而達到文化內(nèi)涵深入人心的效果。企業(yè)利用微信公眾號進行文化宣傳,應(yīng)首先要有清晰的定位,即明確本企業(yè)自身特有的文化傳播理念。
中鐵十局五公司作為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和中鐵十局集團骨干成員單位,始終以中國中鐵“五大理念”為根本,不斷推動中鐵十局“和諧、感恩、品牌、安全、廉潔、執(zhí)行、爭先”七種文化落地生根。改版后的“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選擇“勇于跨越、追求卓越”中國中鐵企業(yè)精神和“誠信、和諧、求知、創(chuàng)新”中鐵十局企業(yè)精神等字眼植入公眾號內(nèi),分別作為開頭和結(jié)尾的“版記”固定下來。每次推文都讓受眾經(jīng)受一次企業(yè)精神“灌輸”,并潛移默化地在受眾心中烙下“中國中鐵”“中鐵十局”這一文化品牌烙印。
在具體宣傳上,“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將文化宣傳融入企業(yè)日常活動報道中,使受眾在了解和掌握相關(guān)信息的同時,充分吸收報道中蘊含的文化元素。比如:2019年1月8日的《還在回味〈延禧攻略〉?這里有一部“廉政攻略”邀您共賞!》推文,報道了項目部打造“陽光工程”的多項舉措,在受眾心中樹立起了企業(yè)“廉潔”文化形象;2019年7月27日的《你怎么這么好看!每一秒都是極致享受!》推文,借助“十二時辰”這一古老智慧,唯美呈現(xiàn)中鐵十局五公司24小時生產(chǎn)活動的情景,讓受眾在感官享受之余,深切體會到了分秒必爭的企業(yè)“爭先”文化。
主動策劃,正面宣傳企業(yè)文化。微信公眾號在時效性方面的傳播優(yōu)勢非常突出。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編寫出高質(zhì)量的推送內(nèi)容,是企業(yè)在策劃題目時應(yīng)該考慮的問題。“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堅持內(nèi)容為王、策劃為先,主動設(shè)置議題,采寫推送優(yōu)質(zhì)內(nèi)容,引發(fā)受眾共鳴。如:2020年5月10日“母親節(jié)”的《我?guī)Ю蠇尅肮洹表椖俊吠莆模筒捎昧颂崆安邉澋牡谝蝗朔Q敘事方式,配以項目文化建設(shè)的生活照片,不僅增強了受眾的節(jié)日代入感,而且提升了文化宣傳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保安全、創(chuàng)精品、爭先進”主題教育是中鐵十局五公司的品牌活動,已經(jīng)被公眾號推送過多次,創(chuàng)新宣傳就成為策劃的應(yīng)有之義。7月5日,公眾號以《推薦收藏!安全活動高頻詞匯TOP7. docx》為題進行推送,通過提取“宣、講、訓(xùn)、賽、送、檢、練”七個關(guān)鍵詞,以滑動圖片的形式展示了各類安全教育活動,很好地宣傳了企業(yè)“安全”文化。
“黨建工作”和“社會責(zé)任”是國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進行文化宣傳的選題策劃方向。如:2020年3月16日推出的《防控疫情黨員志愿者逆行沖鋒》推文,講述了黨員干部職工用初心踐行使命、將使命彰顯在戰(zhàn)“疫”中的感人事跡;2019年3月12日推出的《人間三月冰霜盡,志愿之花始盛開》推文,梳理了公司以“雷鋒日”為契機所做的志愿服務(wù)工作。這些報道內(nèi)容引發(fā)了受眾情感共鳴并自覺轉(zhuǎn)發(fā),形成了廣泛的傳播擴散效應(yīng)。
公眾號推送形式上提“顏值”
多樣表達,生動展現(xiàn)企業(yè)文化。相比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tǒng)媒體,微信公眾號信息表達的方式更加豐富多彩。其中,圖文結(jié)合只是最基本的信息呈現(xiàn)方式,還可以插入音頻、視頻、表情包、相關(guān)題材超鏈接等,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多種表達方式的集納融合。“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在進行文化宣傳時,非常注重對這些表達方式的整合與拓展。如:2019年7月13日,在新入職職工為期5天培訓(xùn)結(jié)束的當(dāng)天,公眾號就推出了綜合報道《終于等到你-萌新來襲!》推文,除了基本的圖文表達外,文內(nèi)還包含動圖展示、素質(zhì)拓展活動Vlog、領(lǐng)導(dǎo)寄語音頻,等等。此外,受眾可以在留言區(qū)發(fā)表感言看法和對新職工的歡迎祝福,還可以點擊超鏈接查看往期相關(guān)精彩內(nèi)容。“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以提升新入職職工培訓(xùn)活動報道“顏值”為契機,通過融合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動圖、超鏈接等多種表達方式,強化了企業(yè)“和諧”文化的宣傳和形象優(yōu)化。
當(dāng)然,并非所有文化宣傳報道都必須集多種表達方式于一體,這需要宣傳工作者根據(jù)企業(yè)宣傳需要做好取舍。梳理“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發(fā)布的文化宣傳作品發(fā)現(xiàn),一些推文僅采用了單一表達方式推送,也產(chǎn)生了非常好的宣傳效果。如:2020年1月23日推送的《恭賀新春!中鐵十局五公司全體職工給您拜年啦》推文,沒有長篇大論,僅短短兩句話加一個拜年視頻就實現(xiàn)了文化信息的傳遞;1月30日推送的《中鐵十局五公司致廣大干部職工的一封信》推文,通篇文字表達,排版極為簡約,卻讓受眾看到了一個有情懷、有擔(dān)當(dāng)?shù)膰笮蜗螅l(fā)受眾紛紛轉(zhuǎn)發(fā)分享,不到1小時閱讀量突破3 000。這種根據(jù)宣傳內(nèi)容選擇合適表達方式的做法,也是公眾號生動性的一大表現(xiàn)。
常態(tài)互動,趣味體驗企業(yè)文化。互動不僅是微信公眾號活躍度的重要指標(biāo),也是其與受眾建立聯(lián)系的重要途經(jīng)。高頻度的互動能夠增加受眾對公眾號的好感,增強受眾粘性。對于企業(yè)文化宣傳來說,與受眾互動不僅在于吸引受眾閱讀和傳播,更重要的是通過受眾參與來增強文化宣傳的感染力,形成文化共鳴和情感認同。
“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改版兩年來,累計推送信息160余條。其中,有關(guān)文化宣傳的互動型作品不乏精品,選題范圍很廣,標(biāo)題設(shè)置也大多采用吸引眼球的“微信體”。比如:2019年9月6日推送的《我們用“大案牘術(shù)”盤點了美麗工地(內(nèi)有投票!)》推文,將文化宣傳與工程駐地建設(shè)報道結(jié)合起來,并設(shè)置投票功能,讓受眾積極為自己選擇的美麗工地打call(打call,表達支持喜愛),最終閱讀量達1.6萬。2020年5月20日推送的《五二零·我愛你!挑戰(zhàn)你心中的中鐵十局五公司“絕色”》推文,通過SVG(可縮放矢量圖形的圖形格式)點擊顯示正確“企業(yè)色”來展現(xiàn)中鐵十局五公司的別樣魅力,增加了受眾閱讀的趣味性和參與性。
除個性化互動外,留言區(qū)也是“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與受眾互動的重要平臺,其包括兩種形式:一是對發(fā)布的文化宣傳作品進行意義解讀或發(fā)表感想,這種形式最為普遍;二是根據(jù)公眾號當(dāng)天推文的話題討論并進行回復(fù)。公眾號與受眾互動參與形成了常態(tài)化,增強了受眾體驗,最終達到了以轉(zhuǎn)發(fā)分享促進文化宣傳的目的。如:2018年12月26日,公眾號發(fā)布了話題 “哪一個字最能代表這一年你對公司的認知和期待”,吸引了眾多受眾留言評論,經(jīng)篩選,精選留言37條。
在新媒體時代,如何持續(xù)創(chuàng)新和提升文化宣傳的“顏值”和“氣質(zhì)”,強化企業(yè)文化的特色優(yōu)勢和品牌形象,是企業(yè)在文化宣傳中普遍面臨的課題,“中鐵十局五公司”微信公眾號的成功經(jīng)驗為企業(yè)提供了借鑒與參考。當(dāng)然,企業(yè)宣傳工作者也應(yīng)進一步錘煉和提升自身能力,不斷學(xué)習(xí)微信公眾號傳播策略的新知識、新技能、新方法,推出“內(nèi)外兼修”的原創(chuàng)作品,以此贏得受眾共鳴,獲得更有感染力、影響力、傳播力的文化宣傳效果。